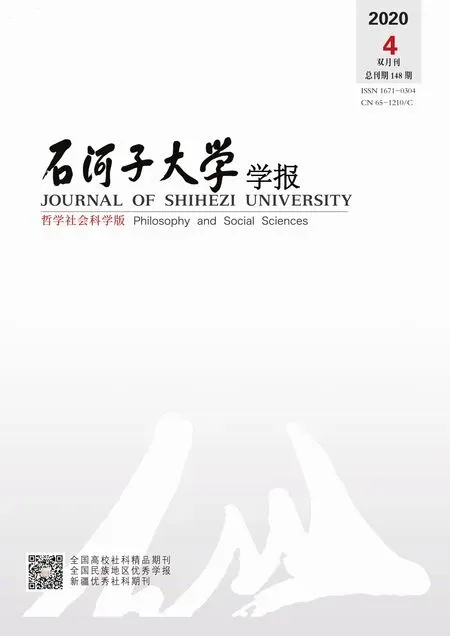2020年后农村反精神贫困探讨
2020-12-09黄国波
黄国波
(泉州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福建泉州362000)
贫困问题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人类反贫困的斗争从未停下脚步。1970年,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最早提出“反贫困”概念,并将他的著作《世界贫困的挑战》标以“世界反贫困大纲”。“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1981—2013年中国减贫人口达8.526亿人,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达78.97%(贫困标准按每人每日支出1.9美元计算)”[1]。中国对全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创造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中国奇迹”,而且这个奇迹还在继续。截至2019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0.6%①数据来源:方晓丹《201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109万人》,国家统计局官网,2020-01-23,http://www.stats.gov.cn/.。当前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到2020年将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成为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永久消灭贫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最为突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乡村。”[2]这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农民不断提升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日益凸显的精神贫困之间的矛盾。2020年后农村反贫困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反贫困的重心将相应进行转移,不仅要努力摆脱物质上的相对贫困,更要加强反精神贫困工作。
一、精神贫困是一种隐性贫困
物质和精神是哲学领域的基本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范畴。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基本观点,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目标主要是物质贫困。人们普遍关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经济上的低收入,而对其政治、教育、文化和人口素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却较少顾及。随着人类反贫困实践发展,人们意识到贫困不仅是物质方面的匮乏,还包括精神生活的贫瘠。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3]。在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上,精神生活质量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生活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随着物质条件的逐渐充实,人们对精神生活需求不断提升,反精神贫困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重要性更加突出。
学界从不同角度对精神贫困进行过界定。按照Bernard Stiegler的判断,当下的消费主义社会迫使人们进入一个“普遍精神贫困”(General Proletarianisation of Sensibility)的时代。普遍精神贫困指的是“知识的普遍丧失……它不仅使劳动者的个人技能成为明日黄花,与之一起消退的还有各种人生知识和理论知识”[4]129。杭承政、胡鞍钢将“精神贫困”定义为“贫困人口志向缺乏、信念消极和行为决策非理性的行为表现”[5]97。王爱桂认为精神贫困是指:“主体的科学文化水平、思想道德素质、价值观念等并没有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相应的提升,甚至落后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或与社会发展方向产生偏差。”[6]44简单来讲,精神贫困就是指人们的基本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不能得到满足而陷入思想困境和信仰危机的状态,自身求富、求知、求乐、求变的内心驱动力不足。许多深度贫困地区农民往往因为物质贫困导致精神贫困,陷入“双重贫困”状态。而刚刚摆脱物质上绝对贫困的农民,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落后于物质条件的改善,则精神贫困相对比较突出。反精神贫困的任务比反物质贫困要艰巨得多,因为反物质贫困可以通过外力精准“滴灌”,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反精神贫困则需要改善政治、文化、公共服务等发展条件,特别是激发人发展自我的驱动力,改变人的思想、心理、习惯等内在精神世界。2020年后农村反贫困工作要更加重视脱贫人口的精神贫困问题。
二、反精神贫困是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精神贫困阻碍人的发展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能仅仅理解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还必须有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7]49。中国反贫困工作成绩斐然,农业经济发展壮大,农民走向共同富裕。刚刚摆脱物质绝对贫困的农民,渴望获得新的发展,而这时候精神贫困的负面影响就显现出来。精神贫困不仅是贫困的精神表象,同时还是导致贫困、阻碍人的发展的制约因素。可以说,精神贫困是农村贫困长期存在甚至代际传递的深层次原因。精神贫困阻碍农民发展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理想信念不坚定,缺乏思想引领。一些农村地区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视不足,对党的“三农”政策宣传不深入,理想信念教育缺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没有完全转化为农民的内在自觉与行为习惯,精神文化层面跟不上时代发展要求。二是教育质量偏低,缺乏发展后劲。根据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乡村15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人口占7.26%(城镇为3.87%),其中男性文盲人口比例达3.92%,女性文盲人口比例达10.66%。乡村6岁及以上人口中未上过学的比重达7.24%(城镇人口为2.83%)①数据来源:《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国家统计局官网,2011-04-28,http://www.stats.gov.cn/.。教育领域的贫困导致农民能力贫困,直接影响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从而影响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三是精神空虚,缺乏文化滋养。一些地区贫困户脱贫后生活刚刚好转,精神空虚的问题就出现了,主要表现为文化生活单调贫乏、趣味趋俗,陈规陋习积重难返。四是小富即安,缺乏发展志向。扶贫容易扶志难,长期积淀的“等靠要懒”思想导致不少贫困户安于现状,不思发展。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班纳吉和迪弗洛在研究贫困现象中发现,“食不果腹贫困者获得金钱援助后不是多买一些食物,而是买了一些味道更好的食物”[8]303。五是健康水平不高,缺乏发展基础。人是最根本的生产要素,身体健康是人获得发展的基础。受到健康教育、公共卫生资源、医疗费用等方面条件限制,农村居民健康贫困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因病致贫在所有致贫因素中排在第一位。根据《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报告(2018年)》,2018年中国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22.44%,农村为13.72%,健康素养水平在城乡、地区、人群间的分布不均衡依然存在,农村居民、中西部地区居民、老年人群等的健康素养水平仍相对较低①《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全国老年护理工作和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报告(2018年)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中国网,2019-08-27,http://www.china.com.cn/zhibo/content_75139559.htm.。除此之外,精神贫困还有权利贫困、信息闭塞、交际困扰、法治意识薄弱等精神领域的表现,这些都成为阻碍人的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反精神贫困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全面自由的发展是人的本质需求,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9]332。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0]649。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中国共产党时刻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初心使命,从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到江泽民“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再到胡锦涛“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而后到习近平关于“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论述,都是几代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思想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和理论发展成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发展方略,始终紧扣“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
农村反精神贫困仍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破除影响农民发展的精神文化障碍,促进农民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些地方政府对发展有过片面的认识,认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度量衡就是GDP,经济收入增长就是人民的发展,反贫困就是反物质贫困。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只是手段。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指出:“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归宿,人的发展以精神文化为内核。”[11]150走过一段弯路以后,中国意识到要全面正确认识可持续健康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逐渐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要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更加追求人的“精神生态”和谐发展。
反贫困斗争永远在路上。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反贫困斗争不是停止而是继续存在,而且将更加艰巨,反贫困的目标已经从以消除物质贫困为主转化为同时消除物质贫困和消除精神贫困,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认为,“发展是一个全面的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发展的过程,其目的是要实现全人类与所有个人的福祉”[12]。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将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人的现代化将充分体现在价值观念、精神状态、思想意识、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社会关系和道德文明素质的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社会公正、和谐相融等诸个方面”[13]。加强农村反精神贫困,改善农民政治、教育、文化、安全、法治、生态环境等方面条件,能够帮助农民达到物质和精神的共同富裕,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
三、2020年后农村反精神贫困路径选择
习近平指出,“扶贫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要坚持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指导扶贫开发,丰富贫困地区文化活动,加强贫困地区社会建设,提升贫困群众教育、文化、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振奋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精神风貌”[14]301。为进一步帮助农民提升精神生活质量,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必须及早谋划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反精神贫困工作。
(一)以经济促振兴,让农民的腰杆硬起来
中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会改变。马克思认为,足够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10]649。中国反贫困斗争的骄人成绩离不开强大的经济保障力量。根据201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项专题调研,近年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年均增长20%以上,2018年达到1 061亿元;2018年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已超过1 000亿元。实施有组织、大规模、高投入的脱贫攻坚战略十分有效地解决了区域整体贫困问题,但今后巩固脱贫成果、解决相对贫困仍然困难重重。据初步统计,目前全国“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存在致贫风险”[15]。2020年后,中国将坚持“摘帽不摘政策”,继续保持经济高投入,确保稳定脱贫、防止返贫。
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恩格斯曾生动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0]776春秋时期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2020年后,摆脱绝对物质贫困的农民基本解决了“吃、喝、住、穿”等生存问题,经济上的发展使他们思想上变得更加自立、自信、自强,对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凸显,对自身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实施反精神贫困要立足坚实的经济基础,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从而为促进人民物质精神生活水平整体提升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二)以政治为统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中国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受益于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2020年后,要认真总结、巩固和发展已有的反贫困经验,在反精神贫困斗争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一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保证。2020年后的反精神贫困斗争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习近平十分重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他认为,“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支部”[16]。村级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基层的“神经末梢”,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要进一步加强村级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把基层党组织建成团结动员群众、引领农村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二是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党员干部要牢记初心使命,胸怀“但愿苍生倶温饱”“大庇天下寒士倶欢颜”的宏愿,对有关人民幸福的大小事情要做到“一枝一叶总关情”,团结带领广大农民群众摆脱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要根据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从本土乡贤能人中培养重乡情、懂文化、懂技术、懂发展的党员干部,从大学毕业生和退伍军人中积极遴选吸收优秀青年党员,打造一支留得住的工作队伍,更好地服务本区域农民发展。三是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推动农村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构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2]。加强村级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构建以“民选、民议、民管、民办”为标志的基层民主政治格局,防止农民陷入“权利贫困”。加强法治乡村建设,为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和公益法律服务,把对农民的帮助从“行政呵护”转为司法保护。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农村实际和农民需求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
(三)以教育挖“穷根”,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导致贫困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但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因素。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解决精神贫困最直接、最活跃、最持久的因素,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措施。人力资本在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社会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一个国家人口素质高低决定人力资本水平。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2016)认为教育扶贫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准扶贫,因为教育可以“切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是“社会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17]22。越穷的地方越难办教育,但越穷的地方越需要办好教育。良好的教育不仅使人拥有一份好的工作,解决生计问题,更能使人提升素养,获得尊重,激发动力,寻求发展。通过教育提升农民素质是一个基础性、系统性问题。办好农村教育要根据不同学龄段和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发展需求,“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动普通高中教育特色发展,依托职业教育拔除穷根,努力提高高等教育贡献率”[18]12。其中,职业教育注重培养生产和管理一线的专门技术技能人才,契合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也是教育扶贫本土化的有效途径。根据《2019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高职院校学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持续稳定在92%,毕业三年后月收入增幅达76.2%,本地就业率60%,到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就业达25%”①数据来源:练玉春《〈2019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在京发布》.光明教育网,2019-06-20,http://edu.gmw.cn/2019-06/20/content_3 2935500.htm.。职业教育对于促进农村本土贫困子弟就业和推动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作用,其中的就业培训是深受贫困户欢迎的一项有效措施。老百姓称之为“培训一人,就业一个,脱贫一家”。
心理健康素养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智利学者萨拉扎·班迪认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19]3。由于心理存在“志向失灵”,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所谓的“自愿型”贫困。过去在贫困地区扶贫工作中,常常会遇到一些“扶不起的阿斗”,有的人“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因为“贫困带来的社会排斥、刻板印象威胁,自我污名、耻辱感和不被尊重感会降低贫困人口的自我效能和心理健康,同样也会降低志向水平。”[20]903-930教育不仅能实现“扶智”,还能促进“扶志”。发展农村教育,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除了提升思想、智力、体能等方面质量水平,还要特别注意加强贫困人口心理健康教育,保持心理、精神和社会生活的良好状态,防止心理层面的贫困。
(四)以文化铸魂魄,滋养农民精神家园
根据文化功能理论,文化能“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精神需要”[21]50。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0]456文化是民族生存和人类发展的根本动力,农村文化建设是反精神贫困的重要内容。一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统筹城乡文化发展,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为农民提供优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立足农业农村现状,深入调查了解脱贫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鼓励开展健康高雅的群众性民俗活动和体育活动。二是传承和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曾指出,“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22]605-606。耕读传家的乡风、守望互助的乡约、淳朴浓烈的乡俗、魂牵梦绕的乡愁,共同构筑起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过去一段时间,受工业化、城镇化的影响,部分乡村出现传统社会伦理失序、传统价值观失衡等现象。反精神贫困应对乡村传统文化进行积极扬弃,传承优秀文化,彰显时代价值,充分发挥其凝聚人心、提振精神的作用。三是建设美丽乡村。中国古人很早开始研究环境对人类发展的作用。“天人合一”“法天象地”“地灵人杰”等,都是中国古代关于天(环境)、人关系的深邃认识。按照环境文化学的观点,环境是人的性格的塑造师,能影响人的情绪、生活和发展。美丽乡村建设是2020年后农村反精神贫困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留住绿水青山,通过旧村改造、新村建设、古村保护留住美丽乡愁,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发挥环境文化功能,促进人与环境共生共荣、和谐发展。
(五)加强精准施策,确保特定人群共享发展成果
2020年后农村反精神贫困除了制定实施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有力措施,还应该加强对特定人群实施分类施策,确保人人共享发展成果。针对特定人群进行分类施策是“滴灌式”精准扶贫的成功经验。反精神贫困斗争要继承和发扬精准扶贫的宝贵经验,针对不同地区发展状况和不同群体发展困难,进一步总结和完善“分类管理”“分类指导”的工作方法。中国实施精准扶贫取得显著成效,但在实践中仍然发生少部分农村脱贫人口再次返贫的情况。这些返贫人口中许多属于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重病和慢性病患者等特定人群。由于经济脆弱、精神贫困,这些特定人群很容易出现返贫。帮助社会保障兜底的贫困线以下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特定人群把脱贫成果稳定住、巩固好,除了防止物质上返贫,还要防止这些特定人群陷入精神贫困。
随着城镇化推进,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趋势日益增强。仅从经济收入衡量,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工已经处于贫困线以上。但应该注意到,农民工虽然完成生产、生活空间的转移,但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筑起的“藩篱”仍不同程度地阻止一些人成为真正意义的“新市民”,“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贫困已经成为城市贫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处于城乡贫困救助的‘真空地带’”[23]23-25。农村反精神贫困应该强化城乡统筹发展理念,覆盖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使他们和城市人口一样享受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是终点,而是新航程、新生活的起点。2020年至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朝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奋力前进。反贫困不能撤摊子、甩包袱、歇歇脚,要接续打响农村反精神贫困斗争,解决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