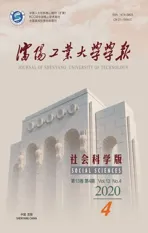“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
2020-12-09陈红娟
李 爽, 陈红娟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1)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1470-1471这段话曾在历史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传诵。然而,学界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质疑及反对的声音。有学者认为:“不能如以往那样简单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认同了甚至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才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2]也有学者认为,该论断“含有浓重的政治意图,不一定完全尊重史实”[3]。又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来不及去深入探究史实,仅凭个人的亲历作出的概述,以偏概全在所难免”[4]。鉴于此,笔者尝试对学界的质疑进行梳理与回应,以期对科学理解经典论断有所助益。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节点的认知差异
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但学者们对于如何理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论断以及马克思主义何时开始在中国传播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主要有四种观点。
1. 十月革命论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才开始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广泛的传播。持该观点的有蔡德麟、林代昭、田子渝、李景治、左玉河等。其中蔡德麟的“两阶段说”在学界较具代表性,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应该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介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两个阶段,其中应以十月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点。他认为,十月革命前后两个阶段虽有着历史的联系,但在性质上是不同的[5]。在此基础上,田子渝又把早期传播分为三个阶段[6]。
2. 五四运动论
持此观点的主要是姚宏志、刘晶芳。姚宏志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强烈示范和刺激下,被广泛地介绍到中国来,并迅速地被中国先进分子所理解和接受”,但并不全面,因此“1919年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分界点”[7]。刘晶芳在《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同样指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但并没有立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不多,国内报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也很少。”“五四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局面。”[8]
3.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混同论
持此观点的学者多以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作为节点,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齐卫平、许门友、陈留根等。与“十月革命论”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处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这一笼统时期,没有明确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齐卫平指出:“从传播史的角度看,早期译介阶段仅仅具有资料性的意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以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为起点的。”[9]其他学者多是在论述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时,提到了其为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相对来说缺乏详细周密的论证。
4. 十月革命否定论
持此观点的主要有郭卿友、彭国运。郭卿友在《试评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与前文“两阶段说”有着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十月革命前与十月革命后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不同历史阶段,划分这两个历史阶段是完全必要的。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毛泽东一种形象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不应以十月革命为启端[10]。另外,彭国运在《十月革命送来马克思主义说质疑》中明确指出:“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是不尊重史实的表述。他认为,毛泽东由于要实行“一边倒”政策而有意夸大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者的影响,实际上中国人转向俄国、转向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因为苏俄对华宣言带来了心理上的震动,从而决定走俄国道路[3]。
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针对上述与该经典论断相左的认识,我们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客观联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语境,省察经典论断的科学性。
1.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具有合理性
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十月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本质区别。“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经典论断是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地传播的层面上展开的,合乎史实,具有合理性。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的学说已经开始传入中国,但各种流派对马克思以及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之传播仅限服膺于自身需求的零星、片段式介绍,且这些内容也是被嵌入到各种其他“主义”之中,作为佐证其他“主义”“学说”的论据,而非旨在真正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传播。最先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的传教士虽然使中国人知道了马克思的名字,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介绍是作为宣传基督教救世说的一种补充。如《万国公报》中介绍马克思的只言片语,只是为了论证其“救贫”“均富”的“安民学说”。中国人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并谈到马克思的是梁启超,他虽然承认社会主义是“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义”,但却认为“极端之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11]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情社会主义,但仅借助社会主义学说来揭露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以避免中国未来的资本主义社会重蹈西方的覆辙。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喉舌《天义报》上虽翻译了《宣言》第一章,但也不过是在践行“吾于一切学术,均甚怀疑,惟迷信无政府主义”[12]之宗旨罢了。
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在俄国的成功使国人加深了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怀疑,认为“现世界经济制度之破绽,世人贻不能不承认之”[13],并对社会主义道路产生期盼,认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14]“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15]“影响世界思潮增进人类福利者,则极无涯量。”[16]而且进一步提出“中国似宜取以为法”[17]等。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受到重视。
“革命行动的实际影响比理论宣传文章传播得快得多”[18]26,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地、全面地被介绍到中国。一是,国内涌现出一批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积极创办期刊、组建社团、翻译经典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组织保障、物质载体以及理论典范。据统计,在1918年以前大约20年的时间里,曾经发表过介绍和同情社会主义的文章(包括译文在内)的报刊不足30种;而1918—1922年前后5年多的时间里,此类报刊多达220余种[19]。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历史论、经济论、政策论:“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20]这是对以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性超越,标志着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进入了新阶段。
二是,十月革命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一个根本变化,国际组织开始有计划地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3月,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共产国际(亦称第三国际),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组织全世界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传播共产主义”[21]“执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训诫,实现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来的理想”[22]。此后,第三国际在近24年的时间里“作出、发出的在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决议、指示、宣言、通知、信件等多达200余件”[23]。共产国际还专门制定政策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的传播,如委派维经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等共产党国际代表在华积极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再如帮助各国共产党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创办刊物,明确指出“各国共产党应当创办一种在工人中间大量发行的新型定期刊物”,“向无产阶级报道革命的消息和提出革命的口号”[24]。
联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梳理毛泽东关于十月革命的相关论述可知,他并不否认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的零星传入。在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之前,毛泽东于1945年就曾指出:“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18]116“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是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而深入地传播层面上进行的论断。
2.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其历史语境中具有正当性
从学术史角度分析,学术界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才开始从学术层面探讨马克思译名的记载和其他流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贡献等问题。要求毛泽东在40年代末即从学术层面给予准确表述,是一种对领导人的“苛求”。此外,从横向视角上来考察与毛泽东同时代的党内理论家、领导人的相关论述可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其历史语境中具有正当性。
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与探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我们来看,李提摩太节译颉德著作的这部分中,提到了马克思和《资本论》,这在国内毕竟是第一回。”[25]而且,学术界对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也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由消极肯定到积极肯定的转变过程[26-29]。20世纪50年代末不少学者认为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派的活动、阐释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障碍,提出“无论封建思想、买办思想或者各种资产阶级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大障碍。”[30]“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都是阻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分裂中国工人运动的。”[31]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有学者消极地肯定了其他流派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他们的活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固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却首先打开了窗户,引进了革命科学理论的第一道曙光。”[32-33]“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否定在十月革命以前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接触或介绍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事实。但也不能对此作过高的评价。”[34]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才开始客观地加以评价:“应该承认,他们(传教士、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努力在客观上是作了有益于人民的贡献的。”[35]我们不能用今人之眼光来苛求毛泽东具有超越时空的能力,不能用后人通过多年的考证与研究才得出的结论来评判毛泽东的论断。
陈望道20世纪30年代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出过“题旨情境”相适应的理论。话语的解读一定不能脱离其语境,正确理解毛泽东的言论首先应将其置于那个时代的历史语境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之前,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时局问题及其他》《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文章中均有相关论述。早在1941年,毛泽东即指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36]这里毛泽东将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的关键节点,其内在逻辑基本上遵循十月革命改变世界革命形势进而影响中国革命的判断。“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十月革命,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变化,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18]493“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两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流行了。”[18]26反观中国,毛泽东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37]正如“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38],毛泽东提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意指作为指导思想而言,在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与彷徨后,马克思主义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才正式进入中国。究其根本,“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1]1515它的传播是近代中国救亡运动在理性世界的必然结果[39]。
同时,客观分析与毛泽东同处一个时代的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家、理论家、党内领导人的认识,与毛泽东的论断基本保持了一致。首先,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先贤肯定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肯定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影响,指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头,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40]
其次,党内其他理论家在论述中亦将十月革命视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键节点。1940年,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指出:“后者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大多数很快地转变成了社会主义者。”[41]王稼祥于1943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问题》中说:“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看见了俄国共产主义挽救和解放了俄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共产党人是这样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这用不着说明的。”[42]
最后,党内其他领导人充分肯定了十月革命在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作用。胡乔木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在中国革命知识界中间传播了起来。”[43]李达认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动了全世界,也震动了中国人,而最敏感的则是中国知识分子。”[44]周恩来提到:“俄国十月革命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使我们认识到要‘走俄国人的路’。”[45]“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46]
三、现实启示:理解经典论断时应坚持怎样的理论自觉
毛泽东结合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形势变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以及中国救亡图存的政治实践等,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得出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一些学者理解该论断时未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忽略经典论断的生成语境,利用碎片化的史实提出质疑,具有片面性和主观性。而对经典论断的否定不是简单的理论探讨,甚至隐含着通过否定经典论断以消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意图。“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许多问题涉及党的历史。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的生命,关系国家长治久安。”[47]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应保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在理解经典论断时坚持高度的理论自觉。
第一,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史实是当代学者在研究中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我们应该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科学认识经典论断,切勿罔顾客观事实,更不能停留在字面断章取义,曲解话语的真正内涵。目前,个别学者在理解经典论断时对一些客观事实“选择性失明”,忽略史料的完整性,有目的地选择一些碎片化的历史事实,武断地对经典论断证伪,其结论必会扰乱群众思想。因此,当代学者在理解经典论断时不仅要理解论断的表面含义,更要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关照历史的整体性,体认论断的深层本质。
第二,回归文本叙事语境。语境具有解释功能,将话语放在语境中才能科学解释它的真正含义。脱离语境的解读不仅背离话语者的原义,而且掺杂着解读者个人的主观意志。任何一个经典论断,都是话语者运用语言文字通过上下文的有机整合而构建起来的理论框架和思想体系。因此,考察经典论断必须回到其所处的文本语境,必须警惕单纯依据文本中的只言片语对经典论断作出随意性的阐释与评价。此外,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话语系统,在当下的话语系统中毛泽东著作中有些词汇已经溢出了现时话语系统,而有些语词、术语、概念与范畴在时代变迁过程中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不能将历史话语系统中产生的经典论断放置于现时的话语系统中,用当下人的思维方式、概念理解以及行为惯习来审视。
第三,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少西方学术研究中流行的研究方法涌入国内,如新文化史、概念史、心理分析、实证法等,这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论断。但研究中也存在一些研究者忽略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聚焦具体的历史细节,忽视宏观历史背景;片面使用史料,以点概面,以偏概全;夸大主体的心理,缺乏对客观历史的把握以及以个人价值观影响学术研究,掺杂明显的主观臆断等问题。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应以此为鉴,注重史料的挖掘、整合,并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审视经典论断。面对各种质疑,学界要积极主动地回应,“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