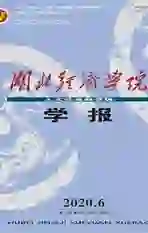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研究的接力与范式
2020-12-07许萌
许萌
摘要:张先飞教授关于“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研究,使长期以来学界对历史中“五四”文学的“隔”变成了“不隔”,使早已进入研究“盛年”期的“五四”新文学重焕生机,而“抹布的人”“国民性”“人间爱”等文论的提出,更使“五四”文学与当代文学创作、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超越时空的共通性与人道主义关怀。张教授的学术研究为当今学界理论研究盛行、历史文献被轻视与破坏的不良风气作出表率,而他关于“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若干研究成果,也将此从传统的研究思维、范式中解放出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现实观照,并在某种程度上建构起中国特有的,而非完全依附于西方思想、文化的现代思潮话语体系与时代精神。
关键词:文学思潮;“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认识性装置;研究范式
一、考镜源流。论从史出
张先飞教授于1990-1997年在河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200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2004-2008年分别在日本东京大学、河南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中外比较文学,鲁迅、周作人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张教授十分注重原始史料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与价值,常常告诫学生“历史也是过去的现实”,“史料是在灰尘堆里刨出来的,只能靠自己挖掘、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张教授的两部力作——《“人”的发现——“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与《“人”的文学:“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学的发生》,在探究“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源起、发生、发展时,无不从史料资源与理论背景(兼顾中西)出发,在对大量原始资料的阅读与筛选之上,在“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研究领域中,作出纵深性的学术开拓与丰硕的学术成果,呕心沥血,用精诚、勤恳的十年磨出了令后辈叹服的宝剑。
无论是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开创的俄罗斯文学中现代人道主义的探源,还是缕析周作人与前者的联系、周氏兄弟在“五四”时期倡导并实践的文学改造活动,亦或是底基扎实的脚注,皆可见张先飞教授在史料以及在史料之上进行文学研究、学术创新的非凡功力。但是,张教授对史料之于文学研究的态度也不是一味的撷取,而是思辨视之:“重视史料,但不能将其神秘化。史料只是文学研究中的沙土、水泥,是历史学的基本建筑材料。”又或“史料本身不是方法,如何搭建、建构才是方法”等等,多次强调在史料阅读中积累自己的史料感觉,由此才可得出与别人不同的结论,平日要有意的培养这种历史感觉、学术判断。并且,张教授进一步提出:“目前研究者们所要做到的,首先是‘悬搁各种预设的话语系统与它们所搭建起的历史框架,以及现有的部分研究结论;之后再重新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进行历史还原,并将其作为一切研究工作的起点与基础。”实际上,张教授为当今学界理论研究盛行、历史文献被轻视与破坏的不良风气作出了表率,而他关于“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若干研究成果,也为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研究作出了独具启发意义的研究范式,将此从传统的研究思维、范式中解放出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现实观照,并在某种程度上建构起中国特有的,而非完全依附于西方思想、文化的现代思潮话语体系与时代精神,以及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文学创作及文学实践活动。
二、独有的“认识性装置”理论体系
在探讨“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与“人”的文学两部专著之后,张先飞教授于2019年的新作《“认识性装置”的建构与运作:以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运动为例》,从研究路径、研究理论,到史料呈现、思维逻辑等方面,为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研究提供了足以学习、借鑒的范式。
张教授在考察五四新文学运动、各类社会改造思潮运动等话语系统及认知机制的建构时,发现柄谷行人提出的“认识性装置”理论模式具有极强的解释能力,便借鉴并深度改造该理论模式,作为分析“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研究及话语体系的认知工具。
此文有三处创新,一为理论创新。这具体表现在将“认识性装置”这一学者使用却从未被说透的理论模式大致分为“搭建一安装—拆除”三个流程。又按照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将“认识性装置”分为“总体性”“小型”“单体型”三种类型,以及提出装置中的“基本组件”“载体”等理论语汇,大大丰富了“认识性装置”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二为思潮研究创新。以各类文学史中的文学思潮为例,大多先介绍时代背景,接着具体分析作家、作品,最后阐释提升。如此以来,文学思潮研究就形成了固定的、僵化的样式,这不仅阻碍文学思潮研究的进步之路,也无法真实还原历史中延绵的、流动的文学发展进程。张教授的文章正是将整个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研究建立在史料研究的基础上,完整的呈现了从史料到思潮,再从思潮到文学的主体循环:三为建构了独属于中国的“五四”话语体系及认知机制。按照平日阅读经验,提起五四文学,必联想到西方思想、文学、文化对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诸多影响,但张教授的思潮研究,在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起源处已将与借鉴、转化西方成果之处阐释清楚,当这一套由周作人“拿过来”的理论真正进入“五四”思潮时,已然有了本国的时代印记与符号。因而张教授对整个“五四”话语体系的分析与建构,是站在正确的、合适的、彼时“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的立场上,以他们的思维、所想所行来解释,是有别于“唯西”或“中西混淆”的文学思潮立场的,同时也是令人欣喜的属于中国自己的理论研究体系。
本文由大视角切入,在“认识性装置”体系内将重要问题一一击破,既有全局性的考察,又有精心的内在逻辑设计。无论从研究层面还是审美层面来看,都显得匠心独运。尤其是章节结构、内在逻辑之精巧,大有“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笔法,譬如在阐释三类认识性装置时,“载体”在其中的环环相扣。张教授在文学思潮研究中治学严谨的态度、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的实事求是,更显现出文学研究中可贵的坚守精神。
三、对“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研究的推进
“认识性装置”为我们研究文学思潮、从历史中发现规律并形成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张教授所言“理论是如何发生的?是在历史事件上归纳的结果”。(可参阅张先飞《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史体制的创制——以国学概论为中心》一文)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于文学思潮研究难度与限度的反思。
首先,研究某一文学思潮,必须回到文学作品中去,不能以西方的文学理论直接套用于中国各时期的文学现象之上,应具备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意识,但在这一过程中,又很难不受到任何西方话语的影响。其次,回到历史现场后,应以历史的眼光对史料进行提取、分析,尽量避免个人主观意志的泛滥,而是让材料说话。此外,文学思潮发生的起点与落潮点的时间界限划分也很难落实到具体的时间。最后,对文学思潮及文学思潮规律的研究,并非孤立的文学研究,而是一个文史哲等具有交叉性的学科研究,这也是对研究者的知识储备、综合能力、研究能力的莫大考验。
在研究文学思潮的规律时,我们发现现象有时会超出规律,或者规律无法涵盖所有现象的限度。这告诉我们,某一理论不一定适合全部的作品,应及时厘清理论与文献的关系。同时也应如张教授所言:“不能被理论震慑,理论也是由零打碎敲的历史现象,经过综合、再综合,而建构起的理论大厦。”
鉴于文学思潮研究的难度与限度,张先飞教授以“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研究为核心的累累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并解决了这些难度与限度的问题。首先,他以“再出发”性质的历史回眸与理论阐释,对已经模式化了的“五四”文学及思潮釜底抽薪,重新出发,建构了一套适合中国自己的、独属于“五四”时期的话语理论体系。这种“先破后立”的学术魄力与精神,在文学思潮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给予后辈学者莫大的激励。其次,张教授关于“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研究,使长期以来学界对历史中真实的“五四”的“隔”变成了“不隔”,“隔与不隔”的解决,是张教授在“五四”文学文论、话语系统、作品阐释、“五四”作家心路历程等方面的重要推進,他将清晰、明透的“五四”文学思潮及创作改造活动的发生、发展呈于人前,使早已进入研究“盛年”期的“五四”新文学重焕光芒,而“抹布的人”“国民性”“人间爱”等文论的提出,更使“五四”文学与当代文学创作、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超越时空的共通性与人道主义关怀。
令人感喟的是,在张教授艰辛地建构一个如此庞杂、精细的“五四”话语体系、认知机构的同时,还解决了一些重大的学术难题,如周作人在“五四”前后的思想变化及心路历程(可参阅张先飞《从普遍的人道理想到个人的求胜意志—论“五四”前后周作人“人学”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又如发现并探究了“五四”先驱是如何为国民性改造进行思想建构的,具体的文学创作等一系列社会改造活动是如何发生发展的等等(可参阅张先飞《旧邦“新人”——“五四”现代人道主义国民精神改造观》)。
四、重读“五四”经典:“人间爱”与“立人”
张先飞教授对“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研究,从宏观上看,为当下文学思潮研究提供了可行的范式与方法:从微观上看,在具体的文学文本阐释层面,也具有拓荒性的意义,如对“五四”时期文学创作中的“人间爱”“立人”“爱与理解”“灵肉一元”等文论、主题的发现与开掘。以此文论与观念,以“五四”现代人道主义先驱的话语再出发,对以往“五四”经典作品予以重新观照时,则能发现曾经对这些文本产生的疑惑与隔膜,在悄然问冰释融解,在心灵感悟与情感层面,也离远去的五四文学、五四先驱更近了一些。
首先,以叶绍钧的《潘先生在难中》(原载1925年1月《小说月报》16卷1号)为例。摒弃以往对小说人物“讽刺式”的解读思路,以“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话语体系观之,“潘先生”分明体现了乱世中一个逃难者的悲哀、一个知识分子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悲哀,而这种悲哀在当时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如对潘先生在逃难途中的描绘:
忽然觉得长衫后幅上的小手没有了……心头怅惘到不可说,只无意识地把身子乱转。转了几回,一丝影踪也没有。家破人亡之感立时袭进他的心门,禁不住渗出两滴眼泪来,望出去电灯人形都有点模糊了。
这是叶绍钧在塑造“潘先生”这个人物形象时,不可忽视的情感基调与理解之同情,也是以“五四”现代人道主义先驱者的思维话语来客观阐释他们笔下的社会改造活动,更是对以往用批判、讽刺之理路来解析文本的纠偏。
而潘师母则将作为一个母亲、女性的“小人物”的生离死别演绎的淋漓尽致,从女性视角扩大了“人类普遍的寂寞与悲哀”。小说中,除了书写成年人对逃难感受的视角外,还有另一重视角——与“悲苦愁”相对的,具有“儿童爱”的情感与感觉,这具体表现在作家对儿童的“羡慕与崇仰”之中。小说中潘先生的两个孩子(阿大9岁,阿二7岁),在逃难中表现的新奇、天真、无忧无虑,以及活在自我的快乐世界里,皆与成年人的悲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要吃火腿汤淘饭,”小的孩子咬着指头说。
……大的孩子也不懂看看风色,央着潘先生说,“今天到上海了,你可给我吃大菜。”
……两个孩子都怀着失望的心情,茫昧地觉得这样的上海没有平时父母嘴里的上海来得好玩而有味。
对“儿童爱”的书写,不仅限于叶绍钧一人,这在“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成为较普遍的现象,这还要溯源到“周作人这一时期抒发‘儿童爱情感的诗作,被‘五四青年文艺家们视为典范性杰作,他对于‘儿童爱的独有观念与个人化的感受方式,成为青年文艺家们思考与创作中积极效法的范式”。显然,《潘先生在难中》里两个“孩童”形象的设置,与“五四”新文论中“儿童爱”的情感、感觉类型一脉相承,互为表里,表现了叶绍钧及“五四”一代作家不仅羡慕儿童的无尘无垢,也崇仰他们心中理想的“神明”境界。
接着,以许地山中篇小说《春桃》(原载于1934年《文学》3卷1号)为例进行观照。小说由三个人物——两男一女构成,讲述了底层人物普通却又不平凡的故事。小说同时还触及到了“五四”时期关于讨论妇女解放、家庭婚姻、男女平等、社会风俗变迁等话题。下面具体从三个层面来进行分析。
从“春桃”这一人物形象来看,她充分的展现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如她在两个男人面前总是发出振聋发聩的宣言:“现在,我是我自己,我做的事,绝不会玷着你……”再如“你若认我做媳妇,我不认你,打起官司,也未必是你赢”。或者是她表现出的对事业的追求与坚持“我还是当捡货的,咱们三人开公司”“尤其是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她更要工作,因为同行们有些就不出去”……这样一个靠捡烂纸为生,却坚如磐石的女性,在爱情、事业面前,都充分的肯定“自我”,具有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这不仅是“五四”先驱现代人道主义“个人”观的体现,更是以社会改造为目的,创作的具有高度发达个性与个体意识的“新人”形象,这实际表现了他们对理想人格的向往与期待。从春桃、李茂、向高三个人的关系来分析,春桃与向高和谐、平静的生活被突然出现的前夫李茂打破,三人陷入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复杂尴尬的生活局面,后因春桃的坚持和“自我”,两个男人居然相互理解、握手言和,两男一女从此风平浪静的同处一个屋檐下。这多少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小说结局,实则是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美好、和谐的人际关系与生活状态的另一种书写,即“建立在坚实‘现实精神之上的‘理想主义与‘社会改造勇气”;最后,从许地山的旁白来看,他对春桃的独立和内心觉醒,是一种认同与期待的态度,他将春桃塑造的越激烈、越与世人格格不入,他对“人”的精神改造与建立在“现实精神”之上的“理想主义”“社会改造勇气”就显得愈发强烈。
除此以外,“五四”的经典作品,诸如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故乡》,郁达夫的《沉沦》,台静农的《地之子》,叶绍钧的“隔膜”系列小说等等,皆力证了张先飞教授关于“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研究的价值和贡献,正如张教授所言:“我们要从历史、文本中呈现出一套适合自己的理论体系,让史料自己说话,让历史来回答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