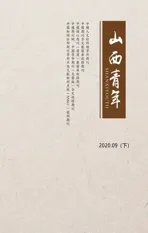以“创伤”为线索重读莫里森的《天堂》*
2020-12-07于程
于 程
湖南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 永州 425000
《天堂》的作者对黑人群体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为黑人走出内心的创伤提供帮助。《天堂》是该作者获得文学奖后的第一部作品,一经发出就在社会范围内产生强烈的反响,人们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赞誉其作品具有创新性的特征。本文以创伤为基础,对小说主线进行梳理。
一、集体创伤
多个不同的个体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集体,集体记忆与种族记忆具有相同性,这些记忆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创伤[1]。为了深刻了解这些创伤,需要经历者对过往经历进行诉述,使黑人种族的集体经历可以直观展示在人们眼前,深刻揭露其所遭遇的创伤。《天堂》这部小说对多位叙述者的伤痛往事进行了回顾,再现悲惨的经历,回忆当时的伤痛,营造一种创伤的氛围。
《天堂》以特殊的历史背景为描写的主要依据,对黑人失去小镇又重新建立小镇的经历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当小镇颓败后,组长带领所有人民重新建造家园。随着鲁比小镇的建立,人们的生活逐渐归于平静,但是镇内外多重矛盾的产生,使小镇又重新回到不安的环境中[2]。
小说具有清晰的历史线索,并从该线索逐渐展开祖辈的记忆,其为了寻找新的生存家园,经历了多重险阻,遭受种族歧视才终于建立了属于黑人的小镇。在小说中创伤记忆就是每个故事经历的核心思想,即使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仍然存在创伤。而对于创伤经历的亲历者,始终通过抗拒和愤怒逃避创伤,认为这些创伤经历是一种屈辱,从不认为黑人与他人存在差距[3]。在摩根兄弟记忆中祖父像族长一般带领全族人民抵达了黑文镇,这样的经历,使黑人群体彻底否认因为拒绝所带来的人格侮辱。虽然可以对自身尊严进行保护,降低羞耻感,但是以神秘色彩的故事来躲避创伤,其也会在心理方面留下阴影。
创伤理论学者认为,以往人们遭遇的暴行一定会对其身体和心理造成创伤,其影响会通过不同的故事逐渐传承,时间久了这种创伤就会表现为后代人对环境刺激产生的反应,这是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创伤感受,其肩负着前人在心理方面未能弥补的创伤,不断传承这些故事,并不是愿意记得这些创伤,而认为建造小镇是一种勇敢的精神[4]。当小镇再次毁灭,需要重新建立时,这些伤痕依然会再现,他们将遭遇更加严厉的拒绝:因为肤色,医生对其放弃治疗,导致摩根兄弟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正是因为自身经历的无数次拒绝,导致其对其他肤色的人也非常排外,并对于任何可能想起创伤的因素进行抑制。其决绝承认集体创伤的存在,信奉祖辈传承的故事,将大炉灶作为小镇得以崛起的证明。鲁比男人始终坚信大炉灶上的文字是祖辈们勇敢抗击危险、带领族群崛起的印记。这种由拒绝而产生的创伤,始终不具有任何的特殊功能,反而是一种象征意义[5]。对于集体创伤的记忆,不仅是无数次拒绝经历积累所成,同时也是种族歧视带来的。因为人们对黑人种族的歧视,导致黑人始终在心中留有深刻的创伤。这类创伤经历使得其对社会产生排斥感,对社会更加抵触。因此,其需要建造属于自己的空间来躲避创伤,这也正是鲁比镇的由来,其对外来人员一律排外,在鲁比镇外来者就是敌人,其想方设法躲避种族主义对其带来的心理创伤。
二、个体创伤
在《天堂》中,男性是集体创伤记忆描写的主要对象,在此记忆中根本无法看到女性的身影,这种集体创伤主要就是以男性为主。如果说男性对历史中的创伤记忆进行了承担,那么女性在现实中却时时刻刻在经历着创伤。与集体创伤不同,个体创伤具有明显的不同,每个人所经历的故事形成了不同的个体创伤,不需要进行讲述,就可以使个体产生强烈的感受,并且伴随着屈辱的不断累积,这是一种难以磨灭的伤痛记忆。
《天堂》分为多个篇章,以女性人物作为每篇的篇名,以创伤为诉述的主要线索。以女修道院与鲁比镇作为对比对象,对其经历的故事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修道院中每位女性在性格方面都有所差异,家庭背景悬殊较大,但是其同样都遭遇了创伤,选择到此躲避灾难。玛维斯始终受到丈夫的压迫,在丈夫的责骂下艰难度日,因为购物意外失去自己的孩子,使其精神遭遇了严重的打击,总认为家人会伤害自己,遂开车到了修道院。格蕾斯因为身体和心灵遭受着严重的折磨,便选择伤害自己来寻求内心的解脱。帕拉斯从小父母离婚,而自己在男朋友的带领下去看望母亲时,却发现母亲与男友之间的事情,因为生气离开家,在路上又遭遇了严重的恶行。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充满了个体创伤,其纷纷选择到修道院缓解内心的痛苦,并遇到了修道院的主人。修道院的主人同样拥有着创伤记忆,其因为被抛弃和养母去世,失去了生活依靠,眼睛再也不能看到光明,为了躲避他人的眼光,掩饰自己的内心,她选择终日带着墨镜,并通过酒精遗忘过去。鲁比镇的女性与修道院的女性一样,都因为创伤来到到修道院。修道院与鲁比镇的封闭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没有任何的封闭性,可以包容不同年龄,不同遭遇的女性,成为其减轻痛苦的避难所。
女性主义始终是理论及研究的重点,在《天堂》这部小说中也对女性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女性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保证男性与女性在关系上的平等。从该小说中可以明确看出,这些来到修道院的女性普遍受到压迫和歧视。女性始终处于男性之后,没有任何的地位,在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中都与男性无法保持平等,即使在家庭私人领域中,女性地位也明显弱于男性。
作者笔下所描绘的女性都有着不幸的遭遇,内心存在难以弥补的创伤,可是他们并没有就此躲避创伤,而是在他人的带领下共同面对创伤,积极治疗创伤。
三、家庭创伤
在《天堂》中,玛维斯这一黑人女性在家庭中是一位贤妻良母,她买了肉肠给家人做饭,两个双胞胎没有人照顾,于是她让丈夫帮忙照看,但是,丈夫拒绝了,最终,使得两个孩子出现意外死亡。因为自己的失误而失去了两个孩子,这让她满心愧疚,也苦不堪言,在事情发生后,她认为两个孩子与丈夫想要谋害自己,所以,终日惶惶,最终,经常出现幻觉。另外,她的丈夫时常对她施暴,为了躲避灾祸,玛维斯只有逃离家庭。玛维斯每一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她作为妻子,没有得到丈夫的关爱,弗兰克还会在肉体上折磨她,在平时更是耍威风,妻子只是自己发泄兽欲的工具。面对家庭给她带来的各类创伤,她只能被迫逃跑。
另外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就是西尼卡,她从小就是孤儿,曾经被两户人家所收养。西尼卡从小就没有享受过父母的爱,这一亲情的缺失给她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伤害。尽管被两家所收养,但是,养父母的虐待让她从小就没有安全感,因此,在长大后,她只能寄情于爱情,但是,她在与恋人结识了6个月后,恋人就锒铛入狱了,失去恋人让她无依无靠,只能漂泊。同时,整个社会也抛弃了她,最后,为了获得归属感,她只能来到修道院寻找慰藉。
不管是作为母亲、妻子的玛维斯,亦或是作为孩子的西尼卡,她们都遭受过程度不一的家庭创伤。遭受丧子之痛、身心受到折磨的玛维斯是父权制下的受害者,她较难在家庭中获得应有的尊重,不具有话语权,她是受到家庭创伤的众多黑人女性的一个缩影;而西尼卡从小失去了双亲,在两个收养的家庭中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得她缺少安全感,她所受到的家庭创伤尽管与前者不相同,但是,她的家庭创伤叙事展示出了一个无家可归的黑人女孩形象,离开了父母的关爱,黑人孩子也会沦为社会的“孤儿”。这样的家庭创伤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实黑人女性这一群体是任人蹂躏的群体,她们卑贱地生活着,在白人、黑人男性的压迫下,黑人女性的生存空间十分狭窄,她们已经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只可以呼吸着微弱的空气,若生存对她们来说是严峻的挑战,那么,尊严对她们来说就是奢侈品,女性尊严已经被社会践踏得荡然无存。在这个遭受了战火、种族隔离等创伤的土地上,创伤小说无法避免地会与集体创伤叙事间彼此关联,个人创伤经历大多喻指集体创伤经历。创伤人物的塑造是创伤小说叙事的核心。在《天堂》中,出现了具有十分鲜明创伤特征的人物,他们对过去、现在均具有疏离感,在内心的挣扎与外界的挑战中,极具张力与勇气。这类创伤人物不但具有个性化,还具有普遍性,反映出了黑人创伤集体记忆下个人成长的痛苦。小说应用立体透视的叙事法,解读了黑人所受到的各类创伤。
四、走出创伤
创伤治疗与发声过程相类似,一个人只有治愈创伤,其才能更加珍惜现在,遗忘过去。同时,也能记起自己在某一时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并且清楚的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怎样才会更有意义,更加享受未来的生活。创伤受害者想要遗忘创伤记忆,分辨现实,认清自我,往往需要对创伤经历进行真实的倾诉,直接面对创伤,解脱内心的束缚。修道院的康瑟雷塔带领所有的女性舒适的躺在地板上,在地板上画出自己的轮廓,并勇敢讲述自己的经历,使其可以袒露自己内心的羞耻感。在整个过程中,每个女性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互相了解彼此,勇敢面对创伤,减少创伤带来的负担,使创伤可以就此治愈。生态主义追求自然和社会的生态平衡,使人与自然可以保持协调,而这也正是走出创伤的真正意义。
然而,鲁比镇的男性对创伤始终产生抗拒心理,不愿意承认自己内心存在的创伤。随着小镇问题的日益凸显,其认为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都来自于女修道院,认为修道院的存在对鲁比镇产生了阻碍,并对女修道院进行了袭击。也正是因为这次袭击事件,使鲁比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通过忏悔找到了自我,成功治愈了创伤,也使鲁比镇逐渐解除封闭。
五、结论
《天堂》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其内心的创伤和苦难的经历,但是在灵光之下,其身心的创伤将会逐渐被弥补和治愈,只有人们走出创伤经历,才能看见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