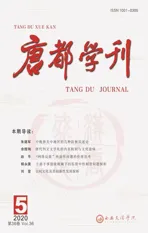唐代判文文学化的内在机制与文化意味
2020-12-07余煜珣
余煜珣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州 510275)
一、唐代判文及其文学化
判文是古代决断讼狱或公务的行政司法文书,在唐代臻于成熟兴盛。唐判可大致分为案判、拟判和杂判。案判即实际生活中决断讼狱或公务的判文,具法律效力。拟判即模拟所作、虚拟而为、不具法律效力的判文,一般是因科举铨选而作的判文,故也称“试判”。试判按其制作场合又可分“官试判”和“私试判”,前者是实际科举铨选考试中的考场判文,后者是士子在私下为考试所作的模拟试判(或练笔或作范文),如张鷟《龙筋凤髓判》、白居易《百道判》(又称《甲乙判》)等。除案判、拟判而外,其他判文形式则可称杂判。现存唐代判文大多为拟判,如《龙筋凤髓判》《百道判》《文苑英华》中的千余道判文。
近年古代判文尤其唐判研究逐渐成为热点。相比于法、史学界,文学界的研究目前仍有欠缺,但有些成果是颇为喜人的,尤其在判文的文学性、文体特征及源流演变等方面研究有了突破和进展。吴承学教授的《唐代判文文体及源流研究》一文,首次对判文文体的演变及其对叙事文学产生的影响做了深入研究。该文认为,唐代之后,在实用领域,具实用性和法学价值的判文兴起,取代了文学性偏胜的唐判。而在文学领域,判文内部发生了一些演变:一是有些判文演变成纯文学文体(如花判),借判文以抒怀,不再应用于政治生活;二是判文对叙事文学形态尤其案判小说产生了影响[1]157-179。此后研究多肯定此文观点,在判文的体制、文学特征、与叙事文学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上继续探讨,但仍较少关注判文向文学文体转化的内在机制,并思考其蕴含的文化意味。在笔者看来,唐判具有三重面相:法律文体、考试文体及文学文体,三种文体特征互相缠结和影响,造就了独树一帜的唐判;而在这影响渗透的过程中实际又隐含了分离的因素,使之演变出新的面貌,经历了由实用文体(法律与考试文体)向文学文体的转化。那么,法律、考试和文学三种属性如何在文体内部造成这种转化?这种转化又有何文化意味?这些问题目前并未得到很好的解答。本文拟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以期有助于判文文体及相关文学研究,并就教于方家。
二、文学、法律与考试的缠结:从文体内部看唐判的文学化过程
唐判文学性的形成,学界以往更多关注其外部因素的影响,如科举铨选的要求、唐代文风的浸染。本文试图将目光转入文体内部,立足于判文文体本身,描述其文学、考试与法律三种属性的互动,探究三者互动在文体内部赋予了判文怎样的文学特质,对文学化过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情节与结构:判文的叙事性
“判文具有关于事件由来、发展及结局等简单叙事因素,具有一定的故事性,或者说具备发展成叙事文学的可能性和空间。”[1]178判文的情节性确实是其对叙事文学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但其情节性是如何产生的还可更深入探索。
事实上,实际司法审判本身就有一定的故事性和戏剧化效果。首先,司法过程一般有法官、当事人、证人、律师等人物,譬如古代司法中就有执行裁决的官吏、当事人、讼师等,各自有其身份和角色功能。其次,司法过程有一定的程序,按时间和逻辑顺序步步发展,而一切都发生在特定场所,有一定的法律仪式,如法庭或官衙、开庭或升堂的仪式等。人物角色、地点、事件,构成了司法活动的过程,这与叙事文学的要素颇为契合。至于司法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事端,则可能更具戏剧性。而审判最终形成的判文,一方面代表这个过程的结束,一方面也是对这个过程的浓缩和复述。换言之,判文实际上隐含了一个潜在的完整故事。在判文基础上进行扩充、加工、演绎,将这个潜在的审判过程显现出来,这就形成了后世公案小说的叙事模式。故而在此意义上说,判文等于为公案小说提供了故事原型或背景。
在运用判文写作的公案小说中,判文实际可看作对案情的一种复述,故也可视为对小说情节的一次梳理或总结,客观上形成一种类似于“戏中戏”“画中画”的复调式叙事效果。这可算小说创作的新变。另一方面,判文在小说中的位置不同,作用也有异。若出现在结尾,就会起到结束全篇叙事、总结全篇小说的作用。若在篇中,则可起到推进情节发展的作用。有些唐代小说以前后两道判文作为主线,作为联结情节、推进情节发展的关键点,如敦煌俗赋《燕子赋》。这种结构可从唐判中找到一些相通点。唐判中存在大量“中间判词”,即当制判者通过对拟判事实的分析,认为尚需作进一步查证才能正确适用法律时,便制作中间判词[2]。如《龙筋凤髓判》“中书省”条之一云:
中书舍人王秀漏泄机密,断绞,秀不伏,款于掌事张会处传得语,秀合是从,会款所传是实,亦非大事,不伏科。
……张会过言出口,驷马无追;王秀转泄于人,三章莫舍。若潜谋讨袭,理实不容;漏彼诸蕃,情更难恕。非密既非大事,法许准法勿论,待得指归,方可裁决。[3]1
张鷟之判,据律区分了几种情形,最终认为要待确定该案所漏泄是否为机密之后,方能裁决。这种中间判词的意味在于,事情并非告一段落,而是有进一步发展延续的可能。在终极判词出现之前,案件有变化的可能,判决也可能随之变化。而诉讼审判活动本身也存在后续性,过程可能十分曲折,比如可能会有上级的反对驳回、当事人的申诉以及可能产生的激烈冲突等。总之,中间判词的写作对相关小说的情节设置可能存在潜在影响。
唐代拟判中有一种特殊形式叫“双关判”,通常认为是为考试练笔而作。《文苑英华》卷550—552“双关门”录双关判36篇,这里以苗晋卿《不帅僰寄军献二毛判》为例看其形制特征:
不帅僰寄判
国子监称,胄子不帅教,将棘寄之。省让其侵冒刑章,置之于理,监固论不已。
军献二毛判
又军旋凯,献俘毛有二者,执法止而劾之,军司云拔距投石者。
文以经邦,武以御寇。开石渠而设教,整金鼓以宣威。爰施上下之庠,式奉孤虚之术。语兹国序,相彼军容。……握兰称过,正合清明;执简弹违,稍乖深识。欲存疏网,宁失不经。[4]2810
唐代拟判用骈对形式是普遍情形,双关判则赋予这种骈对形式更丰富的结构意味。全判除最后一句外,每处骈对均是上判“不帅僰寄”,下判“军献二毛”,一一对应,一文一武双管齐下,由此形成往复交错之感,最后双线汇聚于“欲存疏网,宁失不经”的判语。
其写作技巧与后世小说戏剧中的“双线”平行叙事有相似之处:不同或相关的人物和事件,在叙事中各自发展,相互交错,互相照应,最后汇聚成结局。这在明清小说、戏曲中已成为一种常用的叙事方式。譬如清人但明伦指出《聊斋志异》有些篇目采用了“双提法”,即设置两条叙事线索相互穿插交汇,也就是双线的意思。如他评《香玉》:“乘机而入,双管齐下,篇中惯用此法,另是一样笔墨。”[5]1550在结尾处评道:“爱妻良友,两两并写,各具性情,各肖口吻。入手用双提,中间从妻及友,又从友及妻;复恐顾此失彼,以言语时时并出之。末后三人齐结,笔墨一色到底。”[5]1555这也可以当作对双关判特色的精彩评述。至于其他叙事文学,也常用此法,如《琵琶记》之蔡、赵,《牡丹亭》之杜、柳,《桃花扇》之侯、李,均是两头并进,别具意味。从这个角度看,双关判突出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技巧与叙事效果(1)在诗歌中亦存在此种特殊结构,如杜甫《存殁口号二首》:“席谦不见近弹棋,毕曜仍传旧小诗。玉局他年无限笑,白杨今日几人悲。”“郑公粉绘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每联均是一三句、二四句相应,一存一殁,交织而下,只不过未汇成结局。可见这种叙事方式在不同文体中都曾得到运用,最终在叙事文学中大放异彩。而唐代双关判在其中是否发挥过作用,以及它是如何形成的,是仍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拟作与修辞:判文的虚拟性
唐代拟判的虚拟性显而易见,也正由此与实际案判区分开来。一般认为官试判的命题有一个从“取州县案牍疑议”到“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的虚拟化的过程[6]。而私试判是考生模拟官试判而作,自始就带有虚拟色彩。如白居易判《百道判》中有直接取经籍之故事作为案情,亦有取经籍之义而自制相关案情,虚拟程度更进一步。另据学者考证,《龙筋凤髓判》为避讳而将真实人物姓名进行谐音替换、省略、更改等[7]。如此,尽管该学者认定《龙筋凤髓判》的判词问目是武周、中宗两朝的实录,但这种姓名的避讳无疑使判文带有一定的含糊性和虚拟性。至于白居易判文“假设甲乙”,不著姓名,则已是完全的虚拟杜撰了。总之,官试判和私试判都是对案件的有意虚构。
拟作的判文,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可称为一种“代言体”。在官试判中,考生需为法官代言,裁判案件。私试判的情形则更复杂,制判者首先需要代考官立言,即制题;然后代考生立言,即答题,把自己想象成身在考场的真正考生;答题过程中又需要代法官立言。代言,就是角色的模拟,故判文与小说戏剧又颇有相通之处。代人立言渊源甚早,诗文中早有代言体,考试文体则有宋代经义和明清八股,皆代古人圣贤立言。然唐代拟判之代言,似未有注意者。笔者认为判文亦有一定的代言特征,只是判文不是为特定人物(如孔孟)代言,而是为某种角色类型(法官等)代言。此其不同处,然莫不与小说戏曲之道相通(2)钱钟书谓八股:“以俳优之道,抉圣贤之心。”见钱钟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4-95页。。
判文只要不是在实际司法活动中所作,都可称为“虚拟”的,它们都是对现实案判的一种虚拟。但能否说实际案判就是“真实”的呢?事实上,司法过程是从“自然事实”中剪裁抽离出“法律事实”的过程,即确认法律事实的过程(3)“法律事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一如人类学家所言,它们是根据证据法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辩护技巧、法官雄辩能力以及法律教育成规等诸如此类的事物而构设出来的,总之是社会的产物。”参见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收入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80页。。可以说,所有判决中的事实其实都是一种经过了剪裁与拼贴的叙事,这种剪裁是在法官指导下构建的对于判决叙事的修辞[8]。判决修辞对事实的剪裁,除了法律事实之生成,另一个根源,是法官对于判决的结果判断往往先于事实认定、逻辑推理和法律适用[8],换言之,源于法官的“前见”。法官如何剪裁以生成法律事实,实际也受这种前见的左右,其司法经验、个人经历、价值观、知识结构与水平、对理论的掌握,甚至对事件或当事人的偏见、对公众反应的预期等,都能影响其对“事实”的判断和剪裁。总之,司法过程中所必需的“修辞”,已使“事实”不同程度地虚化。
具体到唐判,可认为判文修辞在一定程度上已然“改写”了案件事实。徐忠明教授指出:“我们只就运用骈偶对仗、堆砌词章这点进行查考,这种判牍显然已经或多或少地‘改写’了案件的固有事实;也就是说,每个案件的事实都是独一无二的,可是经过李清(其他作者亦然)大量援引四书五经以及各类诗文作品的典故构筑起来的案件事实,难免歪曲失真。另外,从口语到文言的转换,也有可能改变案件的真情实况。”[9]55说“失真”则可,“歪曲”则不尽然。语言形式风格、典故运用等修辞所造成的“失真”,可以判文中“以赋为文”的倾向为例。如《龙筋凤髓判》“公主条”:
金机札札,灵婺皎洁于云间;银汉亭亭,少女倭迟于巽位。故潇湘帝子,乘洞浦而扬波;巫峡仙妃,映高唐而散雨。公主秾华发彩,蕣萼延祥,六珈玉步之辰,百两香飞之日。三公主婚,鹓鸾接羽,百枝灯烛,光沁水之田园;万转笙竽,杂平阳之歌舞。[3]9
此判重在描绘公主出嫁的场面,极尽铺叙之能事,类于赋体,而所描绘的实则大部分与案件无太大关系,对案情分析并无助益,恐怕仅是单纯的罗列和铺叙,为描写而描写(4)这还与《龙筋凤髓判》“取备程式之用”“本为隶事而作”的性质有关。。在其他唐判中,这种仅针对某一点进行想象和大肆渲染的情况实则广泛存在,每每予人喧宾夺主的印象。这种想象之辞,一方面是案件内容的填补和扩充,另一方面也因一味扩充而挤压了甚至取代了更重要事实的叙述,使之成为剪裁而成的事实。更何况这种填补扩充更多的是基于想象,而非严密推理,故已是虚拟化了。
(三)同事异判:判文的开放性
与由修辞形成虚拟性相关的,是判文的开放性。这是指对同一案件或相似案件,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判断和裁决。首先,同一个人对相似案件判法可能不同,这往往体现在判案依据是“法”还是“经”的抉择上。如《百道判》中关于妻子“七出”的两道判词,案情类似,但一个依法一个引经,做出了相反的判决[10]。但因为具体案例之间存在差异,也可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角度理解。另一类情况是不同人对同一案件的判法不同,有论者称之为“同事异判”[11],其分歧与开放则更为明显。《文苑英华》中,许多判目下收录了多道判文(5)如卷五○三《习星历判》有六道,卷五○五《西陆朝觌判》有七道,卷五一三《泽宫置福判》六道,卷五一二《毁方瓦合判》五道,卷五一九《归胙判》八道,卷五三六《太室择嗣判》八道等。,学界通常认为这类判文即是在实际考试中所作,即“官试判”,因为这符合考试中考生对同一题目各自作答的情况。由于制判者众多,产生分歧的可能性更大,判文的差异就更为明显,所以上述依经还是依律的问题在《文苑英华》的“同事异判”中比比皆是[11]。
产生上述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古以来儒家思想对司法过程产生深远影响,一个显著体现就是所谓“经义决狱”。自董仲舒“春秋决狱”始,法官援引儒家经典中的“经义”作为断案依据成为一种范式,礼法开始合流。直到唐代,礼法合流在“一准乎礼”的唐律中基本臻于成熟定型,成为中华法系的一大特色。这背后体现的就是“礼法合流”的儒家化法律传统[12]。然而,礼与法并非总是完美融合,也会存在冲突,因此中国传统法律中还存在一个礼法冲突的困境,依律还是依礼,如何把握取舍,这一难题就考验着制判者的思维。此外,经义决狱本身也存在某些问题,经义内部本身就存在分歧和矛盾,因此对经义会存在不同的理解。这种分歧会导致经义解释的随意性,而以经义作为断案根据就更增添了判决的模糊性和主观性,给予判决者能动性的同时又加大了其任意操纵判决的可能性。在判决中,制判者对礼法的理解程度、对判决操作的熟练程度、对问题的态度、价值取向、切入的角度等等,甚至临时起意、一念之差,都可能使之做出不同的判断。“前见”既可造成制判者对事实的剪裁修辞,也可造成其对判决理据的不同选取。前者形成虚拟性,后者则形成“开放性”——一个确定的事实,可从中产生不同理解,换言之,由确定性产生不确定性。
此外,同一判文内部,由于判题信息量有限,案件中人物身份、地位、职业等信息可能缺失,案件事实只是相对确定,故制判者需要根据对这些信息的不同假设,对人物做出不同判决,这是另一意义上的“同事异判”。如《复以冕服判》:“甲复以冕服,御史纠其违失。”制判者梁乘判曰:“复魂不似其服,魂将奚依?”“小者则榆狄素纱,诸侯乃衮衣冕服。未详甲也,其位若何?傥有土之公卿,御史斯为折角;若食菜之乡士,甲也宜从噬肤。”[4]2662-2663冕服当为诸侯所用,而甲以之为其行复礼招魂,则需根据死者身份判断是否合理。因此制判者假设了诸侯和平民两种情况,从而作出不同判决。上文提到《龙筋凤髓判》中有判云“若潜谋讨袭,理实不容;漏彼诸蕃,情更难恕。非密既非大事,法许准法勿论,待得指归,方可裁决”,也是因事件暂时不明而假设可能的情形,不同情形有不同判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中间判词”因其不确定性,也具有了一定的开放性。上文讲中间判词意味着案件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也正是就其不确定性而言。因此,事实中一些关键信息的缺失,也可以产生不确定性,从而产生开放性。
开放性也是判文文学化得以成立的一个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特质就是多义性,其文本具有开放性,在这一点上判文与文学文本有契合处。更重要的是,开放性本身就有生成虚拟的可能。因为理解愈纷呈,分歧愈明显,离所谓“客观真实”也便愈远——但因此进入“艺术真实”,或者说出现更多“艺术的想象空间”。
(四)法意人情:判文的情感化
唐判往往被赋予强烈的情感色彩。其骈俪风格、整饬句式首先就造成一股强劲的气势,再加上繁密的用典、连珠的比喻类比,纵横铺排,使读者不得不受其感染,为其所动。这是其以文学性增强说理性的一面。
其情感色彩还体现在判文中时常融入作者个人的情感褒贬。如《龙筋凤髓判》“内侍省”第二条:
元淹佞幸居怀,谄谀成性。同竖刁之狡狯,翻覆邦家,类伊戾之猖狂,动摇州郡。回天转日之势,况此犹轻,城狐社鼠之威,方斯未甚。有恭石之巨蠹,滥奉前规,无管勃之奇功,叨居近习。往还三辅,威福甚高,去来两京,风霜极烈。苞苴未入,坠以黄泉之深,贿赂潜通,招以青云之上。鞭笞士子,耻辱官寮。犬羊披虎豹之毛,燕雀假凤凰之翼。岂可滥班九掖,点秽罘罳,直可投诸四荒,以御魑魅。驰驿速发,无俾少留。各下所司,即宜催遣。[3]91
作者似乎是有意搜罗各种贬义典故,“以极其典雅的骈体和一连串酣畅淋漓的贬义的典故痛骂了佞悻小人”,这“实际等同于一篇骂文”[13]。作者在此已大可不必进行案件分析推理了,在情感上早就征服了读者。
情感化表达是判文的必要修辞。在试判中,应试者出于追求功名的急切目的,往往有意增强判文的情感特征,试图在情感上、声势上打动考官。除开考试因素,以情理断案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情理法”的儒家化法律传统。“在中国,断案尽法之外,还得照顾‘情’,又是绝大部分司法官的观念。于是,法得、情得,法平、情平,法到、情到,就成了司法者追求的最高的圆满境界。”[14]“情理法”传统下的中国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没有严格地适用法律,更多的时候是参酌人情,“那些受到称道、传至后世以为楷模者往往正是这种参酌情理而非仅仅依据法律条文的司法判决”[15]。不独唐判如此,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谓:“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16]明代徐师曾亦说写作判文应“执法据理,参以人情。虽曰弥文而去古意不远矣”[17],都强调了情理在法律判决中的重要地位。判文所具有的用典譬喻和情感化特征,事实上就形成一种道德说教。以情动人,以理服人,这是“情理法”的一个内在要求。判文情感化的一个重要价值,是制判者在其中有了自我表达、宣泄个人情感的趋向,这有助于实现判文向更私人化的文学形态转变,值得注意。
如上所述,在文体内部,判文的法律和考试属性多少产生了潜在的文学化因素,譬如考试的代言特征有助于形成虚拟性,法律传统中的经义决狱有助于形成开放性。而单就某一文学化特征而言,也大多是由文学、法律与考试三重面相相互缠结、共同促成的结果。例如判文的虚拟性,大体而言,用典、铺排等修辞是文学写作的要求,修辞也为司法所要求,虚构案情与代言性质则因考试而生,虚拟性的形成实得益于三者合力。其他几个文学化特征亦大抵如是。这提醒我们,在判文的文学化中,非文学的因素曾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
判文本身的纯文学化,主要得益于其虚拟性和情感化的形成;判文转化为叙事文学形态,则主要来源于叙事性、虚拟性和开放性的生成。当然,这多种特征是一个整体,它们共同起作用,完成两条路径的转变。
三、从“为人”到“为己”:唐判文文体转化的意味
吴承学教授认为,考试文体之产生,是古代文章史上一大转折,它标志着文人之写作从此与功名富贵结下不解之缘。在以文章考试取士制度产生之前,作文者为己;在以文章考试取士制度确立之后,作文者为人[1]63-64。考试文体的功利性不言而喻。具体到判文,士子们试判前就需要做足功夫,比如像白居易在考前练笔,创作模拟考试的判文,或是背诵大量范文,积累素材,学习模板,以供考试时挪用套用,甚至可能是直接抄袭(6)比如《龙筋凤髓判》和《百道判》,就成为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判文范文集,影响甚大。《朝野佥载》中还有“周大官选人沈子荣诵判二百道,试日不下笔”的笑话,可见背诵范文之风之盛,弊病也不少。参见张鷟撰、赵守俨点校《朝野佥载》卷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2页。。试判中潜在的功利性还在于,司法一般须体现立法精神,亦即体现国家权力与统治者的意志,试判也是如此。试判实质就是国家法律的一种体现,它必须与统治者的意志保持一致,不合主流法律精神的判文是不被允许的。这里的法律精神大致等同于古代法律传统,也包括了情理断案和儒家原则,事实上判文也不可能超出这些基本架构。所以判文的写作实际上是被限定在了法律制度与传统之中,判文作者在写作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与国家意志、政治制度保持一致,如同对国家意志做了一次注解。总言之,对考试判文的写作和作者来说,大抵有两层束缚:第一层束缚是考试制度,包括考试的压力、备考和命题等;第二层束缚来自法律制度,更本质的是来自国家意志。
作为法律文书的实用性案判也同试判一样,必须牢牢蜷缩在法律传统的牢笼里,几无例外,并且因其现实性,这种对法律的适应性也比试判更强。更重要的是,这种适应性还往往表现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论者以包拯为例,认为清官的政治功能往往局限于皇权的范围之内,他们所要伸张的正义只能囿于“王法”所能负载的价值,以“王家法不使民冤”为最后归依和终极目标。虽然他们有时也会超越法律,根据实际情形“自由裁量”,以实现所谓“个别正义”或“实质正义”,但这种“自由裁量”也以无碍皇权专制的根本利益为限,过此界限,依然不被允许[9]379—388。案判尽管是国家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但无论是否出于自愿,无论正义与否,通常都以某种政治权威为依附,故在一定意义上也属“作文为人”。出于对权威政治的畏惧、迎合、倚恃和奉承,判决过程及产生的判文被烙上此种意识形态的印记,或可使人性光辉被意识形态掩盖。
因此,无论试判还是案判,本质上都是带有强烈实用目的的文体,原本由功利性出发,最终却因这功利性而趋于文学化,从功利中超脱,朝着非实用的文学文体转化。笔者认为,这种转化有着深刻的文化意味:它意味着中国文学中原先“作文为己”的文学变成“作文为人”的功利性、实用性文学后,这一类文学中的一些文体又向自主自发的创造性文学转变;并且,这种转变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作文为人”之文学本身造成的,它隐藏着自我突破、解体和变异的因子,无意间成了自己的“掘墓人”。一方面,如前文分析的,判文之文学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考试与法律两种因素赋予的;另一方面,正是考试制度催化了判文的写作,使人们趋之若鹜,在文学性上殚精竭虑。倘若当时不以试判选官,判文在当时不会广受重视,那么这种趋之若鹜和殚精竭虑就不会如此明显,产生判文文学化的肥沃土壤也就较难出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作文为人”之文学促成了自身的瓦解。这是对“作文为人”的反叛,也是对“作文为己”的回归。其间我们看到人的主体性之回归,并且在市民文学蓬勃发展的浪潮中得到逐步加强,被功利实用淹没的“人”逐渐复归于自由之境。在文学史上如判文般经历此种彻底转变的情况恐不多见(7)在考试文体中,八股文也有游戏化的现象。(参见黄强《八股文与明清戏曲》,载于《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但一方面八股文是最为人诟病鄙夷的一种考试文体,故其文学化的可能和空间较小;一方面或许正值中华帝国的没落,八股文难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随着科举遽然终止,八股文也寿终正寝,没有发展的可能了。八股文也会对叙事文学产生某些影响,但总的来说其影响之深远当不如判文。而下文也会提到,许多实用文体都有虚拟化俳谐化的现象,但如判文般对叙事文学产生深刻影响、甚至直接演化出一种叙事文学形态的文体,似乎没有。,故尤其值得注目。
对功利与实用的逃离,对“人”主体性的回归,可从两方面看:一是判文对政治权威的解构,二是法律正义精神向文学的渗透。前者侧重于对纯文学判文的讨论,后者则主要针对公案文学而言。以下析而论之。
(一)解构权威:文体功能的扩张与分化
许多应用文体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仿作、拟作乃至戏拟的情况,出现游戏化、滑稽化的倾向,最后往往成为纯文学文体。除判文外,还有檄文、露布、弹文等。一般而言,这类应用文体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一般是官方公文,存在一定的权力对话关系,严肃庄重,又往往带有一定的情感因素,并且一般是比较受重视的文体。有论者称这种现象为“解构性破体”,即是文体的解构,以戏拟的方式颠覆旧文体,在解构中又有新创[18]。判文等公文的这种演变,即是文体功能的扩张和转变。其原先固有的功能是实现某种政治功能,但随后这种功能产生扩张,脱离特定政治语境而转入历史和日常生活,乃至发生变异,成为“独抒性灵”的一种凭借。
这类公文文体往往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并且通过官方制定和历史累积形成了强势传统。文人们一方面有了“自铸伟辞”的诉求,遂将权威刻板的官方行为变作抒发自我的私人行为,以解构文体的方式解构和嘲讽了文体背后的权威,完成表达自我与讽喻现实的目的;一方面孜孜追求新奇,大力破体,客观上形成了“陌生化”的美学效果。而在这两者中间,文人趣味是重要的黏合剂和催化剂,“雅噱”成为文人常见的创作心理。于是,这类文体往往在随意但并非无意的游戏当中,形成了追求美学价值、表达自我情感和讽刺现实的多重效果(8)如尤侗在《磔鼠判》中以判文形式判决一只鼠,想象大胆而新奇,文学的虚拟意味浓厚。由此抒发了诗稿无存的恼怒,又隐晦地表达了“刺奸”的意图。这种判文并无实用的政治色彩,而是站在了政治的对立面,对政治和世俗做了游戏化的嘲弄。。
判文本身在唐以后有两条发展路径:一是沿着其固有的实用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舍弃文学性,如宋代和明清的散判;二是向纯文学判文演进。这种文体分化也就是功能的分化:一为“载道”,实现政治功能;一为“言志”,完成个人创造。判文演变成散判且重法律性、实用性,是对传统判文文体的复归或“纠偏”,从此走上判文的“正道”,但这也正为判文的文学化留出发展空间。这或许不是历史发展的巧合,而恰是人的主体意识强烈迸发的必然。判文作者本身有“言志”的强烈需求,而要“言志”,就须打破文体中附着的政治因素,突破政治实用性,这就导致了判文功能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分化。
(二)诗性正义:正义精神之于文学
判文的文学化,尤其是其对公案文学的影响和介入,另一种意义在于,它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更多的法律精神、伦理精神和正义精神,丰富了文学的正义和人文意蕴。在中国,法律寓于文学自古有之,涉法文学源远流长。但自判文介入文学而形成公案文学之后,法律故事才算被正式地、有意识地独立出来,当中体现了强烈的创作意识和主体性意识,由此法律精神也正式成为中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内涵,人文意蕴得到增强。这一方面得益于法律的繁荣,一方面文学的通俗化提供了广泛的受众,判文在这双重背景下应时介入文学,形成了独特而深刻的法律文学形态,这是颇有意味的转变。
判文对文学史的意义,或许大于对法律史的意义。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法律精神充分渗透到文学中,其实就是在文学中得到确认和保存。并且文学以其感性动人的形式、人间百态的内容,又反过来增强了这种法律精神,使之充盈着人性光辉,历久弥新。就这一点来说,判文对于中国法律史发展又不可谓无功。总之,文学与法律的双向互动,使判文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诗性正义”的典范和重要奠基,也由此成为超越实用的人文主义文本,与那种抒写心灵、讽喻人世的纯文学判文交相辉映。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谓判文由实用性向文学性转变,并非仅仅以是否实用、是否具有美学价值区分二者。笔者所谓的“实用性”,实在于其背后强烈的功利目的,以及权力话语阴影下人的主体性的隐没;所谓“文学性”,无非是认同和钦羡其中人的主体性之确立和丰厚的人文意蕴,而非仅仅从“纯文学”角度出发。在这个意义上探讨这个转化过程才有更深的文化意义。
判文文体的转化是一个个案,因为这里仅仅指出了中国文学和文化中一根细微的弦。或许在整个文化演变过程中它实在微不足道,但毕竟从中听到了弦外之音,并且希望其能余音绕梁——判文文体的转化不仅是一个个案,其内在的精神遗产仍能流传不息。今天,正朝着现代迈进的中国已然刻意疏离了唐判那种文采斐然的“浮华”,甚至唐后那种虽显质木、仍可赏读的判文亦难以复见,其法意人情之交融、其法律与文学之共生,或许在现代理性社会中亦已举步维艰。但判文丰厚的人文遗产,即其所遗留的正义与独立精神,理应继续为人珍视与铭记。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