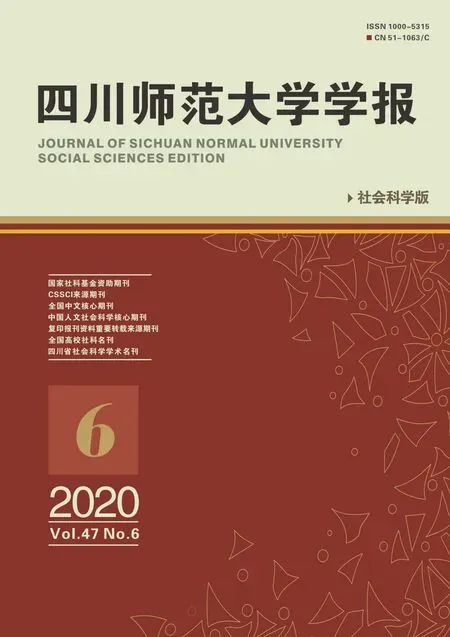“形”:早期艺术观念中人神对话的语言基础
2020-12-02谭真谛
谭 真 谛
(1.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6; 2.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重庆 400065)
诗学理论中的形神理论并非无源之流,学者们对其如何进入诗学理论范畴作出了探源研究,如郭绍虞先生在《郭绍虞说文论》中指出庄子哲学为形神理论的源头,高楠先生在《艺术心理学》中指出先秦早期道家著作《管子》中“精”“气”的哲学思想为形神理论的源头,陈良运先生在《中国诗学体系论》中指出《周易》哲学为形神理论的源头等。就此,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学者们基本上将形神理论的源头定位于先秦时期;第二,形神理论的演变始点是有关于“形”“神”的哲学思想;第三,“人”这一中介是“形神理论”从哲学思想到文学艺术理论过渡的关键环节;第四,研究多聚焦于“神”,而缺乏以“形”为重点的研究。因此,关于形神理论的发展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充实。本文欲以“形”为线索进一步探讨其生发脉络,以见出“形”之于“形”“神”二者关系架构时的基础性地位。
一 “形”“神”内涵考释
我们将中国诗学中形神理论的源头定位于与其相对应的哲学思想,这是一种将思想对标思想的研究方法。但是,我们不禁想问:哲学思想又从何而来,正如“神”又是怎样走入先秦哲学领域的?如若我们给哲学下一个定义,即亚里士多德所言“思想思想”,哲学思想以思想为思想对象,是对于人类一系列观念的反思。按冯友兰先生所讲:“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这种思想,所以谓之反思的,因为它以人生为对象。人生论、宇宙论、知识论都是从这个类型的思想产生的。宇宙论的产生,是因为宇宙是人生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534页。那么,作为哲学思想的“神”应是对关于“神”的思想的再次反思与总结,而关于“神”的思想则是对实际生活经验的反思的结果。因此,在先秦诸子哲学之“神”产生前,必已有关于“神”的思想存在,如西周的“祖先神”,又或更早的夏商时期,即有“使民知神奸”和“率民以事神”中所指的“天神”观念。进而上溯,此类“神”的思想当是源于早期人类具体生活实践中宗教崇拜对象之神灵的内涵。


二 “神以形显”的认识模式
如前所述,“神”的最初内涵是以实在自然为基础,那么,“神”这一概念在没走入哲学领域之前是不能作为一个绝对抽象的观念而存在的,如柏拉图所谈的“理念”,同样,也谈不上老、庄所谓的“离形去知”,即对“形”的否定而实现对“道”的把握。恩格斯认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703页。。由此,无形的宗教观念即是生活中有形事物的“幻想的反映”,“神”的概念形成以“形”为基础。对于早期先民而言,实在的自然界更为强力地影响着人类生活实践,而人的认识能力却局限于不能全方位地把握自然规律,因此,神首先是反映自然力量存在,早期神灵观念中神与有形自然之间存在同质性。即是说,先民们以神秘性的思维感知方式将客体自然附上了超出于物理事实之外的神秘因素,并且通过思维活动将客体自然进行抽象加工,进而出现了神对于客观实在性的超越,并生发出支配一切的形上概念,实际上是希望以此宗教的方式回答强大且未知的自然力量。自此开始,观念的自然与实在的自然逐渐分离,形成了大众公认的抽象概念——“神”(神灵)。这是“神”脱离有形实指而走向无形观念的开始,亦是“形”“神”对应关系认识产生的一个始点。正因如此,为后来“神”脱离纯粹宗教中的神灵内涵,走向指称代表主体和艺术的内在无形观念、意识的内涵,进而延伸为诗学中的形神理论创造了过渡的观念基础。
人类对神意的获取就是对“形”(自然现象)这一神的语言的读取过程,这个过程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重点即是把握自然,其基础在于主体对于客体之“形”的具体认识与感知。如恩格斯所讲:“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更换等等的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由此,尽管宗教上的神以无形观念存在,然而却脱离不了对具体生活经验的反思,即其实质上是以形下之“形”为建构基础。孔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23)《十三经注疏》,第2483页。墨子曰:“是与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请惑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24)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223-224页。从孔、墨二人的认识论来说,“有”(事物存在)和“知”(知识经验)均来自于“见”“闻”,即认识和感知。这种知识起源于经验的观点,否定了超验的唯心之“思”,具有唯物主义精神,相当于列宁所说的“有思想的经验论”,这也符合早期人类的生活实践实情。早在孔、墨二人之前的夏朝,以“形”通神、以“形”知神的认识模式已反映在了造物艺术之中。《左传》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25)《十三经注疏》,第1868页。同理,“备百物”是“知神奸”的前提条件,即通过对百物之“形”的认识和感知,方可实现知晓神意的宗教效果。由此可知这样一种人神关系:因“形”(客体自然)而可“见”(感知获取),可“见”而“有”(神的存在),存在而有“意”(神的意志),知“意”而有“知”(知识经验),有“知”而通神。《周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6)《十三经注疏》,第86页。通神的方式就是对自然之“形”的认识和模仿,突出了以“形”通神的人神对话方式,同时也指明了“形”以通神为最高标准,故而可见“形”与“神”之间在形神理论产生之前便存在双向的互通关系。总之,尽管宗教以追求超验之神为最高标准,但必须经历由“形”到神的对话过程。先民有关“神”的思想是基于实践经验的累积,在早期“神以形显”的认识模式中,“形”起着人神间的中介作用,感“形”是人神沟通的唯一方式。

三 “以物通神”的制形理念
“神以形显”的“形神一体”观念,影响了中国早期“以物通神”艺术观念的兴起。我们说神以自然现象之“形”为语言对人说了些什么,那么人则以人工物之“形”为语言对神表达着诉求,由此神、人之间才实现了无阻碍的双向沟通。前者反映在自然规律认识不成熟和生活经验匮乏时期,人类以“形”为基础认识和感知客体自然的一面;后者则反映为出于生存需要,人对客体自然改造的一面,作为人工物的艺术则是在这一面相中的产物。随着早期人类生活实践经验的积累,在造物工艺和艺术观念上形成了一定的创作自觉,虽并不成熟,也未形成专门的美学或诗学理论,但是器物中所传达的“以物通神”艺术观念与后世诗学理论中“以形写神”的形神理论命题遥相呼应。
《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33)《十三经注疏》,第762页。《周礼》中所提及的苍璧、黄琮、青圭等礼玉一类器物,因其参与宗教祭祀活动,承载了上合于“神”的宗教内涵,而超出了一般的审美和实用功能,成为了隐喻哲学和宗教观念的“形”,即黑格尔所谓的“象征型艺术”。黑格尔认为,“象征首先是一种符号。不过在单纯的符号里,意义和它的表现的联系是一种完全任意构成的拼凑。这里的表现,即感性事物或形象,很少让人只就它本身来看,而更多地使人想起一种本来外在于它的内容意义”(34)黑格尔《美学》第2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页。。不仅礼玉如此,青铜礼器的爵、尊、鼎,或更早的陶制礼器爵、鬶、盉、觚也是如此。礼器成为了蕴含特定观念的语言,因“形”而存在,因“形”而被公众感知和认可,并因有“形”可知而成为人神对话的具体语言,以实现人神沟通,由此,人神之间有了得以实现双向沟通的稳定通路。作为宗教祭祀的礼器,为实现通神目的仍需要以特定形式去承载人们的观念,因此,宗教活动中如何营构器物之“形”,使其成为人神沟通中更能通达神意的语言形式,便是先民们思考的重点。在此基础上,先民们逐步形成了对艺术规律的把握,并将此运用于艺术实践之中。
首先,通神器物之“形”以符合社会和自然规律的事物之“形”为原型。新石器时期的齐家文化出土了大量的玉制品,其中武威娘娘台出土的玉斧,虽是无实用价值的观念承载物,但从造物形式上来说仍保留了旧石器时期石斧、石铲或石锛的造型。从可用之工具的石斧到通神之功能的玉斧,意味着纯粹艺术产生的可能。即对实用性的脱离,使艺术可以突破以实用功能为主导的造型设计,唯有如此,才可以将人类的浪漫想象融入艺术作品之中。艺术打破了形式局限,为艺术形式和内涵的丰富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艺术实是沿这一路径产生:实用物→半实用物半精神物→非实用精神物。以石斧到玉斧为例,在旧石器时期,为了配合早期人类生产活动,人们通过打磨等加工技术发明了重要生产工具石斧,其形式设计以实用价值为导向。发展至以农耕为主的新石器时期,人类更迫切地需要对自然规律进行把握,先民将石斧立于土地之上观测日影变化,由此石斧发生了从直接作用于生产的实用物到认识自然的间接实用物的性质变化,这为产生非实用精神物的玉斧提供了过渡条件。对此,于民先生谈到:“工具本身已部分地不再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不再完全遵守工具的制造和使用的要求特点,而是作为一种间接从属于实践、从属于一定非直接功利的物品……它的形式的结构也因适应认识功能的需要而逐渐发生演化,从最初的与生产工具外形的完全等同,到与生产工具外形的大体相近,直至异于生产工具的外形。”(35)于民《春秋前审美观念的发展》,第14页。此处对于艺术发生的总结,有益于我们理解一般人工品到艺术品的演变过程。即脱离生产实用性需求的艺术品其形制设计无疑更多是无形观念的融入,当艺术品外在之“形”作为内在观念的表达时,其“形”随之发生脱离生产工具之“形”的改变。然而,在看到早期艺术由于通神功利性的突出,反映为以神灵观念主导艺术形式呈现的同时,艺术品之“形”在观念传达之余,其外在形制设计仍离不开早期的造物经验累积,应该说,艺术品之“形”与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相符的工具之“形”仍然具有紧密联系。实用工具之“形”产生于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因此,这类实用物符合社会和自然规律,对人类社会生活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然而,受制于认识局限,先民们喜于将这些积极作用视为神的恩赐,故而在“互渗律”思维作用下,宗教通神物之“形”会出于对神意的尊重,而沿用生产实用工具之“形”。那么,艺术品之“形”因具备了合于神、通于神的形式存在,所以具备了通神的功能,而成为了人神对话的语言。

最后,祭祀器物作为神人沟通的媒介,因此在对器物形式进行设计的时候,还需考虑主体感知和接受的问题,即主体如何更容易察觉艺术品形式的问题。贡布里希曾讲到:“我们走进这些岩洞,穿过又低又窄的通道,一直深深地进入幽暗的山腹之中,向导的手电筒突然一闪,照亮了画出的一头公牛,这确实是一种奇异的体验。”(40)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相较于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壁画将艺术留给神灵、不考虑人的在场,中国早期的宗教活动是人神共在的双向沟通。因此,人如何更容易见到器物之“形”关系到整个宗教活动中人、神、物三者间的信息传递,并最终决定着宗教效果。杨泓先生曾总结过原始艺术的外形特征,他谈到:“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的彩陶,几乎全是将壶、罐类器表的彩纹集中绘于肩和上腹,也就是主要的装饰花纹带集中在器高二分之一以上处,而在器高五分之一以下,一般是平素无纹的。”(41)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9页。可见,艺术之“形”的设计无法脱离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情形。又如三里河遗址发掘的狗型鬶一类仿生陶器,因器物置于地上使用,低于人的水平视线,所以器物形式均是动物抬头仰视,这无疑同样是出于人们审美接受角度的考虑而形成的造型规范。通过便于接受者感知的形式设计,人与器物上的动物仿佛进行着对话,从而更利于人神沟通。总之,宗教是人主观的产物,先民将自认为美好的事物献于神,他们认为神也同样喜欢这些形式的东西。所以,通神之物当是基于先民们的美感经验而营构,并且考虑到了主体感知活动中审美接受的问题。
四 结论
早期艺术是承载了政治、宗教理想的功利性观念物,其创作无疑秉持“以物通神”的美学理想。以此观念出发,我国古代的审美评价延伸出了“道”与“器”“道”与“艺”的高下之分,重“神”而轻“形”,甚至反“形”的“通神”“载道”“言志”等等命题亦成为了中国早期的主流诗学观念,于是我们自然给予了“神”更多的关注。但是按孔子“文质彬彬”的美学理想来说,艺术当是通过外在形式与内在主题的完美结合来彰显其艺术魅力。感“形”是通“神”的重要始点,在早期先民的审美理想当中,无形之“神”不是无法把握的、神秘不可知的抽象哲学概念,神的神秘性充斥于具有生意的天地自然,故而神被人纳为可感知、可沟通的存在对象。人们通过对实在之“形”的把握而通达神意,进而实现超越有限之“形”,最终通向主体内在之“神”与无限崇高之“神”的冥合的“天人合一”境界。所以,研究中国诗学的形神理论,除以“神”为线索的研究思路之外,应当有一条以“形”为线索的研究思路与之并行。如若说艺术品是以“有意味的形式”呈现于接受者眼前,那么这个“神”如何得到更好的传递,当是离不开“形”的。“神”既因“形”而自证存在,又因“形”而与人实现对话,可以说,“以物通神”的美学理想即是以承认“神以形显”这一形神关系为前提的,故而,我们既要看到“形”“神”的紧密关系,同时也需要结合艺术源于生活实践的观点,从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角度考虑早期艺术对“形”的自觉把握,如此,则可以更为全面地把握中国诗学中形神理论的实际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