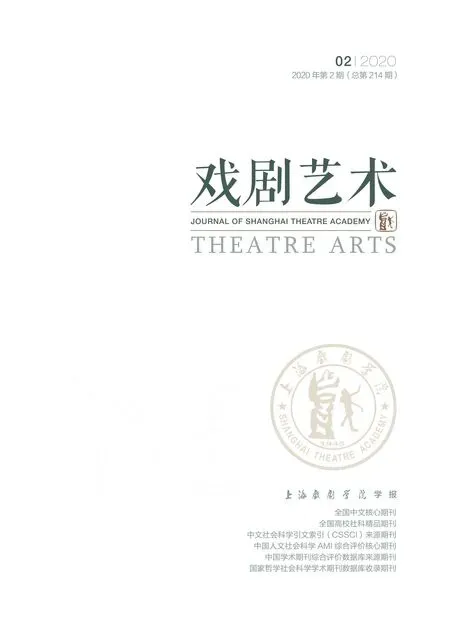纪德的戏剧世界
2020-12-02杨亦雨
杨亦雨
一、问题的提出
纪德(1869-1951)一生跨越十九和二十两个世纪,作为现代法国著名作家,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创作而言,其涉足之域便包括小说、戏剧等。然而,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纪德似乎主要被视为小说家,他在戏剧方面的贡献,则往往被忽略:当代戏剧史几乎没有给纪德留下任何实质的地位。出现这一现象的缘由之一,或许是人们很难将他的作品归入某一特定的戏剧门类。在此背景下,纪德的戏剧写作也经常被遗忘。但是,进一步的考察表明,纪德与戏剧世界并非真的毫无关联。事实上,纪德曾经留下不少经过深思熟虑、具有戏剧意义的作品。早在1889年3月12日的日记中,纪德就有了明确的戏剧创作想法,并萌生了创作一部戏剧作品的意向。以此为前提,纪德先后完成了《扫罗》(Saül)和《康多尔王》(LeRoiCandaule)的创作。
从更广的视域看,纪德创作的戏剧作品并不限于以上几部,他曾在1947年前后出版过一套名为《戏剧全集》(ThétreComplet)的作品集。这套作品由八本剧作组成,收录了纪德所有原创和翻译的戏剧作品。除了上文提到的两部作品以外,还收录了其他14部作品,(1)具体包括:《罗伯特与普遍利益》(Robert ou l’Intérêt Général)、《梵蒂冈地窖》(Les Caves du Vatican)、《菲罗克忒忒斯》(Philoctète)、《哈姆雷特》(Hamlet)、《回归》(Le Retour)、《拔示巴》(Bethsabé)、《大埃阿斯》(Ajax)、《浪子回家》(Le Retour de l’Enfant Prodigue)、《安东尼与克丽奥佩特拉》(Antoine et Cléopatre)、《艾玛与国王的来信》(Amal et La Lettre du Roi)、《俄狄浦斯》(dipe)、《珀耳塞福涅》(Perséphone)、《第十三棵树》(Le Treizième Arabe)和《诉讼》(Le Procès)。其中,《哈姆雷特》《安东尼与克丽奥佩特拉》和《艾玛与国王的来信》均为纪德的翻译作品。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纪德的戏剧作品题材涉猎广泛,如《菲罗克忒忒斯》《俄狄浦斯》《珀耳塞福涅》《大埃阿斯》等均以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命名,其内容也取自相关神话,《浪子回家》源自《圣经》故事,《诉讼》取材于卡夫卡的同名小说,等等。从创作方式及戏剧形式看,《第十三棵树》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梵蒂冈地窖》则来源于历史悠久的傻剧。然而,不论题材如何多样,形式如何变化,纪德始终着力刻画剧中不同人物的个性特点,也就是说,其关注重心,总是指向剧中的个体与自我,而由此展现的自我形象,则既具有多样的形态,也包含内在的张力。通过这些人物丰富的个体形象,不难看到自我及其精神世界的深层展示,纪德戏剧作品的独特之点和内在价值,也体现于此。
回溯纪德戏剧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他对戏剧的最初热情来源于传统戏剧,包括希腊悲剧、法国古典戏剧以及莎士比亚戏剧。在纪德看来,这些作品的特点不在于戏剧技巧,而在于其中某些部分涉及伦理学、美学的问题,引人深思。当纪德在1931年计划创作《俄狄浦斯》(dipe)时,他重读了《俄狄浦斯王》(dipe)和《安提戈涅》(Antigone),并颇有感触地写道:“我对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王这两个人物形象怀有最深的敬意。在我看来,在任何一种文学形式中,都找不到如此美妙的描写。”(2)André Gide, Journal 1889-1939(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51), 927.此外,莎士比亚也是纪德十分崇敬的一位剧作家。在众多莎翁的作品中,纪德偏爱他的历史剧本。在写给亲属的一封信中,他曾这样写道:“我建议你们阅读这些伟大的历史剧本,要知道,在塞内加尔的圣路易,我连续三个月都在阅读这些作品。通常来讲,有两种阅读的方式,我也不清楚哪种方式更胜一筹。就我个人而言,我习惯依照顺序阅读,即根据年代的发展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我遇到一个接一个的惊喜,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奇遇。然而,那些聪明的英国人建议我在重读之时换一种方式阅读,依照他们创作的顺序阅读。这样,我就能更好地体会风格的转变和莎翁思想的演变。”(3)Jean Lambert, Gide familier(Paris: Edition Julliard, 1958), 84.历史上的戏剧经典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纪德的戏剧创作,当然,纪德自身的戏剧创作又蕴含着其独特的个人风格,由此建构的戏剧世界同时成为现代戏剧史中不应被遗忘的一页。
二、纪德的戏剧创作:人物、自我及其内在精神世界
毋庸置疑,纪德最具代表意义的三部戏剧作品分别为《扫罗》《康多尔王》和《俄狄浦斯》。不难发现,三部作品均以剧中主要人物或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它从一个方面表明,纪德试图营造一种特殊的戏剧空间,这种空间乃是以某个剧中人物为中心。确实,在纪德的戏剧作品中,与剧名相涉的剧中主要人物往往居于中心,其他人物则围绕该中心人物而活动,读者只能通过作为中心人物的主人公的所言所行来了解那些具有附属意义的人物。这种戏剧空间是纪德戏剧作品所特有的:传统戏剧空间常由两人或多人建立,其剧情也随着不同人物的活动而跌宕起伏,反观纪德的戏剧,则始终是主人公置身于行为的中心,整部戏剧的结构与具体展开也主要基于主人公个人的活动。由此,戏剧似乎不再是“一群人互相撞击产生力量的一种集体行为了”(4)Etienne Souriau, Les deux cent mille situations dramatiques(Paris: Edition Flammarion, 1950), 56.。在纪德笔下,中心人物成为一个参考的指标,他以这一中心人物为基础,展现丰富的戏剧内涵。戏剧中的人物以自我的个性特点为内在灵魂,从存在形态看,戏剧中的中心人物表现为具体的个体,这种个体既象征着独特的自我,又有多样的个性特点。从这一意义上说,以某一剧中人物为中心的戏剧模式,同时构成了展现自我形象的独特方式。稍加分析便可看到,纪德笔下三个具有代表意义的戏剧人物,即扫罗、康多尔王和俄狄浦斯,都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后者同时展现为自我的内在精神世界,这种内心世界丰富而复杂,并不断通过在各种相反力量之间的抗争而从不同方面彰显自我的个性品格。以上特点体现了纪德本人对戏剧创新的期许:“说到戏剧,就绕不开个性特征。”(5)Gide, Nouveaux prétextes(Paris: Edition Mercure de France, 1911), 151.可以看出,纪德将戏剧作为一种展现个性、表达自我的方式与舞台。
以《俄狄浦斯》为例,纪德创作该剧的灵感来源于古希腊的同名经典悲剧。然而,作者并未简单地模仿名著,而是在剧本中融入自己的疑虑与希望,以全新的形式重写这部经典悲剧。纪德所创作的《俄狄浦斯》,其主要脉络十分清晰:展现个人主义的特点与重要性。在这部三幕剧本中,主人公俄狄浦斯完全无视神谕与神的旨意,努力从家庭和社会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他对自己的过往既一无所知,也不想了解。总的来说,这是一个“迷失方向,没有任何证件和社会身份”(6)Gide, Thétre(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42), 253.的孩子。然而这种无知、混沌的状态却成为俄狄浦斯的力量来源,因为这种状态带给俄狄浦斯无尽的自由:既没有过往的拖累,也没有来自家庭和宗教的负担。
如果说,生存状况受制于自我无法决定的存在背景,那么,对幸福的理解则展现了作为特定个体的俄狄浦斯的自我张力。一开始,他对幸福的理解带有明显的自恋情结。他迷恋自己的灵魂,认为只有完美的自己才能获得幸福。然而很快,俄狄浦斯发现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全都建立在谎言和无知之上。自此,其自我开始被唤醒,作为逐渐觉醒的自我,他渴望了解自己的身世。随着自我的这种觉醒,俄狄浦斯看待世界的角度也发生了改变。从前,过度自信让其盲目。现在,他意识到曾经他以为获得的幸福并不牢固,正在逐渐消逝。事实上,俄狄浦斯此刻正在进行一场自我抗争,试图重新选择人生的方向。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场抗争也是突破自我、认识自我的一种尝试。这里,自我的主题被再次触及并深化。纪德借助俄狄浦斯的转变,表达了对自我比较系统的理解。在纪德看来,自我是一种真正的信念。实现自我意味着唤醒沉睡在规则底下的所有潜能,勇敢面对未来。这是人类唯一的价值和需要达成的目标。正如在面对斯芬克斯的谜语时,自我也是唯一的通行码:“每个斯芬克斯抛出的谜语,答案都很相像;是的,面对这些繁杂的问题,答案却是唯一的;这个独一无二的答案便是:人。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人意味着独一无二的自我。”(7)Gide, Thétre, 283-284.
人类最终战胜了斯芬克斯,这意味着人类可以克服恐惧,实现自我。俄狄浦斯也似乎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幸福。但这并不是故事的最终结局。相反,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当俄狄浦斯踏上前往底比斯开启一段未知之路时,他同时也展开了自我的新的行程。不难发现,这次旅程与科林斯逃亡不尽相同。俄狄浦斯开始试着做出自我牺牲,这一举动意味着他进入了人生的不同阶段:由仅仅面向个体走向同时肩负并承诺对社会的责任。
在阅读剧本的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俄狄浦斯自我形象的如上变迁。开始,他骄傲自大,不可一世,认为幸福建立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之上。慢慢地,他变得愈加清醒、理智,并意识到:“伟大的人生正躲在黑夜的阴影里,等待着我……平静的阶段已经过去。快从幸福中苏醒过来。”(8)Gide, Thétre, 289.自此,他拒绝接受由错误和无知所构成的幸福。最后,这份清醒的个人意识让他超越自我,并认识到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剧终,俄狄浦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敢于承担社会责任与意义的自我形象。
在菲罗克忒忒斯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俄狄浦斯式的狂妄与自大。《菲罗克忒忒斯》是纪德早期的戏剧作品,完成于1893年。菲罗克忒忒斯本是一个城邦的国王。在前往特洛伊的征途中,他被保护克律塞圣坛的毒蛇咬伤了腿,由于其伤势影响了军队的行进进度,士兵把他扔在了四面环海的利姆诺斯的海岸。数十年间,菲罗克忒忒斯在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坚强存活。能够在孤岛上生活的人,必须拥有很强的自主性、独立性,这些都可以视为自我个性的内在体现。在菲罗克忒忒斯看来,自我意愿是唯一也是最高的权威,自我之外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他从自己身上找寻所有规律和法则,甚至认为自我是凌驾于神灵之上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菲罗克忒忒斯逐渐走向封闭的自我,拒绝向外界敞开自身。在他看来,真正的自我总是超越于国家、民族,唯有如此,才能回归人的真实存在:“在这座岛屿上,我一天比一天更不像一个希腊人,而一天比一天更像一个真正的人。”(9)Gide, Le Retour de l’Enfant Prodigue Précédé de Cinq Autres Traités(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12), 119.在孤岛这一独特生存环境中,菲罗克忒忒斯与世隔绝,唯有自我,没有其他,由此,他既感受了自我的孤独、自我的力量,也完成了某种自我的超越。通过构想以上这种极端的存在境域,纪德凸显了个体如何从尘世间的一切中抽身而去,经过脱胎换骨的过程,成就全新的自我。
纪德戏剧世界中另外两个主要人物扫罗和康多尔王同样有着丰富的自我形象。首先可以考察扫罗。《扫罗》发表于1896年,是纪德第一步戏剧作品。剧本的标题让读者很快找到作品的出处:扫罗来自《圣经》,是以色列第一位王。然而,上帝却更偏爱年轻英俊的牧羊人大卫,并最后将扫罗废黜。令人惊讶的是,扫罗非但没有把大卫杀死,还深深地爱上了他。毋庸置疑,扫罗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在他与大卫的关系中,蕴含着肉身(大卫的肉身魅力)与权力(扫罗自身权力的失落)之间、地位和情感之间的内在冲突,扫罗的灵魂因此而充满张力并备受折磨。在儿子面前,扫罗袒露了自己的心声:“我的价值存在于我错综复杂的个性中。”(10)Gide, Thétre, 143.这里同时可以看到对自我内在精神世界的某种自觉意识。
然而,扫罗也有致命的弱点,这主要在于他欲望甚盛,并沉溺其中。在整部作品中,纪德笔下的扫罗都在追求肉体的欢愉。一开始,他便深陷在魔鬼、罪孽和激情之中。这些危险的欲望最终将他奴役,让他始终难以摆脱罪恶的诱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大卫的迷恋。当扫罗第一次遇见大卫时,便沉迷于后者的美貌,并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从此以后,为了取悦大卫,扫罗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个性。面对此种情景,有人提醒扫罗亲近他的人(暗指大卫)可能正试图加害于他,可扫罗却对这些警告充耳不闻。在他眼中,大卫是他满足爱情欲望的最佳人选,但事实上,他却是日后剥夺扫罗王位的人。这位“爱人”从内在的方面慢慢腐蚀扫罗,摧毁他的灵魂,使其失去自我。
此外,扫罗的自我形象也展现出矛盾的一面。从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残暴的君主。他下令杀死所有的巫师,只留下女巫恩朵,为的是成为世上唯一一个能够预知未来的人。他暗想:“当我成为世上唯一一个能够预知未来的人时,就可以试图改变它。”(11)Gide, Thétre, 16.然而,在危机来临之时,他却变得软弱无能,逃避责任。在危难时刻,他关心的是个人安危,而非整个国家的命运,甚至经常委托他人为其决策。纪德在这部戏剧作品中清晰地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疯狂、复杂、矛盾,被自己的欲望和感情所禁锢的人物形象。他的感情过于炽烈,以至于失去了控制。他最后的沉沦也说明个人主义和自由精神有其特有的限度。总的来说,扫罗展现了一个病态而蕴含多样个性、邪恶而脆弱、充满野心而又软弱自私的自我形象。
提到《扫罗》,不由地让人联想到纪德另一部戏剧作品《拔示巴》。两部作品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从故事发展来看,《拔示巴》是《扫罗》的延续,讲述的是大卫从扫罗手中夺取政权后执政的情况。另外,两位君主的命运也几乎相同:他们都是欲望的奴隶。扫罗迷恋大卫,大卫则为拔示巴所倾倒。这是一种来势汹汹的欲望,人们无法预知它的降临,也无法控制它的发展。当他第一次看到拔示巴时,就进入一种心醉神迷的状态:“我的心脏一下跳到了喉咙,并会随时顺着一声惊叫迸出……”(12)Gide, Thétre, 169.然而,拔示巴已经成婚,她的丈夫乌利亚骁勇善战,是大卫的功臣。此时,个人之爱与制度化的爱产生冲突。按照常理,作为一国之主,大卫应当为所有臣民服务,将个人幸福置于民众幸福之后。然而,在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人的冲突中,大卫的选择是借故杀死乌利亚,从而最终牺牲他人和群体,由此成全个体与自我。在这里,读者看到了一个自私、无情,被本能和欲望所牢牢控制的自我形象。
至于《康多尔王》,这是一部出版于1889年到1901年之间的三幕作品。在纪德看来,这部戏剧作品有两个主题:幸福和慷慨。康多尔王的“慷慨”甚至体现于对待自己所钟爱的女人之上:他让自己的心上人尼丝娅公开展示其美貌,表示自己不想独自一人霸占这件珍贵的宝物,甚而把她献给吉杰斯,让他们共享春宵一刻。对纪德而言,以上所作所为显然违背了人之常情和基本的社会规范。在这部作品中,纪德同时试图展现幸福与慷慨之间的畸形联系:康多尔王的幸福往往来源于对他人的施舍。换句话说,康多尔王从慷慨中找到自己的幸福。然而,这种极端的慷慨却将康多尔王引向灭亡。在尼丝娅的命令下,他死于吉杰斯的手中。这里,读者看到一个悲剧性的自我形象:康多尔王的幸福葬送在自己悖乎常理的慷慨之上。
除了经典戏剧作品,纪德还以一种新颖的戏剧形式创作作品。《梵蒂冈地窖》便是其中的代表作。纪德将《梵蒂冈地窖》归为“傻剧”。在中世纪,傻剧作为市俗戏剧,是闹剧的一个变种。它继承了宗教剧的部分基因,又将讽刺剧的特质和闹剧的形式发扬光大。作为喜剧的后代,傻剧通过夸张的手法和诙谐的台词,引发人们对丑陋、滑稽人物的嘲笑。事实上,《梵蒂冈地窖》是一种文体的混合。纪德将傻剧中的某种艺术形式移植到小说创作中。具体来说,《梵蒂冈地窖》既包含了小说的叙事手法,又带有傻剧的戏剧艺术特点和表现形式,书中的狂欢化特征和讽刺性艺术手法都说明了这一点。《梵蒂冈地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则社会新闻,故事颇具荒诞性,讲的是部分主教和共济会相互勾结,将教皇囚禁起来,于是众人便打着解救教皇的名义,展开一系列欺骗行为。主人公拉夫卡迪奥在所谓“无动机”的驱使下将阿梅代推下火车。这一“无动机”行为代表着某种近于自然的“自由”:“无动机”意味着自然而然,既超越于任何价值的意图和责任,也不受任何社会规范的束缚。拉夫卡迪奥通过自己无法解释、毫无缘由的荒诞行为,不仅展现了“自由”与“自然”的关联,而且使自我超越于社会的控制,成为独特的“自由”个体。
以上几部作品虽然分别围绕一个主要人物展开,但剧中的一些附属角色同样也在纪德的戏剧空间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的出场增加了戏剧冲突性,并烘托着主要人物。具体来说,这些配角常与主角持不同的观点,并时时通过不同意见和观点的论争,推动故事发展。虽然他们在剧中似乎没有占主导地位,但其行为却与主人公的发展息息相关。
《扫罗》中的大卫和《康多尔王》中的吉杰斯是两个最重要的附属人物。在《扫罗》这一剧本中,大卫是一个在外形上被刻意美化的人物,他常给人带来感官上的享受。同时,他似乎散发着光芒,拥有青春(他只有17岁)、美貌、力量和勇气。相形之下,扫罗却代表着黑暗和邪恶的势力。同样,吉杰斯的人物形象也与康多尔王大相径庭。康多尔王是一个文化人:“康多尔极富文化修养,包括感官文化、精神文化和道德文化。”(13)Henri Ghéon, Nos Directions(Paris: Editions de la N.R.F., 1911), 74.而吉杰斯却是一个根据自己本能行事的人。具体来说,他的行为带有粗野、冲动的特质,他以极端手段处死不忠的妻子,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一点。然而,吉杰斯又非常贫穷,他生活简朴,且知足常乐。作为剧中的配角,大卫和吉杰斯既展现了自身多样的个性,也从不同方面衬托了剧中主要人物(扫罗和康多尔王)的个性特征。
《扫罗》和《康多尔王》中人物形象的反差,同时营造了一种真正的戏剧冲突。在与配角的互动时,主人公充分展现自我的多样人格,配角的言与行,同时也从不同方面彰显了主人公特有的自我形象。在以上剧本中,通过大卫和吉杰斯的映衬,扫罗阴郁的自我心理和康多尔王慷慨的个性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作为附属性的人物,配角不仅烘托了主要人物的个性特点,而且常常促使主人公更清晰地认识自我的这种个性品格。以大卫而言,他的出现固然扰乱了扫罗的心绪,但也让他窥测到自己隐藏的一面,即对感官的欲望。换句话说,是大卫为扫罗揭示了他的某种情感取向。至于吉杰斯,他引导康多尔王对自己的财富和幸福产生怀疑。在听取他的建议后,康多尔王开始将自己的财富奉送给穷人,直至破产。可以看到,这两个附属性人物触发了主人公的自我认识:大卫的出现凸显了扫罗内在失衡的一面,而吉杰斯的出场则敞开了康多尔王脆弱的内在精神世界。两个配角唤醒了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让他们发现别样的自我。显然,这是一种描写主人公自我形象的巧妙方式:通过周边的人物对当事人进行间接描绘。
正如让·克洛德所论,纪德的戏剧世界就像一首协奏曲:“这几乎就像一首协奏曲:乐队围绕一个主题奏出美妙的音乐……是的,围绕一个主题,在这里转换为围绕一个中心人物,围绕他所有的经历。在这支乐曲中,一个声音占据主导,凌驾于其他器乐之上,为整部作品服务。其他声音隶属于主音,对其支持、评议、反对,不断调整整首乐曲的协调性。”(14)Jean Claude, André Gide et le Thétre Tome II(Paris: Edition Gallimard, 1992), 91.要而言之,纪德十分擅长刻画剧中的不同人物。在他的笔下,不论主角或配角都呈现鲜明的自我形象和个人风格。
三、纪德小说中的“戏剧性”元素及其个体性内蕴
除了戏剧作品,纪德也常在他的小说作品中营造出独立的戏剧空间。更具体地看,“喜剧”一词常出现在纪德的小说中,用以描绘一些故事场景。比如在《窄门》中,杰罗姆的母亲将露西尔·伯格兰的经历比喻成一出喜剧:“我的朋友,我真想告诉你,这所有的一切都像是一出喜剧。”(15)Gide, La Porte Etroite(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71), 15.这一现象从一个方面表明,即使在小说的创作中,纪德也从未放弃对戏剧的追求。事实上,纪德笔下的虚构人物都有着戏剧般的生活。当然,纪德小说中的戏剧空间并非停留在简单的词语运用上。在其小说中,常常可以发现他所融入的“戏剧性”元素,较之“傻剧”的引入,这些元素如同一座天桥,将小说和戏剧更为内在地连结在一起。
毋庸置疑,对话是最典型的具有戏剧意义的元素,因为对话是戏剧的表现方式之一。阿兰·维尔拉曾经写道:“戏剧首先是对话的艺术。”(16)Alain Viala, Le Thétre en Franc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7), 35.在文学作品中,两人间的对话常可以决定故事的走向,揭示人物的真实形象,读者也可以从人物对话中获得大量信息,从而不仅知晓故事的背景与主人公的身份,而且具体把握其自我个性。在纪德的小说《田园交响曲》中,牧师和老妇人的对话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唔!我看她没睡。她是个白痴,总不讲话,别人说什么她也听不懂。从我上午进屋到现在,她差不多就没动窝。起初我还以为她耳朵聋,佣人说不对,老太太是聋子,从不跟她讲话,也不跟任何人讲话,一直就这样,只在吃喝时才张开嘴。
这姑娘多大了?
我想总有十五了吧!别的情况,我知道的不见得比您多……(17)Gide, La symphonie pastorale(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coll.Folio, 1993), 48.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到,主人公吉特吕德第一次通过戏剧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眼前。作者通过对话为读者提供了主人公的基本信息。这些信息是勾勒人物形象的基础,并展现其内在的个性特点:通过上述对话,人们可以对书中这位“瞎眼姑娘”内向、沉默的个性也有所窥见。此外,对话也有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当人物行踪神秘,或情节停滞时,对话可以化解其中的问题。另外,对话让读者和人物一起置身于小说空间中,读者可以根据对话内容,跳开作者,直接形成甚至勾勒出主人公的自我形象。最后,对人物自己而言,对话也是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对话意味着与他人产生多样关联,有时,我们需要通过他人来了解自己,而对话便提供了这样一种场景。读者通过这些坦诚的对话,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一旦进入这些私密空间,人物真实的自我形象便开始比较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除了对话,手势作为人物间的交流方式也是一种典型的戏剧性元素。毫无疑问,富有表现力的手势可以呈现出丰富的戏剧效果,就小说创作而言,它可以让静止的小说空间产生流动的视觉体验。通过手势,小说中的人物以一种更为生动的方式表达自我。他们用手势代替语言,相互沟通,传达内心想法,展现自我形象。在纪德的《伊莎贝尔》中,书中的人物伊莎贝尔和母亲不仅通过语言,还通过手势和各种动作进行对抗:
她再次向前,步履平稳,面色凝重。虽然离她很远,但还是能看到她手上戴满了巨大的戒指。走到屋子中央时,她停住脚步,朝向自己的女儿,身体紧绷,用可以穿透墙面的声音尖厉地说道:
在你身后,你这个不孝女!我不会再被你的眼泪所动,你的反抗已经永远失去了我的心。
母亲一字一句地说道,声音刺耳,却没有太大的起伏变化。伊莎贝尔跪倒在母亲脚边,抓住她的裙摆,不断拉扯……(18)Gide, Isabelle(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62), 145.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读者完全可以通过人物手势来理解其态度和个性:母亲的几个手势或肢体形态,便表达了她对女儿的敌对态度。具体来说,通过一系列动作和手势,读者清晰地看到母亲拒绝原谅女儿的决心和她的个性特征:这是一个专断强势、性格刚烈的母亲。相反,伊莎贝尔下跪、拉扯裙摆等动作则展现出一个软弱、怯懦的人物形象。同样,在《伊莎贝尔》中,通过作者对桑塔尔神父表情、手势的描写,读者一下子就能看出他的虚伪本性:“他们的孙子是我的学生。三年以来,上帝允许我教导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神父紧闭双眼,表情谦和。”(19)Gide, Isabelle, 27.纪德特意突出神父的面部表情,来描绘他的自我形象。显然,桑塔尔神父试图将他的真正意图隐藏在表情、手势之后,却未能如愿。事实上,杰拉德和桑塔尔神父在无声的空间里互相观察。虽然两个人物之间并无实际的言语交流,可他们却用肢体语言(手势或表情)来表达自我,展现个性。毫无疑问,肢体语言作为广义语言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言语、文字具有相同的功能:作为世界体系中的一个符号,肢体语言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同时展现出语言发出者特有的自我形象。
戏剧元素的另一表现形态,是舞台上的灯光。在纪德那里,小说场景常被想象成一个戏剧空间,纪德本人时常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穿插“灯光游戏”。经过仔细阅读,读者不难发现,纪德的小说空间中同时存在着“阴影”和“亮光”。他的作品在现实与虚幻中游走。读者推断:“阴影”是为了保护,隐匿小说人物,躲避他人的目光,“光亮”则是为了突出人物特质。如果说,在《科里东》里,同性恋话题曝露在光亮之下,那么,在《背德者》中,堕落的主题就隐藏在阴影里。纪德的这种小说创作方式,同时也折射了现实的存在形态:纪德的伴侣玛德琳娜是他创作的原动力之一,可在现实生活中,她却一直生活在黑暗或“阴影”中。
具体地说,在纪德眼中,“阴影”是秘密和隐瞒的最佳场所。以《背德者》而言,其中的主人公就喜欢躲在黑暗中讲述自己精彩的过往:米歇尔总是等到夜幕降临之时与朋友分享自己的冒险。毋庸置疑,夜晚代表黑暗或阴影。此外,米歇尔在描绘自己妻子玛丝琳娜时,也经常穿插“灯光游戏”:“随后,在黑暗中,露出一张我认不出的脸庞。我开始感到担忧,一声不响地走向床边。玛丝琳娜紧闭双眼;她是如此苍白,以至于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她死了。她朝我转头,却并未张开眼睛。在房间的阴影处,那张陌生的脸好像一直在活动,一直在整理或藏放不同的物品……”(20)Gide, L’Immoraliste(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coll.Folio, 2017), 126.可以看到,“阴影”与“秘密”和隐瞒存在紧密的关联。然而,阴影有时也是通往光明的必经之路。在《背德者》中,纪德通过塑造米歇尔这一人物进一步表达了这一点。虽然米歇尔习惯于在夜晚讲述自己的经历,可在故事的最后,当阳光升起时,米歇尔却在朝阳中获得新生。这里,黑暗不再是沉重、压抑的象征,而成为通向光明前所需要经历的过程。在纪德的笔下,每一片阴影中都存有一点光亮,每一片光明里,又藏有一点黑暗。
以上现象表明,自我形象涉及不同的方面,它既关乎个体内在的精神之域,也与个体在公共领域中和他人之间的交往、互动相涉,正是在以上多重关系中,自我的形象逐渐变得丰满、充实。纪德在小说作品中融入大量的戏剧性元素,从一个侧面更具体地走入人物内心,描绘出他们真实、多方面的自我形象。通过对话、手势和灯光效果,小说人物仿佛置身于戏剧舞台之上,不再被动地接受作者赋予他们的个性特质,而是更加自由地表达内心,展现自我,从而呈现出一个真实、生动的自我形象。纪德戏剧世界的意义,由此也得到了更深沉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