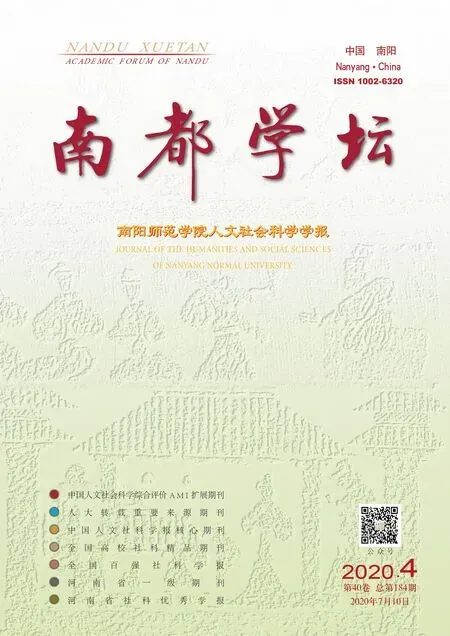汉代凉州刺史考
2020-12-02刘维栋
刘 维 栋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刺史制度是中国古代监察体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汉代刺史制度的研究,已有前辈学者从宏观制度层面进行了诸多考察(1)严耕望先生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汉代刺史制度的形成、发展以及刺史职权的一些变化(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版,第272页;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318页);劳干先生认为汉代刺史是基于汉代丞相椽史而来,并且认为设立刺史最初的目的是选拔人才,以应对汉武帝时期老臣凋零的局面(劳干:《两汉刺史制度考》,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48页);廖伯源则是从皇帝派遣使者的角度探讨了西汉刺史制度的来源(廖伯源:《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页);顾颉刚先生和谭其骧先生讨论了两汉州制及凉州刺史部所属等相关问题(顾颉刚:《两汉州制考》,选自《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第856-861页;谭其骧:《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38页);辛德勇在顾颉刚、谭其骧研究的基础上论述汉代州制时着重论述了刺史制度设立与州制变革间的关系(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4-144页);汪清则对十三刺史部、州的概念及其两者的关系进行了辨别(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载《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第24页);史云贵从整体上对刺史职能的变化,固定的机构及治所,选人、用人等方面的权力拓展做了论述(史云贵:《汉代刺史制度述论》,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115页)。。但此前研究大多从国家整体角度出发探讨刺史制度演变,对具体到地方的刺史研究尤其是处在西北边疆的凉州刺史鲜有论及。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考察凉州刺史职能变化与属国都尉之关系,希冀加深对汉代边疆治理和刺史制度的认识。
一、凉州刺史部的范围
《汉书·地理志》言:“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1]1644-1645至于为何名之曰凉州, 按 《晋书·地理志》所说“凉州,盖以地处西方,常寒凉也”[2]432。关于凉州刺史部(2)张俊民认为:刺史之部,有别于“乡部”“亭部”中“部”之含义,作为一种行政组织的刺史部位于郡国之上,一“部”可督察数郡或国,使中央更为有效地管控地方,亦加强了地方与中央的联系。见张俊民:《“部”与“候长”论略》,载《西北史地》,1988年第4期,第47-53页。所辖的区域,顾颉刚认为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设立刺史部是综合《尚书·禹贡》中的九州和《周礼·职方》中的幽州、并州,加上朔方、交阯,形成了“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幽州、并州、朔方、交阯” 十三刺史部。武帝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1]1543,雍州实际上就是凉州。辛德勇认为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刺史部的辖区是在武帝元封三年(前108)设立十二州的基础上形成的,十三部刺史辖区与原先十二州区域之间既有套叠也有区别,凉州刺史部与先前凉州的区域是吻合的(3)观点出自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3-178页。;周振鹤在顾颉刚、谭其骧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汉武帝时凉州所属郡 “陇西郡、天水郡、安定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为”6个郡(4)吕祖谦认为凉州刺史部在汉武帝的辖区有“陇西、金城……安定、北地等九郡”,见吕祖谦:《吕祖谦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但经辛德勇考证吕先生之说对应的是东汉之事。;汪受宽认为武都郡在汉武帝设置刺史部时就是归属于凉州刺史部[3]。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七月“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1]224,在政区上增加了金城郡,但实际的范围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综合以上所述,在西汉末以前,凉州刺史部的辖区至少确定有“陇西郡、天水郡、安定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金城郡、武都郡”等8个郡。除设置这些郡外,汉武帝时期还在凉州区域设置了属国,元狩三年(前120),匈奴投降后“乃分处降者于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1]2483,关于属国的位置区域存在许多争论(5)陈梦家认为符合史书记载的“五属国”只有天水、安定、上郡、五原四个地区,见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王宗维认为汉武帝并没有同时设置“五属国”,而是先把匈奴降众安排在“陇西、北地、上郡、西河、朔方(包含五原)五个边郡”,参见王宗维:《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论集》,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熊谷滋三对王宗维否定“五属国”的观点不赞同,认为汉武帝时期先在“陇西、北地、上郡、西河、五原”等地设置属国,其后因为政区重新划分,在元鼎三年(前114)后属于“天水、安定、上郡、西河、五原”,见熊谷滋三:《前漢における属国制の形成——— “五属国”の問題を中心として》,载《史観》,1996年,第134册,第31页。,但是不管争论如何,在西汉凉州刺史的辖区设置属国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凉州刺史的辖区应是在以上八郡的基础上加上“安定属国”“张掖属国”(6)经考证张掖属国的设置时间是在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详见高荣:《汉代张掖属国新考》,载《敦煌研究》,2014年第4期,第97页。“天水属国”“金城属国”等。
西汉末、新莽时期对汉代的州制进行过改革[1]357-358,将凉州改为雍州,阎步克认为王莽时期的政区设置有巨大的改变[4],随着职能的转变,此时的凉州改为雍州,不仅是政区名称的转换,也是政区划分范围的变化。原来的三辅地区(京兆、冯翔、扶风)划入雍州,就意味着凉州刺史的辖区是在原来八郡、四属国的基础上加上三辅地区。
光武帝刘秀在更始元年(23)曾对王莽的执政措施做过一次清理[5]10,时值刘秀出抚河北,并没有涉及中央层面的州制改革,《后汉书·郭伋传》中记载“世祖即位,拜雍州牧”[5]1901,说明在光武帝初年,雍州还没有被改回凉州。在建武十二年(36)“省金城郡属陇西”[5]60,政区名称和数目上就恢复到西汉武帝时期的形态,但在次年又恢复金城郡。光武帝建武十八年(36)“罢州牧,置刺史”[5]70,根据《续汉书·百官志》中所记“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属司隶校尉,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后又记“豫州部郡国六……凉州部十二”[5]3617-3618。那么此时应该是在中央层面对王莽时期的执政措施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辖区可能恢复到汉武帝时期的监察区域。凉州部郡国十二,根据《续汉书·郡国志》中的记载,应为陇西、汉阳、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等十二部,根据顾颉刚先生考证,司马彪撰此志时值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7)参见顾颉刚先生在《两汉州制考》中对两汉州制相关问题的论述,选自《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第884页。。那么,汉代凉州的区域范围基本固定下来。
二、凉州刺史部的特殊性
就凉州刺史部的特殊性而言,此时汉朝政府划分并设立凉州刺史部有其特殊战略意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加强对新开拓疆土的控制。“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凡十三部,置刺史。”[1]1543凉州刺史部的监督范围主要是汉武帝反击匈奴时期设立的“河西四郡”(8)关于河西四郡设置的年代,学术界多有争论。可参见张维华:《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收入《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309-328页;王宗维:《汉代河西四郡始设年代问题》,载《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158页;日比野丈夫:《河西四郡の成立につぃて》,收入《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日本同朋舍出版社,1977年版,第69-82页。。据《汉书·地理志》载:“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1]1644-1645由此可见设立“河西四郡”的目的有二:一是联通西域;二是隔绝羌与匈奴的联系,防止二者联合起来侵扰汉朝边境。四郡之所在,亦即匈奴、西域、羌等族群活动交汇的河西走廊地区,战略位置十分显要。虽然此前,汉朝在战略层面已经击败了匈奴,但是在陇右和河西走廊地区,匈奴、羌人依旧有很强的力量,情形十分复杂。羌人在汉景帝时被安置在狄道、安故,至临洮(今甘肃岷县)、氐道、羌道县,且在汉元鼎五年(前112),“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5]2876,匈奴也派大军“入五原,杀太守”[1]188,与之配合,一时声势颇大。在这种边疆危急的形势下,在新开辟的疆土上设置郡县,进而设置刺史部以实施监察,这就从制度方面保证了汉中央对新开辟疆土的控制。
其次是推行汉武帝时期“广关拓边”政策。在西面设置政区以屏卫关中或者作为拓边的基础,符合汉武帝时期的大政之策。在原有的基础上设立凉州、益州刺史部正是这种政策下的产物。凉州刺史部的设置,使汉朝势力在河西走廊不断延伸;西汉神爵二年(前60)始置“西域都护”[1]3006;扬雄在其撰写的《十二州箴》中《雍州牧箴》写道“并连属国,一护彼都”[6],也说明了凉州(雍州)在关中与西域都护间起到了重要的连接作用。
最后是纾解社会矛盾。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出巡郡国,“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往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7]1438。官员的自杀,既是汉武帝时期吏治严酷的反映,也是当时官员面对辖区政务而焦头烂额的真实写照。同时汉武帝也认识到“惟吏多私,征求无已,去者便,居者扰,故为流民法,以禁重赋”[1]2198。元狩(前122—前117)、元鼎(前116—前111)年间正是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兵役、赋税都要为战争服务。针对这一地区羌人的反叛势力,元鼎六年(前111)汉武帝“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人”[1]188平定羌人叛乱,我们不确定陇西、天水、安定等郡征发的士兵有多少(9)根据学者研究西汉边郡的常备兵为每郡万人。见黄今言、陈晓鸣:《汉朝边防军的规模及其养兵费用之探讨》,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且河西、陇右地区还要为征伐的军队提供相应的后勤补给服务,因此可能造成了该地区社会矛盾的突出。元封四年(前107),也就是汉朝设立刺史部的前一年,关东地区出现了大量流民,“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适之”[7]2768,没有资料显示关东的流民影响到了陇右河西地区,但流民现象说明当时的国家出现了巨大的危机。北击匈奴的军事和后勤任务刚刚结束,全国性的流民问题陡然而起,对当时的西汉政府和陇右、河西地区来说都是一种考验,再加上反击匈奴的大战略胜利后,原本被忽视的社会矛盾逐渐释放。为了缓和河西、陇右地区的社会矛盾,在该地区设立限制地方官员权力、打击豪强的监督机构——凉州刺史部是十分必要的。
三、简牍所见“凉州刺史”
刺史制度设立之初,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刺史职能系“掌奉诏条察州”[1]741,“诏条”即指“六条问事”(10)“六条问事”内容见《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途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也。”见孙星衍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08-209页。。“六条问事”核心就是针对郡级官员的限制以及对于地方豪强与官员勾连的打击。在“六条问事”之外,“非条所问,即不省”。严耕望在其著作中援引颜师古注,认为“黜陟能否,断治冤狱”是刺史奉诏察州的两个重点[8]。除诏条所规定之外(11)有学者对刺史监察之外的职能做了系统的梳理,见周长山:《是惟主监察,还是兼及行政——对西汉刺史制度的新认识》,载《史学集刊》,2005年第4期。,凉州刺史还有其他一些职能。
在河西地区出土的汉简中,发现了关于凉州刺史的相关史料:
金城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东南。天水平襄二千八百卅,东南。东南去刺史□三□……一八十里……长安四千八十……(B)(V 1611:39)[9]59
坐从良家子自给车马为私事论疑也□檄书到相,二千石以下戍吏,毋过品刺史禁督,且察毋状各如律令。(40·6)[10]28
刺史治所且断冬狱。(482·19)[10]247
诏书必明白大书,以两行着故恩泽诏书。无嘉德,书佐方宜以二尺两行与嘉德长短等者以便宜从事,毋令刺史到,不谨办致案,毋忽(12)据“嘉德”大致判断为王莽时期。。(II 90DXT0114:404)[9]2
出土简牍印证了凉州刺史的职能,并与传世文献相对应。在《元康四年鸡出入簿》中,有“以食刺史,从事吏一人”,按《后汉书·百官志》中言刺史“皆有从事史、假佐”[5]3619,此处的“从事吏”应为“从事史”,为刺史的佐吏;敦煌悬泉汉简中“东南去刺史”则证明刺史有固定治所,《汉书·朱博传》言刺史“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1]3399,与简牍中体现的“治所”相符合;“六条问事”中刺史有针对“二千石不恤疑狱”之杀目,简牍有刺史“断冬狱”之载,与《后汉书·百官志》“录囚徒”之事相对应,说明刺史在县令、太守之后,在司法上有相关的审理权限。设置刺史监督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刺史对“二千石”官员是否能奉“诏”守“法”行事之察是刺史的主要任务,“二千石”成为刺史监察官员的界限与核心,简牍中也明示“毋过品刺史禁督”。
关于凉州刺史如何巡部奏事,简牍中也有记载:
九月刺史奏事簿录。(EPT51:418B)[11]
延熹二年四月庚午朔十二日辛巳凉州刺史陟使下,郡国大守、都尉,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各实核谁为州集 七□□尹□书到言。(散49正面)[12]
下中二千石部刺史、郡大守、诸侯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督□。(2376)[13]258
“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初岁尽诣京都奏事”[5]3615,但简文中凉州刺史是在九月“奏事”,因此凉州刺史在巡部奏事的时间上有待进一步深究。面对较为广阔的监察区域,刺史是如何有效监察地方官的呢?《汉书·朱博传》中则有“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1]3399,恽寿任冀州刺史时也“使部从事专住王国”[5]1033。在相对广阔的地域,凉州刺史为了更有效地监察,派遣“从事”代其行部进行考核是行使监察权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六条问事”的大部分内容在出土的简牍中得到验证,而且由于简牍时间跨度较长,那么可以认为凉州刺史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除治所外,始终保有了监察“二千石”和断狱的职能。
凉州刺史职能的变化反映出刺史制度在西汉晚期的重大变革。由简牍中“二千石部刺史”可知,刺史的禄秩变为“二千石”,则是继汉成帝改变刺史禄秩后仍然不断变化的反映。“成帝绥和元年,以为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乃更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复为牧。后汉光武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灵帝中平五年,改刺史,唯置牧。”[14]“刺指刺吏,属于监察;牧指牧民,属于行政。”[15]何武、方进曾向汉哀帝进言:“令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统,选第大吏,所荐位高至九卿,所恶立退,任重职大。”[1]3406朱博也向哀帝上奏“前丞相方进奏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弟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禁。臣请罢州牧,置刺史如故”[1]3406。由此可见,在成帝改革前,刺史通过监察地方官并进行干预,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行政权力,凉州刺史通过派遣“从事”代其行部,则已是将郡国守相视为其所属。而原有之郡、县二级的地方行政体制势必出现相应的变化,这也正是凉州刺史所能反映的汉代刺史制度变革的体现。通过简牍文书中信息传递顺序,也能印证这一观点:
□□阳朔五年正月尽十二月府移丞相、御史、刺史条。(EPT56:77A)[16]
建平三年五月庚戌朔己未,治书侍御史听天、侍御史望,使移部刺史、郡大守、诸侯相……(EPT43:31)[17]
此处简牍文书传递顺序为丞相—御史—刺史、部刺史—郡大守—诸侯相,凉州刺史在行政层级中处于中央行政与原地方行政之间,再根据时间推断,在汉成帝绥和改制之前的一段时间,凉州刺史所辖的区域已初步形成了刺史—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制。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凉州刺史所属部分区域的偏僻与信息不畅。“阳朔”为汉成帝年号,但只存在四年,并无五年之号,且在同批简牍中发现“五凤五年”之类似逾期年号(13)据此推测“阳朔五年”应为汉成帝鸿嘉元年。[13]26,这种与行政核心区更换年号的差异,既表明了居延等边区官员对中央政权的认同与服从,同时也暴露出该地区因距离行政中心路途遥远而导致信息闭塞。
凉州刺史在西汉末的复杂环境中逐渐具有军事职能。自成、哀二帝以来,刺史名称、禄秩变化数次。刺史在变革中既一直保留着职能,又有嬗变更新之举。王莽在代汉之后,对西汉的制度做了变更调整,在刺史制度方面,天凤元年(14),“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见礼如三公”[1]4136,确立了刺史为高位显贵。在天凤三年(16)“遣并州牧宋弘、游击都尉任萌等将兵击匈奴”[1]4144,此时的州牧(刺史)兼领军事,将兵之例逐渐显现。光武帝在征伐新莽政权幽州牧苗曾时,命朱浮为“大将军幽州牧,守蓟城,遂讨定北边”(14)此在光武帝建武元年之前。[5]1137;作为凉州牧的窦融,也被任命为“河西大将军”。
建武十八年(42),光武帝恢复刺史旧制,“中兴但因计吏”[5]3617,免去了刺史入朝奏事之例,正如刘昭所言“断亲奏事,省入异烦,渐得自重之路”[5]3620。光武帝虽复旧制,但凉州刺史事实上的军事职能却基本得以保留。如元初元年(114)“先零羌败凉州刺史皮阳于狄道”[5]221,且“大败,死者八百余人”[5]2889;“凉州羌动,以暠为凉州刺史,甚得百姓欢心”[5]1828,永建元年(126)汉顺帝曾诏“幽、并、凉州刺史,使各实二千石以下至黄绶,年老劣弱不任军事者,上名。严敕障塞,缮设屯备,立秋之后,简习戎马”[5]252。永建三年(128) “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三万余人,讨疏勒,攻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5]2927;中平四年(187),“凉州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讨遂”[18];“胡尝出钞,多虏民人,凉州刺史成就辟卓为从事,使领兵骑讨捕,大破之,斩获千计”[19]。
综上所述,监察、行政、军事权力的集聚对凉州刺史职能的发展嬗变有着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军事职能是凉州刺史的核心职能,在匈奴、羌等族群密集活动的河西地区,首先要保证的是对疆域的有效控制,其次才能是有效治理,而将兵作战是凉州刺史对所属区域进行有效控制的重要手段,不管是出征作战还是控驭威慑,都需要有必要的军事力量;凉州刺史行政、监察职能的实现,也必须以其军事职能为后盾,因此,事实上形成了在一定区域拥有绝对权力的行政层级,虽然一方面提高了行政效率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疆域稳定与治理,但是另一方面也潜伏着分裂割据的危险因素,因而才会有原本为加强中央集权所设之职,在东汉末年却因“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大权在握,封疆裂土而致使汉四海分崩、王朝更迭。
四、“凉州刺史”与“属国都尉”的关系
按照刺史设计架构,凉州刺史应是对“属国都尉”有监察之权。刺史“周行郡国”中的郡指代很明确,就是监察郡一级长官,“国”指代的可能是藩国,也可能是其他。汉代施行郡国并行的制度,在中央王朝下还有相对独立的藩国,汉武帝之前藩国实力较强,发生过数次叛乱,对中央集权产生威胁,所以对藩国的监督和控制也是必要的。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关于刺史所言:“历考诸传中凡居此官者,大率皆以督察藩国为事……部刺史总率一州,故以为要务。”[20]98虽然此处论述的是汉武帝以后的事情,但也可以大致推断出汉武帝时期也是如此,刺史监察藩国也是一项重要使命。凉州刺史部所辖区域中虽然没有藩国,但有另外一种相对独立的机构——属国。凉州刺史部监察区内有安定属国、天水属国、张掖属国、金城属国四个属国,属国都尉就是朝廷派往属国的官员,《后汉书》中记载:“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5]3619;“每属国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5]3621。“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两千石……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初置”[1]742。属国都尉一般设在郡境内,要受郡太守节制(15)属国都尉、农都尉大约也受郡太守节制,参见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上)》,选自余太山、李锦绣编:《20世纪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82页。,但东汉设立的属国,属国都尉领县,与郡太守平行[21];又据学者研究,西汉属国与郡同级,并无低于郡太守之制[22]。
那么凉州刺史是如何行使对属国都尉的监察权的?从出土的简牍中,我们发现了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年凉州刺史对属国都尉行使监察权的相关证据:
九月乙亥,凉州刺史柳使下部,郡大守、属国农都尉(16)属国都尉在兼屯田之事时亦称属国农都尉。见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承书从事下,当用者明察,吏有若能者,勿用。严教官属,谨以文理遇百姓,务称明诏厚恩如诏书/从事史贺、音。 (EPT54:5)[23]5
□月甲午朔乙未,行河西大将军、凉州牧、守张掖属国都尉融,使告部从事□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太守,张掖、酒泉农都尉,武威太守言,官二大奴许岑。(EPF22:825A)[23]148
刺史在成帝至哀帝时已是郡的上一级机构,而且“属国都尉”也明确了受刺史监察。简牍中“凉州刺史柳”派“从事”下部监察太守和属国都尉,证明刺史监察“属国都尉”;又窦融任“行河西大将军、凉州牧,守张掖属国都尉”(17)根据前人研究,此简时间为建武十二年(36)之前,并认为此时窦氏以试任“属国都尉”的身份代摄“河西大将军、凉州牧”,应是光武帝对于窦融的惩罚。见初师宾、任步云:《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吏奉例略考》,载《敦煌学辑刊》,1982年,第31页。,窦融本职为试用“属国都尉”,代摄“河西大将军、凉州牧”,以低品暂代高品,更是说明凉州牧与属国都尉的上下级关系。《后汉书·窦融传》中载窦融任“张掖属国都尉”是在更始年间[5]796,且拥有万骑属国精兵,距此时已隔数年,但仍然是试用,可以看作是光武帝在承认窦融权力基础上的一次妥协调整。属国都尉原是为归降之“蛮夷”所设,其区域在汉王朝疆域构成的第二层,汉王朝对这一区域的统治方式是介于郡县和羁縻统治方式之间[24]。因而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在武帝设置刺史之初,凉州刺史就对辖区内的“属国都尉”有监察设计,但因其是特设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直属中央“大鸿胪”,并无管辖之权力。但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尤其在设置西域都护后,凉州刺史部的辖区是连接汉朝核心区域与西域间的唯一纽带,其边疆边缘属性减弱,可逐渐视为内属之郡,复后刺史制度更迭变化,在成哀二帝前后,成为事实上的行政层级,凉州刺史对属国都尉的监察设计逐渐异化为直接管理。
在监察管理属国都尉的同时,凉州刺史还试图对护羌校尉(18)关于“护羌校尉”的设置时间,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是依据《汉官仪》记载的始置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二是依据《资治通鉴》记载的西汉神爵二年(前60)。刘国防认为护羌校尉的设置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最迟在神爵二年,“护羌校尉”这一官职正式设立。参见刘国防《西汉护羌校尉考述》,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施加影响。至迟在西汉神爵二年(前60)已正式设置护羌校尉,其禄秩根据《后汉书·百官志》的所载为“护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3]3626。从品级来看,护羌校尉似乎是在凉州刺史部的监察范围之内。东汉建武九年(33),班彪奏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5]2878;永平二年(59)“护羌校尉”窦林因罪免官,“会凉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狱死”[5]2880。“凉州部署护羌校尉”更是能表明凉州刺史与护羌校尉的密切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仅能反映东汉初年两者之关系,因羌人分布地域涉及凉州、益州两刺史部,其关系纷繁复杂,似乎并不为一部刺史所辖。此后有《后汉书·种暠传》将凉州刺史种暠与羌人活动直接联系起来,而原本负责管理羌人的护羌校尉并无显绩,窥测缘由,除凉州刺史掌兵权可直接以武力震慑不轨活动,还极有可能是因凉州刺史直接或间接越过护羌校尉处理羌人问题,其中隐情以及凉州刺史与护羌校尉之关系有待进一步考察。
五、结语
凉州刺史部原本是在汉朝整体战略下综合河西、陇右匈奴与羌人活动的压力而设置。刺史职能在监察基础上有所变化:首先是刺史的品秩由六百石升为两千石,跟郡守是同一品级,刺史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其次是刺史职能的变化,刺史有了固定机构及治所,刺史选人用人的权力扩大,刺史监督对象的范围扩大等;再次是刺史拥有军事职能,能够将兵作战;最后是刺史的地方官化,称谓上的变化就能体现出这种趋势,“刺指刺吏,属于监察;牧指牧民,属于行政”,是刺史向地方官转化的一种表现。
凉州刺史职能的继承与嬗变是基于汉代职官制度变革与河西特殊地理位置的背景下对行政体系所做的调适。自西汉晚期刺史逐渐异化为行政层级,凉州刺史在此过程中集监察、行政、军事权力于一身,在刺史职能异化扩张的背景下,凉州刺史还有了监察管理“属国都尉”之权力,并试图影响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之职能辗转反复,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国家刺史制度变革影响下的自身职能的变迁,中央层面的品级职能调整与权力变化深刻影响到地方行政层面,表明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另一方面是凉州所处地域的独特性,信息沟通并不能做到及时有效,在危急情境下,需要有相当权力之官员在一定区域内进行果断处置,而权力集聚下的凉州刺史正可以担当此重任。
关于刺史之功用,刘昭在《后汉书·百官志》注中言西汉末年“六合危动,四海溃弊”,但“八方不能内侵,诸侯莫敢入伐”,盖是刺史设置以来“干强枝弱,控制素重”,到东汉末年,刺史则“非有忧国之心,专怀狼据之策”,成为汉朝分崩离析的诱因[5]3617。刺史职能的变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有刺史监督职权的扩大,又有刺史职能的异化,逐渐成为兼有军事职能的一级行政机构,两者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之过程。凉州刺史的职能承袭变迁是汉代刺史制度变化的映照,也是当时国家疆域版图拓展的现实需要,制度与实践相互调适,进而推动了国家政治体制与边疆治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