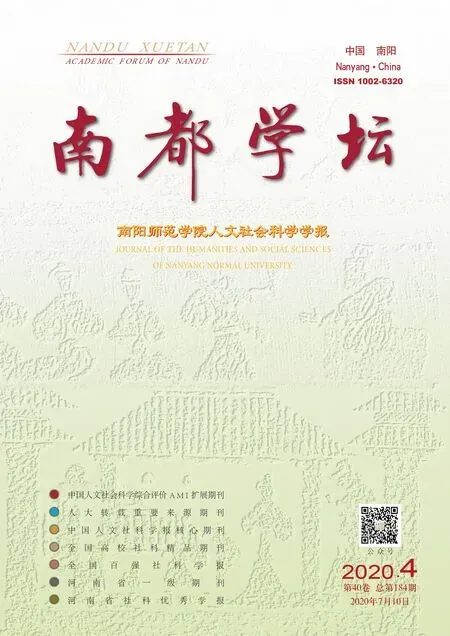邓小平“不搞争论”的财产哲学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性
2020-12-02常青
常 青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针对目前社会中的一些争论现象,我们重提邓小平的“不搞争论”,并通过对西方现代财产观的批判,揭示其哲学基础,以进一步从理论上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崭新道路。
一、关于“不搞争论”的基本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思想观念不断发生着碰撞。据刘吉著《碰撞三十年》记载的思想观念交锋就多达十次,包括:1.个人崇拜与群众是真正英雄的争论;2.“两个凡是”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争论;3.姓“马”与姓“修”的争论;4.姓“社”与姓“资”的争论;5.姓“公”与姓“私”的争论;6.“有产”与“无产”的争论;7.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前与取得全国政权后作为执政党面临变化的争论;8.社会变革中各种矛盾激烈与社会和谐的争论;9.唯“GDP”与科学发展的争论;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等[1]。
而贯穿这些争论的是“争论”与“不争论”的争论,最终的结论是“不争论”。据高正礼的观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既有允许、倡导“争论”的思想,也有主张“不争论”的思想。邓小平倡导和主张的争论主要是:重大路线方针和原则、不同工作意见和学术问题的争论。反对和批评的争论主要是:政治运动式的争论,具体改革举措的争论,不同国家政党间意识形态的争论和空泛背时的争论[2]。而当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确立之后,邓小平主要提倡“不争论”。并且,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宣示了知识产权,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搞争论”得到了其后历届领导人的很好贯彻。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到胡锦涛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国企和私企关系强调的“我们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也毫不动摇地支持、保护、扶持民营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3],都是邓小平“不搞争论”思想的继续发展。因此,研究邓小平“不搞争论”思想在当前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不搞争论”的本质,社会各界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尹汉宁认为“不搞争论”体现了改革的坚定性、改革的实践性和担当精神[4];常绍舜认为“不搞争论”“体现着我们党在认识社会稳定机制方面的质变”,改革开放的基础是政治稳定,而稳定的基础在于我国改革实践中的“不争论”和“不折腾”[5];巍巍珠山认为“不搞争论”体现了实干精神,“在实干中体现能力、在实干中展现追求、在实干中推动发展”[6];高长武认为“不搞争论”是手段,是针对“左”的特定问题讲的,是为利用和平与发展机遇争取时间,是用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人们,其目的是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平稳、健康进行[7]。当然还有其他观点,如认为“不搞争论”是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特征,“不争论”是为了进行科学的改革试验等[8]。概括来说,各界认为“不搞争论”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种重要手段、一种重要策略。而正是在“不搞争论”作为压舱石的基础上,我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了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时代。
“不搞争论”的出发点和服务对象必须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为前提。邓小平自信地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党的十九大报告同样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9]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封闭僵化的老路的摒弃,是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结果。而且,改革开放以前实践的经验教训以及苏联的解体,已经把这条道路的结局昭告于天下。因此,防“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已经没有障碍。然而,最近出现的“私营经济离场”的奇葩怪论,却以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左”的论调并没有消除。辩证地来看,其原因就在于“改旗易帜的邪路”并未在实践和理论上被证伪。
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左”的一套和右的一套必然作为完全对立的两极出现,每一极都可以自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本体,意图遏制或消灭对方。只有我们在哲学上明确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极才能化为两翼,成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事实是,邓小平从“不搞争论”的策略出发,并未直接阐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只是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他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0]另外,他还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0]可以说,邓小平以基本路线、衡量标准、社会主义本质等为基本特征标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轮廓。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把这个轮廓清晰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1]不过,这并不是哲学上的明辨。
“不搞争论”的手段本质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不搞争论”的策略本质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性。这种正确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是“左”的一套,也不是右的一套。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哲学上讲明白,和“左”的一套、右的一套区别开来。如前论述,“左”的一套并不足惧,右的一套才是根源。“左”的一套存在的原因是右的一套的存在。因此,我们的批判应当着眼于右的一套。
对右的一套的批判难点就在于其缺乏在中国的实践。但这并不能难倒我们,鉴于右的一套存在的根源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存在,我们可以借助西方学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来完成我们的批判,从而把批判转向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如果有人提出反驳说这对于我国来说没有现实可行性,那么我们也可以反驳说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作为西方学者存在的早期资本主义的批判者。我们要完成的批判是在走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的批判,是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对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的继续批判。而且,我们这一批判并不违背“不搞争论”的思想。我们这一批判充其量是学术批判,我们这一批判充其量是以和谐方式进行的讨论。我们这一批判事实上是对资本主义的继续批判。我们这一批判既不针对“左”,也不针对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哲学明确。
二、西方现代财产观及其自我批判
我们要完成这一批判就必须找到一个恰当的切入点,所谓蛇打七寸,必须从要害下手。这个要害,邓小平告诉我们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10]而《共产党宣言》告诉我们:“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12] 第1卷,414-415所以,我们的研究就必须从财产的哲学认识出发而展开。
西方财产观有其漫长的糅杂历史。西方财产观源于日耳曼传统与习惯,同时滥觞于古典文明与基督教,可以说它是上述三元素的混合物[13]。西方财产观起始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间经历了古罗马的西塞罗、中世纪的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然后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在资本主义时期,西方现代财产观得以确立。西方现代财产观的确立建立在西方学者们的共同贡献基础之上,他们是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康德、柏克、边沁、黑格尔等。总的来说,他们奠定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理论的统治基础。而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他们的批判者的角色出现的。至于当代的西方学者,其研究主要是在这些众学者基础上的运用与发展,比如现在流行的《西方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等。
(一)西方现代财产观到处充斥着矛盾
我们借助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关于财产的观点来初步确立我们对西方财产观的基本认识。汉娜·阿伦特界定的“现代”始于17世纪,也就是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时期,其标志是哥白尼地动说、伽利略望远镜、塞维利工业蒸汽机等。这一时期,利玛窦第一次觐见明神宗。它的前一阶段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汉娜·阿伦特认为现代与前现代的区别就在于社会领域的兴起。社会问题的出现不但占据了公共领域,同时侵犯了私人领域,从而模糊了前现代原本分明的公领域和私领域,由此引起了人们财产观念的变革,使之由空间概念走向了物质概念。汉娜·阿伦特认为前现代的财产意味着空间,“意味着一个人在世界的特定部分内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从而属于一个政治体”[14]。正是这一席之地的存在,使得人区别于可以被随意猎杀的动物。这种财产观念随着社会对公私领域的侵蚀转变为现代财产观。现代财产观随着空间意义的丧失,仅仅剩下了财富这一含义。的确,美国《独立宣言》表明,“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非法国大革命所宣言的:“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与反抗压迫。”看来,杰斐逊并不认同财富意义上的现代财产观,而用追求幸福代之。
(二)西方现代财产观事实上处于分裂状态,并相互攻讦
其主要派别包括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契约主义。其代表人物分别为柏克、洛克和卢梭。柏克和洛克在主要观点上直接对立,柏克认为财产起源于历史和惯例,他说:“有可能你周围的许多资产是凭借武力取得的,那是几乎与迷信一样恶劣的事情,而且不乏无知。然而,那是很古老的暴力,在开始时可能是错误的事情,却会被时间神圣化,成为合法的事情。这或许是我身上的迷信以及无知,但是,我宁愿留在无知和迷信之中,不愿被启蒙和净化,从而离开法律和自然正义的种种首要原则。”[15]而洛克则直接否定了历史和惯例,把讨论推进到了这些事实的原初的自然状态,完成了对“君权神授论”的批判,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在自然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劳动获得财产。而卢梭则更激进地认为财产是人类堕落之源。他把人与物分开,强调劳动只完成了占有,而财产所有权的确立需要由公意决定。他说:“为了权衡得失时不致发生错误我们必须很好地区别仅仅以个人的力量为其界限的自然自由,与被公意所约束着的社会的自由;并区别仅仅是由于强力的结果或者是最先占有权而形成的享有权,与只能是根据正式的权利而奠基的所有权。”[16]
(三)西方现代财产观的内在焦虑源于其虚无化
尽管西方学者都认可私有财产的神圣地位,但是现实却在不停地挖掘着这种神圣。他们清楚,“尽管我们的社会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但产权还是有限的。社会决定‘你的’财产”[17]。洛克尽管声称“货币的使用就是这样流行起来的——这是一种人们可以保存而不至于损坏的能耐久的东西,他们基于相互同意,用它来交换真正有用但易于败坏的生活必需品”[18]。然而,“金融体系似乎已产生了一种新的、魔术般的‘货币—货币’循环,在这些循环中,仅用货币本身就能制造出货币来,而无需实际生产的介入”[19]。Richard Weaver说:“股票和债券等抽象财产……实际上毁灭了人和他所拥有的物之间的联系,并使得工作的神圣化成为不可能……大企业和工业的理性化于是支持了我们试图克服的罪恶……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实际上被迫反对今天很多以私有企业名义完成的事,因为企业组织和垄断是财产丧失它的神秘性的原因。”[20]这样保守主义就以事实否定掉了自由主义。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汉娜·阿伦特对前现代财产观的推崇。不过,西方不可能因此而回到前资本主义时期。然而,自由主义的被否定并没有证明契约主义的成立。卢梭否认财产所有权与自由、生命的同等地位,而且《独立宣言》也把财产排除在“不可剥夺的权利”之外。然而,“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21]第21卷,201。的确,以财富为基础的现代财产观占据着不可置疑的地位,资本是真正的王者。杰斐逊有可能是在不断地纠结中度过了他的一生。
西方财产观的虚无化源自对财产认识处于盲人摸象状态。洛克所谓的财产并没有统一的用词,最起码包括“property”“possessions”“estates”“fortunes”和“goods”等,还要包括“人的生命和自由,甚至还包括了人的劳动及行为规范,它是个人所有的东西的总和,包括身心和物质两个方面的内容,或者说无形和有形的两种状态”[22]。梅雪芹将之称为“大财产”[23]。相似的用法还有尹田提出的“广义财产”,这是法国民法理论中的“patrimoine”概念的中文翻译[24]。柏克的财产定义比洛克较为狭窄,但同样是一种大财产。其内容不但包括物,而且包括长久以来形成的人与物之间的直接的权利关系。保守主义者的“物”是指包括房屋、土地等在内的被威廉·哈珀定义为“硬财产”之类的东西。保守主义的直接权利关系是指“由于其自身扩展成为一种惯例和方式, 因此它本身就是目的”[25]。显然,汉娜·阿伦特将现代财产观直接定义为财富观是很值得商榷的。而契约主义将财产定义为所有权同样是很不周延的,所有权只不过是“作为荒谬的神秘主义为中介来恢复人与土地的温情脉脉的关系”[21]第3卷,262-263。
总之,西方现代财产观的自我批判告诉我们,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西方现代财产观。也就是说,右的一套翘首以盼的是对西方私有财产想象出来的一个幻影。这样就不存在“争论”的基础。可见“不搞争论”在哲学上是正确的。
三、从马克思出发对西方现代财产观进行批判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马克思实质上秉持多维财产观。由此出发,我们应当可以终结西方现代财产观乱象。
(一)马克思将财产归结于生产关系
把财产归结于生产关系,统一了前现代财产观和现代财产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21]第13卷,8-9。在谈到私有财产时他指出:“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21]第3卷,410-411这样,保守主义所求的稳定生活不过是对农业生产关系的向往,自由主义所求的生活不过是对菲尔麦爵士所推崇的君权神授社会的否定,契约主义也只不过是对封建专制社会的抨击。而汉娜·阿伦特忧虑的财富不过就是在现代社会中猖狂的资本,而资本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在打破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后形成的新的生产关系。这显然为我们开启财产谜团之门提供了一把钥匙。
(二)马克思持一种复杂的财产观
显然,无论是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契约主义,他们在具体使用财产概念时都侧重于某一个方面。而且,在不同的场合他们都把财产定义为某种本质,比如:权利、权力、能力、劳动、外物、人口、关系、制度、功利、功能等。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过程中并没有提出明晰的财产概念,这就为我们发展马克思的财产思想提供了机会,我们可以在他将财产归结于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生产关系提法的逻辑前提是,财产是个综合概念。首先,私有财产是财产的子集。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和财产是两个概念,他批判施蒂纳故意混淆了Eigentum(财产)和eigen(自有的)这两个词的用法,把私有财产变为财产的概念。他认为财产是对个性的拥有,他进一步说:“实际上,我只有在有可以出卖的东西的时候才有私有财产,而我固有的独自性却是根本不能出卖的物品。”[21]第3卷,253-255其次,财产是个多层次的概念。从资本财产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工人实际上把他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把他的劳动和别人的劳动为一个共同目的的结合,看成是一种和自己相异化的权力;实现这种结合的条件,是和他相异化的财产。”[21]第25卷上,101具体表现为生息资本(利息或作为所有权的资本)的权力、执行职能的资本(作为职能的资本)的权力、社会资本(社会财产)的权力、私人资本(私人财产)的权力、信用(对社会资本的支配)的权力。最后,财产是个系统概念。生产关系实际上整合了各种要素。马克思说:“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 把它们看作是他本身的自然前提, 这种前提可以说仅仅是他身体的延伸。”[12]第2卷,744“实际的占有,从一开始就不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想象的关系中,而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能动的、现实的关系中,也就是这些条件实际上成为的主体活动的条件。”[12]第2卷,746
(三)马克思的财产观可以用三维财产模型直观表述
首先,三维财产模型意味着主体、客体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像包括汉娜·阿伦特那样将现代财产直接定义为作为外物的财富的人们所持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而像契约主义者把财产主体(人)与财产客体(物)分开并且把其联系归结于虚幻的所有权显然也是错误的。其次,三维财产模型意味着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只不过是“一藤二瓜”。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并不能独存,它受到保守主义尤其是契约主义的制约,受制于社会与国家。而马克思所明确反对的是“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的社会状态,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12]第1卷,416。最后,三维财产模型意味着财产的生产方式本质。从共同体内部环境来看,生产方式决定着其社会基本状态,包括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制度及其运行状况。从共同体外部环境来看,生产方式决定着其对外的存在状态,是其军事、外交、话语、安全等综合影响力的直接根源。保守主义代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自由主义代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契约主义不过是脱离了生产方式考量的一种政治幻想。当然,以上三者都是幻想,是各走了一个极端的幻想。
四、邓小平“不搞争论”与三维财产模型相一致
邓小平宣称“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的自信源自对马克思财产观的深入理解。这种深入理解与三维财产模型高度一致。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三维财产模型一致
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把客观世界看作运动着的世界的思维。三维财产模型不仅给出了财产的具体形态,使我们可以直观把握,而且给出了财产运动的具体原理。财产的具体形态更多地要靠财产关系(即生产关系)去把握,这就是求本质,就是实事求是。财产运动则更多地要靠财产主体和财产客体去把握。财产主体的变化和财产客体的变化必然引起财产关系的变化,社会状态也必然因此发生变化。而要认识这样的变化就必须突破旧认识,放弃旧本质,就必须解放思想。
(二)社会主义本质论与三维财产模型一致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从财产主体的变化和财产客体的变化、而且是积极进步的变化方面考虑问题。而在生产力发展变化带来社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财产关系(即生产关系)的调整必然是滞后甚或是无序的。财产关系的调整过程伴随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行动。其要实现的目标是财产模型的理想状态,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那种看到问题就想退回去走老路,以及那种得了便宜就想借口走西方邪路的想法,都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三维财产模型一致
我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的状态,以及改革开放前的实践告诉我们,通过制度强力调整财产关系进而实现现代化甚或超现代化是一条死路。没有财产主体的变化和财产客体的变化,财产关系的单独变动并不能带来社会的转型升级。而那种脱离中国现实,照搬西方经验及其制度的做法,同样也不可能获得成功。认识到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正是认识到我国的财产状态既不同于过去的农耕封建财产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资本财产模式。当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哪个组织是完全相同的。
(四)改革开放理论与三维财产模型一致
“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26]138只有这样才能纠正扭曲的财产关系,才能释放财产主体、财产客体在变化中产生的能量。“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26]117邓小平认识到了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只不过是“一藤二瓜”的关系。二者既有竞争关系,更有互相借鉴与合作关系。他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6]373因此他主张大胆开放,认为“改革是中国的二次革命”[26]113。
(五)邓小平理论的其他主要方面也与三维财产模型一致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强调了财产本质(即生产方式)的根本地位,两个基本点要服务于生产方式的转变,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坚持两个基本点,从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有可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来自对社会主义制度适应并推动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生产方式的自信。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党,突出了财产主体的重要性。社会的变化来自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化来自生产力的变化,生产力的变化来自人的变化。财产主体的发展变化是第一位的。
邓小平所倡导的“不搞争论”以及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建立在其对马克思财产哲学理论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是其洞悉财产运动规律的结果。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崭新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前世界多样化道路中的一条。并不存在脱离实际的“左”的本体和右的本体。“左”右只是中国道路演进过程中波动的两极,“左”右的力量都是中国道路演进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出来的一条崭新道路,就是邓小平以基本路线、衡量标准、社会主义本质等为基本特征标定的一条崭新道路,就是符合马克思财产哲学所揭示的财产运动规律的一条崭新道路。
那种强调把某一方面、某些因素、某类特点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质的纯粹化的观点都是背离了三维财产模型的孤立、静止、片面、本本、主观的非科学、非实践、非客观的观点。
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正确看待“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实现生产方式的持续转变,使国内国外态势持续向好。通过综合国力的提升为中华民族赢得长期竞争优势,为中华民族每一成员创造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条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