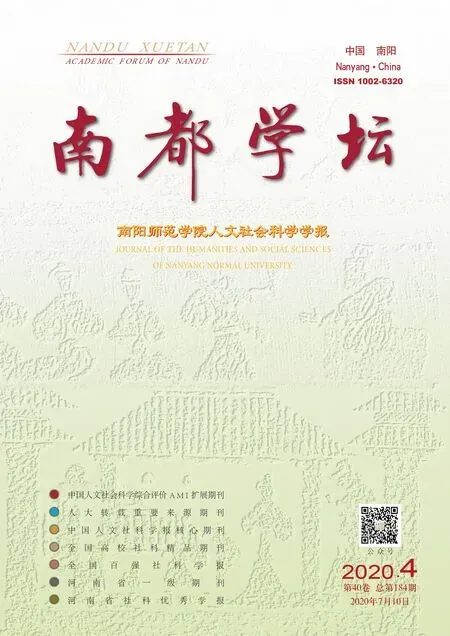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妇女回家论”的批判
2020-12-02秦宁波
秦 宁 波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上海 200241)
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深入以及“妇女回到家庭去”外来思潮传入的影响,国内舆论界逐渐掀起一股“妇女回家”的言论和政治逆流,进而引发舆论对“妇女回家”问题的大论争。围绕“妇女回家”问题论争,学术界已有相关的前期研究(1)代表性的论文有刘丽威的《浅议中国近代关于贤妻良母主义的论争》,载《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第3期;夏蓉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关于“妇女回家”与“贤妻良母”的论争》,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何黎萍的《20世纪40年代初关于“妇女回家”问题的论战》,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范红霞的《20世纪以来关于“妇女回家”的论争》,载《山西师大学报》2011年第6期;《妇女、家庭与民族国家——以“妇女回家”论争为中心的考察》,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这些文章主要对“妇女回家”问题论争进行历史梳理或整体分析。,但对于中国共产党与这场论争关系的专门研究则有待深化。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场论争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并直接参与指导了这场论争,直到20世纪40年代争论才告一段落。拙文试梳理分析中国共产党重视“妇女回家论”问题论争的外部缘起、论争中中国共产党的表现及论争对中国共产党妇女动员工作的影响等,以期还原并呈现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论争中扮演的角色与所处的地位。
一、“妇女回家论”批判的缘起
妇女解放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妇女解放运动是近代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上却悄然弥漫起“妇女回家”的反调,这成为全社会妇运工作和全民族抗战的一个阻碍因素。“从前,回到厨房,回到家庭的口号,家事儿女之累,曾限制与妨碍了妇女运动的顺利开展。”[1]1“妇女回家”论争是内外多重因素交织下促成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绝不会对此置若罔闻,通过对当时的德国因素、国民政府政策以及外界保守舆论的分析,可以透视中国共产党重视这场论争的外部缘起。
(一)德国“妇女回家论”的传入及在中国的传播影响
“妇女回家论”是从遥远的德国传入中国的舶来文化,在当时的中国引发广泛的传播(2)德国“妇女回家论”在中国传播广泛,直接涉及该内容的刊物可谓俯拾即是,如《申报》《国民新闻周刊》《时与潮》《女权》《妇女生活(上海1935)》《国际译报(上海1932)》《妇女杂志(上海)》《黑白》《妇女共鸣》《妇女青年》《福建导报》《公教周刊》等。。1931年希特勒上台执政,为了解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失业人口剧增问题,竟将大批女职员、女工解雇,驱赶她们回到家庭,腾出更多就业机会给男性。“为了调剂失业恐慌德国政府对于劳动的妇女采取了两种办法,主要的一种,就是大批地把些女工们无条件地,无保障地从工厂里赶回家去,把原来妇女所占有的位置让给男的,而且雇来的男工,薪金和女的一样。”[2]希特勒在演说中讲“妇女天职在教养”[3],公然说妇女的位置是在家庭里、厨房里、教堂里。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宣传部长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在柏林妇女会议上的演说也持相同的论调,“第[帝]国社党视贤妻良母为任何妇女至高尚职务,故志在动员妇女取此而舍其他,今伪君子反对妇女吸烟与烫发,渠殊为不然云”[4]。他还胡说道:“你们的幸福绝不在工厂里,你们真正的势力范围是家庭,你们还是去主持家政吧。”[4]释因在《妇女青年》刊文也讲到德国的这种做法,“就男女自然分工的天职而言,一些不自然的女子职业,既不是女子自身赋性所特长,又不是社会上特别的需要,自然不如让这些职业的女子,享用宽余的时力,来理家育儿”[5]。
除了经济危机的原因外,希特勒为了向德国人民灌输扩张主义,拼命鼓吹“种族优越论”,进而又将“保国保种”的所谓“神圣职责”强加在妇女身上。他承袭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观点,即“妇女的存在唯一的就是为着传播人种,她们的意义就止于此”。“所以他(希特勒)造就一学说,以妇女最伟大的事业就是结婚,而且必需大量的生产小孩,他为了有一个标准起见,规定每个家庭至少要有五个孩子,少一个就算有犯罪的行为。”[6]德国宣扬的这种狭隘的生育观念实质上让妇女成为简单的生育机器而无其他自主的选择,最终只能是被束缚于家庭而失去大量从业的可能性。
德国的这种思想传播到中国后引起中国共产党的关注,他们认识到这种论调是不合乎时代的“开倒车”行为。妇女社会活动家罗琼认为:“事实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在这资本主义世界正在没落的现在,经济恐慌日益深刻,希特勒为缓和国内的失业问题,和政治上的危机,首先驱逐妇女重回家庭,重去负担她们服侍丈夫,抚育儿女的‘天职’。”[7]143-144中共党员郭耘创办的《福建导报》刊文公开反对与谴责德国的这种落后行径,“希特勒要实现三K主义,要把妇女赶到家庭里,教堂,和厨房里去,倒退到妇女最黑暗的时代,重新把锁链扣在德国的妇女身上……说服自己的女同胞,强固我们的阵线,是最重要的事”[8]。“妇女回家”论调是与当时社会发展与现实需要相背离的一种思潮,对它的传播和轻信会使整个妇女运动遭遇“黑暗的时代”,其传入中国也必将遭到进步共产党的摒弃与批判。
(二)国民政府鼓吹贤妻良母主义及复兴“礼义廉耻”传统道德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工作的同时,却又相反地为“妇女回家论”在国统区的活跃提供官方的生存土壤。在女子教育上国民政府鼓吹贤妻良母教育,如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发展女子教育,培养仁慈博爱体力智识两俱健全的母性,以挽种族衰亡之危机,奠国家社会坚实之基础。”[9]2941939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主席陈仪公开宣称:“妇女们在家中第一件事,就是教养儿女。”[10]为了限制进步妇女运动的发展,国民党浙江执行委员会于1940年制定《非法妇运防止办法》,此种办法的推广使许多职业妇女被迫回到家庭。此外,国民党还要求妇女生更多的孩子,制定奖励生育的政策。国民党的妇女政策实质是在鼓吹贤妻良母主义,也成为“妇女回家”的官方依据。
中国的妇女在抗战中受尽了各种非人的灾难和折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遭遇和践踏。194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在《持久抗战中的中国女工》一文中讲道:“一切保护女工、童工的待遇,不管在中国任何地方都被取消一无所有,甚至故意优待男工分裂工人以便孤立女工,更好压榨苛待女工,至于禁止女工有任何组织,不准女工参加抗日活动,限制女工参加文化教育,更是普遍的现象。”[11]365这种不顾民族利益,非人对待妇女的状况是与团结全民族坚持抗战的国策方针相违背的。
国民政府十分重视儒家传统道德对维护政权的作用,蒋介石认为“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总理所讲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这就是三民主义的灵魂,现在我们再将这八德归纳起来,就是我所到处提倡的‘礼义廉耻’”[12]。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一文,在江西南昌发起一场以提倡“礼义廉耻”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随着抗战的深入,1939年11月20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宣言:“首先注意者,在国民自身之修养而言,必须明礼义知廉耻,以严是非、邪正之分别,而励百折不挠之勇气。”[9]593在这种传统道德复兴言论的荫庇与笼罩中,足以助长整个社会的复古心理。比如,华北广大妇女也处于敌人的欺骗麻醉之下:“敌人所到之处,新民会和宣抚班马上就进行复古的宣传,提倡封建的旧道德,主张遵守‘三从四德’,做‘贤妻良母’,新民会的汉奸头目缪逆斌曾公开提倡说:‘男性刚,女性柔,男属阳,女属阴,男主外,女主内……这是不移的天理。’因此,他便得出结论:‘如果叫妇女去参政,岂不等于叫男子去喂奶和生孩子吗?’”[11]371反动政府宣传这种荒谬绝伦的道理,让广大清醒的同胞义愤填膺和意图反抗。
妇女和男人一样应该参加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运动,绝不是去做贤妻良母或恪守“三从四德”的妇道。“许多姊妹们误解了‘解放’两个字,以为念几天中学,剪发,天足,穿最摩登的衣服,在学校里鬼混张文凭,将来好找个比自己学级高一层的丈夫,自由结婚,便算解放了,其结果仍然是男子的玩物,花瓶。这种错谬的见解,可笑亦复可怜。最可恨的是现在的学校有时就专门造就这种女子,或授以良妻贤母,‘回到厨房’的教育。事实上这种不自觉的女子和奴隶教育都是女性的敌人。”[13]509要过人的生活,为什么专做男性的木偶和花瓶呢?妇女解放运动和中国的命运一样,自己的地位,只能靠自己的奋斗来提高,痛苦的桎梏和悲惨的樊笼,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摆脱。
(三)保守舆论对“妇女回家论”的遥相呼应及大肆推波助澜
与“妇女回家论”遥相呼应,“贤妻良母论”是封建保守主义者对妇女一贯的伦理要求与期望。特别是从1930年6月始,林语堂在上海中西女塾的讲演中明确提出“我国女子最好的归宿还是婚嫁”,为响应“妇女回家论”发出声音。林氏的论调引起当时舆论的轩然大波,从当时发表报刊的统计看,仅围绕“贤妻良母”一题直接展开论述的文章就数量庞大(3)据报刊发文统计,以“贤妻良母”直接为主题刊文的报刊涉及数十种,如《妇女杂志(北京)》《妇女界》《朝气》《三六九画报》《天声半月刊》《长城(绥远)》《妇女共鸣》《妇女月报》《现代家庭》《新妇女》《黑白》《每月评论》《健康家庭》《现代评坛》《福建妇女》等。,从文章的具体内容分析看支持“妇女回家”的论者甚多。
从当时的保守舆论看,许多人肯定“贤妻良母”的意义。金铎在国民党刊物《正论》上大讲:一个妇女,能叫一般人对她油然而生尊敬之心,一定是一个尽了责任的女子,或是孝女,或是良妻,或是贤母。白雪认为:“家庭还是社会的主要机构,最大多数妇女,还是生活在家庭里,并且每每是它的主持者。因此主妇的贤良与否,不只直接地关系一家的幸福,而且间接地影响到整个社会。所以‘贤妻良母’的意义,还是应该存在的。”[14]这些颇具代表性的声音,宣扬把妇女的生活区域主要限制到家庭,过分地肯定妇女贤良对于家庭幸福的意义,最终只会使妇女被束缚于家庭而无大的作为。
特别是1934年之后,一批封建文人、官方的妇女团体及刊物纷纷发表演说文章,大肆鼓吹妇女应回到厨房去,去做贤妻良母。如上海妇女教育馆创办的《妇女月报》,针对社会上的“妇女回家论”(“女子的智力及不到男子,不能负起社会的责任,应该忍辱悔过,回到家庭里去教养儿子和体贴她的丈夫”),认为“他们的诡论完全是以一种浅薄的现象论做为根据而企图把妇女推进了黑暗的地狱,同时极力把妇女天赋的弱点做为证明想稳固男子中心社会的地位,这种浅狭的妙论,却忽略了史的发展和现在的实践”[15]2。更有甚者,如《妇女共鸣》社还出了一个“新贤良专号”,“新贤良”是用所谓男女双方都尽职的理由来大肆宣扬贤妻良母的合法性。这些所谓的“新论调”也不过是略带浅薄的狭隘认识,依旧没能打破“妇女回家”的怪圈,反之却在一定程度上对保守的论调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妇女回家论”的问题分歧与思想论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妇女回家”问题论争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可谓此起彼伏,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论争发生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第二次发生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妇女回家”和“贤妻良母”陈词滥调的危害性,在论争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先锋作用。许多共产党员,如周恩来、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罗琼等都直接参与到论争中来,撰写大量文章据理批驳“妇女回家”及“贤妻良母”的错误论调。仅从中国共产党的刊文出处分析,整个论争涉及的参战报刊数量众多且论争相当激烈。从当时的传统守旧论调及中国共产党的批驳回应分析,“妇女回家”论争绝不是“回家与否”的简单辩驳,而是内含许多细化问题的双方大论战。拙文试围绕“妇女位置在家庭或社会” “贤妻良母与妇女职责” “教养(齐家)和解放(治国)关系” “新贤良主义”等4个具体问题,探讨“妇女回家”问题论争的基本内容和其背后的思想分歧。
(一)关于“妇女位置在家庭或社会”问题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和民族危机的加剧,必须摆正妇女在革命实践中的位置,使广大妇女成为妇运工作和民族抗战的骨干力量。实践证明,妇女位置的正确与否关系到民主革命的发展轨迹。但对于妇女位置如何定位的问题始终夹杂喧声,“回家庭?到社会?是妇女运动的基本论争,贯穿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整个历程”[16]。众多封建保守人士(4)代表性观点:陈仪提出“男子在社会上服务,女子在家庭中服务”,详见《我的理想国》,载《改进》1939年第5期;端木露西号召妇女“在小我的家庭中,安于治理一个家庭”,详见《蔚蓝中的一点暗澹》,载《大公报》1940年7月6号;尹及认为“女人的真正位置是在家里”,详见《谈妇女》,载《战国策》1940年第11期等。,把妇女位置定位到家庭,这些不绝于耳的落后言论成为阻碍民族抗战的不良因素。
妇女的位置被定位到家庭而非社会,妇女们会成为贴有“家庭妇女”标签的群体,她们都难脱离家庭生活的羁绊。当封建保守主义者仍高喊“妇女回到厨房去”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察觉这些“绊脚石”般言论的危害性。邓颖超针对端木露西所谓“小我幸福的家庭”的言论,尖锐地批判道“这些也正是个人自私主义和享乐主义最好的反映”[11]382。《现代妇女》刊文《什么是家庭妇女进步的阻力》指出:“自从家庭起源到现在,这样冗长的历史过程,无数的妇女是被历史决定了放下劳动工具离开生产,走进家庭去,以料理家务养儿育女作为她们唯一的天职。烦琐的家事麻木了每一个家庭妇女的神经,无论是生来就没有跨出家门的也好,或是受过教育,做过一些事情的知识妇女也好,只要生活在家庭里长久之后,自然而然地会变成除柴米油盐外无所知无所觉,对于周围的刺激都能逆来顺受。”[17]隶属于家庭位置的妇女们,仍旧无法自主地做出自己的选择。《现代青年(福州)》也刊文批判这种把妇女位置定格到家庭的言行:“德意志等法西斯国家,不是在大开倒车,驱逐妇女们回到家庭去吗?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翻开几页历史,从国家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去追索出育儿问题的发源。”[18]147宣扬“家庭妇女”只能是“大开倒车”,它无法适应革命发展的大潮。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在当时落后的社会制度和紧迫的革命形势之下,妇女的位置绝不应局限在家庭中。1937年1月20日,《绥远妇女》发刊词指出:“妇女也是人,在这个非常时期,妇女和男子是一样应该参加抗战救亡的民族解放运动,把国家、社会的责任担在自己肩上一部分的。”[13]5091937年9月,中央组织部《妇女工作大纲》指出:“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任务。”[11]335《大纲》在“妇女群众组织问题”上指出,妇女群众组织的对象包括农妇及家庭妇女等。因而,“要使‘男女平等’获得一个合理的社会基础,妇女必须跑到社会中去,去和最进步的男子同来改造社会”[7]146,这样的论调符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待“妇女位置”问题的基本态度。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对妇运工作和妇女的社会责任有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中国在艰苦的抗战过程中,正需要动员广大的妇女力量……无论在前方,在后方,在城市,在农村,都需要妇女的支持与协助,换句话说,就是需要妇女走出家庭来”[18]147。我们自己必须挪开“妇女位置在家庭”这一块绊脚石,但它只是挪开,而不是取消,把它挪到适当的地方,使其绊脚的作用完全消失。“中国在抗战,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的战士正在胜利进军,它要求动员得更广泛,更深入,因此,鼓动妇女们从家庭里跑出来,参加一切抗战工作,实是一件要务,妇女们自愿的走入社会,更是求之不得的事,如果驱使之复返家庭,让有用的精力浪费在这个小天地之中,就好比使一个瞎子睁开了眼,领略了这个世界的风光之后,又重复令其失明一样地可怕,是万万使不得的。”[19]正如邓颖超所讲,要发挥广大妇女潜在力量,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现实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恰当地运用妇女这一部分力量,如何给妇女们以恰当的社会位置,而绝不是把妇女们单单关到家庭的“樊笼”里。
(二)关于“贤妻良母与妇女职责”问题
“贤妻良母”概念是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而形成的。就妇女职责而言,“贤妻良母”是传统社会对“妻职”与“母职”的伦理规范和最高要求。在这一名分的束缚下,妇女的职责被规定得很死,只能是做一个伺候丈夫的妻子,做一个养育孩子的母亲。同时,妥协主义者也认为家务、教养子女,这是“贤妻”的义务,做“良母”也是女子的天职。“不要高喊反对贤妻良母型的奴隶生活,事实上并不能立刻彻底去铲除,为了现实的生活,只能节节改进,才是正当的理则。”[20]激进者与妥协者把“贤妻良母”贴上“三从四德”“孝顺公婆”“尊重丈夫” “操作家事” “养育子女”的标签,这些旧式迂腐的训条和传统桎梏的礼教,奴隶似的压迫束缚着广大妇女。
所谓“贤妻良母”,就是封建社会奴役妇女的美名,就是要把妇女职责局限于“妻职”和“母职”。1937年1月17日,《江声报》副刊《前进妇女》刊文《活玩物的训练》,针对《妇女生活》3卷12期“所谓生活班”的通讯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生活班”附设在中学部以“训练贤妻良母为宗旨”,“这训练的是什么?是‘贤妻良母’吗?不,不是的。日益贫穷化的中国大众,讨不起,也不需要这种不必亲自煮饭做菜的老婆。这是连‘贤妻良母’还不如的活玩物的训练”[13]508。1940年7月,康克清在介绍华北妇女运动之环境及其发展特点时,也尖锐地讲到华北广大妇女曾处于敌人的欺骗麻醉之下:“敌人所到之处,新民会和宣抚班马上就进行复古的宣传,提倡封建的旧道德,主张遵守‘三从四德’,做‘贤妻良母’……如果叫妇女去参政,岂不等于叫男子去喂奶和生孩子吗?”[11]371针对专做“贤妻良母”的复古封建言论,她指出要进行猛烈的宣传教育,来加以痛斥荒谬的理论,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妇女组织。
关于“贤妻良母与妇女职责”问题的论争,颇具影响的批驳是在1942年9月25日,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他说贤妻良母本来同贤夫良父一样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但贤妻良母成为固定的连在一起的名词,就专限于男权社会用以强调夫权、束缚妇女的桎梏。要把“妻职”与“母职”区别开来,不能完全地等同看待。对于“妻职”与“母职”重要程度,周恩来认为:“在谈母职妻职的时候,毋宁着重于母职,妻职较之母职来说,不仅应置于次要地位,而且也不应相提并论。”[21]609他提出为了人类的绵延,尤其为了强健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应当尊重母权,提倡母权,以此新观念代替“贤妻良母”的旧观念。
抗战形势的发展对妇女职责提出更高的要求,妇女绝不是局限于“贤妻良母”的职责。只要不是有意掩饰事实的人,谁都会相信,中国妇女要求彻底解放,只有主动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职责。妇女社会活动家罗琼认为:“目前我们就得在全民族一致抗战的口号下,把占全民族半数的姊妹,从家庭中间叫出来,要他们把烧饭煮菜,侍奉丈夫的精力,节省起来,贡献给保卫祖国运动,到最近统一救国运动高涨以后,贤妻良母主义的说教,似乎已经完全销声匿迹。”[22]所以当时最为紧迫的妇女职责,已经不是像封建妇女那样做贤妻良母,而是怎样承担更重要的职责。
妇女也有事业性吗?除了做妻子母亲外,妇女还能做别的事吗?“妇女是有事业性的,已用不着争辩。妇女的做妻子做母亲与男子的做丈夫做父亲是有同一意义的。妇女必须为人妻,为孩子的母亲,也必须有自己的事业前途。”[23]妇女的经济独立,是获得解放的基础。“我们承认妇女应该为妻为母,但是我们觉得妇女还有更重要的‘天职’,这就是参加社会生产工作,进而促成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改革,假使背着妻母这块招牌,而用贤良的美名,想把妇女骗回家庭中去过她们的奴隶生活,这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7]143周恩来也讲道:“我们反对藉口妇女应尽母职,因而取消其社会职业,使其陷于更大的困难,转致妨碍母职。我们更反对以同样藉口不承认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21]611中国共产党非空口号反对“贤妻良母”,而是要尊重母职,更要求妇女主动承担起社会生产和投身革命的职责。
(三)关于“教养(齐家)和解放(治国)关系”问题
数千年来中国的妇女主要是住在家里,从古书堆里吟诵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礼记·大学》),于是乎妇女就只能寄生在男人下面生孩子、做饭、安守本分。恰如1940年7月6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的端木露西《蔚蓝中的一点暗澹》一文,文中鼓吹“十分之九的妇女还是要在家庭里做主妇做母亲的”。这种代表性的风靡言论是与中国封建传统的礼教相一致的,其实质是把“齐家”放到“治国”的前面。但是,在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下,这种把妇女与政治完全割裂开来的观点是存在极大问题的,幻想在帝国主义侵略下苟求“齐家”也是无法企及的。
如果忽略当时整个客观的物质条件,“齐家”至多只能是遥远的乌托邦。“所谓‘齐家’是有很多条件的,最低限度也必须具有维持生存最低限度的物质必需品,若把这些也忽略,向着一般饥饿者喊‘齐家’,我想在天下未平之前,她们早已变成骷髅去了。”[13]514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来看,人类社会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黑暗,越来越多的家庭失去起码的安全与生活保障。碧天月在《战时妇女问题》一文中讲道:“到希特勒当国以后,德国便和意大利的把妇运完全镇压下去,回复到十九世纪以前的模样,日本亦然。所以妇女运动在法西斯蒂的国家是无法抬头的。因此,我们要谈妇女运动,要想妇运能够成功,首先要反对法西斯侵略主义国家,首先要把法西斯国家打倒。”[24]这些话告诉我们,放到首位的是反法西斯战争,是要打倒帝国主义而绝不是首先经营家庭。
因为,家庭是离不开社会的,要使家庭得到美满的生活,只有在合理的社会才能实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支离破碎的中国已经无力让人们去固守家庭的教养。“要先有‘国治’才能有‘家齐’,只有国治以后,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使我们建立美满的真实的家庭。”[13]514吴玉章在《中国妇女在“五四”运动中走上了自己解放的道路》一文中分析指出,在法西斯的德国里,“教堂、厨房和儿童”这就是妇女被分配于这三个范围的社会生活;在所谓民主的资本主义的英国有句老话,“妇女的位置是在家庭里”;在五四时代最有文学革命声誉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胡适也说:妇女的美德是“贤妻良母”。针对这些落后的思想言论,他进一步分析道:“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妇女,如果不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私有财产制度,即阶级社会,则永远不能得到解放。”[11]368其表明妇女运动的发展,绝不是从齐家、教养出发,而应从社会解放、民族解放的观念出发,必须适应革命发展的斗争形势。
由此观之,齐家而后国治,服务家庭是间接服务社会的论调是存在片面性的。邓颖超认为:“无论男女,都应当在‘献身大我国家’,‘抗战’,‘救国’的原则下,而‘齐其家’。”[11]382妇女社会活动家罗琼也认为,新的妇女运动是坚决反对妥协的改良主义及盲目的复古主义的妇女运动,而彻底执行“五卅”以后女权运动所放弃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因此“她在目前民族革命的高潮中,成为整个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翼,直接参加一切革命的斗争,她们知道,目前我国民族的真正的解放,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前提,换言之我国民族得不到真正的解放,所谓妇女问题也无从解决”[25]。抗日救亡运动中,妇女要敢于牺牲“小我的家庭幸福”,优先为国家民族服务。
的确,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女性,面临着日寇入侵,到处天灾人祸,难道这是她们“齐家”的时候?妇女教养根本无从谈起。恰如《职业妇女》创刊的话中所讲的,“职业妇女是在历史上最先觉悟而最能进步的一群妇女”[26]。新的社会毕竟是由我们今后的斗争、战争取得的,摆脱帝国主义的剥削、推翻罪恶的现制度,妇女们尤其需要到社会斗争中去实践。或许,“在生育期间,的确会妨碍了她们的工作,然而女子是否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在生育?当婴孩产出了一二个月之后,我们不可以组织托婴所把他(或她)寄托在里面,而再从事自己的工作吗?……只有使‘国’先‘治’,然后才有美满‘齐家’的实现”[13]515。妇女“教养(齐家)”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简单孤立的,而是与妇女“解放(治国)”有着密切关联的。国家的政治优良与否可以影响到妇女日常的教养,妇女“齐家”必须建立在“国治”的基础之上,二者的关系绝不能错位理解或本末倒置。
(四)关于“新贤良主义”问题
与传统的“贤妻良母”观念相比,“新贤良主义”是极具隐蔽性的一种落后观点。它以“男女平等”观念为虚晃和外衣,在“贤妻良母”的基础上又提出“贤夫良父”,以创造夫妇共贤共良的“合理社会”。在这一问题的论争中,尤以《妇女共鸣》的“新贤良专号”的叫嚷最响(5)代表性文章:蜀龙的《新贤良主义的基本概念》,1935年第4卷第11期;蜀龙的《读了“从贤妻良母到贤夫良父”以后》,1936年第5卷第2期;李峙山的《贤夫贤妻的必要条件》,1935年第4卷第11期;李峙山的《贤良问题之再论辨》,1936年第5卷第2期;叶辉的《男女对于家庭的共同责任》,1935年第4卷第12期等。。他们在推崇贤妻良母主义的同时又加以批评修正,大力宣扬所谓“新贤良主义”。对于“新贤良主义”,如蜀龙曾讲过两个赞成和反对,“我们赞成——贤妻良母与贤夫良父。我们赞成——夫贤妻贤与父良母良。我们反对——为夫者或为妻者的不贤。我们反对——为父者或为母者的不良”[27]。“新贤良主义”便是赞成贤良的原则,而反对偏于女性的贤良,于是更进一步而赞成男女双方共同贤良,以维持幸福的家庭。
仅就“贤良”标准而言,中国共产党并非完全反对。周恩来认为:“母职妻职犹之父职夫职一样,可以成为分别贤良的标准,也可以成为男女的分工和各自的任务。所以我们站在妇女解放的立场上,并不反对良母或者贤妻这两个独立的美称和赞意,而只问其所指的标准和含义如何。我们更不反对提倡母职或妻职,而只问其所指的职务内容和有关方面的相互关系如何。”[28]71但事实上,真正合理的社会,绝不会要求妇女成为“贤妻良母”,也更不会要求男子去做“贤夫良父”。恰如邓颖超所言:“新的贤妻良母主义,绝不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直接主要方向和任务。”[11]383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新贤良主义”并不是“合理社会的催化剂”,而是现存社会的“续命汤”,不但不能促进社会制度的变革反而会阻碍社会制度的改革。
虽然新贤良主义者意识到传统封建礼教对女人严苛的束缚性,却在要求妇女“贤良”的同时,又对男子提出关起门来“改善家庭关系”的可笑要求。对此,罗琼在分析新贤良主义的背景和内容的基础上,尖锐地回应道:“真正的合理社会,绝不会要求妇女回到家庭中去做‘贤妻良母’,更不会要求男子也到家庭中去做‘贤夫良父’;他们要求男女同到新社会中去参加各种生产工作。”[7]146新贤良主义倡导者的摇旗呐喊,实际上只是旧贤良主义的“借尸还魂”。这种“新”,只是在旧贤良主义的基础上,加上一点“乌托邦”的幻想。贤妻良母、贤夫良父,表面是承认“男女平等的原则”,实际上只是一个“美梦”罢了。幻想用这个家庭牢笼去解决社会上存在的问题,这至多只是虚无缥缈的理想。要积极创造“男女平等”的合理社会,“须使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工作,争取妇女独立人格,进而去同最进步的男子共同改革现存社会制度”[7]147,但绝不是像“新贤良主义者”所言叫男子跑回家庭中去。
三、“妇女回家论”批判的意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妇女回家论”批判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重要事件。在这场论争中,中国共产党围绕“妇女位置在家庭或社会” “贤妻良母与妇女职责” “教养(齐家)和解放(治国)关系” “新贤良主义”等具体问题与封建守旧者展开激烈论战。该论争对中国共产党妇女动员工作产生了广泛影响,推动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一)认清妇运工作不足,重视“妇女走出家庭”问题
论争中呈现的问题,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过去妇女工作努力仍不够,妇女工作依旧没能深入到各个方面。比如,“在全国各地的社会中存在着很多度着‘商女不知亡国恨’的生活的女性:她们所追逐的是红灯绿酒、歌笑欢娱,妇女工作者的呼喊与奔走,不过博得她们几声冷笑而已”[29]。此外,“许许多多的姊妹们,(尤其是家庭妇女)还在装饰的浪费、跳舞场、麻雀台消磨可贵的辰光,她们没有解放的觉悟,没有爱国的思想,这实在是妇女工作的憾事”[21]230。的确,虽在抗战中妇女工作取得了发展,但还有许多亟待解决或改变的现象。1943年2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指出,妇女工作是有成绩的,却仍然存在脱离妇女群众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倾向,如“没有切实调查研究妇女的具体情况,不深知她们的情绪……主观的意图去提出妇女运动的口号”[11]407,这些都是使妇女工作停滞不能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在认清妇女工作不足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妇女走出家庭”问题。1939年7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21]149。比如,在这一阶段,新疆召开了本省历史上的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大会是由中国共产党从延安派去的女干部促成的。大会通过《新疆妇女第一届全疆代表大会决议案》,要求“广泛宣传家庭妇女参加社会工作,并宣传男子不得藉口阻碍女子走出家庭”[21]623。要重视“妇女走出家庭”所孕育的伟大力量,努力克服妇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使更多的妇女投身于职业工作和革命事业中。
(二)非空口号反对“贤妻良母”,培养“新贤妻”“新良母”
在双方的激烈论争中,中国共产党对“贤妻良母”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1939年3月3日,《中央妇委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中,对当时妇女工作的意见中讲道:“这里我们不应空口反对‘贤妻良母’的口号,而应作新的解释,应创造无数抗日革命的模范妻子(贤妻)、模范母亲(良母)以至模范女儿、媳妇、婆婆等。”[11]3501939年7月,王明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做报告指出:“现时代中国所需要的新良母,应该是教子精忠报国的岳母一类杰出的人物;新贤妻应该是能在前线助战的韩夫人(梁红玉)一流超群的干材;新孝女应该是能够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式的女英雄。”[21]157(6)梁红玉,宋朝楚州(今淮安)人,南宋抗金女将。建炎四年(1130年)其夫韩世忠在黄天荡阻击金兵,她击鼓助战,因功封安国夫人。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非空口号反对‘贤妻良母’,而是主张以尊重母职提倡母职为中心的新观念。”[28]74在当时坚持抗战、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下,必须培养更多的“新贤妻”“新良母”,动员和组织更广大的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各方面的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批“新贤妻”“新良母”涌现出来。1940年12月8日,罗琼在《驰骋在江南战场上的女战士》一文中讲到东南各省拥护参军的模范母亲和妻子,“在实际中,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当兵的故事,经常传入耳鼓”[21]413。康克清在总结3年来的华北妇女运动时,讲到不少妇女鼓励自己的兄弟和丈夫家属去参加军队,“在晋察冀,曾形成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教儿打东洋的轰轰烈烈的热潮,有一个郑老太太,亲自把三个儿子送到八路军,被誉为光荣的母亲”[11]373。晋东南和冀中的妇救会还发动了“归队运动”,反对兄弟、丈夫、儿子开小差,开小差就是家庭的耻辱。在“归队运动”中,涌现出许多模范妻子、母亲。此外,蔡畅讲到陕甘宁解放区生动的模范例子,例如“柳林区二乡的妇女从事纺织,不仅实现了她们的多生产多储蓄,妇女及其家庭生活都过得很好,而且在‘婆姨汉一条心,沙土变黄金’的体验中,增进了家庭的和睦与全村的团结”[21]652。一大批“新贤妻”“新良母”的出现,成为全民族抗战中的重要力量。
(三)妇女运动不是孤立存在的,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要统一
“妇女回家论”实质是把妇女与政治完全脱离开来的一种思潮,这种错误思潮是与现实社会情况脱节的。妇女真需要回家吗?妇女回家的环境具备吗?“希特勒上台以后不久,他的第一道命令,就要职业妇女统统回到厨房去,回到寝房去——做生育机器,做贤妻良母!……她们不但不肯回家,其实是无家可回,无从做起贤妻良母。”[30]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趋势下,妇女运动是人类解放的一部分,不能把它孤立起来,不能把它与整个人类的解放事业分开,妇女解放事业是人类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妇女要想求得自身解放和实现新的妇女生活,就必须从积极参加抗战建国的实际斗争中去努力。”[31]彭德怀写给《华北妇女》出版时的话中,讲道:“妇女解放与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是不可分离的问题,谁要是关心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谁就不能不同时关心妇女解放。”[21]494为了克服困难,缩短实现抗战胜利的过程,假使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积极参加,成功是不可能的。在认清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关系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妇女走出家庭投身于解放事业。
中国妇女运动,是伴随着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成长而向前发展进步的,且是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由于日寇的进攻与压迫,使中国妇女更深切地感觉到民族的压迫与蹂躏,大大激起了妇女的民族观念和民族仇恨。“有一些妇女,毅然决然的离开厨房,走出家庭,走上民族革命战争的战场,在炮火连天中,进行战地的服务。参加者虽只限于少数的妇女,但她们的奋勇英态,已足表现出,中国妇女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不顾一切牺牲,反对日本强盗的无上毅勇精神。”[1]11939年9月,邓颖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妇女运动》中指出,“在日本法西斯军阀疯狂的侵略下,许多妇女同胞被惨杀了、奸淫了、蹂躏了。自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给予妇女的压迫是比较减轻了,社会上曾一度高唱的‘妇女回到家庭去’的口号,被消灭了。因为妇女已失去了自己的女儿,丢掉了自己的财产,战争的环境已强迫妇女从那狭隘的家庭中走到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11]355。妇女们以英勇的姿态出现在抗战中,在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妇女们发挥着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