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山水画中景的再现
2020-12-01边凯
◇ 边凯
谈到宋代山水画的再现风格自然要涉及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宋代画家观察自然;二是宋代画家表现自然。从古代画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画家认真观察体悟自然的很多例子,《宋朝事实类苑》中介绍郭忠恕“多游岐雍宋洛间,纵酒,逢人无贵贱,常口称猫。遇山水佳处,绝粮数日不食”〔1〕。在《宋朝名画评》卷二中对范宽的日常生活描述有如:“居山林间,常危坐终日,纵目四顾,以求其趣。虽雪月之际,必徘徊凝览,以发思虑。”〔2〕对于这些画家来说,自然山水不仅是他们生活、活动的场所,也是他们观察、描摹的对象,更是他们的老师,此时的宋代山水画家对自然的观察与体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一、观察自然
以自然景物为师在宋代山水画家心中并非空谈,这些画家长时间与自然山水为伴,观察自然山水四时的变化,对自然山水的熟悉度极高,恐怕这是现代山水画家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生活与创作状态。
1.宋代山水画家观察自然的方式
我们无法得知宋之前的山水画家的观察方式,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就是宋代画家对于自然的观察极为深入。逐步成熟起来的宋代画家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自然观察方式。首先,郭熙的画论中有“学画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临其上而瞰之,则花之四面得矣。学画竹者,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于素壁之上,则竹之真形出矣。学画山水者何以异此”〔3〕?这段话可以断定此时的宋代山水画家在观察自然时具备了三维与平面两种空间意识,观察自然的方式是三维与平面相结合的方式,以及“山形步步移”“山形面面看”“朝暮之变态不同”“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郭熙在运动中把握观察对象的观察方式,正如刘继潮所谓的“目识心记”的“游观”〔4〕。这一系列完整而又具有逻辑顺序的观察方式未出现在宋代之前的画论当中。这种由远及近、由表及里以及在运动中把握观察对象的观察方式,使宋代山水画家必将得出与前代画家不一样的观察结论。这种认知方式得出的结果自然会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所体现,这也要求在分析、品读宋代山水画作品时同样要采用两种空间意识由远及近、由表及里和在运动中观看的方式来解读,因为只有在按照画家的观察方式来解读宋代山水画作品表达方式时,才能在画面中得出更为真实可信的结论。

图2 圆形(浑厚华滋)、多边形(雄健挺拔)、简化的多边形(嶙峋)
2.观察方式对宋代山水画发展的指导意义
中国画家的学习方式可能相对比较特殊,自古以来,画家都是先临摹前代大师的经典作品,在脑中建立图式概念,只有当画家脑中已有图式与眼中所见的自然景物格格不入时,画家才会选择调整或修改图式,这一过程与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中提到的图式修正理论不谋而合。画家只有通过自身的观察与体验才会发现脑中已有图式的不足,也就是说宋代山水画家的观察方式对改变已有图式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他们表现出不同于之前山水画图式的前提。宋代之前的山水画表现出的图式与风格,已经无法满足宋代画家的表达需求,这样迫使他们必须以开拓者的心态来重新审视自然与画面。今天的画家都了解创造一个相对合理可行的表现技法的难度。宋代山水画家必须对传统山水画图式做出挑战与修正,对已有的绘画习惯加以克制,才能表现出更加贴近自然山水物象的山水画。他们对自然的精微观察与体会,使画家对自然山水的视觉印象在画面中转化成连贯的形式与法则,并将其固定下来以便绘制成完整的作品。换句话说,就是将画家观察体会到的视觉经验提炼成山水画语汇,以便在画面中表现真实的自然。宋代山水画家为了表现他们所观察到的自然,在画面中做了哪些巨大的调整与修正,下面分而述之。
二、表现自然
虽然宋代之前相对可信的山水画非常少,似乎只能通过一些墓室壁画来了解宋之前的山水画,但通过这些作品还是能够想象宋代山水画家对之前的山水作品做了相当大的图式修正,从而得到今天我们眼中的宋代山水画图式。本文对于宋代山水画家表现出的对于已有图式的修正表现在三个方面:空间布局、造型、表现技法。从这三个方面来谈,宋代山水画如何通过修正已有图像进而达到更充分的表现自然物象的目的。在谈这三方面之前先须做一个简单说明,本文在“再现”部分谈及的空间布局、造型、表现技法这三方面,说明宋人试图在画面中描绘自然,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中所提出的观点,画家对于自然对象真正客观的“转录”是不存在的〔5〕。如果我们能在画面中看到或感受到艺术家有这方面的愿望,那我们就初定这种绘画是在试图“再现”自然。在宋代的不同阶段,那些开宗立派的画家对山水画再现自然的程度与侧重点确实有所不同,但整体来说,宋代山水画家对于再现自然的愿望是有的,而且画面中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在中国整个古代山水画史中,宋代山水画家对再现自然的愿望最为强烈。

图3 《溪山行旅图》中前景树中画家所暗示的多边形结构

图.4 [北宋]李成(传)《寒林骑驴图》局部

图5 《寒林骑驴图》多边形示意图

图6 《溪山行旅图》中前景山石
1.山水空间合理化的探讨
宋代山水画的布局是三维空间的幻象。以北宋全景式山水空间为例,方闻《心印》中提出在画面中出现了统一的虚拟平面,山体以虚拟平面状依次向后延伸的观点。这样在观赏者眼中形成了一种虚拟三维空间的视觉暗示,这正是《山水纯全集》中所说的“凡画全景者,山重叠覆压,咫尺重深,以近次远,或以下层叠,分布相辅,以卑次尊,各有顺序”〔6〕。
宋代虽然没有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法,但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有关山水空间合理化的探讨,只是这些设想最终在宋代山水画面中开花结果。宋代山水画家运用“平远”“高远”“深远”的朴素透视法的观察与表现手法,体现了物象与物象之间的前后关系,暗示了同一空间中物体相对合理的摆放位置。虽然画面中景物位置的布局与真实的自然山水空间中有一定的区别,而且物体所在画面中存在的角度也有不合理之处,但画面中这种空间往往与观者在游览一地区之后的感受有心理上的暗合,是对真山真水空间感受的总结,是一种类似“游后感”式的山水空间。可以说宋代山水画是对真山真水某种心里感觉上的空间意识或是某种空间记忆叠加的再现,我们可以称之为“心理上的山水空间的再现”。虽然有画家的主观因素,但画面中山水布局的产生,一定来源于对自然的观察,而且是长期观察得出的结果。当然也不排除宋代山水画家对于之前山水画在布局图式上的继承与发展,但无论怎样说宋代山水作品在布局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空间感,在中国整个古代山水画史中,最接近于自然所呈现给我们的心理状态。至少说,宋代山水画家在中国古代山水史中最有欲望表现自然山水所呈现的布局。
2.造型
宋代山水画家如果没有深厚的造型基础,是无法创造出被后世画家所敬仰的山水画的,因为深厚的造型基础是表现自然景物的前提,“以轻心挑之者,其形略而不圆,此不严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体疏率而不齐,此不恪勤之弊也”。可见宋人对自然物象形状的感觉是极其细腻的,在态度上也极其重视。

图7 [北宋] 范宽溪山行旅图轴(局部)206.3cm×103.3cm 绢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8 陕西翠华山照片

图9 [北宋] 郭熙早春图轴(局部)158.3cm×108.1cm绢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0 山西省吕梁照片

图11 [南宋]李唐万壑松风图轴(局部)188.7cm×139.8cm绢本墨笔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4 照片拍摄于福建省漳州市云洞岩景区

图15 [北宋]李成(传)茂林远岫图卷(局部)45.4cm×141.8cm绢本墨笔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16 [南宋] 无款长桥卧波图扇23.9cm×26.3cm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图17 无款江亭晚眺图扇(局部)24cm×26cm绢本设色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18 照片拍摄于北京十三陵附近的龙门湖

图19 [五代后梁至宋朝]关仝(传)秋山晚翠轴(局部)140.5cm×57.3cm绢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0 照片拍摄于太行山王莽岭上

图21 [南宋]无款溪山暮雪图轴(局部)252.5cm×139.7cm 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图22 照片拍摄于辽宁省鞍山市千山景区

图23 [北宋]范宽(传)雪景寒林图轴(局部)193.5cm×160.3cm天津博物馆藏

图24 照片拍摄于辽宁省鞍山市千山景区
(1)宋代山水画造型的特点
在整个中国古代山水画中,宋代山水画家的造型能力极高,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学者忽视。大多美术史家认为宋代山水风格的演变在于图式与绘画语言风格的演变,但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考虑,图式与绘画语言是一方面的原因,时代因素或不同画派对形状上的审美要求也是不可忽视的。对认识物象的形与表现物象的形是比较不同时期、不同画派之间绘画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形状最为直观,不同画家建立自己独特风格与语汇的基础就有着自己鲜明的造型观。
图1更能代表以上所述观点。我们将自古以来中国画最为自豪的笔墨元素去掉,只留下剪影式的图形,但依然可以感受到上面三幅作品是属于宋代哪一画派的作品,而且这种鲜明的图式让我们印象深刻,单从这种剪影的外形就可以感受到宋代山水画的再现之美。谈到这里,本文似乎产生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即以简单的类似剪影一样的图像就能分辨各个画派的主要画家的作品,而且差别是如此明显,那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宋代画家的造型并非来源于自然,并非是在画面中再现自然的结论?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一书中,引述了18世纪德国插图画家路德维希·里希特自传中的一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路德维希·里希特与三个一起在罗马学习的朋友,试图用最适于刻画物象最硬、最尖的铅笔,以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情的方式画同一幕风景,他们对每一片草、每一片叶都不肯放过,自以为是以最为客观的方式尝试在画面中真实客观地还原自然。按逻辑来说,他们四个人的作品应该是一模一样的,但当他们把完成的作品摆在一起时,四个人的作品却有非常大的差别〔7〕。这则故事提供给我们两个信息:一是自然无法真正、客观地被画家在画面中还原;二是即使画家试图再现,不同画家在画面上表现出的物象也会千差万别。这则故事佐证了宋代山水画家创造的鲜明有个性的图式来源于自然,而不是不着边际的想象,也解释了为何上面三张图片很容易被判定是哪个画派的作品这一问题。任何画家都会从自然中学习和提取他所最为钟情的部分,并非是将自然景物完全搬移到画面中(即使画家想这样做也是绝不可能的),所以自然景物与画面中的景物很自然会产生极其大的差别。
(2)宋代山水画家在画面中运用多边形来概括物象
在阅读宋代山水画论时,我们无法找到宋代山水画家有关造型的诀窍或是体现画家造型观的话语,要了解这些,我们只能从现存的宋代山水画作品中寻找答案。
从现存的大量山水画图像中,我们可以得出宋代山水画家大都喜用多边形进行状物的这个结论。多边形的表达方式比起汉唐时期的圆形更有助于表达自然界中的物象,这种方式增加了表现物象细节的可能性。我们看到的早期出土的一些汉唐时期的墓室山水画中的细节,接近自然真正状态的刻画很少,大多是对某种山水意象的表述,或是偏向于想象化的符号化元素的叠加。宋代山水画中山水元素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然物象更为接近,这一方面是与观察自然、表现自然的能力提高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这个时期对表达画面中物象形状的准确度的要求有很大关系。如图2所示,用简易的勾勒能看出不同时期对表现山体所使用的不同形状。多边形状物的特点不同时期对于画面中形状的选择,又体现了不同时期画家对于审美的不同追求,所描绘单个形体的造型由汉唐时期表现浑厚华滋的圆形,逐渐演化成了更有助于表达自然界物象的多边形,这种转变使得山体具有了石质的坚硬感,同时也使北宋早期北派山水变得雄健挺拔,物象更具体量感。从北宋晚期到南宋这段时期的画家喜欢运用相对简化的多边形表现物象,这种形状也使得画中的物象更能够体现作者的主观性格。形状上的转变是画家主动的行为,但宋代山水画家所选择的这种多边形作为表达景物的手段有助于表达物象的细节,有助于画中的山水元素表现更为细节化的自然物象,达到画面更接近自然物象的目的。
以范宽《溪山行旅图》中的一棵树的主干为例,多边形外形的主干很自然地使观者联想到一系列多边形在树干内部空间的组合。如图3,这与宋代之前出现的圆柱形树干相比,宋代山水画的单个物体的丰富程度大大增强。再加上画家对树干的皴擦,其复杂度不言而喻,相比之前山水作品的局部,毫无疑问更接近于我们眼中所见的自然景物。此外这种采用多边形集合的方式来表达物象,不仅对于单个物象表述得更为准确和深入,而且更能够唤起观者的视觉记忆。由于宋代各个画派表现的地域地貌的不同,这种准确度的提高也使得宋代山水画各流派之间单个山水元素的差别变得更大,各个画派都能够相对准确的表现画面中具有各个画派特点的代表性的山水元素。这就是宋代山水画家能在统一的审美价值观下创造出不同流派与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平面空间外,宋代山水画采用多边形与多边形的叠加来表现自然界中单个物体空间的复杂性。
以图4传为李成的《寒林骑驴图》中的树头为例,虬龙一般的树枝从主干向空间四周伸展,在这张平面的绘画作品上表现出了树的枝干之间错综复杂的叠加,从二维的角度观看图4,图中的松树具有统一、完整且优雅的平面造型。再来看图5。图5为《骑驴寒林图》简易的示意图,我们可以将画家设置的三维幻象看得更为清楚,将这棵松树的不同枝杈整理成简单的多边形时,会发现多边形在空间中的分布状态,这种穿插叠压比宋代之前的山水画表现的树木简化“伸臂布指”的平面表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种画家对于物象在三维空间中的思考与暗示,以及物体的复杂性与表现的深入度,很自然地使观者在自己的三维视觉经验记忆中搜索。这样的图像比较倾向于三维的视觉幻象的图像,无疑比之前的单纯二维图像的表达显得更为可信。将平面与空间两种造型观念容于单个物象的表述,符合上文提到的画家观察自然的方式。这两种表达方式的成功运用使画面再现风格的形成变为可能。这种视觉图像的建立也为观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三维空间幻象,不会被单个物体展示的单纯二维平面图像阻止,而是不知不觉间被画面吸引,思绪可在画中任意游走。

图25 [南宋]马远踏歌图轴(局部)191.8cm×104.5cm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图26 照片拍摄于安徽九华山莲花峰附近

图27 [南宋]李唐清溪渔隐图卷25.2cm×144.7cm绢本墨笔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8 照片拍摄于南雁荡山会文殊院山下

图29 佚名 寒鸦图卷27.1cm×117.2cm绢本设色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30 照片拍摄于辽宁省凤凰市凤凰山下

图31 [南宋]李迪雪中归牧图页24.1cm×23.4cm绢本设色日本大和文华馆藏

图32 照片拍摄于北京大觉寺附近

图33 [北宋]李成(传)群峰霁雪图轴77.3cm×31.6cm绢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34 照片拍摄于辽宁省辽阳市庆阳南场附近
3.技法
宋代山水再现风格的形成与新技法的出现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此时的山水画表现技巧趋于成熟,画家可以以一种相对自由的状态来创作山水画。但笔墨技巧是需要画家一生不断练习与改进的,只有当娴熟的技巧与画者本人的精神融为一体时,才能做到庄子所说的“得之心,符之手”。画者只有“心手相应”才能将自己的精神从技巧的层面中解脱出来,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1)宋代山水画技法的发展
山水画绘画技法经过长期酝酿,五代时已经基本成熟,宋代是成熟之后的又一次大发展。技法在宋代又一次发展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对五代和之前优秀绘画技法的传承;二是宋人重造化、重自然,不断从自然中汲取绘画元素和感悟的结果。宋代的优秀画家们已经具备了描写真山真水的能力,他们的技法并不花哨,优秀作品中几乎都体现出一种朴素而娴熟的绘画技巧。这种技巧是由于画家渴望画面比前代作品更真实自然而产生的,画家并没有留恋这些技法本身,而是将这种技法还原到原始目的上。这正是荆浩所说的“可忘笔墨,而有真景”〔8〕的绘画状态。这种技巧的朴素性也体现宋代山水画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上。宋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间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契合点,即人与自然处于平等的关系,朴素的技巧体现了宋代山水画家并非试图凌驾于自然之上,他们创造的画面与自然的关系平等。
(2)笔墨表现物象的能力增强
由于对物象造型写实要求的提高,从五代以来,画家对笔墨表现自然的可能性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以山石为例,较之前代的山水画,宋代山水画家在勾勒时更注重山石的起伏、转折,对表现裂缝及同一块山体中石块之间组合的合理性要求的刻画相比前代画家有很大的提高。以图6中范宽《溪山行旅图》前景的石头为例,画家用刀劈斧凿一般的笔墨表现山石的坚硬感,又运用笔的提按来表现石块不同面的转折,充分运用了线条的粗细变化来表现山石的形体与结构。例如在画面中区分多个物体的外轮廓线明显强于单个物体内部的结构线,山体立面的线条明显强于平面的线条,这样就不仅表现了山石自身的体块,同时又表现出受光照下的山石状态。我们可以在作品中感受到极具逻辑感的笔墨秩序,感受到宋代作品中笔墨秩序的合理性。同时画家在勾勒时“用焦墨,用宿墨,用退墨,用埃墨,不一而足,不一而得”〔9〕,使画面中的物象更丰富。为了表现物象时提高准确度,画家使用各种毛笔,配合各种墨色的变化,使画中景物呈现出不同自然状态下应有的状态,“用浓墨、焦墨欲特然取其限界,非浓与焦则松稜石角不瞭然故尔,瞭然然后用青墨水重叠过之,即墨色分明,常如雾露中出也”〔10〕。通过郭熙在画论中的描述,用这种墨法与水法交融产生在画面中层次丰富的浓淡变化来表现雾中的景物,可见在宋代,笔墨形式已经可以对不同气候状态下的自然山水状态进行表述,而且对笔墨状物的认知度也在不断深入,这种随着状物功能不断深化发展起来的笔墨技巧没有停滞,一直在发展。

图35 [五代]巨然层岩丛树图轴144.1cm×55.4cm绢本墨笔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36 照片拍摄于天台山真觉寺附近

图37 [宋]夏圭山水十二景卷(局部)27.9cm×230.5cm绢本墨笔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馆藏

图38 照片拍摄于天台山真觉寺附近

图39 [北宋]李唐万壑松风图轴188.7cm×139.8cm绢本墨笔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40 照片拍摄于九华山华严寺附近

图41 [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轴(局部)206.3cm×103.3cm绢本墨笔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42 照片拍摄于南雁荡山五色杜鹃林

图43 [南宋]李唐万壑松风图轴(局部)188.7cm×139.8cm绢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44 照片拍摄于天台山琼台仙谷
(3)皴法的普遍运用与发展
宋代山水画发展进入繁荣期的一个标志,就是出现了大量表现不同地域风貌的作品,并且这种表现地域性的山水画语汇显得更为明确,更容易激发观者的视觉感受,使观者对于外在自然的情感性审美体验被画面中力求真实的情境再现调动,皴法的多样性在画面中大量的运用使得画面更具真实感。
皴法在唐代山水作品中的运用已见雏形,宋代山水画家将皴法的状物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林泉高致》中写到“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这句话中的“质”在我们看来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山石的质地,一个是山石的本质,在此处我们将“质”解释为质地。在宋代山水画作品中,用皴来表现山体的质地是画家对绘画语言的探索,这极大拓展了笔墨对表现不同地域特征的可能性。《益州名画录》中最早记载了这种山水画技法:“居宝以笔端摤攃上七赏反,上七赏反,下七葛反。文理纵横夹杂,砂石棱角峭硬,如虬虎将踊,厥状非一也。”〔11〕皴法的运用使宋代山水画中单个物体更具质感,使画面中单个物体的复杂度大大增加。比起前代“空勾无皴”的山水画,宋代山水画中的单个元素显得更为真实、更为完整,也更具说服力。此外,皴还有填充画面、增强画面节奏的作用,皴法在画面中物体内部结构的强度,还起到抵消了一部分外轮廓线强度的作用,使画面中的物体呈现出块面状,增强了画面中物体的重量感与体块感,大大增加了画面中单个物象的再现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画家在画面创作过程中对皴法的组织非常灵活,不是刻板僵硬的符号。试想一下,在运用皴法时,看似最为不灵动的北宋山水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中的皴法也是极具变化的,如图6画家运用雨点皴的长短、疏密、干湿浓淡,以及流淌的水渍等变化来营造画面中山体主峰的质感、量感及光感。北宋时期各家的皴法并没有完全固定下来,画家往往是根据画面中表现物象的需要来不断地调整与探索。正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到的笔法与墨法的多样性,画家主动运用各类皴法、墨法、水法相互组合,从而使画面中的物体更接近自然界物象。证明这一点的最好证据,就是当我们真正临摹北宋那几张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时,会发现原本我们心目中各种相对统一的皴法在画面中变化百出,甚至有些被眼花缭乱的画面处理所替代,很难找到明清作品中笔笔生发的绘画状态的有效秩序。画面中看似有序实则这种秩序又无处可寻的绘画状态正是宋代画家对于造化的真正意义上的解读。
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将山分为了“石质”与“土质”两种质地的山体。“山有戴土,山有戴石。土山戴石,林木瘦耸;石山戴土,林木肥茂。木有在山,木有在水。在山者,土厚之处有千尺之。”〔12〕依据郭熙划分的自然地貌我们在宋代作品中也能找到相应的例子。
如图7北宋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局部中,运用了豆瓣皴、雨点皴等技法来表现光照射在秦岭一带白色的花岗岩山体上所呈现的效果,这种效果与图8带给观者的视觉感受是极为相似的。范宽将关陕一带的山石地貌特征提炼成的雨点皴是再现这一地貌特征的成功范例。同为北宋山水画家的王诜对其有过极高的评价:“如面前真列峰峦,浑厚气壮雄逸,笔力老健。”
图9郭熙《早春图》山石的局部图中,所使用的水墨淋漓的卷云皴,正如图10所展现的那样,是表现当时黄土高原一带土石相间、土质肥沃且质地蓬松状态的非常贴切的表现形式。
图11中李唐在《万壑松风图》所使用的斧劈皴,正是描绘山西河南交界一带太行山地貌特征的最好表述(图12)。李唐通过一系列大小斧劈皴的组合与朝向的变化,使得山石的整体量感与受光后凹凸不平的表面状态跃然纸上,观者仿佛是在极近的距离观看山体的每一处表面。
对于皴法这种山水语汇的发展并非到北宋末期就结束了。南宋时期,画家还在不断地探索各种皴法,如马远的大斧劈皴。单纯从绘画符号的角度讲,这种皴法是李唐创造的斧劈皴的变种,但大斧劈皴的长度远远长于李唐使用的斧劈皴。方闻先生在他的《心印》与《超越再现》中都认为,南宋的这种具有代表性的皴法完全延续了北宋的山水语汇,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可能就会得出更为可信的答案,图13马远《踏歌图》中前景的巨石与右面照片中(图14)的山石相比较,可以看出马远表现画面中的山石不再是《万壑松风图》中太行山区岩石表面凹凸不平的山崖,而是雨后一种表面极为光滑而外形棱角鲜明的山体,在马远画面中的大斧劈皴的作用就从李唐表现山体凹凸起伏变为了表现光滑且湿漉漉的山石表面上被雨水长时间冲刷后留在山石表面的痕迹。即使马远延续了李唐的这种语汇,但这种皴法还是继续有所发展的。南宋的山水画家往往是将北宋时期创造的皴法在画面中进行继承与修正,进而表现出同一种皴法的不同功能,使北宋晚期逐渐被各派固定下来的山水语汇再次被激活。在宋代,画家对山水语汇的探索一直在进行中,从未停止。此外还有夏圭使用的拖泥带水皴,更是将李唐的皴法继续发展的一个绝佳范例,画家通过对于水的大量使用,使得看似来源于李唐、马远的大斧披皴变为了表现湿润空气中山石不同块面朝向的方法,这同样是对已有皴法在画面中的再定义。宋代时期这一系列皴法发展的形成,标志着宋代山水独立绘画语言的成熟,而且在真正的宋代山水画大师手中并没有固定和僵化,这也说明在宋代,那些开宗立派的画家们不仅向前辈学习,还能够通过自己的眼睛向自然山水学习,不断地调整画面中的绘画语言,使之能够表现他们认知的自然世界。在这一点上,宋代山水画家有着强烈的愿望与冲动。

图45 [北宋]郭熙窠石平远图轴(局部)120.8cm×167.7cm绢本墨笔故宫博物院藏

图46 照片拍摄于温州附近的永嘉县林坑村

图47 [南宋]米友仁潇湘图卷(局部)28.5cm×296.7cm纸本墨笔上海博物馆藏

图48 照片拍摄于九华山金刚寺附近

图49 [南宋]马远(传)山水舟游图轴127.5cm×85.2cm绢本设色大英博物馆藏

图50 照片拍摄于陕西吕梁山碛口,碛口客栈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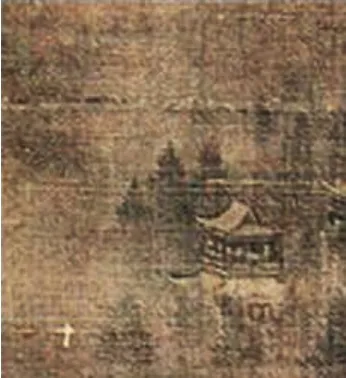
图51 [北宋]翟院深(传)雪山归猎图轴155cm×99cm绢本墨笔安徽省歙县博物馆藏

图52 照片拍摄于武当山雷神洞附近
(4)渲染
渲染并不是宋代山水画特有的技法,但在整个古代山水史中对画面进行渲染最多、画面层次最为丰富的作品当首推宋代山水画。而且渲染在画面中大量的运用,也是成就宋代山水画再现自然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在宋代山水画作品中,画面传达的情致无论是强而有力的明快,还是低沉委婉的忧郁,都蕴含着精致、细腻的心理感受,这种画面气氛的营造与宋代山水画家不厌其烦的渲染是分不开的。从表现山体自身体量感、山石质地、固有色方面说,宋代早期的一些山水画的皴法与渲染在表现山石时是很难区分的。以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传为燕文贵的《茂林远岫图》〔13〕为例,乍看之下会感觉此图的局部不太清楚,但在观看原作时也会发现很难区分出作者在进行山体的刻画时哪里是皴、哪里是染。这种不容易区分皴与染的描绘山体质地的方式,在“李郭画派”与南宋夏圭的作品中的运用表现得更为突出,“李郭画派”所使用的卷云皴、拖泥带水皴就是皴法与染法结合的一种方式。从这一点来看,染与皴一样,是塑造物象有力的方式之一。
宋代山水画表现空间的纵深感,首先依靠相对合理化的空间布局与用笔的轻重变化,其次画家往往依靠物体与物体上的微妙色差,这种物象之间的色差主要是由宋代山水画家层层渲染而得。宋代作品中用水反复“淋之”“渲之”不露笔墨痕迹的染法,对于表现真实的、具有空气流动感的画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将原本坚实突起的物象包裹上一层淡淡的空气,使物象退回到画面中本该属于他的空间之中。郭熙画中通过大面积渲染得到的“早气如蒸”的相对真实的空间感与空气感是宋代山水作品区分于宋之前装饰性山水画作品明显的特点之一。南宋的山水画面中对于渲染的使用就显得更加精微。由于画面中空间布局的需要及南宋山水画诗意性空间的表述,需要通过画面中大面积的天空与水汽渲染来完成,渲染就成为表达画面沁人心脾的江南湿润空气有效的表现手段之一。南宋院体画家马远在表现烟树、远水等雾气笼罩下的景象时,也是通过水接墨,而后通染的方式完成的。
此外,宋代山水画家还通过染来表现自然界中光的效果,如清晨的微光、中午的强光、日暮时分的霞光、夜晚的月光等等。这些都出现在宋代的作品之中。宋代山水画家们关注了这些光的变化,通过在画面中大面积的渲染,使光的描绘成为宋代山水画作品中表现自然的手段之一。
沈括描写董源的《落照图》没有传世,但从上面图16这幅南宋团扇《长桥卧波图》中仍然能够感受到沈括描写山体的“反照之色”。画家将画面中除远山以外的所有地方都进行了大面积的渲染,使画面中的远山呈现出了日暮时分,夕阳余晖照在山体上的效果。从图17这张《江亭晚眺图》局部与照片图18对比,我们能够感受到画家描绘自然界傍晚时分湖光山色的效果非常贴切。在《江亭晚眺图》中,画家主动将日暮时的山体与周围天空染暗,留出波光粼粼的湖面。我们会发现图17、图18湖面与山体的黑白对比度关系非常相似。由于光线的原因,两幅图片中的景物都呈现剪影状,画家将光线集中于湖面远处,而将近处湖面用淡墨层层渲染以获得傍晚时分湖面受光的真实感。可见,画家通过渲染达到对光线的描绘,以便表现自然界某一特定时间段的山水状态。

图53 Jang Scarlett 在《Realm of the Immortals-Paintings Decorating the Jade Hall of the Northern Song》一文中还原的1082年玉堂内的场景
三、宋代山水画再现风格的具体表现
1.宋代山水画作品局部与照片的对比图
如果上面对于空间、形状、笔墨技巧的论述不足以说明宋代作品有再现自然倾向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对宋代山水画作品的局部与自然界真实的风景比较,从而得出更为真实可信的结论。通过下面一系列作品的局部与照片的对比,我们能够更为肯定的是宋代山水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拥有超过我们想象的亲近度。图19图52“成对”图中左侧是一些宋代作品局部,右侧的照片是我在写生过程中拍摄到的自然界风景照片。
(1)山石对比图:见图19 图28。
(2)树木对比图:见图29 图38。
(3)水口对比图:见图39 图46。
(4)烟云对比图:见图47 图52。
2.“再现”在画面中的范围界定
上面一系列图片展示画中局部与自然界中的景物拥有非常大的相似度,我们可以肯定说画家在画面的局部表现中也确实有着再现自然的某种愿望,并不代表宋代画家所画的就是照片中当时当地的风景,但也足以说明宋代山水画家在画面中表现的物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能够唤起观者的视觉经验,而且这种相似程度似乎超过了以往我们对宋代山水作品再现自然的程度界定。这一系列作品中的局部与真实自然照片的图片比较说明宋代画家如果没有认真观察与体悟自然,以及上面提到的画家再现自然能力的提高,就无法如此贴切地在画面中表现自然景物元素。如果说北宋早期的全景式山水空间是对唐代以来山水空间布局的继承与发展,那么五代、北宋初年的山水画家对整个山水画史最大的贡献就是画面中局部山水元素的写实性再现,这种局部的写实性再现给宋代山水作品带来的是全新的视觉感受,一种在中国古代山水画史中最为接近自然的真实再现之感。宋代山水画家在画面元素中表现的真实度与复杂度是宋代山水画作品再现风格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宋代山水画再现风格区别于中国美术史中其他时期山水作品再现风格的一个非常大的标志之一。图53是JangScarlett还原的1082年北宋翰林学院聚会之地玉堂内的景象,我们可以通过上面这张图片展开想象,对宋代山水画作品完成后还原到他的展示空间进行讨论,进而得出宋代画家对画面整体氛围是否有再现自然的倾向。当观者走进这间由巨大的山水画作品装饰的房间时,会感到墙壁隔离室外与室内的功能似乎消失了,观者被董羽所画的瀛洲巨大的海面环绕,置身其间的观者一定会被周围这些具有自然之美的作品所震撼。仙境近在咫尺,这种画面与整体展示空间的空间布局一定,可以唤起观者对自然界真实的视觉感知。通过这幅简易的宋代室内效果图,不禁让人想起宗炳的名句“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14〕。我们无法得知董羽是如何在公元980年到983年间画出这一组巨大的山水作品的,但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当时画家对画面中局部的再现能力是非常强的,再加之整体画面在展示空间的摆设方式很容易就能唤起观者的自然视觉经验。雇佣董羽来作画的出资人代表着宋代宫廷乃至整个社会大的审美的趣味,从被装饰在墙面的巨大作品我们可以想象到这种审美要求在当时一定有着再现自然之美的愿望。我相信,被画面装饰的墙面的不仅能够唤起观者对自然界已有的视觉经验,更能唤起观者对美好景致的向往之心,同时我也相信这种观赏感受一定能够打破“似与真”的界限,画面中的内部世界必将转变为观赏者内心世界记忆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得出一个比较肯定的结论,就是宋代山水画家不仅有着对画面中山水局部的再现的愿望,而且他们已经具有了一整套相对完备的表现自然的方法来达成这种愿望。此外,宋代山水画所展现出的整体氛围也拥有与观者直接交流的那种再现自然的“卧游”功能,使观者能够感觉到仿佛置身于真实自然之中的错觉,这也正是宋代山水画的再现风格的完整表述。通过图53的例子,我们也能在宋代山水画作品中找到同样的答案,那就是画家与出资人似乎对山水画作品单纯的表达自然之美还不够满意,画中的山水还要像仙境一样是理想的、完美的,而且还要加入画家自身的情感与想象。对宋代画家而言,自然界是不完美的,完美的山水只存在于他们的心中。
注释:
〔1〕 [宋]江少虞撰:《宋朝事实类苑·卷第四十三·仙释僧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10 月版,第571 页。
〔2〕 [宋]刘道醇著:《宋朝名画评·山水林木门第二》,引自潘运告编著,云告译注《宋人画评》,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 年10 月第2 版,第57 页。
〔3〕 [宋]郭熙、郭思撰:《林泉高致·集·山水训》,引自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修订版(下),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年版,第634 页。
〔4〕 刘继潮著:《游观:中国古典绘画空间本体诠释》,北京:三联书店2011 年1 月第1 版,第154 页。
〔5〕 [英]贡布里希著,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译:《艺术与错觉》,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年4 月版,第59 页。
〔6〕 [宋]韩拙撰:《山水纯全集》,引自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修订版(下),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年版,第665 页。
〔7〕 前揭《艺术与错觉》,第44 页。
〔8〕 [五代]荆浩撰:《山水·笔法记》,引自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修订版(下),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年版,第609 页。
〔9〕 〔12〕 [宋]郭熙、郭思撰:《林泉高致·集·画诀》,引自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修订版(下),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年版,第643 页。
〔10〕 同上,第644 页。
〔11〕 [宋]黄休复撰:《益州名画录·卷中·妙格下品十一人·黄居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12 月版,第71 页。
〔13〕 《茂林远岫图》在《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中专家一致认为是北宋的作品。傅熹年认为:跋真,原画明代已佚,以另一北宋画裁割上下,以配原跋。可见,《茂林远岫图》虽然可能不是李成的真迹,但对于研究北宋早期的山水画技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4〕 [梁]沈约撰:《宋书·第八册卷九十三·列传第五十三》,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74 年10 月版,第227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