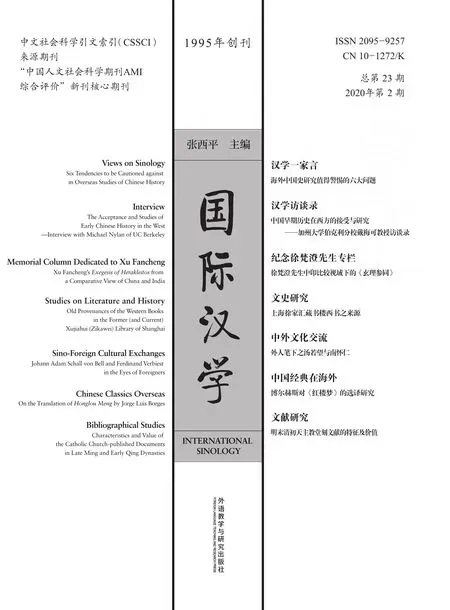明末清初天主教堂刻文献的特征及价值*
2020-11-30王申
王 申
堂刻文献(1)堂刻文献的数据来自《天学初函》《天主教东传文献》《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东传福音》、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收录的堂刻文献影印本的牌记信息以及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据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目录,重新校订补录的《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法]伯希和编,高田时雄校订、补编,郭可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该目录还吸收了古兰[Maurice Courant,1865—1935]、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斯达理(Giovanni Stary)和王重民等人撰写的目录成果)、陈纶绪(Albert Chan,1915—2005)《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文书籍和资料(日本 - 中国卷1—4) :目录和介绍》(Albert Chan,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Japonica-Sinica I—IV,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New York City: M. E. Sharpe, 2002)和CCT-Database 电子数据库。需要指出的是,出版信息来自这些文献的部分,除个别需要特别说明外,均不再标明出自哪一册,读者可借助相关目录查询。肇始于明末,发展于清初,赓续至民国,主要指基督教(天主教)在教堂及会院刊刻的文献。因其牌记通常署“某某堂”梓刻,故称之为堂刻文献。堂刻文献内容涉及宗教、人文和科技诸方面,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天主教传播史和中国出版史等领域均应有重要地位。不足的是,既往研究仅有张秀民注意到北京南堂的刻书,(2)张秀民:《明代北京的刻书》,《文献》1979 年第1 期,第298—309 页。何朝晖介绍了部分教堂的刊刻情况,(3)何朝晖:《明清间天主教文献出版的演变》,《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4 期,第136—147 页;何朝晖:《论晚明至鸦片战争前天学文献的刊刻出版》,载赵克生主编《第三届“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16—30 页。堂刻文献的基本情况、特点和价值尚未见系统探讨。本文讨论的堂刻文献是以明末清初天主教在教堂或会院刊刻的关于西方学术、宗教和中西文化比较的文献为中心,清末和民国时期堂刻文献情况待它文再述。
一、堂刻文献的概况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常采用书籍传教的方法,结交国人,传播天主教。传教士在华编刊有汉文、满文和蒙文的文献,其中,教堂刊刻的主要是汉文文献。目前所知天主教会在中国大陆刊刻的第一份汉文文献是《祖传天主十诫》,约刊刻于1583—1584 年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称:“鉴于很多人来向神父们问道,并对他们自己的宗教产生了一些疑问,神父们便把《天主十诫》译成了中文,交付刊印,提供给前来问道的人们,告诫他们要遵行这些戒律,因为它们都极为符合真理与自然法则。”(1)利玛窦著,文铮译,梅欧金(Eugenio Menegon)校:《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102 页。影印本《天主实录》后所附《祖传天主十诫》《天主经》和《圣母经》(2)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 Dudink)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台北:利氏学社,2002 年,第 84—85 页。,字体、板式与《天主实录》明显不同,可见并非刊刻于同时。利玛窦1584 年9 月13 日致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Giambattista Roma,生卒年不详)的信中称:“我们已印刷了中文的《天主经》《圣母经》和《天主十诫》。”(3)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57 页。利玛窦1584 年11 月30 日致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Claudio Acquaviva,1543—1615)的信中称:“我们同时也把‘十诫、天主经、圣母经’的中文译本寄给您。”(4)同上,第60 页。罗 明 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天主实录》后所附者,虽未题《天主经》《圣母经》,但前半部分是拜告“圣母娘娘”,后半部分是拜告“大父”,应该就是利玛窦所称的《圣母经》和《天主经》。由此可推断,《祖传天主十诫》等极可能是现存最早的在中国大陆刊刻的天主教文献。(5)陈拓:《求其友声:明末清初汉文天主教文献序跋中的中西互动》,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
明末,杭州的天主教教堂建立了刊刻系统。根据堂刻文献的牌记,“慎修堂”梓刻《畸人十篇》附《西琴曲意》《灵言蠡勺》和《教要解略》,“昭事堂”刻有《进呈书像》,“超性堂”刻《圣人行实》《与弥撒功程》《天主圣教念经总牍》《天主圣教约言》《西方答问》《天神会课》和《天主降生引义》。此外,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CHINOIS 7046 的文献中收有“浙江杭州府天主堂刊书版”目录,载有40 种文献,均为杭州天主堂刊刻。
北京“领报堂”刻有《三山论学》《畸人十篇》《七克》和《圣母行实》,“天主堂”刻有《司铎典要》和《超性学要》,“宣武门天主堂”刻有《涤罪正规》和《出像经解》,“金台景教堂”刻有《天主经解》《圣母经解》和《涤罪正规略》,“首善堂”刻有《圣体仁爱经规条》《万物真原》《济美篇》《德行谱》《天神规课》《性理真诠》《涤罪正规略》《天神会课》和《哀矜行诠》,“圣母领报会”刻有《畸人十篇》,“始胎大堂”刻有《七克》《天主降生言行记略》和《圣母行实》,“皇城堂”刻有《真道自证》,“仁爱圣所”刻有《朋来集说》《盛世刍荛》和《圣经广益》。明末清初,北京有东西南北四堂,北堂(西什库教堂)居西安门内,《圣经广益》牌记署有“皇城西安门内首善堂仁爱圣所藏板”,可知上述“首善堂”“皇城堂”和“仁爱圣所”同指北堂;南堂又名领报堂、京都始胎大堂,居宣武门,上述“领报堂”“宣武门天主堂”“始胎大堂”“圣母领报会”“金台景教堂”应指此处;而“天主堂”似是泛称。由此可知,北堂和南堂是天主教在北京的主要刊刻场所。
福建的“福州钦一堂”刻有《西学凡》《圣梦歌》和《二十五言》,又据法国国家图书馆CHINOIS 7046“福建福州府钦一堂刊书板目”,福州钦一堂刊刻文献有51 种。“福州景教堂”刻有《圣母行实》和《大西利西泰子传》,“闽景教堂”刻有《教要解略》,“晋江景教堂”刻有《降生言行纪略》《西方答问》《代疑续篇》和《天主降生出像经解》,“清漳景教堂”刻有《实义续篇》,“闽中景教堂”刻有《弥撒祭义》《十慰》《则圣十篇》《涤罪正规》《几何要法》和《三山论学》,“三山景教堂”刻有《圣记百言》,“敕建闽中天主堂”刻有《性学觕述》《圣若撒法行实》和《五十余言》,“闽中天主堂”刻有《三山论学》,“闽福州府玫瑰堂”刻有《圣女罗洒行实》和“闽三山怀德堂”刻有《天主圣教要理》。其中,“闽福州府玫瑰堂”和“闵三山怀德堂”分属多明我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其他均为耶稣会的教堂。在福建,耶稣会刊刻文献的牌记多署“天主堂”和“景教堂”之类的泛称,难以辨别哪些是同堂异称,这为文献所属教堂的认定带来困难。
广东耶稣会的“大原堂”刻有《圣母行实》《妄推吉凶辩》《妄占辩》《天神会课》和《万物真原》,“全能堂”刻有《天主圣教日课》,“粤东天主堂”刻有《真福直指》和《天主圣教略说》,“横浦翼翼堂”刻有《告解四要》和《领圣体紧要》;方济各会的“朝天路教堂”刻有《永福天衢》和《进教领洗捷录》,“杨仁里福音堂”刻有《涤罪正规》《成人要集》《万物本末约言》《圣父方济各行实》《天主十诫劝论圣迹》和《圣教要训》,另有“广东圣方济各会堂书版目录”(1)叶尊孝(Brollo Basilio,1648—1704) :《字汇腊丁略解》,梵蒂冈图书馆藏Vat.Estr.Or.2,转引自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第186 页。载有23 种文献。奥思定会在肇庆的“真原堂”刻有《要经略解》《圣教切要》和《四终略意》。由此可知,不仅耶稣会,广东的方济各会和奥思定会的教堂亦刊刻不少文献。
绛州的“景教堂”刻有《修身西学》《齐家西学》《三山论学记》《圣梦歌》和《神鬼正纪》。松江的“敬一堂”刻有《坤舆格致略说》《圣若瑟行实》《(圣母领报会)显相十五端玫瑰经》《四末真论》《天主圣教撮言》《圣记百言》《天主圣教百问答》和《圣教问答指掌》,另《求说》的牌记署有“云间天主堂梓”,似应指“敬一堂”,“天主堂”为泛称。七宝的“圣多明我堂”刻有《天神会课》。常熟的“天主堂”刻有《提正编》。苏州的“大原堂”刻有《真福八端》。湖北的“郢天主堂”刻有《圣洗规仪》、“郢钦一堂”刻有《天主圣教四字经文》和《涤罪正规》以及“楚中钦一堂”刻有《教要序论》和《天主圣教约言》。济南的“天衢堂”刻有《总牍·五伤圣方济各祷文》《正学谬石》《圣方济各第三会会规》《圣伯多禄亚甘太辣祝文》《圣人文度辣赞圣人安多尼祝文》《圣若瑟七苦乐文》,“补儒堂”刻有《默想神功》,根据何朝晖的研究,“天衢堂”和“补儒堂”为同一教堂。(2)《论晚明至鸦片战争前天学文献的刊刻出版》,第24 页。江西的“钦一堂”刻有《天主圣教四字经文》,“曰旦堂”刻有《善终助功规例》和《天学蒙引》,另“南昌天主堂”刻有《默想神功》,此处“天主堂”似为泛称。长溪天主堂刻有《形神实义》。南京的“正学堂”刻有《涤罪正规略》。
由上可知,明末清初天主教会在杭州、福建、北京、广东、绛州、上海、江西以及湖北等地的教堂均有刊刻活动,其中,杭州、福建和北京的教堂刊刻数量较多,这与传教士在华的活动范围和中国传统刊刻文化发达所在基本一致。这说明天主教的刊刻活动受到传教需要和中国出版文化的双重影响。
二、堂刻文献的基本特征
堂刻文献在天主教会刊刻的文献中占据主导地位。与官刻、私刻和坊刻等其他形式刊刻的汉文西学文献相比,既有共同点,又有显著特征。这些文献是中西人士合作完成的,一般是对欧语文献的翻译,而且拥有独立的编辑刊刻发售网络。然而,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刊刻,传教士的传教使命决定了大部分堂刻文献题材和内容的宗教属性。由于传教士传教策略的差异性,不同修会的堂刻文献具有不同特征。
同汉文西学文献的其他刊刻形式一样,堂刻文献的编辑采用传教士独撰、传教士口授国人笔译国人独著、国人撰写传教士指正的形式,大部分文献有序、跋、引,序跋多为有一定名望的国人所作,用来抬升作品的地位。“引”是作者为文献做的介绍。国人参与文献的编辑主要集中在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福建和陕西。较为著名的有被称为“天主教三柱石”的徐光启、杨廷筠和李之藻,陕西的韩霖和韩云、段衮和段袭兄弟。他们大致靠同年进士、宗族、姻亲和师生的关系联络,成为堂刻文献的编辑文人群体。如杨廷筠、冯应京、曹于汴、苏茂相和陈民志同为万历二十年进士;李之藻、吕图南、祁光宗和张维枢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徐光启、刘胤昌、周炳谟、樊良枢、王家植和张京元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在宗族、姻亲和师生关系中,上海的徐光启家族、陕西绛州的韩氏和段氏家族都极力支持文献的编刊;徐光启的姻亲许乐善和他的学生孙元化也助力文献的编刊。因此,通过传统的人际网络,天主教建构了堂刻文献的编辑群体,他们亦可被称为早期的译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天主教徒,推动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客观上,他们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在西学与中学的融合中起着筚路蓝缕的先锋作用。
除文献翻译编辑外,堂刻文献还建立了独立的刊刻发售网络。明末,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福建和北京等地都有成体系的印刷网络。来华传教士发现将天主教的教理和教义刊刻成书不仅便利,还可弥补传教人手的不足。利玛窦在书信中写道:“刻板在我们会院中,是我们所有,只费些纸印刷罢了。我们中有的会印刷,有的会装订。有教友,也有教外人捐献纸张,以便印刷要理问答和我们其他的著作。”(1)《利玛窦书信集》,第279 页。有时,编撰文献也在教堂,利玛窦《西国记法》的序署有“东雍晚学朱鼎浣书于景教堂”,说明朱鼎浣在教堂中为该书作序。各个教堂之间的刻板是共享的,有时会运输到异地教堂翻刻,潘国光(Francesco Brancati,1607—1671)《天神会课》署有“武林超性堂藏版,七宝圣多明我堂刊”,说明刻板在杭州,在松江七宝刊刻。可见,教堂既是天主教会刊刻文献的机构,又是文献编撰和传播的场所,在天主教文献的刊刻和传播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就题材和内容而言,堂刻文献具有特殊性。按照现代的学科分类,汉文西学文献的内容可分为宗教、人文和科技,堂刻文献也包含这些类别。事实上,很多以人文和科技为主的作品亦有不少宗教思想杂糅其中。传教士刊刻的文献内容与其处境有一定关联。杭州、福建和北京教堂刊刻的文献以宗教为主,辅以人文和科技文献,人文和科技文献的刊刻时间主要在明末,这时传教士的传教对象主要是士大夫阶层,借人文和科技等致用之学走上层路线,期待赢得高层知识分子的好感。广东的教堂主要刊刻宗教文献,这与清初传教士被驱除至广东,传教活动转入地下有关。官刻、家刻和私刻的汉文西学文献,国人的选择权更重些,刊刻的主要是人文和科技类文献,如官刻《崇祯历书》。据“清代内府刻书总目录”,清代官刻的汉文西学文献有《御制数理精蕴》《御制历象考成后编》《钦定仪象考成》《钦定仪象考成续编》《新制仪象图》《西洋新法历书》(30 种)、《新法历书》(26 种)、《新法历书》(7 种)、《律吕正义》(四卷)、《律吕正义》(五卷)、《律吕正义》(六卷)、《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一百二十卷)、《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十二卷,其中九卷至十二卷为抄本)。(2)翁连溪编著:《清代内府刻书图录·清代内府刻书总目录》,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年,第8、9、35、36 页。从内容上看,官刻的汉文西学文献主要是大部头的历书、乐类等科学文献。邓玉函(Johann Terrenz,1576—1630)与王徵合作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在明代有1628 年武位中(扬州)刻本、约1628—1631 年汪应魁(新安)广及堂刻本和1631 年西爽堂(新安)刻本。(3)张柏春、田淼、刘蔷:《〈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与〈新制诸器图说〉版本之流变》,《中国科技史杂志》2006 年第2 期。广及堂和西爽堂是徽州府重要的书坊。《涤罪正规略》有庞天寿刻本。(4)张西平、任大援、马西尼(Federico Masini)等主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第4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第257 页。上海许府刻有《天神会课问》(1661)(5)Ad Dudink & Nicolas Standaert, Chinese Christian Texts Database (CCT-Database), http: //www.arts.kuleuven.be/sinology/cct.和《圣教四规》(6)《圣教四规》署有“云间许府藏板”字样,法国国家图书馆藏,CHINOIS7217。。堂刻文献的选材内容反映了传教士的意志,如前文统计的教堂主要刊刻的是宗教内容的文献。总体而言,堂刻文献以宗教为主,人文和科技次之,这充分说明传教士将传教贯穿于在华活动中,堂刻文献的主要功能还是服务于传播天主教。
在传教士内部,不同修会对文献刊刻持有不同的态度。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和奥思定会均参与堂刻文献的刊刻。相较而言,耶稣会的刊刻活动范围广,数量多,多明我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主要在福建,方济各会在广州和山东。耶稣会对人文学术、科技和宗教文献均有不少刊刻,其他修会主要刊刻宗教文献。耶稣会主要是在国人的帮助下进行翻译、校订与刊刻活动,完成整个流程,而方济各会除自己编译刊刻外,还直接翻刻耶稣会编刊的文献。如在广东,耶稣会教堂主要重刻以往在他地编刊的文献,而方济各会刊刻的文献过半的撰著者是耶稣会士及其在华发展的教徒。各修会在华传教过程中虽有不少冲突,但在刊刻文献上,其他修会还是效仿耶稣会。甚至,19 世纪来华的第九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团领班比丘林(N. Y. Bichurin,1777—1853)将1739 年的“皇城西安门内首善堂藏版”《天神会课》改编后于1810 年刊印。(1)肖玉秋:《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东正教经书汉译与刊印活动述略》,《世界宗教研究》2016 年第1 期,第93—103 页。
堂刻文献在明末清初到底影响如何,哪些文献受时人欢迎抑或受传教士的重视,可以从文献的初刻与翻刻中窥见。有些文献不仅初刻、重刻,还有三刻,甚至四刻。如高一志(Alfonso Vagnone,1568—1640)《教要解略》“闽景教堂重刻”(2)Albert Chan, op. cit., p. 104.,杭州“慎修堂第三刻”,绛州第四版。(3)《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第46 页。一些重要的文献在不同地方的教堂反复刊刻,《天神会课》在杭州的超性堂、北京的首善堂、广东大原堂、七宝的圣多明我堂均有刊刻。有的在同地同堂刊刻,如冯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圣体仁爱经规条》在皇城西安门内首善堂校梓,本堂藏版;有的需要去别的教堂借用木板,如利玛窦《畸人十篇》康熙甲戌岁京都领报堂藏板,金台圣母领报会重刊;(4)Albert Chan, op. cit., p. 83.有时还需要将木板长距离运输,在异地刊刻,如潘国光《天神会课》武林超性堂藏版,七宝圣多明我堂刊。这充分说明堂刻文献的影响和受欢迎程度。另外,堂刻文献的影响也反映在一些藏书目录中。(5)钟鸣旦、杜鼎克著,尚扬译:《简论明末清初耶稣会著作在中国的流传》,《史林》1999 年第2 期,第58—62 页;王申:《明清间汉文西学文献的编刊与流传》,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年。
三、堂刻文献的价值和意义
堂刻文献在天主教传教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从全球范围来看,借助文献传教不是天主教的主要传教手段,在美洲,印第安人在武力的胁迫下归信天主教,其他地区也多使用口头传教的方式。采用刊刻文献的方式传教,主要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汉文化圈。事实上,来华传教士内部,还曾存在口头传教与刊刻文献传教的争议,龙华民(Nicola Longobardo,1565—1655)等人主张口头传教策略,利玛窦和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等人坚持刊刻文献。从1583 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入华,至1773 年教宗下令解散耶稣会为止,共有多达472 位耶稣会士先后抵华。(6)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6 页。清初禁教时期,传教活动转入地下,正是通过这些文献天主教的经文才得以流传。根据张先清的研究,禁教时期流通的主要是经文类的宗教文献。(7)张先清:《刊书传教:清代禁教期天主教经卷在民间社会的流传》,载张先清编《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83—141 页。这些文献主要是原来的堂刻文献,流入到民间社会进行流传,对天主教在华的扩散和传承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清末,基督新教传教士来华后,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等人还去寻觅这批文献,并延续其刊刻文献传教的方法。上海的土山湾慈母堂刊刻了大量文献,其中不少是重刻明末清初的宗教文献,如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和《畸人十篇》、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的《天主降生引义》和《涤罪正规》、高一志的《教要解略》、柏应 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 的《 天主圣教百问答》和《四末真论》、朱宗元订阳玛诺(Manuel Diaz,1574—1659)译的《圣经直解》和《轻世金书》、潘国光的《天阶》、孙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1695—1767)的《性理真诠提纲》、冯秉正编译的《圣年广益》等。(8)邹振环:《土山湾印书馆与上海印刷出版文化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3 期,第1—14 页。至1869 年止,用木版重印了70 种。(9)李天纲:《新耶稣会与徐家汇文化事业》,载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172 页。因此,堂刻文献是天主教传教史上的璀璨明珠,是天主教本土化的重要尝试,它所带来的影响从明末延续到清末。
堂刻文献在中国刊刻史上也有重要意义。通常而言,学界将传统文献的刊刻分为官刻、坊刻、私刻和佛道寺院刊刻,教堂刊刻的地位尚未充分揭示。如前文所述,北京、杭州、广东、福建、绛州、湖北、江西、山东、松江、常熟和南京等地的教堂均有文献刊刻,文献的编撰、刻板的存放和印刷均可在教堂实现。与其他刊刻机构相比,堂刻文献主要服务于传教活动,刊刻种类相对单一,大致类似于佛道寺院刊刻,因此,教堂刊刻应与佛道寺院刊刻地位相当。堂刻文献有初刻、重刻和再刻等版本,这丰富了中国刊刻史的内容。
就内容而言,官刻文献主要是技术方面器物层次的文献,如天文历算类的文献;坊刻以猎奇和趣味为文献卖点,如《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私刻文献中宗教文献较多,如上海许府刻有《天神会课问》和《圣教四规》,庞天寿刻有《涤罪正规略》;堂刻文献更关注宗教方面的内容,教理教义和行为规范类的文献占主导。从影响来看,官刻文献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高层次或者拥有天文、数学等专门知识的人;坊刻文献以市场销售为导向;私刻文献以吸引新入教者和教友为目标;堂刻文献则为传教服务。
堂刻文献与其他方式刊刻的汉文西学文献一样,对国人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促进了汉语新词汇的产生。据黄一农考证:“韩霖在《铎书》的字里行间,除提及自己所撰的《救荒书》外,还曾多次直引如高一志的《齐家西学》、《修身西学》、《童幼教育》、《达道纪言》、《神鬼正纪》,以及庞迪我的《七克》、艾儒略的《涤罪正规》、罗雅谷的《哀矜行诠》等耶稣会士的著述。”(1)《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第281 页。这些文献多数在教堂刊刻。堂刻文献的编译需要将大量西方词汇译成汉语,这导致了新词汇的产生。以地理学新词为例,邹振环参考日本学者荒川清秀的研究指出:“明末清初的这些新词(地理学名词)在晚清受到了中外地理学学者和地理学译著者的高度重视,成了这批学者从事新的西方地理学著作翻译的重要语词资源……晚清时使用频率较高并在今译名中能够找到对应词的地理新词共138 个,其中明清之际所创译的就有25 个,占到总数的18.1%。”(2)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 至1911 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237—238 页。马西尼(Federico Masini)的研究表明:“耶稣会士的汉语著作对一些其他词汇的创造起着贡献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地理学领域),而这些词汇现在仍然在现代汉语中使用着。”(3)[意]保罗:《17 世纪耶稣会士著作中的地名在中国的传播》,载《国际汉学》第15 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 年,第238—261 页。黄兴涛进而指出:“要想弄清近代中国所流行的相当一部分新名词的真实来源,并辨析它们与明治维新后日本汉字新名词之间的复杂关联,非得下定决心,去一一翻检明末清初直至清中叶那些承载和传播西学的各种书籍不可。”(4)黄兴涛:《明清之际西学的再认识》,载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 种重要文献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23 页。可见,堂刻文献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新名词的创造和思想的变迁中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堂刻文献在天主教传教史、中国出版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都有重要的意义,值得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去探究。前文简单梳理了堂刻文献的概况、基本特征和价值,但对于其他重要问题,如传教士在华建立的教堂所在与堂刻文献中牌记所署教堂名称的对应问题、堂刻文献各个版本的差异,以及文献刊刻过程中所形成的天主教人际网络等诸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