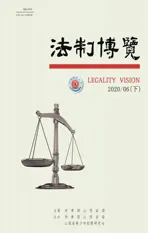证明妨碍规则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运用与完善
2020-11-30陈治儒
陈治儒
四川轻化工大学,四川 自贡 643000
一、知识产权诉讼中证明妨碍规则的内涵
学理上对于证明妨碍的定义有多种,张卫平教授认为,“证明妨碍指不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通过作为或不作为阻碍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对其事实主张的证明①。”知识产权诉讼由于涉及商标、专利、著作权等特殊的知识财产权利,其侵权形式相较于传统民事侵权有所差别,证明妨碍情形更时有发生,且主要发生在对于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上,因此笔者认为知识产权证明妨碍是指不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通过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妨碍作证从而使待证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数额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的证明。为此,探析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完善知识产权证明妨碍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二、知识产权诉讼中证明妨碍规则之检讨
(一)《商标法》第63条第二款
首先,该款是关于确定侵权赔偿数额的规定,对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的要求为“已经尽力举证”,换言之,对其举证要求并不高,客体为“账簿、资料”,由不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掌握,法院可以责令其提交相关账簿、资料,若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法院可以参考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的主张或者证据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
其次,通过对该款关于证明妨碍的剖析,不难发现,其客体仅为“账簿或资料”,客体规定得较为单一,而在商标侵权案件中还会涉及如“电子数据”等众多证据,当然立法者或许是基于该条款本身是针对确定商标侵权的赔偿数额所设计的,因此仅有“账簿、资料”,但是在商标侵权纠纷的案件中赔偿数额的确定是属于案件发展的最后所需要确定的内容。进一步来说,证明妨碍的规则仅规定在确定赔偿数额的时候又是否合理呢?因侵权行为的发生才会产生确定损害赔偿,因此在商标侵权行为阶段明确实施证明妨碍行为后所产生的证明妨碍效果是有必要的。
最后,在证明妨碍的效果上,法院可以参考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的主张或证据确定赔偿数额。该条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可以结合被侵权商标的知名度、被告的经营规模、侵权情节及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等情况综合进行确定赔偿数额。
该条款证明妨碍的效果建构初衷上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由于原告举证存在困难,或者举证后仍然难以确定赔偿数额以及法官对证明妨碍规则的理解可能参差不齐等多方面原因,法官不敢贸然适用该条款,因此该条款在实践中的适用非常少。截止2019年12月23日,通过“无讼”数据库对该条进行检索发现,第一款被3537篇案例引用、第二款被126篇案例引用、第三款被5949篇案例引用,通过比对我们发现作为证明妨碍规则的第二款适用率非常低,原因来自于原告举证存在困难导致赔偿数额往往难以查清或无法准确计算,如在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杜十一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中②,由于原告金红叶公司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损失以及被告杜十一因侵权所获利润均无法准确计算,法院直接适用了63条第三款赔偿数额无法查清时的规则。因实践中第二款的难以适用,不得不产生对其完善的法律反思。
(二)《侵犯专利权解释二》第27条
与《商标法》63条第二款的目的一致,该条规定了专利侵权案件中认定赔偿数额的证明妨碍规则,然而两条规定也存在着部分差别。首先,商标法对于权利人的提出证据的要求为已经“尽力”举证,而专利法对于权利人的要求为“已提供侵权人所获得利益的初步证据”,通过对比,在认定侵权赔偿数额时显然专利法对于权利人提出证据需达到的证明标准要求更高一些。
其次,商标法与专利法对于认定赔偿数额的证明妨碍规则中关于不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即侵权人的不作为的妨碍行为规定也不一致,在专利法中规定了侵权人“无正当理由”的情形,换言之,在被告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则不产生妨碍之法律效果,而商标法中并没有正当理由的规定,那么何为专利法中证明妨碍的正当理由?
(三)《民诉法解释》第112条
该条第一款规定的是书证为侵权人所控制的情形,第二款规定了证明妨碍行为以及效果,当侵权人不作为的实施妨碍行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之时,人民法院即认定权利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因此民诉法解释第112条的证明妨碍规则的效果上属于事实推定,而商标法和专利法中的证明妨碍效果上则是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当然,民诉法解释中的证明妨碍规则当然地适用于知识产权诉讼中,也弥补了关于著作权纠纷以及其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的证明妨碍情形,但客体较为单一,仅为书证。在知识产权的侵权案件中证据种类繁杂,如仅设定书证的证明妨碍情形显然具有局限性。
三、知识产权诉讼证明妨碍规则的完善路径
(一)完善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证明妨碍规则
1.优化证明妨碍规则的启动标准
《侵犯专利解释二》中关于认定损害赔偿数额的证明妨碍规则在实践中由于权利人举证困难,故而其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证明妨碍效果也难以适用,因此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权利人提出证据后的证明标准问题,尤其是在侵权人通过不作为的方式妨碍权利人举证的情形中,因此此种证明标准不宜规定得过高,否则将导致证明妨碍规则的适用形同虚设。从实践经验来看,商标法中适用证明妨碍规则的证明标准规定为“已尽力”举证具有合理性,利于证明妨碍规则的适用。
其次,从证明妨碍规则构建的目的来看,本就是为解决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由于侵权人通过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妨碍其举证,进而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所规定的规则。在不作为妨碍的情形中,若原告容易举证,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也没有必要适用证明妨碍规则,而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关键证据通常为侵权人所掌握,并通过不作为的方式妨碍举证使案件事实不清,故而,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对于不作为的方式妨碍举证,规定较低的证明妨碍规则启动标准具有合理性。
2.完善证明妨碍规则的效果
如前所述,商标法第63条第二款与侵犯专利解释二第27条的证明妨碍效果为法官结合权利人提出的证据,运用自由裁量权来认定损害赔偿的数额,然而在实践中运用率较低。基于侵权人对其不利益的关键证据的控制,通过不作为的方式妨碍作证发生的可能性较高,笔者认为,在已确定侵权成立的情况下,对于损害赔偿数额的证明妨碍效果构建为推定成立更具有合理性,即推定权利人主张的事实成立。实施妨碍行为的侵权人在权利人夸大损失的情况下,必定会拿出关键的被妨碍证据予以抗辩,从而有利于法官查明案件事实以认定损害赔偿的数额。
(二)拓宽证明妨碍规则中的客体种类
在专利法解释以及商标法中证明妨碍规则的客体仅为账簿资料,而民诉解释中的客体也仅为书证,而对于其他的妨碍客体则没有规定。知识产权诉讼涉及一些专业领域,难免涉及鉴定意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种类,为此针对其他种类的证据实施的妨碍行为也须予以规制。
(三)明确正当理由的范围
证明妨碍规则中的正当理由是侵权人拒绝提出被妨碍证据时所主张的原因,理由正当则不至于承担证明妨碍的效果,而何为正当理由,专利法解释二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因此有必要界定正当理由的合理范围。
笔者认为,正当理由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如其他学者所言,若侵权人提出相应证据,将承担难以估量的后果,侵权人可以拒绝提供该证据,具体要法官根据个案情况来判断。③第二,商业秘密不属于正当理由的范围。在实践中,侵权人常以涉诉证据为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提交,然而商业秘密是否是实施妨碍行为的正当理由?诚然,若该证据确为商业秘密,出示后存在给侵权人利益造成损害的可能,但法院可以根据民诉法解释第94条的规定依权利人申请调取涉及商业秘密的证据并进行查证,从而获得对争点事实的正确心证,因此商业秘密并不属于正当理由的范围。
注释:
①张卫平.民事证据制度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65.
②(2018)苏13民初109号.
③李娇娇.知识产权诉讼证明妨碍的规制[D].海南大学,201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