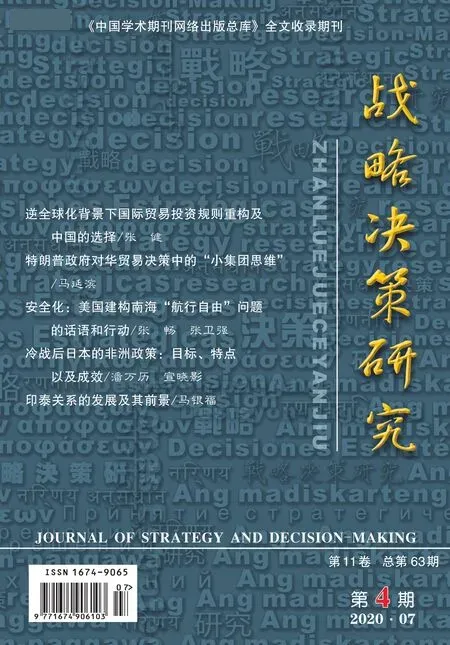安全化:美国建构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话语和行动
2020-11-29张卫强
张 畅 张卫强
随着中国崛起和周边战略的调整,美国逐渐将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视为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并开始在中国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积极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中美两国都明确支持“航行自由”(freedom of navigation)原则,但两国对这个原则的具体实施条件存在不同理解,由此造成中美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美国指控中国在南海妨害“航行自由”原则,对该原则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从2010年开始,美国开始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话语建构;进入2015年,美国开始采取实际行动,冲闯中国所属岛礁。2017年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美国海军大幅度增加了在南海地区采取“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并对中国主权进行更为直接的挑衅。①张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在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变化与应对》,载《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9期,第94-100页。中美在航行自由问题上客观地存在利益冲突,但南海地区基本保持着稳定的局面,商业航行自由迄今并未受到影响,可以说,美国所感知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主观威胁、潜在威胁,②关于威胁的属性,参见Milburn,Thomas W,“The nature of threat”,Journal of social Issues,Vol 33,No.1 ,1977,pp.126-139.加以传播后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美国是如何将南海“航行自由”建构成一个中美之间的安全问题的?本文试图运用安全化理论来加以讨论。
一、安全化:国家如何建构安全问题
与关注权力对安全的影响的物质主义理论不同,安全化理论提供了一个超越传统安全研究的新路径,一方面,它指出“安全事实上是主体间的社会化观念建构,并不客观地、独立地存在”,③Šuloviç,Vladimir.,“Meaning of security and theory of securitization”,Belgrade Centre for Security Policy,October 5,2010,http://www.bezbednost.org/upload/document/sulovic_(2010)_meaning_of_secu.pdf.换言之,安全威胁可以被怀有某项政治动机的行为体通过安全化行为建构出来,安全问题本身可能被政治化;另一方面,本体假设的演化推动了研究方法的变革,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概念,安全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家行为体与武力威胁的分析,而应当同时纳入文化、身份、意识形态等观念因素的影响。④Buzan,Barry,et al.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8,p.8.
那么安全问题是如何被建构的?“安全是一类特殊的社会范畴,它缘起于政治实践、同时也经由政治实践构造”。⑤Buzan,Barry,et al.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8,p.12.就政治实践而言,语言运用是最为重要、基本的形式之一;言语行动并非简单对客观世界的呈现,相反言语行为本身决定了客观世界呈现的方式、甚至结果。安全化理论的始创者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化、或曰安全问题的构建离不开作为言语实践的话语行为。通过话语行为,安全化主体向受众呈现针对特定指涉对象的存在性威胁,使相关议题进入安全领域、表现出紧迫性,并相应地被提升至“常规”政治之外,安全化主体得以动员社会资源与公众支持,采取非常规措施予以应对。
(一)基于话语行为的安全化
首先,话语宣称了安全问题的存在。尽管不同于强调物质能力及其属性的现实主义诸理论,安全化理论并不否认物质能力在安全问题中发挥的影响,它认为安全问题依然应当集中关注“存在性”(Existential)威胁与生存问题,①Buzan,Barry,et al.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8,p.21.以及着眼与此的理性算计,这一点与传统安全观念并无二致。但物质能力本身并不构成威胁,只有在被话语行动等安全化行为赋予意义后,才具有安全问题的属性地位——它的理论重心在于威胁的指认,或曰威胁的话语建构。“安全并不是某种指涉真实存在的事物的现象,言说本身便是安全。当我们在言说事物时,便完成了一种行为。”②Buzan,Barry,et al.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8,p.28.具有权威的行为宣称威胁存在,一个问题就可能成为安全问题。
其次,安全话语必须符合特定的规则、具备相应的结构。迫切性、优先性是安全化的决定性修辞结构,“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一问题,一切将变得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或者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已经无法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应对”,③Buzan,Barry,et al.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8,p.26.当一项问题被呈现为紧迫并关乎生存时,安全化行为体则能够超越常规政治,采取非常措施、动员社会与资源。具体言之,在安全化行为过程中,被威胁的指涉对象往往被指认为关涉最为核心的利益,被“提升至绝对的重要地位”,④Buzan,Barry,et al.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8,p.176.以期利用观众的“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心理,提升安全化主体的说服、动员能力。
第三,成功的安全化话语要借助总体的社会性语境。安全不仅仅是一个“自我指涉”的概念,它需要满足一定的社会性条件,进而取得观众的认可。立足于奥斯汀的言语哲学,言语行为的述行力(Performativity)决定了言语不仅能够描述现实、同时也具有创造现实的潜力,这是安全话语能够推动安全化的原因所在。但为什么某些安全化行为能够成功“取效”,有些不能?局限于言语行为本身的“内部”理论不能对此充分做出解释,因为言语行为既是一个言说(utterance)的事件,同时也是主体间建构威胁的过程,安全化主体的权威、地位等外部的促成因素,①Buzan,Barry,et al.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8,p.28.或者更进一步言之,作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的物质呈现,成功的话语实践应当反映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汲取言说者的话语资源,往往是行为体利用特定的策略生产、传播的结果。
因此,言语行为的完成必须遵守“约定性程序”。②Austin,John Langshaw,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14.具体言之,安全化主体、观众、话语行为均处于、或者说嵌入于特定社会秩序、意义结构或曰语境之中,③Stritzel,Holger,“Towards a theory of securitization:Copenhagen and beyond”,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3,No.3,2007,pp.357-383.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语言的选择需要顺应社会的、文化的语境。安全化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样一种作为认知环境的语境,特定的语境能够激发、凸显事态与概念的某些特征,同时隐匿其他特征,让观众更加接受威胁与安全的某一方面特定内涵。④Balzacq,Thierry,“The three faces of securitization:Political agency,audience and context”,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1,No.2,2005,pp.171-201.因此,既有的建构规则与主流叙事对威胁的理解会产生深刻的影响,诉诸规则、秩序等代表集体共同利益的概念,以此为目标,往往易于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同。
(二)非话语实践的安全化
安全化进程需要动员多种资源,既包括话语的、也包括非话语的,非话语实践可以施加结构性作用,影响对安全问题的认知和理解。⑤Balzacq,Thierry,ed,Understanding Securitisation Theory:How Security Problems Emerge and Dissolve.Routledge,2010.p.15.尽管哥本哈根学派将话语之外的行动视为话语行动的附属与结果,⑥Buzan,Barry,et al.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8,p.25.但其同样意识到了安全实践并未由安全话语合法化的情形。官僚体制运作、公共政策的制定、各种程序的实施都能够实现威胁的指认,与此同时,实践行动能够有力的支持安全化的话语。①Leonard,Sarah,“The“securitization”of asylum and migr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Beyond the Copenhagen School’s framework”,SGIR Sixth Pan-Europe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ference,September 15,2007,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b53e/9bee6d2ad4d668f328331181b9a7559b0dfb.pdf.事实上,安全化并不是一个言语指认威胁、而后采取非常措施的简单线性过程。②Balzacq,Thierry,ed,Understanding Securitisation Theory:How Security Problems Emerge and Dissolve.Routledge,2010,p.94.可以说,哥本哈根学派开创了安全研究的全新领域,发掘研究了安全问题的“主体间”维度,即安全内涵意义的建构性,然而许多学者指出(以巴黎学派为代表),③袁莎:《‘巴黎学派’与批判安全研究的‘实践转向’》,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5期,第139-156页.因其过于狭窄地关注言语行为,哥本哈根学派忽视了言语行为之外的意义建构活动。
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话语本身需要动员大量的资源以支持之,④Mogire,Edward,Victims as security threats:Refugee impact on host state security in Africa.Routledge,2016,p.22.政策行动作为成本的投入,相应地将增强话语的可信度;其次,意义的表达并不局限于言语或文本,阐释性行动与具体实践都能够建构、传达意义;⑤Weldes,Juttaed,Cultures of insecurity:states,communities,and the production of danger,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p.16-17.或者从更为根本的角度视之,言语行为中的“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本身并不是言语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言语行为试图创制安全问题,而进一步建构安全问题、或者说使言语取效则同样离不开实践的作用;⑥McDonald,Matt,“Securit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4,No.4,2008,pp.563-587.其三,实践与政策工具本身具有结构性作用,实践的实施会影响他者对实践对象意义的看法。⑦Balzacq,Thierry,ed,Understanding Securitisation Theory:How Security Problems Emerge and Dissolve.Routledge,2010,p.15-18.安全化是一种话语实践,更是一系列社会性实践,它包含隐喻、政策、图像、类比、刻板形象等等,在特定的情境中被安全化行为体动员起来,以使观众形成连贯的意义与认知网络。⑧Balzacq,Thierry,ed,Understanding Securitisation Theory:How Security Problems Emerge and Dissolve.Routledge,2010,p.3.
因此,政策实践,或着说安全化工具的使用,也构成了安全化行动的重要内容。①Emmers,Ralf,“ASEAN and the securitization of transnational crime in Southeast Asia”,The Pacific Review,Vol.16,No.3,2003,pp.419-348.可以说,安全化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使用各种决策、实践、特别是非常规措施,制造不安全感。在政治技术设计之下,安全化的非话语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带有特定目的的自我呈现,以向观众传达特定意义、带入特定情境为目的。
话语实践与行为实践相互配合,前者以威胁指认等方式启动安全化进程,并为后者提供了行动理由与依据,后者则以前者为进路,展开了“威胁”的意义传播与形象呈现,两者均为安全化操作的关键组成部分。鉴于此,本文从话语建构与非话语实践两条路径展开,按照安全化启动、实施非常措施、评估观众反应三个步骤,分析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安全化。
二、安全化启动: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话语建构
在2009年内南海形势升温之前,美国并不认为南海航行自由面临真正威胁,人们对这一主题亦少有论及。②刘琳:《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探析》,载《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1期,第84-97页。事实上,存在相当一部分观点认为,美国以“航行自由”为名实施的行动对沿岸国(中国)的安全构成了挑战,③季国兴:《南海航行自由原则的歧义及增进信任措施》,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9至13页。美国主张的航行自由事实上是“军事自由”,因为美国在南海滥用航行自由权利、威胁到了中国的安全,因此中美之间多次出现摩擦。④Valencia,Mark J.,“The South China Sea:Back to the Future?”,Global Asia,Vol.5,No.4,2010,pp.8-15.
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公开宣称南海权益属美国国家利益,改变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不介入立场;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二次美国与东盟首脑峰会发表共同表明,反对以武力解决南海争端,并强调所谓的南海“航行自由”与“地区稳定”的重要性。以此为发端,美国“发现”了“航行自由”问题,并开启动对这一问题及其安全威胁有意建构,为日后“航行自由行动”的实施寻求必要的合法性。为了取信于安全化观众,话语建构需要有意的策略与操纵,进而指向威胁的三个基本层面:谁在威胁,威胁的程度,正当与否,共同形成安全化动议的完整逻辑。
(一)指认安全威胁:对中国海洋能力发展及意图的解读
识别存在性威胁是安全化的起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构成了美国话语中的“威胁代理”(threatagent)。首先,美国反复界定、渲染中国海洋力量发展的影响与中国的战略意图,据此指认中国对航行自由构成的挑战。中国国防现代化事业的迅速推进,特别是海军力量的增长,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宣传中国海上力量及其威胁成为美国官方政策立场文件的常见主题。美国防部2009年以来发布的中国军力年度报告,均专门阐述中国“胁迫性”的军事战略、海军“区域拒止”、“远程投送”等进攻性力量的发展,在美国看来,中国军力的建设旨在满足改变现状、建立地区霸权的对外战略目的;在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支持下,中国位南海地区的坚定立场可能引致摩擦、甚或武装冲突,未来最终将危及该地区的航行自由,①Robert M.Gates,“Strengthening Security Partnerships in the Asia-Pacific”,US Defense Department,June 5,2010,https://archive.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483.因此,有关国家应当就军力增长进行共同研讨,“以确保这些能力不针对本地区内的其他国家”。②Robert M.Gates,“Remarks by Secretary Gates at ASEAN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 Plus”,US Defense Department,October 12,2010,https://archive.defense.gov/transcripts/transcript.aspx?transcriptid=4700.通过对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渲染,美国建构了中国“危险他者”的身份。
根据中国南海问题的具体特点,美国还针对性地选择了威胁表征的方式。如果说由于可能的国际冲突导致“航行自由”受到妨害无法完全归咎于中方,那么岛礁建设与“军事化”则成为美国话语中中国威胁航行自由的最有力证据。为了证明中国岛礁建设的规模与影响,美国采取力度空前的舆论宣传,并直接由军方出面向媒体提供相关的情报材料,③Ivan Watson,“Battle for the South China Sea”,CNN,August,2018,https://edition.cnn.com/interactive/2018/08/asia/south-china-sea/0形成极具冲击力的舆论效应。美国军政人士还提出了极具内涵的隐喻性称谓——将中国岛礁比喻为海上的“沙之长城”(Great Wall Of Sand)。④类似的隐喻还有特朗普所说的“巨大的海上堡垒”,参见Patrick Winn,“No,Mr.Trump,China did not build a‘massive fortress’in the sea”,December 16,2016,PRI,https://www.pri.org/stories/2016-12-16/no-mr-trump-china-did-not-build-massive-fortress-sea.作为一种说服工具,隐喻在阐释与表意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它将复杂的现实政治世界简单化,使之易于理解与操纵,同时唤起观众心中既有的认知图式,最终使观众易倾向于接受言说者的见解。①Mio,Jeffery Scott,“Metaphor and politics”,Metaphor and symbol,Vol.12,No.2,1997,pp.113-133.“沙之长城”既反映出中国岛礁建设的“规模与速度”,也在暗指其“目的意图”与“军事属性”,或者说暗示了其封闭海洋、阻隔自由航行的消极影响。
其次,在这一过程中,话语明显地选择性地突显了某些现实,同时边缘化了另一些现实。尽管中国不是在南沙最早部署武器的国家,也不是部署武器最多的国家,更不是军事活动最频繁的国家,但美国不顾其他国家在南海侵占岛礁、部署军事力量的事实,指责中国在南海岛礁实施军事化以威吓邻国,②US Defense Department,“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ember 18,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NSS-Final-12-18-2017-0905.pdf.对其他国家的岛礁建设行动,美国官方与媒体罕有论及。上述种种言论为典型的话语界定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能力与意图,共同形成了中国航行自由“挑战者”身份认定。在这一身份界定之下,中国的任何行动某种程度上都已被美方界定安全挑战。例如,2016年1月4日,针对中方民航飞机位南海进行校飞并降落南沙永暑礁机场,美国务院指责中国的行为“加剧紧张、危及地区稳定”,并再次呼吁中国停止岛礁“军事化”。③韩梅:《美官方妄称中国在永暑礁试飞“威胁”区域稳定》,环球网,2016年1月5日,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6-01/8318559.html?agt=15438。
(二)渲染威胁
除了指认威胁外,营构紧迫性与优先程度,才能够显示出安全问题的真实存在,获得受众的认同。在这一方面,利益概念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描述情境、定义问题,政治精英得以建构出国家利益,实现对国际事务的理解、驱策行动。④Weldes,Jutta,“Constructing national interest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No.3,1996,pp.275-318.与此相应,在美国的对外政策表述中,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紧迫性大体呈现出逐渐升级的过程:泛化利益之内涵,完成意义的再界定——“南海不仅对沿岸国家至为关键,对这些在亚洲拥有经济与安全诉求的国家同样重要”,⑤Robert M.Gates,Secretary of Defense,“Remarks by Secretary Gates at ASEAN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 Plus”,US Defense Department,October 12,2010,https://archive.defense.gov/transcripts/transcript.aspx?transcriptid=4700.因此,航行自由、亚洲公域的准入、对国际法的尊重均构成了美国的国家利益,①Hillary Rodham Clinton,Secretary of State:“The South China Sea Press Statement”,US Department of State,July 22,2011,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1/07/168989.htm.尽管美国是一个完全不涉及南海争端、对主权争端亦“不持立场”的域外国家,中国在南海的坚定立场与军事能力,“不仅对美国和(亚太)区域利益,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利益构成直接挑战”。②John McCain,Chairman of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Senators McCain,Reed,Corker,and Menendez Send Letter on Chinese Maritime Strategy”,U.S.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March 19,2015,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press-releases/senators-mccain-reed-corkerand-menendez-send-letter-on-chinese-maritime-strategy.这种看法的着眼点显然已经超出地缘视角,而上升至国际秩序高度。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安全政策体系中,中国行动引发的“航行自由”问题逐渐向安全挑战靠拢。2010-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外部威胁从暴力极端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演变为国际恐怖主义、俄罗斯在乌克兰对国际规范的挑战、朝鲜的挑衅及东海、南海紧张局势,最终聚焦于中俄两个“修正主义”大国、“流氓国家”伊朗、朝鲜,以及跨国恐怖活动,并点明中国在南海建立军事化的前哨,威胁自由航路、地区稳定,同时将海洋自由视为印太地区政策的首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将包括航行自由在内的南海问题与朝核问题等美国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并列陈述,③Donald Trump,“Full text:Trump's 2017 U.N.speech transcript”,United Nations,September 19,2017,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7/09/19/trump-un-speech-2017-full-text-transcript-242879.开始成为美国政策话语中的新现象。受到深层认知图式的影响,人们倾向于将像似性视为临近性(nearness),话语的并置(juxtapositon)致使被并置事物之间呈现出某种相同特点,并被突出强化,④Colston,Herbert L,Using figurative langu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41.在体现出美国领导者认知变化的同时,航行自由问题的威胁色彩也相应地得到增强。
南海问题在美国对外政策关切中的排序明显提升,“南海是美国的最高国家利益”则构成了这一进程的终极表现。⑤周远方:《美高官首度宣称南海是最高国家利益中方回应》,观察者网,2016年7月14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6_07_14_367515.shtml.这一过程伴随着渐趋尖锐的措辞,中方的行动致使航行自由等问题从受到“关切”(concern),最终航行自由原则面临着(中国的) “挑战”,①Joe Biden,“Commencement Address by the Vice President at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White House,May 22,2015,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5/05/22/commencement-address-vice-president-united-states-naval-academy.变得“令人不安”(troubling)②John Bolton,“AHS Event with Ambassador John Bolton”,Alexander Hamilton Society,November 18,2018,http://www.alexanderhamiltonsociety.org/newsfeed/2018/11/7/ahs-event-with-ambassadorjohn-bolton.且“极度令人焦虑”(extremely worrisome)。③Reuters,“Tillerson says China should be barred from South China Sea islands”,January 12,2018,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ongress-tillerson-china-idUSKBN14V2KZ.
在这样一种重大利益与紧急情势的影响下,“不作为”已成为不可能。据此逻辑,美国不仅“绝不接受航行自由受到妨害”,将“使中国确信美国捍卫航行与飞越自由权利的坚定决心”,④Reuters,“John Kerry to take tough approach in China over South China Sea”,May 14,2015,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1796322/kerry-take-tough-approach-chinaover-south-china-sea.并就此做出了措辞强烈的行动承诺:尽管美国在主权争端问题上保持中立,但“在国际法问题上并非中立,在遵守规则方面,我们会采取强有力(forcefully)的反制行动”,⑤PrashanthParameswaran,“US Not‘Neutral’in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Top US Diplomat”,The Diplomat,July 22,2015,https://thediplomat.com/2015/07/us-not-neutral-in-south-china-sea-disputes-top-us-diplomat/.“中国的行动将承担后果”。⑥Reuters,“U.S.warns China on militarization of South China Sea”,March 2,2016,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southchinasea-usa-carter-idUSKCN0W404R.通过紧迫性的凸显,观众得以感知事态的严重性,“航行自由”问题呈现出现实存在的重大影响,成为一项关乎安全的、需要予以应对的挑战。
(三)诉诸规则:强化安全化建构的合法性
针对国内受众,国家与政府官员天然地处于言说安全的权威地位,对安全问题的阐述往往容易获得认可,但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质,以其他国家为受众的安全化必须诉诸特殊的权威。布赞指出了一种独特的安全化模式:建构对国际社会、国际秩序、国际法的威胁,以合法化自身干预他国主权的单边行动,这是美国惯常采取的安全化手段。⑦Buzan,Barry,et al.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8,p.159.因为规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此外,作为一种机制性权力,规范比强制性权力更容易得到他者的接受。①Barnett,Michael,and Raymond Duvall,“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1,2005,pp.39-75.
美国对中国单方面的指控并不会轻易取得其他国家的认同,还需要借助规则话语使其可信、正当,进而影响安全化观众的共同认知。规则与法律成为美国话语中的突出主题与关键修辞。尽管涉及中国行动的军事维度,美国更加侧重于指控其对“秩序”“规则”的挑战。在此过程中,美国对中国的指控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表达之间形成政策之间的“互文”,获得了话语的合力。一方面,“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各种外交场合、文件中被申说强调,特别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等重要地区论坛中,成为美国重点宣贯的话题。作为一种设想之中的认同与言说的预设,美国认为其主导之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给亚太带来了和平与繁荣,这一秩序立足于国际法规,构成了美国的、同样也是国际社会的利益所在,应当得到遵守维护;另一方面,中国在南海的种种行动正在对这一秩序构成挑战,特别“航行自由”这一“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受到影响,美国对此不会无动于衷。②Reuters,“Trump's secretary of state nominee Tillerson wants to deny Beijing access to South China Sea islands”,South China Morning Post,January 12,2017,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2061356/trumps-secretary-state-pick-tillerson-hits-out-china.
与此相应,美国着力呈现积极的自我形象、同时有意刻画出一个负面的他者:美国的指控法据充分、并且诸多国家持有相同看法,“我们认为《海洋法公约》中体现的国际习惯法为海洋的合理使用、准入权利提供了指导方针”,美国“与东盟成员国家及其他海洋国家、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一道,均将南海的航行自由、公域准入与国家法秩序视为国家利益”;美国不仅自身一贯行使航行自由权利,同样也“支持其他国家行使位国际水域航行、活动的权利”,③Hillary Rodham Clinton,Secretary of State,“Remarks at Press Availability”,US Department of State,July 23,2010,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0/07/145095.htm.是一个保护其他国家权宜的秩序捍卫者;相反,中国在南海则是一个“使用强力胁迫、违反国际法”的问题国家。
作为中美之间、拥有特定空间指向的议题、“航行自由”与“国际规则”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可操作的标准是什么,其合理性在何?美国所诉求的航行自由,是否估计沿岸国的安全与正当权利?这些重要的问题都被加以规避。通过秩序话语规约与我—他形象的对比,美国将内涵复杂的“航行自由”分歧简单化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规则追求,完成了“航行自由”“国际规则”的意义锚定。美国主张的航行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滥用这一自由的海洋霸权行为,国际社会历来存在对其质疑的声音,①Valencia,Mark J.,“The South China Sea:Back to the Future?”,Global Asia,Vol.5,No.4,2010,pp.8-15.然而经过话语的组织与表征,美国的安全化操作完成了自我的“正当化”。
以指认威胁、突显紧迫性、论说合法为主要内容,上述言语行为共同构成了“断言”与“警告”,完成了安全化的议题设置,②JuhaVuori指出安全化话语有着不同的取效(perlocutionary)目的,都可以通过断言、警告、命令等基本言语行为构成复杂的言语序列去实现。参见Vuori,Juha A,“Illocutionary logic and strands of securitization:Applying the theory of securitization to the study of non-democratic political order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4,No.1,2008,pp.65-99。或曰存在性威胁的建构,中国影响航行自由的叙事也就具有了意义的连贯性,因而它需要特定的措施行动加以应对。
三、采取非常措施:美国在南海实施的“航行自由行动”
在以话语建构威胁、启动安全化后,采取“非常措施”实践成为安全化建构的第二个重要构成部分。2015年美国开始实施冲闯岛礁的“航行自由行动”,中美“航行自由”问题进入全新阶段。通过广泛的话语建构,美国向观众宣称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存在与影响,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被高度放大,因此采取非常措施予以应对已成为必要。而非常措施的实施,一方面,使观众更加倾向于相信美国所宣称的威胁的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则推动了威胁与安全等等相关概念意义的传播,进一步塑造了受众的认知。
作为前一阶段提出的“航行自由”问题的应对与解决方案,“航行自由行动”的实施将抽象的话语转变为现实存在,具体可感的挑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诸多评论者对“航行自由行动”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在外交手段足以达成法律宣示效果的情况下,冲闯中国岛礁反而会致使对方升级行动。③Mark J.Valencia,“US FONOPs in the South China Sea:Intent,Effectiveness,and Necessity”,July 11,2017,the Diplomat,https://thediplomat.com/2017/07/us-fonops-in-the-south-china-sea-intent-effectiveness-and-necessity.为什么美国需要进一步升级行动,达成一种“例外”应对?分析表明,美国在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的同时,对这一行动的形式和内涵也进行了很大的调整,以更好地达到安全化的效果。由美国单方提出问题、加以应对、并由自己对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解释与评价,同时“扮演者控方、法官、陪审团、执行者”①Etzioni,Amitai,“Freedom of navigation assertions: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world's policeman”,Armed Forces&Society,Vol.42,No.3,2016,pp.501-517.的角色,“航行自由”问题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挑战,有关这一问题的建构随之进入高峰期,藉由这一过程,对安全化观众的动员得以实现。
(一)提升“航行自由”问题关注度,促进威胁意义传播
无法引起关注的问题自然无法进入安全领域,议题的关注度是安全化的重要条件,受众正是在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当中,接受安全化行为体的影响与形塑,建立主体间关于安全问题的共同理解。美国位南海实施的“航行自由行动”则大大提升了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
传统上“航行自由行动”在实施后依然处于保密状态,仅仅在年度报告中简略提及,除却行动针对的对象国家,既不公布行动的时间地点,亦未透露行动的具体细节。在2015年前,“航行自由行动”几乎未见诸主流媒体的报导。②Etzioni,Amitai,“Freedom of navigation assertions: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world's policeman”,Armed Forces&Society,Vol.42,No.3,2016,pp.501-517.概因美国认为“航行自由行动”是一项“法律宣示”行动,而非服从于特定的政治、军事目的,因此应当低调进行、避免被过度解读,③Mira Rapp-Hooper,“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Is business as usual?”,Foreign Affairs,October 12,2015,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5-10-12/allgood-fon.继而有损于美国行动的“合法性”。为了实现广泛的动员效应,美国不惜打破常规与历史惯例,开始围绕“航行自由行动”进行国际公关。
2015年10月美国海军“拉森”号驱逐舰位南海岛礁实施了首次“航行自由行动”,评论认为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为公开的一次“航行自由”行动,④Jonathan G.Odom,“FONOPs to preserve the right of innocent passage?”,the Diplomat,February 25,2016,https://thediplomat.com/2016/02/fonops-to-preserve-the-right-of-innocent-passage.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首先,美方前所未有地在行动前释放信号、进行宣传。在对中方岛礁建设进行大规模持续报道等前期准备后,2015年5月,美防长卡特宣称“美国可以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区域飞行、通航”并“将派出军舰和战机进入中国在南海岛礁12海里以内的区域”,这是美国官方首次明确表态可能在南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表明一向对南海问题持谨慎立场的美国终于考虑直接采取行动、升级措施。
此言一出,政客、学者、军方等等安全专家就行动的依据、影响、可能形式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安全专家或者身居就重大安全问题进行决策的职位,被赋予制度性的权力,或者具备安全问题的相关专业知识,其话语相对“超然”,相应地获得了对内的“权威性”。尽管存在着对该行动合理性与有效性的质疑,支持行动的声音在上述各界人士中总体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影响较大的观点包括:美国会内强硬派议员参议员、武装力量委员会主席麦凯恩、众议院武装力量海上委员会主席福布斯纷纷批评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行动不力,敦促美国军舰与飞机进入中国岛礁12海里范围内;美太平洋总部司令哈里斯、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则认为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挑战了既有的国际规则规范”,美国军方将重新重视航行自由计划,①Mira Rapp-Hooper,“All in Good FON:Why Freedom of Navigation Is Business as Usual in the South China Sea”,Foreign Affairs,October 12,2015,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5-10-12/all-good-fon.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论证了“航行自由行动”的必要性。
在官方发声后,美国国内的知名智库相应地展开技术性细节讨论,以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对外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国家利益》杂志(National Interest)为代表的学术团体,就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的理由、法律依据、行动样式、可能影响等刊文论述。以国会听证会、智库研讨会等交流形式,官员、军方、智库之间的观点相互支撑、产生“共鸣”,形成了连贯的意义网络,共同为行动的开展提供支持。在“航行自由行动”真正实施之前,针对观众的动员行动便已经展开,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力地促成威胁建构与意义表征的传播拓展。
(二)推动安全问题表征的具体化,凸显中国挑战
安全化理论揭示出安全问题的主体间维度,即安全这一概念在本体层面并非全然由某种客观的物质性因素决定,而是观念的社会性建构的产物,包含对特定问题的共同理解与处置方式。②Taureck,Rita,“Securitization theory and securitization stud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Vol.9,No.1,2006,pp.53-61.问题解决的方案本身蕴含着深刻的倾向性,手段与政策的效果并非中立,手段工具自身的逻辑将会结构政策本身,就议题产生特定的表征。①Léonard,Sarah,“EU border security and migration into the European Union:FRONTEX and securitisation through practices”,European security,Vol.19,No.2,2010,pp.231-254.处理议题的具体方式将影响议题的阐释与认知,其“表现性”(expressiveness)深刻影响着公众对行为体角色与身份的看法。②Benford,Robert D.,and Scott A.Hunt,“Dramaturgy and social movement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power”,Sociological inquiry,Vol.62,No.1,1992,pp.36-55.
通过“航行自由行动”,组织、锚定事件的意义,建立中方行动与“秩序挑战”之间的关联、构建主体间对“威胁”的共识,可以推动安全化建构的顺利实施。对此,“航行自由行动”的实施以实践支持着威胁话语,完成了上述指控的“例证”。
在此过程中,大体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行动—阐释”模式,进行意义的生产与传播:首先由军政官员释放行动信号,海军军舰随之实施“闯礁”行动,军方、外交部门择机披露行动的有关细节,官方与新闻媒体、学术机构对行动对其进行相应“解读”。例如,2015年10月美国位南海实施的第一次航行自由前,美国消息人士先进行预告,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于12月就此次行动做出详细声明,澄清美方行动系“无害通过”而非自由航行、并给出相应解释;2016年15月美方第3次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后,美方官员点明“事先没有知会中方”;2016年10月美方第4次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后,美方官员透露美国军舰进入了中国领海,但“并未进入中方岛礁12海里内”;美国媒体、智库除了紧跟形势、对当局的行动做出报道分析外,同时积极预判,为当局行动“建言献策”,其中不乏与官方“不谋而合”的情形:2016年12月,CSIS发表《特朗普总统的首个“航行自由行动”是否在美济礁》一文,分析美方可能行动的实践地点,建议当局在美济礁实施,以呼应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结果,2017年5月美方“果然”在美济礁实施了“航行自由行动”,美智库传统基金会随即盛赞此为“真正的”航行自由行动。
事实上,国际法经常被用作安全化的“规约性工具”——规定何种行动应当得到应允,何种行动作为威胁应当禁止,③Balzacq,Thierry,ed,Understanding Securitisation Theory:How Security Problems Emerge and Dissolve.Routledge,2010.p.16同时将特定的对象“非法化”(delegitimization),为己方的安全化举措增添道义资本。在这里,美国单边话语中的国际法趋于“符号化”——将符合某一社会群体利益的、本质上是任意的某种原则误以为是普遍真理,它无视了国际法“航行自由”原则的相对性,把蕴含美国特殊政治动机的行动伪饰为符合国际社会的共识:具体言之,一方面以美国的单边解读为对照,美国的冲闯行动形成了三种类型的国际法宣示。其一,派遣军舰穿航领海、冲闯岛礁12海里范围、实施“无害通过”,挑战“外国军舰无害通过本国领海期间应提前告知并获得允准”的要求;其二,派遣军舰在西沙领海内实施“公海航行”,否认在中国在西沙划定的直线领海基线。其三,在美方单方面认定的“低潮高地”12海里范围中进行自由航行,否定中国的海域管辖、进而否定中方对岛礁地位的主张;另一方面,同步宣传中方在“航行自由”行动过程中对美国军舰采取的“危险动作”,借以证明其内在敌意及对抗倾向。①Joseph Trevithick,“U.S.Navy Releases Images Of Chinese Warship's Dangerous Maneuvers Near Its Destroyer”,October 2,2018,the Drive,https://www.thedrive.com/the-war-zone/23986/u-s-navyreleases-images-of-chinese-warships-dangerous-maneuvers-near-its-destroyer.
可以看出,作为实践与主体间互动的安全决定了“安全化是一种政治选择”,②Šuloviç,Vladimir.,“Meaning of security and theory of securitization”,Belgrade Centre for Security Policy,October 5,2010,http://www.bezbednost.org/upload/document/sulovic_(2010)_meaning_of_secu.pdf.而不仅仅是理性行为体对事件的反应与感知。当以对待安全问题的手段处置某一问题时,这一问题则显得不安全,当美国在南海实施了“航行自由行动”后,南海则开始呈现出“不自由”。
(三)激活对抗性框架,在南海营造不安全感
作为组织和表征问题和事件的方式,框架在大众理解具体事件意义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③Entman,R.M.,“Framing Bias:Media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57,No.1,pp.163-173.不同的框架会带来不同的诠释方式和政策意涵,如果以法律分歧的框架来界定航行自由争端,那么意味着这一问题应当主要以对话和外界途径予以应对。长期以来,中国倾向于以发展为导向的合作框架下解读南海问题,依照“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路径,推动这一问题的和平解决,④KivimäkiT.Legalism,Developmentalism and Securitization:The Case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InFels E.,Vu TM.Eds,Power Politics in Asia's Contested Waters.Global Power Shift,Springer,2016,pp.57-76.美国实施的“航行自由行动”则对这一框架产生了冲击。
美国自认为其传统意义上的“航行自由行动”旨在进行法律宣示——定期、经常性的派遣军舰进入他国领海,以挑战对航行自由权利的“过度限制”,尽管由军人实施,但本质上仍属于一种外交行动,①Mira Rapp-Hooper,“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Is business as usual?”,Foreign Affairs,October 12,2015,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5-10-12/allgood-fon.不针对特定国家并力避挑起冲突。随着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开展,这一逻辑很快遭到颠覆。由于冲闯岛礁的高度敏感性,相当部分的国际舆论将“航行自由行动”视为美国对中国发出的强硬警告信号,甚至美国对中国的“进攻性”行动的遏制,而并非单纯的法律宣示行动,其对抗性也随之大大增强;美国军政官员也逐渐接受并公开传导这一观点: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指出,美国必须持续实施‘行自由行动’,以反制日渐好战的北京,只有通过维持地区军事能力,明确地展示出决心,才能够威慑中国,防止他们控制南海的航路、自然资源,甚至不惜与中国一战;②Jamie Seidel,“US Pacific Command Admiral Harry Harris says US fought its first war over freedom of navigation”,December 14,2016,https://www.news.com.au/national/us-pacific-command-admiralharry-harris-says-us-fought-its-first-war-over-freedom-of-navigation/news-story/1b27c3aa1987059bd 7c3393aa2ed92bd.在被问及中国如果进一步在南海推进岛礁“军事化”美国将如何应对时,助理防长薛瑞福指出,美国将持续开展“航行自由行动”,扩大行动的参与,以应对中国的侵略性行为。③Randall G.Schriver,“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Indo-Pacific Security Affairs Schriver Press Briefing on the 2019 Report on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 China”,US Department of Defense,May 3,2019,https://www.defense.gov/Newsroom/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1837011/assistantsecretary-of-defense-for-indo-pacific-security-affairs-schriver-press.该行动已经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其意义远远超过法律宣示本身。
在此基础上,“航行自由行动”与美国海军在南海的实战训练结合日趋紧密,2016年美国海军开始按照新作战概念编组作战“水面行动大队”,同年10月按照该方式派遣军舰进入南海,实施岛礁冲闯,此后基本延续这一行动模式;④张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在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变化与应对》,载《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9期,第94-100页。“航行自由行动”军事色彩日益浓厚。受到上述背景的影响,在很多亚洲国家看来,由军舰冲闯岛礁的“航行自由行动”,总体上已经成为美国展现介入南海事务决心的窗口和政治宣言,是美国向地区盟友提供安全保障、维护地区安全架构的“再保证”;作为“反制”中国的行动,它的法律宣示效果已经大大弱化,逐步被视为一种威胁使用武力的行动。①Mark J.Valencia,“US FONOPs in the South China Sea:Intent,Effectiveness,and Necessity”,July 11,2017,the Diplomat,https://thediplomat.com/2017/07/us-fonops-in-the-south-china-seaintent-effectiveness-and-necessity.
被视为军事遏制举措的“航行自由行动”激活了冲突框架和敌人意象,在攻讦对方的同时,也提升了自我的形象:中国对航行自由的妨害是对南海周边国家的霸凌,美国是在以冲闯行动捍卫地区国家的利益,这种“威胁—应对”认知结构的出现,逐渐影响着公众理解“航行自由”问题的方式,很多周边国家将美国的行为视为“选边站队”的信号;②BhavanJaipragas,“America’s message:time to pick sid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South China Morning Post,October 6,2016,https://www.scmp.com/week-asia/politics/article/2167247/americasmessage-time-pick-sides-south-china-sea.这种敌人意象异常强烈,以至出现了一种近似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冷战叙事:如果美国不从速采取“航行自由行动”,东南亚国家自身没有力量维护相关海域的开放,将会认为美国正在亚洲退却,进而把中国当作可靠的大国伙伴,致使整个力量平衡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③Mira Rapp-Hooper and Charles Edel,“Adrift in the South China Sea:The High Cost of Stopp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Foreign Affairs,May 18,2017,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17-05-18/adrift-south-china-sea.“航行自由行动”的意涵远远超出了法律宣示,被打上了“安全”的标签,成为了美国为南海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措施。在“航行自由行动”中,美国使用武装力量、以侵入性的方式保卫“国际规则”,与此相应,作为行动对象的中国则自然地构成了一个“挑战者”,二者之间“威胁——防御”“挑战——保卫”的对抗性框架就此形成,挑动地区局势紧张升级,营造了不安全感,促进了安全化的拓展。
四、安全化的效果
众所周知,具备合法性的权力运用往往成本最低,收效最大。④DavidBeetham,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Macmilla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2013,p.28.成功的安全化得到了受众的接受和承认,实现了安全问题的主体间认知,进而会得到其他行为体的认可甚至追随。因此,行为体可以战略性地进行安全化操作,通过安全化赢得他者支持,顺利实现其特定的政治议程。基于这一标准分析,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安全化的效果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航行自由问题并非完全出于美国对安全的真实忧虑——因为这一自由很大程度上被用于服务其霸权,而是有着特定的政治目的驱使。美国作为远在大洋彼岸的域外国家,其本身缺少介入南海争端的正当理由与着力点,与此相反,域内的东盟国家对大国影响高度敏感,对大国的干预介入多有防范。以中国为责任方将“航行自由”问题安全化,无疑使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种种举措一定程度的“合法化”。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传统盟友,以及一小部分南海争端的当事国存在制衡中国的战略诉求,他们构成了美国安全化行动的天然受众。针对这一情势,出于稳定南海局势的考虑,中国采取切实行动,力求实现航行自由问题的去安全化。在上述背景下,随着安全化观众的接受抑或拒斥、纷纷做出回应,特别是由于缺少关键国家的支持,“航行自由”问题争议逐渐退潮,自2017年开始,美国对南海的安全化举措明显有所降格。
(一)“航行自由行动”的常态化实施及示范效应
以实践形式呈现的安全化行动不可避免地涵盖一个过程。经验研究的案例表明,安全化不仅存在开始与终结(去安全化),其程度在历时与共时维度同样存在变化,换言之,安全化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二元的状态。①Bourbeau,Philippe,The securitization of migration:A study of movement and order,Taylor&Francis,2011,p.42.那么,安全化如何得以维持、或曰再生产?在福柯“治理术”、布迪厄“惯习”理论概念的启发下,立足社会学视域的安全化理论学者指出,哥本哈根学派过于强调言语行为的功能与“例外”逻辑,安全不仅需要塑造紧急情势的例外状态,同时离不开“惯例”的逻辑——安全化主体惯常性的安全化实践。
具体言之,将“例外”逻辑视为安全化主要机理的观点认为(以哥本哈根学派为代表),安全言语行为将导致用以应对存在性威胁的重大决断、非常举措,进而引致一种超越常规政治的例外状态;②Buzan,Barry,et al,Security:Anewframeworkforanalysis.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8,p.25.“惯例”逻辑则将安全化视为“通常由官僚与安全专家实施的一系列惯例化的实践”,用以营造不安、不确定感、对风险进行管控。意义在不断的惯常化运作中为人们所熟知、习惯、接受,在“表演”仪式的过程通过对共同体道德价值的表达性再现和重申,①Durkheim,Emile,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vii-xxv.从而确立社群的共识。通过安全化行动的反复实施,安全化状态得以“正面强化”,避免了安全化状态消逝或被其他社会建构取代。②Léonard,Sarah,“EU border security and migration into the European Union:FRONTEX and securitisation through practices”,European security,Vol.19,No.2,2010,pp.231-254.
2014年,美国实施的“航行自由行动”达35次,较前1年出现了接近一倍的增长,强度达到冷战时期的高峰水准。美国针对中国在南海实施的“航行自由行动”数量也在相应强化,③2015年1次、2016年3次、2017年6次、2018年5次、2019年9次.John Power,“US freedom of navigation patrols in South China Sea hit record high in 2019”,the South China Moring Post,February5,2020,https://www.scmp.com/week-asia/politics/article/3048967/us-freedom-navigation-patrolssouth-china-sea-hit-record-high.与此同时,为了行动的顺利实施,美方还对“航行自由行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改变每次行动单独申报审批的模式,由海军制定统一的年度计划,提交美太平洋司令部、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批,按照年度计划统一实施,避免行动受到政治因素中断或延期,相应地美方的主张将更具说服力,④Chong,Ja Ian,“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Better Quiet Resolve”,S.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November 6,2015,https://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5/11/CO15236.pdf.“航行自由行动”得以“正常、稳定的节奏开展”,⑤Laura Zhou,“Trump signs off on plan to allow US Navy more freedom to patrol in South China Sea,report says”,South Chin Morning Post,July 22,2017,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2103718/trump-signs-plan-allow-us-navy-more-freedom-patrol.强化了“航行自由行动”基于国际规范、而非出于政治目的的形象。
常态化实施的“航行自由行动”的示范效应正在逐渐显现,域外国家成为受到美国安全化动议最大影响的主要观众。借助各个国家场合的宣介与“航行自由行动”造成的广泛影响,美国自2017年以来开始试图推动对中国实施的“航行自由行动”的国际化。一方面,关于“航行自由行动”的高强度报道部分影响了国际舆论,美国的冲闯行动获得某些国家的支持,以日澳为例,这些国家乐于见到美国采取行动制衡中国的影响;①蓝雅歌:《美在南海不断挑衅推行海上霸权,日澳公开支持》,环球网,2016年2月2日,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9CaKrnJTCiN?w=280。另一方面,美国开始直接推动一些国家加入其“航行自由行动”,进一步搅动南海局势,②Ben Werner,“Future South China Sea FONOPS Will Include Allies,Partners”,US Navy Institute,February 12,2019,https://news.usni.org/2019/02/12/41070.其行动本身则成为了有关国家的指引和鼓励,特别是与西方价值理念高度契合的“航行自由”原则,以此为指涉对象,足以引起美国盟友的广泛共鸣:2017年3月,美英法三国海军,决定加强联合巡航力度,实施自由的海上航行行动。2017年10月,英国国防大臣、首相先后公开宣称,未来将派遣海军最新装备的“伊丽莎白”号航母参与南海“航行自由行动”,2018年2月,英国海军派遣“萨瑟兰”号护卫舰位南海部署,以“捍卫航行自由”;2018年9月,英国海军“海神之子”号船坞登陆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领海;2018年10月,法国国防部长表示法海军旗舰“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未来将前往印太地区“维护航行自由”,应对“类似在南海的违反国际法的情况”。可以看出,作为自由主义价值体系重要构成的“航行自由”规范得到美国西方盟友的广泛附和与追随。
(二)相关国家对美国安全化动议的抵制
并不是所有安全化动议都会无条件地获得成功,得到其他行为体的全面承认与信服,它还取决于行为体本身的能力与适当的社会语境——特别是安全化观众本身的偏好与传统。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航行自由”的实质是维护美国海洋霸权的“横行自由”,绝非为了南海国家的利益福祉,以此为安全化逻辑建构中国的威胁挑战,难以得到多数国家的接受。以越南为例,其对海洋法中关于航行自由条款的解读事实上与中国相近,明确要求军舰进入领海海域前事先知会当局,美国“航行自由行动”所认定的法理依据与其相悖。其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还面临着天然的“权威不足”,进一步制约了其安全化行动的取效。
规范约束国家行为,建构国家利益,如果外部规范与国内规范能够产生共鸣,规范则容易传播,③Checkel,Jeffrey T,“Norms,institutions,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Europ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3,No.1,1999,pp.83-114.反之则容易遭到抵制。长期以来,“大国平衡”或曰对冲,成为南海周边国家对待中美之政策的一个决定性考量,“大象打架,草地会遭殃”,①Lee HsienLoong,“US-China tit-for-tat threatens global prosperity:Lee HsienLoong”,May 16,2018,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us-china-tit-for-tat-global-prosperity-lee-hsienloong-trump-10238944.生动概括了其背后的战略理性,中国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国际事务,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互利合作项目助推地区发展,获得了有目共睹的认可;在此背景下,稳定的国际环境与良好的大国关系符合地区国家利益,南海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决定了这一问题尤其需要稳妥处理。从目的与手段看,美国建构的“航行自由”都与上述愿景相冲突:“航行自由问题”服务于美国介入南海、制衡中国的目标,应对该问题的“航行自由”行动,则直接诉诸武力予以实施(尽管是法律宣示),蕴含着相当的风险,美国的安全化举措与地区国家的关键政策。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对美国提出的“航行自由”问题回应总体有限,态度审慎;尽管与中国的主权争端较之其他国家更加复杂,针对美国所实施的“航行自由行动”,越南当局虽然表示其支持航行自由原则,但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间接反映出对美国实施冲闯行动、导致局势紧张等系列行为的保留态度。
更具代表性的是菲律宾对外政策的调整:作为原先美国在南海地区最紧密的追随者,菲律宾在国内政府更替后,全面调整南海问题的政策导向,充分反映出美国安全化建构面临的认同不足问题。杜特尔特改变了紧随美国的对外方针,公开反对“他国插手南海事务”,并对南海的“航行自由”问题提出质疑,“南海问题最好通过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谈判解决”“美国及其盟友的‘航行自由’行动自会通过展示武力来激化矛盾”。②李东尧:《杜特尔特警告美国:认清现实吧,别在南海挑衅中国》,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8_11_16_479850.shtml。南海仲裁案中做出的非法裁决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诸多权益,成为美国指控中国妨害“航行自由”的关键依据。然而杜特尔特政府搁置仲裁案问题,重建中菲政治互信,通过双边对话磋商解决争议,跳出了“国际规则”、南海问题国际化的框架,直接对美国所倡议的“航行自由”规范构成挑战,进一步致使其失去了扭曲国际法、制造威胁的正当性。
面对美国试图将“航行自由”问题安全化的指控,中国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回应行动,反驳了美国建构的威胁逻辑:中国并不是南海地区“危险的他者”,相反中国希望南海地区的稳定以及相关争端的和平解决。加强对南海周边国家的劝说和外交工作,稳定双多边关系,其中最为突出的进展是在机制层面提出了管控南海问题的基本路径。2017年5月,中国与东盟国家举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14次高级官员会议,正式通过“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奠定了日后行为准则最终出台的基础。这是中国与东盟国家自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来取得的最重的磋商成果,化解周边国家对中国行为及根本意图的担忧,特别对“军事化”问题的误解,有力地增加中国同东盟国家的互信,也有效地展示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良性动机,部分冲销了美国将安全化行动的影响。由于越南、菲律宾等关键国家并未接受美国的问题建构及解决方式,同时中国进行了去安全化的努力,南海的“航行自由”问题进入相对停滞阶段。
五、结论
绝对意义上的航行自由关乎各国的经济发展与国家生存,无疑是一个安全问题,但在美国的政策语境中,这一概念象征着美国不受限制的海洋霸权,因而中国事实上是美国“航行自由”问题的受害者,对此,美国对中国施以种种安全化操作,以加害于受害者,实现其有效入南海、制衡中国的战略目标:尽管中国的岛礁建设是维护主权的正当行动(而美国宣称对主权争端不持立场)、中美围绕航行自由的争端属于法律理解分歧,美国却将其建构为规则挑战与安全威胁;与此同时,它罔顾一项最根本的事实: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中国才是南海陷入不稳定的首要的和最大的受害者,中国最需要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
对美国的安全化操作的分析表明,它在话语层面将中国的能力建设、利益伸张视为挑战,本质上与其他类型的“中国威胁论”无异,形成“航行自由”问题的“话语陷阱”;行动层面,美国在国际社会面前以“航行自由行动”维护“国际法”,通过戏剧化地方式形塑观众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将中国的“挑战者”身份具体化。目前,部分西方国家、美国的域外盟友对这一问题的认可度较高,已经逐步内化相应规范并采取行动追随,域内国家则对美国的安全化航行自由问题的动机及影响保持一定警惕,在中国去安全化行动的努力下,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呈现出了相对稳定的态势,美国的安全化动议暂时处于停滞阶段,但在中美新一轮博弈深化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存在再度激化的可能。中国依然要在话语与行动两个维度予以应对——一方面,解构美国“岛礁建设—违反国际法—安全威胁”的安全化路径,法律问题存在法律的解决方式,本身与安全问题之间仅存在“弱关联”,中国维护主权权益的行动与美国所言说的“国际规则”无关,同时,应当与广大拥有相同看法的国家一道,在国际舆论当中争取更大的声音,对冲美国曲解国际法的影响;另一方面,除却话语回应,我们可能更需要采取实际行动、消解美国指控的合法性:例如,加强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军事交流合作,在适当的时机展开联合演习,证明顾及他国权益的航行与飞越、甚至军事活动事实上充分享有“(航行)自由”;宣传中国岛礁建设在领航、搜救等领域发挥的积极作用,证明中国对“航行自由”做出的实际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