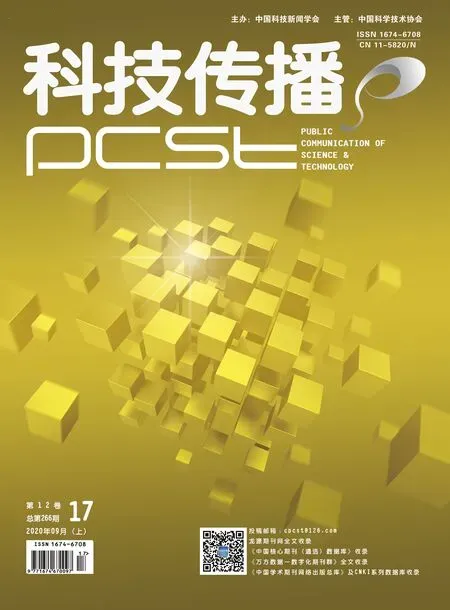融媒体时代风险传播中媒介污名化研究
2020-11-28范宁
范 宁
人类进入风险社会和媒介化社会并存的时代。洪水、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和恐怖暴力袭击、核污染等人为灾害屡见报端。融媒体时代,媒介生态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媒体是信息沟通者、舆论引导者和风险传播者。污名化现象与风险控制和媒介传播息息相关。本文以风险报道中的媒介污名化为研究对象,运用案例研究法,基于框架理论和符号互动理论,探究融媒体时代媒介污名的特点、路径和影响,以期对规范媒体的道德伦理失范行为和更好地进行风险传播有所裨益。
1 融媒体时代媒介污名的特点
1.1 新闻叙事中情感的强化
污名源于偏见,偏见是一种认知预判。融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事实让位于情感更替,公众被情绪裹挟。部分媒体使用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句进行悲情化叙事。当一方拥有话语权形成强势意见气候,“沉默的螺旋”效应被强化,并因风险的隐形性更加难以控制。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心理疾病的罹患风险显著增高。在抑郁症报道中媒体往往将患者与“自杀”和“他杀”相勾连,形塑危险人物的形象进行突发事件报道,不经意间加剧受众恐惧,产生疾病的隐喻。
1.2 施受主体的泛污名化
融媒体时代,施污主体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自媒体信息碎片化、扩散范围广,污名对象会转换,涉及内容会偏移。此外,公众为自我防卫主动贴上弱势标签,以示不具污名身份的属性。部分蒙污者自我炒作,将“污名”视作“出名”。媒体将“中年人”进行叙事指代报道中年危机的议题,建构了“油腻中年男”形象,引发公众的嘲弄和讨伐。部分蒙污者则以“油腻”自我标榜进行“自污”。污名化由单向度变为反向度和双向度,后期蒙污者可能是前期施污者,施受主体界限模糊。
1.3 污名风险的放大化
媒体是强有力的形象塑造者。媒介对风险事件的加工形塑了风险的社会经验,影响社会效应。融媒体时代,风险事件报道数量增多、持久性增强、半衰期减弱,污名风险被放大。风险的社会放大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灾难事件与心理、制度和文化状态相互作用,其作用方式会加强或衰减风险感知并塑形风险行为。反过来,行为反应造成新的社会或经济后果[1]。2018年沈阳出现首例非洲猪瘟疫情后,媒体以“猪毒”“吃死人的猪肉”等误导性词句报道。公众“谈肉色变”,猪肉价格暴涨,出现“炒猪”等群体性事件。
2 融媒体时代媒介污名的路径
2.1 主动污名化
标签化是主动污名化的有效路径。媒体以“概念化”模式对报道对象的负面属性定性,并根据受众信息匮乏和注意力失焦的特点,迅速制定标签,设置污名议程。传播者没有必要向受众过度陈述事实,并刺激他们独立思考,只需发出若干符号,这既减轻传播者的压力,也适应受众迅速得出明确结论的需要[2]。标签化行为迅速波及具有类似标签的群体,引发权力博弈。连续性报道不断强化污名记忆形成刻板印象,当受污者和公众形成“我们”和“他们”的区隔时,主动污名化完成。
从符号互动论来看,这是“符码”和“解码”的过程。一方面,媒体根据原始事件的特征编码,扩展为社会事件。另一方面,标签在公众讨论中泛化,原始事件脱离原有情境被赋予新的意义,引发情感共鸣,并随事件发展持续进行新的“符码”和“解码”。
主动污名化受两种因素影响。一种因素是新闻内部选择。新闻是选择和重组新闻事实的过程。新闻从业者受固有认知和价值观等影响,在报道时自动生成新闻框架。恩特曼认为框架包含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3]。“农村留守儿童”具有新闻价值,这种固有认知方式影响报道的叙述方式、情感倾向和态度评价。在报道《农村留守儿童的艰难童年:不止是霸凌》中媒体用新闻框架去框限符合自己心中负面认知的报道对象,造成“问题儿童”的媒介污名。另一种是外部因素。融媒体时代,时间和眼球成为新闻的生命。部分媒体报道未经证实的网络信息,以耸动为看点,以标题党煽动受众情绪,以媒介污名迎合受众心理,预设观点倾向,歪曲新闻事实。某些媒体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利用社交媒体的圈层化传播制造污名化事件,转嫁风险,放大污名效果。
2.2 被动污名化
媒体是“船头的瞭望者”。突发公共事件中,一方面媒体作为信息处理者,要在第一时间传递信息。另一方面媒体作为信息沟通者,是公众与政府沟通的桥梁。媒体传送外部环境的风险,管控风险的政策给公众,同时反映舆论,及时呈现风险的发展态势、各方反应等,推动信息快速流动。
然而现代风险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突发公共事件伴随着信息恐慌和信息饥渴。媒体作为风险传播的关键一环,受到权威信息缺失和信息不确定性的困扰,但又必须将掌握的信息尽快公布于众。因此,媒体常常被动污名化报道对象。现代社会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不可避免带来一定的风险。部分媒体因专业知识困乏将转基因食品妖魔化报道,刺激了公众关于食品安全的敏感神经,引发新技术恐惧症。
融媒体时代,媒介被动污名化往往与公众污名、自我污名形成联动机制。一方面,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交织,传统二元权力结构被打破,受众拥有话语权。公众抢先对社会事件进行标签化定性,并通过转发、点赞和评论等在社交媒体中传播,自觉形成议题焦点,主动进行污名建构。由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开放性,公众污名往往伴随着人肉搜索和网络暴力,情绪化和宣泄性较强。另一方面,传统媒体“把关人”功能弱化。传统污名现象的三要素是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融媒体时代,污名现象的素材来源和构成要素更丰富,指涉群体更广泛,造成污名泛化。施受双方基于虚拟空间的冲突更激烈,延伸到现实社会,造成交错污名。
3 融媒体时代媒介污名的影响
3.1 干扰受众的风险认知和决策
污名化信息通过社交化网络传播,引发舆论高潮,造成恐慌,误导受众。信息碎片化和更迭速度加快,消解了污名的难度。受众在形成客观认知并做出决策前,媒介建构的风险图景先入为主造成认知干扰。即使专业人士或当事人澄清,也无法确保之前偏向性报道的受众接收并信服。
3.2 影响蒙污者的自我认知和评价
媒介污名导致蒙污者否定自我,形成与污名标签相符的自我评价,社会形象遭到破坏,社会名誉不断受损。当污名标签成为身份区隔和价值判断时,蒙污者承受自我贬损和群体偏见的双重负担。尽管事后污名化效应随真相披露和时间推移而削弱,但其影响并不会完全消失。谈及同类事件时,蒙污者会再次出现在公众话语叙述中。
3.3 损害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媒介污名将“价值判断”凌驾于“事实判断”,消耗公众情绪。由于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权威性不足,公众更信任媒介污名。蒙污者处于被报道的地位,缺少话语权。媒介污名解构社会互信的基础,消解构建理性对话场域的可能,损害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3.4 激发社会的冲突和矛盾
媒介构建潜在风险,掩盖真实风险,形成风险放大。公众把特定群体当成“标签化”的他者,进行言语和人身攻击。污名泛化使现实社会和网络空间充斥污名话语,同类标签信息“累积效应”明显。公众反复接触这些话语,产生态度和行为的对抗,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4 结语
媒介污名化的背后是值得检视与深思的中国媒介伦理的镜像。媒体作为社会守望者和风险预警者,扮演着传播者和沟通者的角色。在风险传播中,媒介是风险认知的重要渠道,参与社会对风险的定义和治理。媒体应科学理性地报道风险,在不确定的信息环境中及时反馈信息,规避潜在风险,同时积极进行消除污名化引导,避免主动或被动污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