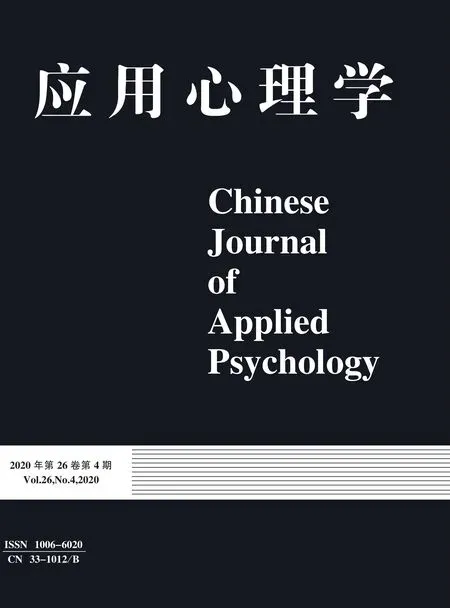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的客观危险与主观恐慌:全球范围内的“心理台风眼效应”
2020-11-2613李纾
13李纾
[1.中国科学院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2.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北京 100049;3.福建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学院,福州 350118]
1 引 言
2020年1月,新冠肺炎(COVID-19)在武汉市爆发,担忧、焦虑、恐慌与害怕是人们在疫情防控期间最本能的反应。然而,以往研究显示外部环境的客观风险与内心的主观风险知觉并不一致,即,客观危险与主观恐慌、担忧、害怕之间的关系常常并非一一对应。尽管危险事件(hazards)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并不存在“真实的风险”(real risk)或者“客观的风险”(objective risk)(Slovic,1999)。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中科院心理所李纾研究组对灾区和非灾区居民进行了大规模调查,研究发现,非灾区居民对灾情严重程度的担忧反而高于灾区居民。即,非灾区、轻度灾区、中度灾区和重度灾区居民对灾区居民恢复到灾前生活水平所需时间和每户受灾家庭所需资金的估计存在显著差异:非灾区居民比灾区居民认为恢复到灾前生活水平所需时间更长、所需资金更多(李纾等,2009);从非灾区、轻度灾区、中度灾区到重度灾区,居民估计核心灾区对医生和心理学工作者的需求量、发生大规模传染病的可能性及需要采取的避震措施的次数均依次减少(Li et al.,2009)。这种反直觉的现象亦得到其他研究的重复验证(谢佳秋,谢晓非,甘怡群,2011;Li et al.,2020)。后续的调查进一步显示这种效应并不是暂时出现的,在震后1个月、4个月和11个月后,灾区与非灾区间仍然存在这种现象(Li et al.,2010)。因此,李纾团队借“台风眼”一词对该现象进行了命名(李纾等,2009)。所谓“心理台风眼”(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指的是越接近风险中心区,个体对灾区危险的心理反应越平静,风险知觉水平越低。
新冠肺炎疫情所导致的风险显然不同于2008年发生在汶川的大地震灾情。在汶川地震中,地震中心是明确且唯一的风险源。而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虽然疫情的重灾区源于武汉,但客观的风险源已遍布全国,并且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也先后暴发疫情,即使离开了武汉,身边仍有客观的风险源存在(许明星等,2020;温芳芳等,2020;Zhang,Huang,& Wei,2020)。
为了探索心理台风眼效应是否有可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再次被侦测到,研究者于2020年2月20日至2月25日开展了一项由多国受测者参加的调查研究。对受测者反复强调,本次调查是对“武汉市疫情”的风险知觉的调查,而不是对“一般的、身边的疫情”的风险知觉的调查。
2 方 法
2.1 受测者
通过微信推送“问卷星”电子版问卷(国外受测者通过海外高校联盟群、捐赠者群获得),调查了353名身处中国和国外(据填写居住地)的成年受测者。所有受测者均是无报酬地完成调查问卷。样本的组成比例情况见表1。

表1 人口统计学变量(N=353)
2.2 变量测量
在调查中,受测者填写其性别、年龄、居住地、身份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信息(表1)。
参照前期在汶川地震中所采用的测量指标(Li et al.,2009;Li et al.,2010),设计了民众在防疫期有关安全健康的问题,作为投射人们对“武汉市疫情”(客观危险)的主观害怕的测量指标。
这些问题大致可分为2类:一类是“个人防范”相关的安全题项,如对“量体温次数”与“换洗衣次数”;二类是与“人际防范”相关的安全题项,如“聚会次数”和“握手次数”。
本研究沿用了前期在汶川地震研究中对风险知觉的评估方法(Li et al.,2009),我们假设受测者对武汉市疫情的风险知觉水平越高,受测者对“个人防范”相关投射问题所评估的数值(如换洗次数)则越大,对“人际防范”相关问题所评估的数值(如握手次数)越小。
3 结果与分析
为了考察离武汉不同距离的受测者对武汉市疫情的风险知觉,本研究采用了两种衡量“距离”的维度。
3.1 国门之内的近距离和国门之外的远距离
研究者根据受测者受测时所处的国家地区,将自变量“距离”分为“中国”“亚欧”“大洋及北美”三水平。此分类有两个依据。首先,从地理空间上看,除中国外的亚欧地区与中国同属亚欧板块,而大洋及北美与中国相隔太平洋,这三个地区与武汉市的客观距离逐渐增加;其次,从疫情发展轨迹看,在施测时中国仍为全球疫情最严重地区,但亚欧其他地区疫情发展迅速属于中等严重程度,大洋及北美疫情严重程度最轻,疫情严重程度也是层级递减。因此,此分类满足了客观上国内、亚欧、大洋及北美三个地区与武汉距离有层级递增的关系。
因变量“聚会次数”由题项“您估计武汉人在春节期间会聚会几次?______次(0~30次)”测得;因变量“握手次数”由题项“您估计武汉人在春节期间会与人握几次手?______次(0~100次)”测得。
以性别、年龄、身份
由于“知道附近小区有确诊病例的人”“参与相关工作的医务人员和疾控人员”“密切接触者”“患者或疑似患者”“其他”此5类身份受测者对疫情均有一定的卷入程度,且人数也较少,因此统计分析时将此5类身份合并为同一类。以下统计中处理方式相同。
、地区客观风险


图1 受测者受测时身处的国界与“人际防范”风险:估计武汉人聚会次数(a)和握手次数(b)的关系
3.2 主观(心理)距离和客观(物理)距离
主观(心理)距离。采用受测者自我评定的离武汉市的主观(心理)距离(最远距离为100,最近距离为0)作为自变量。
客观(物理)距离。将受测者离武汉市的空间距离(最远距离为11,664公里)的对数值(lg客观距离)作为自变量。
因变量“量体温次数”由题项“您估计武汉人在春节期间测量了几次体温?______次(0~100次)”测得;因变量“换洗衣次数”由题项“估计武汉人在春节期间会换洗几次衣物?______次(0~100次)”测得。
以估计武汉人“量体温次数”和“换洗衣次数”作为因变量,性别、年龄、身份、地区客观风险作为控制变量,剔除因变量中超过±3个标准差以外的极端值,分别进行层次回归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主观(心理)距离对“量体温次数”和“换洗衣次数”的回归方程显著(F量体温次数(5,344)=2.97,p=0.012,R2=0.041,调整后的R2=0.027,BF10=19.272;F换洗衣次数(5,335)=2.80,p=0.017,R2=0.040,调整后的R2=0.026,BF10=5.018)。在控制了性别、年龄、身份及地区客观风险的情况下,受测者所在地离武汉市的主观(心理)距离越远,他们对于“量体温次数”(图2a)估计越多,对“换洗衣次数”(图2b)估计越多(β量体温次数=0.23,p=0.002;β换洗衣次数=0.19,p=0.012)。
lg客观距离对“量体温次数”回归方程边缘显著(F量体温次数(5,344)=2.08,p=0.068,R2=0.029,调整后的R2=0.015,BF10=2.681);对“换洗衣次数”的回归方程显著(F换洗衣次数(5,335)=2.79,p=0.018,R2=0.040,调整后的R2=0.026,BF10=4.889)。在控制了性别、年龄、身份及地区客观风险的情况下,受测者离武汉的客观(物理)距离越远,他们对于“量体温次数”(图2c)估计越多,对“换洗衣次数”(图2d)估计越多(β量体温次数=0.23,p=0.026;β换洗衣次数=0.27,p=0.012)。
总之,在审视图1、图2所示的结果后,可得出一个较肯定的结论: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仍然侦测到了心理台风眼效应。即,“远离”武汉的民众,他们知觉到的武汉疫情的风险水平显著地高于“接近”武汉的民众知觉到的武汉疫情的风险水平。处在“心理台风眼中心”(武汉)的受测者,他们对疫情中心风险水平的估计反而相对是最低的(最风平浪静)。
4 讨 论
本研究侦测到了延至国门外的“心理台风眼效应”。调查显示,远离武汉、身居国外的受测者甚至比身居国内的受测者对武汉的疫情更加担忧(如,估计武汉人聚会次数、与人握手次数更少)。在汶川大地震时侦测到的心理台风眼效应(Wei,Tao,Liu,& Li,2017)在武汉市疫情中得到再次验证。该效应提示我们应谨慎对待风险调研结果,应该充分认识到风险中心区民众评出的风险等级与非风险中心区民众评出的风险等级的“不匹配”或“偏差”。以下,我们从该效应的潜在机制以及影响作用入手,对研究结果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以及局限进行讨论。

图2 受测者身处地与武汉的主观(心理)距离与“个人防范”风险:估计量体温次数(a)、换洗衣次数(b)的关系(上图);受测者身处地与武汉的客观(物理)距离与“个人防范”风险:估计量体温次数(c)、换洗衣次数(d)的关系(下图)。
“心理台风眼效应”潜在机制的探讨。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心理台风眼效应”能够同时出现在汶川大地震和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之中?我们猜测“风险信息占比”或可成为该效应的主要原因。风险信息占比是指“某地区发生风险事件的相关信息量”与“某地区发生所有事件的总信息量”之比,其中,某地区发生所有事件的总信息量=某地区发生风险事件的相关信息量+某地区发生其他事件的信息量。以近段时间发生的澳大利亚林火事件为例,去年没有到过悉尼的人会认为悉尼山火非常危险,而去年到过悉尼的人会觉得悉尼山火没有那么危险。这是因为,身处悉尼的人,所听所闻既不完全是与林火无关的信息,也不完全都是林火信息。对于疫情而言,2020年2月,中国累计确诊人数从2月1日的11821人升至2月29日的79394人,其中湖北累计确诊人数占比从60.51%升至83.6%。海外累计确诊人数从132人升至6009人,其中,亚欧地区其他国家(除中国外)累计确诊人数从105人升至5178人,其间日本钻石公主号以及韩国大邱地区爆发了集体感染,意大利自2月下旬确诊人数从20人骤升至千人以上;大洋及北美地区确诊人数从23人升至101人。可以看出,2月期间,全球疫情“震中”仍是中国。但亚欧地区其他国家确诊人数迅速增长,而大洋及北美地区在此期间疫情并不严重。因此,虽然此次疫情在国内外多点爆发,但在我们调查期间,全球民众主要接收的仍是武汉疫情信息,即“某地区风险事件相关信息总量”相对稳定。据此,我们推测,对于大洋及北美地区民众而言,他们从新闻报道获取的武汉信息可能均与疫情有关,因而导致其判断武汉疫情非常严重;而国内民众在了解武汉疫情的同时,也获取了与疫情无关的信息,比如民众生活物资充足,居家生活丰富多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于武汉疫情的过度反应。如果这种猜测能在此次疫情中得到实地、实时验证,那么,媒体在报道疫情中心武汉或者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时,应该同时报道与新冠肺炎无关的信息,让国内其他地区的民众像武汉本地人一样感受到真实、完整的武汉,让国外民众像我们一样感受到真实、完整的中国。从而有效避免国内民众对武汉市或湖北省产生“地域黑”,避免国外民众对国内疫情的过度反应和偏见。
建议舆情处置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心理台风眼效应”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在舆情信息分析、预判预警阶段,对于灾情中心区:应着重预判民众是否“低估”灾情的严峻性,民众是否具有基本的危机意识;对于非疫病中心区:应注意预判民众是否“高估”灾情的严峻性,国内,甚至国外广大民众是否对新冠肺炎疫情产生了不必要的担心、焦虑或者恐慌心理。在此基础上,保证后继的风险响应措施与灾区的实际风险程度高度匹配,从而“无偏差”地为舆情干预做出正确的决策。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的研究局限。首先是抽样问题,本研究涉及的被试遍布世界各地,虽然我们尽可能地保证了被试居住地的多样性,总计共来自19个不同地区。但是不同地区的被试数量比例却相差很大,最多的为国内被试,占比63.7%,最少的为0.3%,包括印度、意大利、新加坡等地。由于我们是通过微信链接分发问卷,填写问卷的受测者均是汉语为母语且身居海外的华人或华侨,所以我们并未测量到母语为外语的国外民众对于武汉疫情的知觉。未来可以通过丰富样本地区多样性来改进研究。其次,关于心理台风眼的潜在机制问题,本研究只提出了事后假设(梁觉,2011),未来当收集数据进一步对该事后假设进行实证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