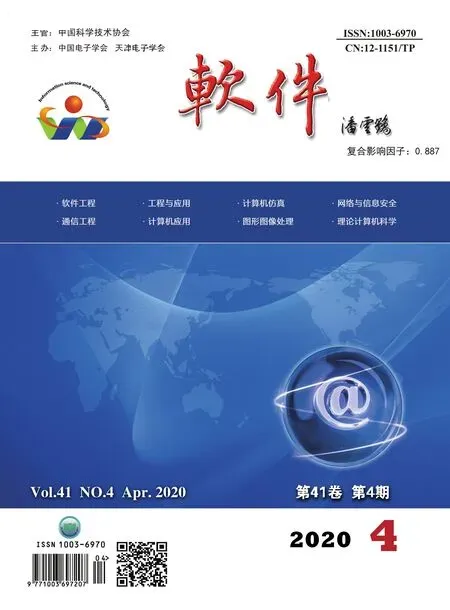论信息技术运用境域中的当事人诉讼权保障
2020-11-26詹乔乔
詹乔乔
(扬州大学法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7)
0 引言
当今世界是一个信息技术社会,司法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屏障,使用信息科技变革诉讼方式,也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电子诉讼[1]也应运而生,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更为全局性的智慧法院。由于电子信息技术对传统诉讼程序的变革不是简单地将传统诉讼搬运至网络虚拟环境,必不可少地会对当事人的诉讼权产生影响。因此,关注信息技术在民事诉讼的主要运用方式、对诉讼权利行使的影响,并探讨如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非常重要。
1 民事诉讼中电子信息技术的基本应用
最高院对地方各级智慧法院提出的建设要求更进一步促进司法实践从受理起诉直至执行的全流程自动化进程。民事电子诉讼是以“全业务、全流程、全方位”为标准的“一站式”信息化系统建设,涵盖网上调解、网上立案、电子送达、网上办案、网络司法拍卖、电子卷宗等诉讼业务的实践应用。[2]其中,网络远程执行是目前电子信息技术对于民事诉讼现存问题解决的最大助力
电子法院可分为外部电子法院与内部电子法院,内部法院并不改变法院传统的组织结构、管理原则,是法院内部关于案件的电子数据管理形式。而外部电子法院则是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司法服务,也是研讨电子诉讼中当事人诉权保障的核心部分。[3]
2 信息技术适用中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影响
“诉讼是一个信息传递和交流过程,表示信息的符号和承载符号的物理介质的变化,必然会相应地改变诉讼行为与审判行为的方式。”[3]这种改变势必会影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这就需要谨慎观察并正确看待电子诉讼变革带来的影响。
2.1 对起诉权的影响
电子信息技术已实现从起诉开始就能通过互联网便捷完成一系列诉讼行为。但由于缺少人工比对认证,可能出现他人冒用当事人的身份提起虚假诉讼,网络平台本身的安全隐患也可能造成当事人信息泄露。其次,网上提交诉状的平台未必实时,当事人可能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或其他原因短缺相关材料时就不能及时得知补正信息而影响立案成功。根据最高院相关文件不难看出,推动电子诉讼的普及势在必行。然而,网上投递诉状对基础设施和当事人的知识水平有一定的要求,这方面也对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2 对受送达权的影响
人们对于网络技术使用的频繁也给法院的送达带来了便利,电子送达原本是以节省人力物力为初衷,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于往往真正偏远的需要电子送达的地区不具备受送达的基础条件,即使技术不成障碍,“同意电子送达的当事人往往不存在送达难的问题,真正有送达难的当事人却往往不同意电子送达。”[4]那么如何在电子送达的情况下确保当事人已受送达是应当解决的问题。
2.3 对举证质证权的影响
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对当事人举证质证权产生以下两种影响:一是证据本身为电子数据时如何举证;二是证据由当事人、诉讼辅助人及证人在各空间通过远程传导技术实时完成诉讼活动。
电子数据本身特性决定了若将其转换为文本或图片反而不能精确保存证据本身的特点,且一经转换就成为传来证据,实务中往往需转化书面材料并公证。但对电子数据进行公证其实是将该证据固定在特定的时间点,而电子数据可能是实时变化的。[5]而电子数据本身却也存在着易修改、易伪造的特点,如果单纯地直接提交又难辨真伪,不利于双方当事人的质证以及对举出的证据事实的证明。导致实践中司法人员对电子证据往往不敢大胆采用,也出现了直接不予说理或说理不明的情形。[5]
其次,远程视听技术确实为当事人举证质证提供了技术便利,但再清晰的视频和音频的技术水平都无法代替当事人的现场观测。当事人可能通过对实物证据的触摸、近距离观测或者对出庭作证的证人的现场接触而对证据三性提出异议,此都并非远程网络可以取代,当事人极有可能就是通过利用远程网络极难反应出的细微细节差异而提出质证意见。
2.4 对庭审辩论权的限制
辩论权是当事人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在远程视听传导技术的帮助下,当事人可以免除舟车劳顿的成本,但双方都使用视听传导技术的情况下却产生了对诚信原则的高度依赖。
在一方当事人使用远程庭审技术的情况下,如若该方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因技术原因出现画面中断、音视频不清晰、提前撤除信号等情况,当事人也可能故意在提前约定使用远程庭审后而不参加庭审等情形,都影响了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其次,在被告必须出庭的民事诉讼中被告也可能在同意远程的情况下缺席庭审,也损害了原告的辩论权。有学者提出在互联网法院的建设中可以加强书面审理减少成本,笔者认为辩论权作为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不应因电信技术的发展而受到限缩,因无论是网上辩论(即使是文字辩论)或是线下辩论都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一种行使方式,也是实现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保障。
2.5 对直接言词主义的影响
直接原则又称直接审理主义,即审判的法官必须亲自聆听辩论和调查证据的原则。”[6]“言词原则要求法官、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法庭上都要以言词的方式进行诉讼行为。”[7]直接言词原则强调法官对庭审的亲历性而形成自由心证。
依托远程视听传导技术,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可以不亲至法院庭审现场便完成诉讼活动,但是现场视频的画质、音质却未始见得会与当事人亲临法院庭审现场的效果相同,这就不利于法官通过观察当事人、证人的诉讼行为而形成准确客观的心证。此外,视听技术容易架空法院的威严感,技术便利提供了轻松的氛围,而一定程度上减损了司法裁判的权威。
3 民事司法信息化发展中当事人诉讼权保障的完善
2018年9月最高院颁布了《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对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从起诉至执行都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裁判指引。笔者认为在实施《规定》时应注意对当事人诉权的切实保障,既要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维护法庭的权威,也不能放弃电子诉讼的推广,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 程序选择权保障的完善
为防止他人冒用适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身份加入诉讼从而损害其他人正当利益,《规定》第六条要求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使用诉讼平台实施诉讼行为时应当通过国家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在线完成身份认证等安保措施。笔者认为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智慧法院(广东)实验室的做法,与公安数据实时对接,可迅速验证诉讼参与人身份信息,[8]防止他人冒用当事人的身份信息提起虚假诉讼。
“信息时代比以往人类的任何发展时期都更加注重用户体验,用户体验感不佳的产品都会被市场迅速淘汰。当事人作为诉讼程序的用户,其程序自由选择权也理应得到彰显。”[9]《规定》未明确规定当事人是否可以在进入线上后转为线下提交文书。由于电子诉讼运用对当事人的能力水平有一定的要求,极有可能产生当事人原本在网上发起诉讼,却发现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诉权的情形,此时应允许当事人提出转换申请,法院应令当事人说明理由并作出决定,以避免当事人滥用权利而拖延诉讼。若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则应尊重双方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
3.2 举证质证权与庭审辩论权的保障
《规定》中关于当事人举证质证权保障的内容集中在对电子数据真实性产生异议时的审核标准,但偏向于对证据生成、保存的主体、环境等方面提取共同点做出较为抽象的规定。笔者认为《规定》对于电子数据采纳与否的标准可以更细化至种类,才能使司法实践人员更有依据、更有信心采纳电子数据。此外证人作证是一项义务而非权利,对证人作证的要求应以当事人的需求为优先。对于非因法定原因需要远程作证的证人,法院应在庭前准备阶段寻求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只有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才能允许证人远程作证。但如果证人出庭作证所可能实现的实体利益远大于其出庭作证所需成本,受诉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在庭审辩论权方面,由于电子化庭审面临着会出现技术内或技术外的原因使诉讼行为不能顺利完成的风险。目前仅少数国家允许远程庭审。因此,庭审环节不应作为电子诉讼的重点——视频庭审只应被作为例外对待。[10]《规定》中限定了互联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在与互联网有实质关联的民事、行政案件,这一谨慎的态度体现了对当事人辩论权的尊重与保障。笔者认为,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互联网法院管辖的涉网案件,电子化庭审只宜经过双方当事人同意才能采用。《规定》没有要求当事人在庭审前就与法院确认一个稳定的信号环境以保证庭审的顺利实施,笔者认为这一环节的确认是必须的,以避免一方当事人因技术原因不能顺利进行庭审而造成对方当事人诉讼成本的浪费,法院甚至可以指定方便当事人实施诉讼活动的邻近信号稳定的场所,根据此类场所能提供的音画水平给予许可。
3.3 受送达权保障的完善
《规定》虽认可了网上公告送达的效力,对于不同程序却没有做出不同的送达标准区分,笔者认为在此基础之上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重大程度对送达确认标准划分等级,如对重大、疑难的案件中的电子送达要求当事人通过电子签名予以认可。如果是商事主体、国家机关等经过法定登记的主体,可允许此类主体在法院相关系统备案电子签名便于认证。其次,现行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虽未许可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的电子送达,但电子技术便利的当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意愿。考虑到电子送达的确认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裁判文书、调解书又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则宜作为补充送达方式,由当事人约定适用。
4 结语
在电子信息技术为法院、当事人提供诉讼便利的同时也应注意诉权保障的价值位阶高于效率的追求,电子诉讼地进行不能损害当事人的诉权。只有明晰传统诉讼行为变革对诉权的影响,发掘变革隐藏的问题并把握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才能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