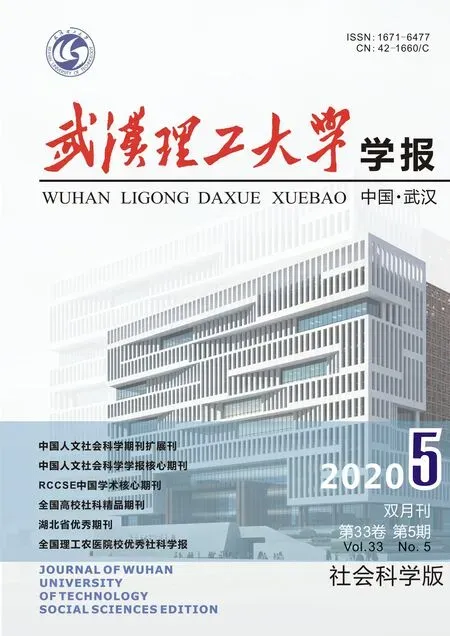智慧城市的可沟通性三重维度建构*
2020-11-24王震
王 震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商学院,江苏无锡 214081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智慧城市的愿景,对普通市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1]来自美国学者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de Sola Pool)对智慧城市建设意义的追问,引发了人们对智慧城市建设“重技术轻沟通”的反思和批判:一方面,智慧城市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者”认为,“智慧城市”是能够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实现各项系统运行的城市,其概念涵盖硬件、软件、管理、计算、数据分析等业务在城市领域中的集成服务;另一方面,智慧城市的“人本主义学派”认为,智慧城市不是局限于“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概念,而是一项注重人本因素和市民体验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创新共享的全球事业。
肇始于ICT(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技术革命带来的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十年前我国智慧城市的概念尚属于技术层面的概念,研究主要偏向以物联网、传感网、云计算、数字技术为主的通信技术,也涉及一些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研究。可以说,智慧城市是以物联网、宽带等智能技术高度集成为基础,以智慧服务高效便民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发展新模式,城市建设逐渐向物联化和互联化的人、物发展,其研究涉及到了智能楼宇、智能家居、智能医院以及数字化生活等等领域。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已走过了十多年历程,如今,“智慧城市”概念早已不等于“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智慧城市需要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扩容性,须落实到人和城市的有效沟通机制上来,才能避免“能上天但不能落地”的情况。城市建设是否“可沟通”引发了从技术理念到人文理念的哲学思考,把“沟通”理念纳入到智慧城市的规划中,探究智慧城市的可沟通性是什么以及如何构建分析维度,正是本文研究视角所在。
二、城市可沟通性理论溯源与评述
与“智慧城市”建设发展时间轴同步,“可沟通城市(Communicative city)”作为城市传播研究的创新理论,其提出亦有十多年时间。1997年德国学者昆茨曼(Kunzmann K. R.)首次提出“可沟通城市”,谈到了信息和通讯技术服务于公众,奠定了可沟通概念来源。2008年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杂志同期刊登了关于城市传播的三篇论文,充分奠定了可沟通城市概念的理论来源与基础: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传播学者尼克·卡彭铁尔(Nico Carpentier)通过The Belly of the City : Alternative Communicative City Networks一文延展了昆茨曼提出的可沟通城市的话语和实践基础,通过公民参与维度探讨了可沟通城市的公共空间多维开放性[2];美国首批传播学者哈姆林克(Cees J. Hamelink)在Urban and Conflict and Communication一文中,正式提出城市的“可沟通”是“公民行使城市权利的基本要素”[3];美国城市传播基金会(Urban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学者甘珀特(Gary Gumpert)则直接以Communicative Cities (可沟通城市)为题撰文,给出了“可沟通城市”的三个基本面向:公共空间、沟通交流、物资设施[4]。此后的2010年,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传播学院学者Jeffres在The Communicative City: Conceptualizing, Operationalizing, and Policy Making中提出,“可沟通城市”的研究策略应包括如下层面:(1)培养城市凝聚力;(2)加强包容性,如不同年龄、种族、民族、政治态度、消费阶层、新旧居民等各类群体之间沟通;(3)促进对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5]。2016年,德鲁克和甘珀特在国际传播杂志再次发表The Communicative City Redux一文,明确了可沟通城市的几个传播维度的视角,如:城市的物理结构(Physical structure)、基础设施、连接设施和服务(Infrastructure or connective facilities and services)、连接个人的社会结构和组织(Social structures and arrangements that link individuals)、虚构和非虚构的描绘构成(Fictional and nonfictional depictions that structure the imagination)[6]。基于以上文献梳理可知,“可沟通城市”的提出在城市与传播之间已形成较为独立的学术内涵,其探索正击中了“可沟通性”这一概念的源头。
“可沟通城市”概念提供了理解城市的一个全新视角,它是继芒福德的“城市容器论”、基特勒的“城市即媒体”、麦奎尔的“媒体城市”等城市传播理论之后的又一创新理论,上述理论或者从“社会与城市的关系议题”、“媒体与城市的关系议题”,或者从“传播与城市的关系议题”来开展城市研究,而“可沟通城市”理论则更进一步揭示了“城市作为人居中心”的本质特征,着眼于人本身,从人的体验与关系入手,勾连了城市的多种要素与过程,对城市建设提出了更加人性化的品质要求。2014年,深圳大学吴予敏将“可沟通城市”概念首次引入国内,从城市媒介化生存现代性取向和城市沟通的公共性取向的二者区别出发,指出智慧城市建设应解决人机交流、城市文化认同、弥合“数字鸿沟”等问题,可沟通城市是媒介化变革推动下形成的基于城市文化认同的社会共同体[7]。2015年始,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连续推出关于城市可沟通性的系列论文,对“可沟通城市”进行了系列研究。“‘可沟通城市’概念是基于传播研究新范式——城市传播——的理论创新,而以‘可沟通性’作为评价城市的基本指标则是这种范式与理的具体应用”[8],作为媒介的城市,只有可沟通才可实现“连结、沟通与共享”的传播学价值主张。孙玮教授从认知城市与人类的关系出发,提出城市可沟通的四大议题:一是城市如何既尊重多样性又打破区隔;二是城市传统与现实的时空感平衡问题;三是城市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融合;四是城乡、社区、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9]。“可沟通是现代城市的基本品质”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信息传递的快速、高效、透明,二是社会交流的自由、通畅,三是文化意义的建构与分享[10]。复旦学者们从传播来理解城市,提出“地理网(或物联网)”、“社会网”和“意义网”作为城市网络形态的传播学解读[8],并又从城市传播的不同面向凝练出了“地理网”、“信息网”、“意义网”三重网络作为城市“可沟通性”评价体系[11],促进了城市“可沟通性”的跨学科理论基础的形成,初步厘清了“可沟通城市”与城市“可沟通性”的概念与价值内涵,开拓了跨学科研究城市的新领域、新范式。
从昆茨曼、卡彭铁尔、哈姆林克、德鲁克、甘珀特、Jeffres等国外学者对“可沟通城市”理论的不断探索和发展,再到吴予敏、谢静、孙玮等国内学者对城市“可沟通性”的价值诉求分析和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可以看到“可沟通性”作为一个技术哲学名词是“可沟通城市”理论在城市传播范式研究下不断演进和创新的一条学术进路,更可被视为探究“智慧城市可沟通性”的理论基石与逻辑起点。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最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智慧城市正在成为全球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而如何运用已有的可沟通性理论,探讨智慧城市的可沟通性维度构建,这是城市传播在“智慧城市”层面的又一次理论纵深和创新性尝试。
三、智慧城市的可沟通性议题与维度建构
通过梳理,可以说智慧城市的“智慧化”显然是和“可沟通城市”概念的提出是同步的,智慧伴随着沟通,2009年IBM公司发布《智慧城市在中国》的报告,提出“智慧城市”的四大特征,即全面物联、充分整合、激励创新、协同运作。十余年来,以物联网技术演进为导向的智慧城市建设仅仅是窄面向的后现代数字城市,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促进了媒介城市研究的物质性转向,也加速了主流传播学对社会基础设施、城市建筑物以及包括人类身体等物质进行跨学科化的融合研究,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正进入3.0阶段,智慧城市概念亟需跨学科的多维度建构。同时,智慧城市作为全球城市发展的主流,是技术智慧、治理智慧和公众智慧的多元融合和有机汇聚。技术智慧是基于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运用的城市数字化技术系统,用于构建城市环境的物质要素和物理结构,属于智慧城市的“硬件”要素;治理智慧,是基于政府规划与治理的社会空间管控系统,用于构建连接个人和管理检测环境的社会结构,属于智慧城市的“软件”要素;公众智慧是基于公众参与的人文诉求价值系统,用于构建城市意象和文化精神的虚构和非虚构结构,则是智慧城市的“湿件”要素。智慧城市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具有涌现性、动态性和自组织性的复杂网络——智慧城市网络,不仅指城市物质、地理之间通过技术而实现的广泛连接,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与协调合作,以及经由象征符号而实现的文化共享与认同,这些网络的形成都是基于可沟通城市的传播特质而建构的。
“智慧城市的可沟通性”其实是作为一种媒介城市空间的智慧哲学理念而构建的,应主要包括“物联网”、“社会网”、“意义网”三重维度,其具体构成要素如下:(1)物联网的可沟通性具有实体性、实时性、实效性特质,包括基于技术互联、物质互联和地理互联的可沟通性;(2)社会网的可沟通性具有媒介化、信息化、社交化特征,主要包括基于媒介城市维度、信息传播维度、社会治理维度、公众参与维度的可沟通性;(3)意义网的可沟通性具有符号性、象征性、形象性特征,主要包括地域认同与象征符号、城市精神与品牌形象等文化维度的可沟通性。三个交互融合的“网络”形成了智慧城市虚实互嵌的开源特质,由此可建构智慧城市可沟通性维度理论,如下表1。

表1 智慧城市可沟通性维度
(一)物联网:智慧城市可沟通性的实在面向
最早的“物联网”概念是麻省理工学院Auto-ID研究中心1999年提出的,物联网是指利用射频识别技术(RFID)、无线数据通信技术等构造的一个实现信息实时共享的实物互联网。在智慧城市建设的信息技术视角下,物联网是互联网进化的一个全新理念或形式,“物联网”即“物与物相连的互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简称IOT)。“物”的含义必须要满足有相应的信息“接收器”、数据传输的通路、有一定的存储功能,并且关键要有处理数据的CPU并获得属于自身网络节点的IP地址以实现智慧城市的泛在感知场域。智慧城市在媒介融合视角下“物与物、物与网、物与人相连”的可沟通形态网络建设,主要包括技术、地理和物质三个构面的可沟通性要素,具有实体沟通、实时沟通、实效沟通的传播特质。
1.技术互联。传播学界把“数据挖掘”、“云计算”、5G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冠以“媒介融合技术”之名,归类到传播学的媒介场域中进行推演,物联网本身的定义即可作为智慧城市可沟通性的技术维度。与智慧城市相关的物联网技术主要基于三个层次:即感知层(通过人机交互射频识别、地理遥感等技术进行人工智能化的深度学习而实现人、建筑、汽车等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等的全面感知);网络层(通过5G和IPV6技术、三网融合等组成的泛在的无线传输网络技术);数据层(通过云计算、边缘计算平台实现城市各系统的数据集成,促进城市运营系统服务的交互与共享,以提高智慧城市的协同治理、运作与服务)[12]。随着2020年实现5G商用,预计2020年—2025年,5G直接拉动的物联网连接数将累计达到124.5亿,物联网无疑是智慧城市实现可沟通的技术支撑。
2.物质互联。智慧城市场域下,物联网首先具备“物质”特征。智慧城市建筑表皮媒体化,建筑物和街道公共空间的意义文本与文化符号得到了聚合化传播,城市的物质性互联意涵实现价值归拢和放大。城市各种形态的基础设施中介在任意时空和地点,公众都可以进行沟通,诸如城市中的建筑立面大屏幕与人的互动、建筑本身与人的互动、公交车与人的互动等等,都是城市空间和时间交织成的数据流,最终转化为被人类触及并感知的意识流,不断形塑着人类日常居住的空间场景。物质性传播域展示了地方空间的象征表现力量、空间媒体传播意义的力量、公共空间的意义竞争的力量、流动空间网络化与塑造真实空间的力量,以及隐身在这些都会区域空间媒体之后的都市价值与市民角色建构之过程。传播学的“物质性转向”是2019年上半年我国传播学界较为前沿的视角,物质性是指媒介的作为一种基础设施的存在和连接,可视为媒介理论演化对“万物皆媒”的学理回应。城市的基础设施和中介物提供了跨越时空的联结性,促使人类的主体意识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感知重构,人类大脑和身体自身也以共时性沟通机制纳入到物联网的传播中。物联网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城市的物质都具场景意识的神奇世界,也是“作为媒介的城市”沟通表征,而各学科的跨界研究才刚刚站到了起点。
3.地理互联。地理互联主要基于测绘技术领域的地理遥感技术的运用,用来解释物质和人的“连接”。在大数据时代,地理互联将为智慧城市提供包括人类活动的室内外及地面上下所有空间的各种不可移动的实体(对象)的“全息三维”服务。基于GIS地理位置服务的地理网互联下的智慧城市拥有两个“万亿产值”的地理信息:“万亿产值的智慧城市中的地理信息”和“万亿产值的虚拟现实技术中的地理信息”,比如基于AR(增强现实)的自动驾驶、智慧旅游、智慧停车、智慧交通、智慧公安、智慧物流,以及测量城市美丽指数、综合指数等。当AR得以普及,对三维的地理信息将会有更大的市场需求,IP地址空间化,GIS网络空间与实体空间将发生更深层次的融合,城市“大社交”神经网络系统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城市地理互联空间。
(二)社会网:智慧城市可沟通性的交互面向
城市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建构的网络,在城市中,每个人尝试建立与自己生活相关的网络。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将城市空间从物理意义上的居住空间扩展到精神交流、文化交融和社会表达意义空间,指出市民自由、公开地辩论公共事务从而形成的公共舆论是一种市民化社会,是公共领域形成的基础。2018年英国Smart Cities World最新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排名前三的智慧城市需求是“共享数据、公民参与、公民服务”。依托各类传感终端进行感知沟通和社会信息生产,可以说智慧城市就是一张“社会网”的缩影:一个媒介化的、信息化的、治理化、参与式的沟通性社会。
1.基于媒介化城市的社会网。无论从传播学拉斯韦尔的“5W”经典模式、香农韦弗的编码和译码,还是两级传播理论出发解释,城市大量传感器收集的数据构建了智慧城市公众的社交网络,公民的意见和情绪通过传感器反馈,城市的居民和游客通过社交媒体及时分享他们的观察、思想、感受和经历,打造全新的传播意识和理念。按照《未来简史》一书中的说法,人类正在从“智人”迈向“神人”,人类正在借助VR(虚拟现实)和AR等典型技术把现实空间和赛博空间联系起来,城市“万物皆媒”的形容已成现实,城市就是物联网布局下“连接一切”的媒介化社会,城市万物包括人类本身都将陆续完成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智慧城市打造的社会网络空间大幕正在徐徐拉开。城市的人、物、流都可以在数字空间里获得数据同步,社会网化的虚实沟通空间正在还原为一个全息三维的城市运行状态。
2.基于信息化城市的社会网。卡斯特(M.Castells)曾经把信息主义范式下的城市新形态表述为“信息化城市”:“由于新社会的特征,即以知识为基础,围绕着网络而组织,以及部分由流动所构成,因此信息化城市并非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的特征是流动空间的结构性支配。”[13]智慧城市的信息化建设主要从城市规划建设、城市基础空间数据库建设、城市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应用、城市整体信息化四个角度来展开,通过射频网络识别(RFID)等技术建构的传播场域,促进了智慧城市的虚拟化、移动化、泛在化,从互联网、电网、通信网、车联网、数字传感网、工业数据网等方面实现社会沟通的协同共享和信息资源立体化,城市居民由此发展成智慧城市的网络化居民。
3.基于规划治理的社会网。智慧城市的建设、运营是面向社会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所有参与建设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对整个城市规划治理的高度整合和设计。要从城市的发展方向的纲领与指南的战略体系,以市民生活为核心的社会活动体系,资源可循环利用的绿色可持续经济产业体系,城市各子系统(社区、建筑、生态等)布局的空间体系,信息技术支撑下的技术体系(感知层、网络层、数据层)等方面,来规划智慧城市的战略与综合治理。“为民、便民、惠民”的以人为本导向是顶层设计的第一原则,依据城市的战略定位、历史文化、资源禀赋、信息化基础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进行科学定位,合理配置资源,最终实现以人为本、融合共享、协同发展、多元参与、绿色共赢、创新驱动的城市社会环境[14]。
4.基于公众参与的社会网。1961年,美国城市规划专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谈到:“唯有人的参与才能实现城市为人所用”,这一强调社区和公众参与的“雅各布斯传统”正在被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多样性、智能化发展所增强和实现,各国政府都在积极运用多种新媒体方式加强政府和民众的沟通协作,促进智慧城市的可沟通性建设。如西班牙马德里决策公共参与平台、英国智慧城市咨询平台、新加坡“民情联系”平台(Reach Everyone for Active Citizenry @home,REACH)、欧洲2020战略等,都在积极实施自下而上的智慧城市建设路径,注重发挥“公众智慧”。一个显著的成功案例是,雅典市在2018年实施了基于云计算的“Novoville”公民参与平台,在运营的五个月内,应用程序帮助雅典市民解决了22500个请求,同时向市民发送了8500条短信和2500条推送通知,显著提高了公众与市政当局之间的沟通质量和频率。
正如前文所述,城市的“可沟通性”是“公民行使城市权利的基本要素”,基于公众参与的社会网建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要建设具有高度聚集、纵横交错的智慧城市运行系统,使人流、资金流、物流、能量流、信息流高度交汇,在城市物理环境、信息空间和人类社会之间形成多要素、多维度、多结构的关联耦合沟通空间,并通过开放公共服务数据、搭建智慧城市平台以提高行政效率和透明度;二是城市居民愿意通过博客、微博、照片和视频共享、社交网站等沟通介质,形成对公共生活的多元参与,愿意通过社交APP、电子商务、智慧旅游、移动数字营销等模式参与政治、经济、教育、公益活动。只有基于公众参与的社会网络才能促使智慧城市在“自下而上”与“从上至下”的建设模式之间找到平衡。
(三)意义网:智慧城市可沟通性的文化维度
意义网是“城市在精神、文化层面的共享与认同,体现了传播的象征性”[11],是基于“物联网”和“社会网”多元互动而成的城市符号的意象化沟通。全球共同面对增强城市可沟通性的命题,但构成城市可沟通性的传播实践与一时一地的独特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紧密勾连,“可沟通性”在不同城市有不同的意义表达和呈现。智慧城市“意义网”更指向可沟通性的价值多元性和文化包容性,更主张体现历史人文传承和城市品牌形象的聚焦和传播,以更好地形成城市品牌形象的符号空间,扩大城市形象影响力。
1.地方认同与文化包容。地方认同是个人对特定环境产生的想法、感受、价值观、目标、偏好、技能和行为倾向的复杂镜像,是个体自我认同的组成部分[15]。人与城市的关联方式给智慧城市空间、文化精神和地方情感留下无法抹去的印记,这些印记共同塑造了智慧城市意义网络的“可沟通性”。城市作为媒介的核心是人的存在,与人相关联的是城市作为物质性媒介到社会空间媒介的哲学归属。如芒福德提出媒介技术作为人的生命意义的延伸;帕克认为现代城市环境可以被视为一种心理状态,所有诸如人类在城市中进行的交通和通讯、报纸和广告、电车和电话,以及运动、购物、人际交往、信息交流、文化意义分享和其他沟通实践等行为,都可作为地方认同的主要构成因素。人能够认识自己并拥有自我观念,与自我进行沟通,城市作为地方媒介也可把自己作为认识的对象,和人类产生意义生成与交换。因此,城市意义网络可被描述成由象征符号而实现的文化共享与认同,城市在地域、文化层面的认同与共享体现了城市可沟通性的意义价值。
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市民对城市空间的意义生产并引导市民建构城市的地点认同。如何让各类城市群体感知自我的存在,让不同价值观、审美趣味的群体得到充分的尊重,是城市可沟通的人文取向。智慧城市的发展应当在如何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促成异质人群之间的沟通并最大限度加强市民间对话,形成包容、和谐、美好的城市生活叙事空间,实现市民“共享互治”是意义网络的价值达成。
2.城市精神与品牌形象。城市精神与品牌形象是城市意义网络生成的一个重要面向。智慧城市通过物联网与社会网勾连机制实现城市内部关联与外部诉求之间的意义解释,从而弘扬城市的精神认同、促进文化消费,形成城市意义空间互动的“齿轮效应”。意义网络可视为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文脉传承、价值认同和情感寄托等元素形成的心理镜像集合体,并从城市故事和叙事的角度进行跨文本传播和解读,形成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城市本体论记忆场域。在“城市即故事”的哲学人性观关照下,通过城市的“人、事、物、场、境”五维框架元素建构好城市的叙事生态空间、聚焦好城市的品牌IP打造,以达到地域认同和精神认同,从而全面塑造城市的形象体系[16]。
智慧城市在充分尊重地域与文化个性认同的基础上,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服务于城市精神形象的塑造,彰显城市品牌与特色、维护城市历史风貌、传承本土文化,更是智慧城市长远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内涵,是智慧城市加强社会的注意力,达成与可沟通性的人本与文化要义。
四、结 语
世界万物正在数据化、感知化,并一直带给着人们惊喜和好奇。智慧城市作为一个复杂而多视角的人类实践,各类学科对城市研究正朝着多元跨界乃至无界镶嵌的模式探索发展,形成了一种人类社会的网络化空间哲学。无论是媒介融合产生的城市大数据,还是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AI一切”,智慧城市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概念和平台,让学术的智慧得以翱翔。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通过构筑好人与城市、人与物、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实现智慧城市可沟通性三重维度融合:实体面向的“物联城市”、交互面向的“社会城市”、虚构面向的“意义城市”,是城市建设加强可沟通性的实践要义。
放眼未来,城市传播的研究将继续顺着智慧城市的“花样年华”不断推进,去了解、分析智慧城市的观点、信仰、结构和体验。从人文关怀角度继续探索发现,去讲好城市“实体空间”的故事,讲好城市“虚拟空间”的故事,从而讲好“可沟通城市”的故事,讲好智慧城市品牌的故事。也许将来,城市已不仅仅是城市,而是“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的全息世界,人类已不再是人类,而是无处不在、呼风唤雨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