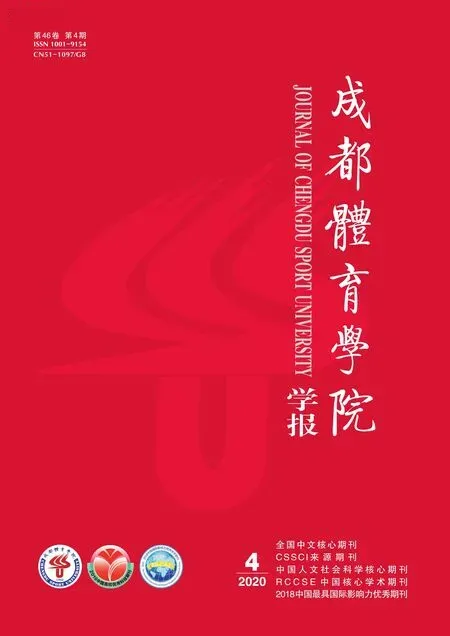万历援朝战争与浙兵武艺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2020-11-24蔡艺
蔡 艺
东洋武艺史是日本、韩国体育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特别是万历援朝战争引发的中、日、朝三国武艺交流,尤为日韩学界所关注。反观国内学界,尽管中国在东洋武艺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但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涉及古代中朝武艺交流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这种学术失声不仅弱化了中国在东洋武艺史上应有的地位,还易滋生谬误。如松田隆智认为《武艺图谱通志》“是按照宣祖、英祖、正祖三代朝鲜皇帝的命令而不断补充完成。……初版本是在朝鲜宣祖三十二年(1598)完成的。”[1]不仅存在着“1598 年应为宣祖三十一年”的时间界定问题,还存在着“将宣祖时期成书的《武艺诸谱》视为《武艺图谱通志》的初版本”[1],从而忽略了万历援朝战争时期浙兵武艺东传所产生的重要历史作用问题。基于此,本文围绕万历援朝战争时期浙兵武艺东传朝鲜半岛这一“中朝武艺交流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武术史上的大事”[2],针对什么是浙兵武艺? 为何会传入朝鲜半岛? 如何东传朝鲜半岛? 产生了什么影响等问题展开研究,清晰浙兵武艺在朝鲜半岛传播的历史脉络。
1 浙兵及其武艺体系
1.1 浙兵的声名鹊起
明代倭乱频发,为平定倭患,明廷广集兵力予以应对。在诸多抗倭军队中,“浙兵”声名最为显赫。
关于“浙兵”,《明史》专有记载:“乡兵者,随其风土所长应募,调佐军旅缓急。其隶军籍者曰浙兵,义乌为最,处次之,台、宁又次之,善狼筅,间以叉槊。戚继光制鸳鸯阵以破倭,及守蓟门,最有名。”[3]东南沿海倭乱平定后,明廷又不断从浙江征发士兵戍守蓟辽,先后参加了万历三大征,对浙兵的募集也一直持续到天启、崇祯年间。
万历援朝战争时期浙兵的英勇表现,使其在朝鲜同样威名远扬。在扭转战局的平壤之战中,戚家军旧将吴惟忠“中丸伤胸,策战益力。骆尚志从含球门城持长戟麻牌,耸身攀堞。贼投巨石,撞伤其足,尚志冒而直上。诸军鼓噪随之,贼不敢抵挡。”[4]平壤之战后,浙兵声名大振,“若请兵,则当请浙兵可也”[5]的主张得到李朝上下的一致认同。以至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倭寇再欲侵犯时,朝鲜急奏明廷星夜遣兵救援,并一再请求务必先发浙兵,“复破此贼,非得浙兵不可。”[6]对浙兵的倚重与信赖可见一斑。
1.2 以“鸳鸯阵”为核心的浙兵武艺
浙兵之所以能克敌制胜,得益于戚继光针对倭寇,创制了长短兵器“迭用互救”的鸳鸯阵。倭寇斗无定势、战无定规,又善刀法。明代军事地理学家郑若曾感叹“倭之刀最精利,长六尺,两手两刀,共长一丈二尺。虽左刀以木假之,然其右之真者,亦足以杀人而无敌。故中国之畏倭者,畏其刀也。”[7]因此,明军克制倭寇的关键,在于化解近身相搏时倭刀的杀伤力。戚继光充分发挥狼筅的防御优势,并在此基础上整合藤牌、长枪、腰刀、镋钯等武器之长,“以牌盾佐其下,以长枪夹其左右,镗钯、大刀接翼于后”[8],创制了长以卫短、短以救长、互救依存的鸳鸯阵。
鸳鸯阵以十二人为一队,队长一人居前,次二人持牌佩腰刀,次二人持狼筅,次四人持长枪,次二人执短兵,末一人为伙兵。因鸳鸯阵还要配合火砲、鸟铳和弓箭等军阵,为区分兵种,《纪效新书》将鸳鸯阵中使用冷兵器的士卒称为“杀手”,由藤牌、狼筅、长枪、腰刀、镋钯等“杀手”武艺构成的鸳鸯阵,是浙兵杀敌致果的法宝。从戚继光著《纪效新书》收录武艺的名目来看,无论是“十四卷本”还是“十八卷本”,均以“杀手武艺”为主体。
浙兵作为明代中后期颇具影响力的军队,武艺体系自有其独特之处。首先,浙兵武艺注重实用性。戚继光对武艺与战争的关系有着独到的见解,强调武艺简单实用,不落虚套,指出鈀、棍、长枪花法甚多,皆应剔除。凡武艺,务照彀习实敌本事,真可搏打者,不许仍学花法。[8]其次,浙兵武艺强调武艺之间的互补性。戚继光吸收了《司马法》“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的精髓,重视长短各种兵器的互相补充,均衡配置。再则,浙兵武艺具有系统性。戚继光不仅强调长枪、狼筅、镗鈀等鸳鸯阵所用武技的精熟,更是汲取唐顺之、余大猷等人的武学思想,形成了以拳棍为基础,进而通达诸技的武学体系。“棍为诸器之基。……若能棍,则各利器之法,从此得矣。”[9]拳法亦是如此,“似无预于大战之技,然活动手足,惯勤肢体,此为初学入艺之门也。”[10]戚继光打破武艺流派的壁垒,博采诸长,不局限于单一武艺技法的掌握,而是强调以拳棍为基,精熟各艺的系统习练。
2 壬辰倭乱引发的浙兵武艺东传
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以朝鲜拒绝联合攻打明国为由发动战争,史称“壬辰倭乱”。
壬辰倭乱爆发后,朝鲜武备废弛、兵力羸弱的颓势让君臣上下惊愕不已。“今人习见壬辰以来兵兴之后,士卒喜于溃散,以为‘我国之军,性本懦怯,虽操练,难用于战阵。'此论一行,一唱百和,主以练兵之事,为无用之具,而守令中,自以为高见者,尤不思操练军兵。”[11]为改变兵不堪战的局面,朝鲜在摈弃其传统“五卫阵法”的同时,开始了探求“他山之石”的尝试。浙兵在抗倭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技战术优势让朝鲜艳羡不已,赞叹“其兵勇锐无比,不骑马,皆步斗,善用火箭大炮刀枪之技,皆胜于倭。”[12]浙兵由弱到强的涅槃经历,亦为朝鲜树立了典范和信心,“今以中原之事观之,江南之兵,最号懦怯,不如北方之健儿,自古有言矣。故嘉靖年间,浙兵数千,不能当一倭,诚若真不可敌。及戚继光以一偏裨之将,起于行伍,设法操练,数年之后,浙兵之强,甲于天下,至今所恃以御倭者,不在燕、代,而在于江南。”[11]朝鲜对浙兵的仰慕溢于言表,期望“师其长技以制夷”,实现从“懦怯”到“勇健”的蜕变。
明军东征,为朝鲜提供了学习先进军事理论及武艺技法的机会。浙兵入朝后,朝鲜历经周折求得《纪效新书》,责令领议政大臣柳成龙与从事官李时发精心研读,又遣通晓汉文经典的儒生韩峤请教东征将士,力求通晓真义。宣祖结束流亡生涯返回汉城后,旋即设立“训练都监”“募饥民为兵,应者颇集。……旬日得数千人,教以戚氏三手练技之法,置把总、哨官,部分演习,实如戚制,数月而成军容。”[11]壬辰倭乱引发的中、日、朝战争,推动了朝鲜以《纪效新书》为轨范,全盘吸纳浙兵技法构建军事防御体系的变革,浙兵武艺也由此东传朝鲜半岛,并落地生根、广为流传。
3 浙兵武艺在朝鲜半岛传播的脉络梳理
3.1 《纪效新书》:浙兵武艺东传朝鲜半岛的理论基础
《纪效新书》是浙兵操练之标准,其涉及武艺的记载,亦是探讨明代武术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渊薮。朝鲜引入浙兵武艺,亦始于对《纪效新书》慕求与研习。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平壤大捷后,宣祖探访李如松,得知明军获胜关键是使用了戚继光《纪效新书》的御倭技法。宣祖当即表达了观瞻诉求,被婉拒后密令译官从其手下购得。“初,平壤之复也。上诣谢都督李如松,问天兵前后胜败之异,都督曰:‘前来北方之将,恒习防胡战法,故战不利。今来所用,乃戚将军《纪效新书》,乃御倭之法,所以全胜也。'上请见戚书,都督秘之不出。上密令译官,购得于都督麾下人。”[13]这是《纪效新书》传入朝鲜半岛的最早记载,但据郭乐贤等韩国学者考证,这部《纪效新书》只是粗略的摘要本[14]。此后,朝鲜一直在为得到《纪效新书》全本而努力。同年9月,“戚继光所撰《纪效新书》数件,贸得而來。但此书有详略,须得王世贞作序之书贸来。”[15]万历二十六年(1598)二月,明军将领戚金在归国之前将《纪效新书》作为礼物赠予朝鲜。至此,朝鲜收集了多个版本的《纪效新书》。
《纪效新书》奠定了朝鲜学习浙兵武艺的理论基础,朝鲜购得后不久,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操练士卒的尝试。“今此各样武艺,用剑用枪之法,能中《纪效新书》规式者,别为论赏,立试于科举,以变沉痼难改之习。”[16]为督促武臣学习《纪效新书》,朝鲜专设讲堂勤勉教诲、奖优惩劣。“前日抄择有将来堂下武臣,学习《纪效新书》于训练都监,被抄者二十余人。其后因外任出去者甚多,而年少武士中,有志自愿来学者,连续有之。”[17]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使《纪效新书》的操练技法在朝鲜上下备受推崇。朝鲜高宗于1874 年曾言“夫编伍约束,莫如戚继光之《纪效新书》,而我国武事,专靠是书。”[18]说明从万历援朝战争乃至此后两百余年的时间内,朝鲜的军阵操练、武艺传习等,皆以其为标准。与此同时,《纪效新书》的影响也开始波及民间,一些难民为求自保,跟随驻留明军学习武艺。“壬辰乱后,聚满城饥民,学艺于唐官,乃《纪效新书》也。”[19]朝鲜地方武装和私募军队也争相效习戚氏技法,忠清道人李梦鹤倭乱期间募集私兵,“时以《纪效新书》束伍法,置军练技。”[20]
3.2 训练都监:职掌浙兵武艺操练的中枢机构
为系统学习浙兵抗倭技法,明军参将骆尚志提议从浙兵将士中选派教师操练朝鲜士兵。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骆尚志致书朝鲜领议政柳成龙:“我今正欲卧薪尝胆,以图报复,或将倭巢出来之人,一万数千有余,立一大元帅统之,定立头目,教习武艺,修整器械,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千教万,务成精兵,虽倭奴有复来之念,我有精兵待之……”[21]柳成龙回应:“近于城中招募年少伶俐之人得数十,伏愿老爷先下营中,各以南兵一人,主教一人……所选四十余人,其中十余人乃砲手,其余枪、剑、狼筅、阵法,随其所习。又已令京畿诸道挑选习斗骁健者各数千人,以相传习。”[22]随着训练规模的逐渐扩大,使得朝鲜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操练事宜已迫在眉睫。万历二十一年(1593)八月,宣祖训示设立训练都监,全面职掌教官选派、技艺传习、武籍编纂等操练事宜,是朝鲜破旧立新,以浙兵武艺为基础构建全新军事防御系统的标志。
为推动浙兵武艺的传习,训练都监制定了试艺、武举等激励制度。通过试艺,训练都监可以及时掌控操练情况,规避存在问题。如宣祖曾在检阅“杀手”试艺后训示:“近观杀手所习者,唯长枪、狼筅等技,而习剑者无几。于势急仓卒之际,短兵相接,莫剑若也。今后使诸军皆为习剑,试才时亦优取剑士事。”[23]与此同时,训练都监遵照《纪效新书》,要求“杀手”两两为对偶进行试艺。试艺的赏罚,亦“遵用《新书》规式,……“杀手”亦当一例论赏,而考试之际,精察其舞对生熟,各势正彀,少有违于《比较篇》所论者,勿以入格看,斯合较艺之式。”[17]对于习艺不精者,则效仿《纪效新书》的规制进行赏罚。
除此之外,朝鲜还制定了扩大武举录用人数、设立专门试取通道的政策。万历援朝战争期间,朝鲜一改重文轻武的科举惯例,武科试取人数大幅增加。宣祖二十八年(1595),“武科立试,取六百人。”[20]宣祖三十年(1597),“取文科尹继善等九人,武科一千七十人。”[24]“杀手”试取方法亦参照《纪效新书》,“今此各样武艺,用剑用枪之法,能中《纪效新书》规式者,別为论赏,立试于科举,以变沉痼难改之习。”[16]“杀手”试取则开辟专门通道,技艺超群者可直赴殿试。宣祖二十九年(1596)的武科殿试,朝鲜甚至制定了“片箭、鸟铳俱不中者,如或自愿杀手才试之入格者,取之事命下”[25]的优渥政策,足见其良苦用心。
3.3 “三同”训练法:确保浙兵武艺操练效果的重要举措
为确保操练效果,在朝鲜操练浙兵武艺伊始,明军备倭总经略宋应昌就提出了“同衣甲、同器械、同技艺”的“三同”训练主张。“亟行全罗、庆尚、京畿等道,令陪臣募选膂力精壮军人,以多为善,即使陪臣管辖,尽发副将刘綎、吴惟忠、骆尚志等营……令其所服衣甲与南兵同,所执器械与南兵同,令各营教师起伏击刺之法与南兵同,不数月间自南兵无二。”[26]宋应昌的主张得到了明军赞画兵部员外郞刘黃裳、游击骆尚志等人的支持。万历二十一年八月一日,刘黃裳返京之前致书朝鲜国王,“亟募八道之兵,四十以下、二十以上强壮男子。每道万人,得八万人,送与刘副将綎,换其衣甲,受以利器,編入天兵队伍,乘此秋涼,逐日操练。”[27]对于朝鲜练兵之事,明廷亦有训谕:“水陆兵若干万名,易衣甲、标旌,编入唐营。”[28]
“三同”训练法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明军在取得第一阶段胜利后班师在即,但此时朝鲜兵力羸弱,帮助朝鲜迅速构建自身的军事防御体系迫在眉睫;其次,军事操练本为极尽严谨之事,浙兵武艺作为“舶来品”,在操练之初难免会有水土不服之处。例如,“我国武士,宽袍阔袖,每为唐人所嗤讥。故曾下禁令,而顿不举行,尚循前习,今又为陈游击所讥。”[29]朝鲜要想习得浙兵武艺之精华,就必须改服易帜,一尊其制。为推行“三同”训练法,朝鲜变其服色,依照《纪效新书》样式制造兵器,“置阵制器,皆仿浙法”。“忠淸、全罗、庆尚道上番军士,令各其道监司,照例抽出,依京上番例,定日起送于都元帅处,一听刘总兵节制。兼与南兵,同其起居,衣甲器械,渐习与同。”[30]
朝鲜遵照“三同”训练法操练浙兵武艺,训练内容与方法完全脱胎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打造了一支戚家军的海外嫡脉。对于“三同”训练法的操练效果,朝鲜赞誉有加,“军粮稍裕、士卒渐集,则演为五营而备五方之色,常作留都之兵,递营教练如中国矣。”[31]“三同”训练法是短时间内迅速改变朝鲜武备的必要举措,是浙兵武艺保持纯正基因的重要保障,也是浙兵武艺能够深入了解朝鲜民情,因地制宜进行本土化改造,进而将明代武艺植根朝鲜半岛的基础。
3.4 明军教官:传教浙兵武艺的核心力量
为配合朝鲜操练“杀手”,明廷陆续选派教官予以援助,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 十月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主要由骆尚志及其驻留朝鲜的属下组成。“今朝使郞厅李自海,往质于骆参將留营之人骆尚忠称云者。尚忠,乃参将亲属。又有宋侍郞所送金文盛七人,同在一处,见自海,言以侍郞之命,将就刘总兵之营,训练我国之军……”[28]应柳成龙邀请,骆尚志在明军归国之前选留“委官闻愈等代生以为授受之勤,倘或略有次第,即当遣发归来而莫迟滞。”[32]朝鲜则募选70 余人,“送于骆公阵下,请学南方技艺鸟铳、狼筅、长枪、用剑等事。骆公拔营中南校十人分教之,公或亲至卒伍中,手自舞剑、用枪而教之甚勤。”[33]通过留朝浙兵教官的努力,“杀手”操练“数月之间,颇有其效”[34],虽未成规制,但已粗晓其技。
第二阶段从万历二十三年(1595)初至次年年底。由于第一阶段朝鲜选派士兵的数量有限,加上操练重点在于砲手,故宣祖认为“今砲手则已稍成形,“杀手” 虽似冗杂,亦当加意教训,使之成就。”[26]为扩大“杀手”操练规模,明廷陆续向朝鲜派遣了千总陈良玑、游击胡大受等百余名教官,开辟了传教浙兵武艺的新局面。这些浙兵教师被选派到朝鲜各地,“其中武艺绝妙之人,欲特留京城,教训各哨军兵,则把总杨贵、陈伯奇为其类之冠。……叶大潮,武艺胜人,曾从事于戚继光军中,多有所闻见之事。叶大潮先往全罗教训后,及于庆尚则何如。”[35]随着入朝教官人数的增多,浙兵武艺的操练规模开始从京都辐射至地方,“三手军”的动员能力达到两万余人。对于“杀手”技艺的习练效果,朝鲜也予以了肯定,“教师逐日教练,作队勤奖,故“杀手”则比前大胜。”[36]第三阶段始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二月结束。由于日本再次发动侵朝战争,为增强朝鲜军队的御倭能力,明朝在出兵救援同时复遣教官赴朝传教。经过此前两个阶段的训练,朝鲜“杀手”操练已卓有成效,“于诸技,颇已向熟,只是手法、足法,有些少未通处云。”[37]然而受战事影响,朝鲜难以维系大规模练兵,故传教重心开始转向选拔技艺精炼者进行强化训练,从而为朝鲜培养技艺精湛的本土教官。“近日天将中许游击,自谓得妙于诸技,洞晓《纪效新书》之法,故自都监抄出“杀手”中最为精习者十二人,名为教师队,使加设主簿韩峤领之,就正于游击阵中,颇有所学。艺成之后,当以此辈为教师,编教中外军人,则其法庶可流行于我国,不至湮废,而所谓以一教十,以十教百者在此矣。”[36]战争结束后,朝鲜又多次向明朝提出派遣教官的申请,明廷均予以婉拒,浙兵武艺的传教开始转由朝鲜本土教官负责。
在明军教官的精心传教下,朝鲜“手足行伍之法精习可用,旗麾武服一新其制,器械兵仗罔不坚利”[38],操练成效可见一斑。明军教官的言传身教,让以浙兵武艺为代表的中国武术文化在朝鲜大放异彩。朝鲜对此自是感恩戴德,“小邦于军旅之事,专未谙练。嚮者咨请教师,粗晓武艺,亦莫非皇上字小之仁,而诸大人矜恤之恩,其亦至矣。”[39]
4 浙兵武艺东传朝鲜半岛的历史影响
4.1 丰富了朝鲜的武艺内容
浙兵武艺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改写了朝鲜武艺“自昔但习弧矢,仅有弓矢一技”的历史,谱写了中国武术传播史的华丽篇章。作为戚继光抗倭技法的重要环节,以鸳鸯阵为核心的浙兵武艺承载着朝鲜强军御倭的殷切期望。为此,朝鲜费尽心机求得《纪效新书》,将其所含藤牌、狼筅、长枪、镗鈀、双手刀、棍棒6 技摘抄成《武艺诸谱》,作为“杀手”操练的武艺教材。此外,朝鲜还专设训练都监负责操练事宜,并通过改革武举、试艺等制度来激励“杀手”育成,使得狼筅、长枪等浙兵武艺在朝鲜落地生根,不断传衍。
“杀手”技艺虽是操练重点,但浙兵将士大多身怀各艺,所擅武艺并不止于藤牌、狼筅等技,偃月刀、棍棒、拳法、剑等武艺也由此得以东传。《朝鲜王朝实录》有明军教官操练双刀、拳斗、手搏、偃月刀、棍棒等武艺的记载,宣祖亦感叹明军勇士“跳身跃上,其疾如飞。且击拳为戏,若猿猱之状。”[40]谕示“凡诸武艺,无不学习可也。”[41]尤其是棍棒与拳法技艺,宣祖观瞻之后赞叹不已,命令训练都监将《纪效新书》木棍、拳法两技单独抄出,督促士兵勤加练习。这些武艺的东传,极大地丰富了朝鲜的武艺内容,并逐渐沉淀为朝鲜传统武艺不可或缺的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浙兵武艺的东传使朝鲜认识到博采武艺之长的重要性,拉开了朝鲜系统学习中国武术的历史序幕。壬辰倭乱之后,以习练浙兵武艺为主的“杀手”,成为朝鲜最为重要的兵种。训练都监作为培养“杀手”的国家机构,也一直延续至朝鲜王朝末期。宣祖三十七年(1604),朝鲜以《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为基础,纂成《拳谱》并予以刊行,对拳法进行推广。光海二年(1610),朝鲜将戚继光《练兵纪实》中的夹刀棍、钩枪收入《武艺诸谱翻译续集》,作为防御建州女真的武艺技法。英宗三十五年(1759),朝鲜纂成《武艺新谱》。该书在《武艺诸谱》基础上增加竹长枪、旗枪、锐刀、倭剑(交战)、月刀、挟刀、双剑、提督剑、本国剑、拳法、鞭棍12 技,是为朝鲜“武艺十八技”。正祖十四年(1790),李德懋等人在“十八技”基础上又增添骑枪、马上月刀、马上双剑、马上鞭棍、击球、马上才6 技,撰成了集中、日、朝武艺之大成的《武艺图谱通志》。
4.2 奠定了朝鲜武艺发展的理论基础
万历援朝战争之前,朝鲜“从古所传只有弓矢一技,至于剑枪则徒有其器,原无习用之法”[42],其武艺理论之匮乏可想而知。作为浙兵武艺的理论承载,《纪效新书》成为朝鲜体认武艺精髓的上源活水,其武艺见解和撰写体裁亦奠定了朝鲜武艺发展的理论基础。
《纪效新书》强调长短兵器相救互补,“夫天有五行,以应五兵,长短相救,势所必至。”[8]朝鲜同样恪守长短相依,不可偏废的原则,注重长短兵器均衡发展,“杀手”技艺分类习练。在论及长短兵器关系时,《武艺图谱通志》的观点与《纪效新书》别无二致,“牌筅枪鈀棍剑及鸟铳弓矢之技,虽有远近之殊,其所以杀贼一也。近技之不可施于远,远技之不得用于近,是皆理,势之所必然者也。远技、近技之不可缺一也,不亦较然矣。”[43]朝鲜儒臣李颐命亦言“五兵之用,长短相须,其不可废一,正若五行之生克相成也。”[44]同样延续了戚继光长短兵器相救互补的武艺思想。
“立正法,禁花法”是《纪效新书》武艺习练的基本要求,“凡武艺,务照彀习实敌本事,真可搏打者,不许仍学花法。”[8]戚继光针砭镗鈀、棍棒花法甚多,认为“转身跳打”等招式皆为花法,“不惟无益,且学熟误人第一。”[8]这种强调技击实效,反对花势虚套的武艺思想亦为朝鲜所尊崇。韩峤在谈及编纂《武艺诸谱》的原因时曾言:“以此杀手诸技迄无其谱,学之者徒信其目,故正法日废,花法作矣。……自今其所试武艺,一依此谱,则虽或不中,亦必不远花正,由此而可辨庶不为虚套之所欺矣。”[43]目的在于匡扶正法,以为后效。
与此同时,《纪效新书》的撰写体裁、技法招式、兵器规制等,亦为朝鲜所借鉴。因《纪效新书》卷帙繁冗,难以晓读,为便于“杀手”习阅,朝鲜以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为基础,围绕“杀手”技艺进行了编修本土教材的尝试。宣祖三十一年(1598),《武艺诸谱》付梓并得以刊行。其“兵器制式”“谱”“诸势总图”的编纂格式与《纪效新书》如出一辙,技法名称也毫无二致。《武艺诸谱》的刊行,奠定了朝鲜武籍编撰的理论基础。在其引领下,《拳谱》(1604)、《武艺诸谱翻译续集》(1610)等武籍相继问世。即便是在百余年之后,李德馨编撰《武艺图谱通志》(1790)时亦言“韩峤之书即出,戚氏源派明白,有图有谱,按而行之,如指诸掌,亦可谓有用之学矣”[43],充分肯定了《武艺诸谱》的示范作用。除《武艺诸谱》之外,朝鲜汉文武籍的编撰基本上都以《纪效新书》为主要参考,《武艺图谱通志》直言“戚氏《纪效新书》,茅氏《武备志》俱为是编之表准。”[43]而《纪效新书》中诸如“泰山压卵”“白猿拖刀”“直符送书”等技法名称在骑枪、本国剑等新收录的武艺中也被广泛使用,影响之深远足以见之。
4.3 促进了朝鲜传统武艺的革新
万历援朝战争时期浙兵武艺的东传,丰富了朝鲜的武艺内容,开阔了朝鲜闭塞的武艺视野。在中国武术文化的浸润熏陶下,朝鲜开始正视与反思自身武艺贫瘠的不足,并以中国武艺为镜鉴,进行了传统武艺革新的尝试。
朝鲜“本国剑”的脱颖而出,是最为典型的例证。《武备志》专有“朝鲜势法”的记载:“古之剑可施于战斗,故唐太宗有剑士千人,今其法不传,断简残篇中有诀歌,不评其说。近有好事者得之朝鲜,其势法俱备。”[45]这段记载朝鲜亦有所见,并予以了回应。朝鲜显宗十四年(1673)4 月1 日例行的阅武活动中,“上曰:‘先试本国剑。'上谓柳赫然曰:‘此剑之制,见于何处?'赫然曰:臣见中国《武备志》有此刀,而称以朝鲜国刀云。”[46]围绕“朝鲜势法”来龙去脉的论争从明末一直延续至今,《武艺图谱通志》假托本国剑起源于新罗时代的黄昌郎,“今因黄昌郎为本国剑之缘起焉。”[47]马明达先生言其“毫无疑问出自中国某个佚名武艺家之手。”[2]从朝鲜在壬辰倭乱之前“所传只有弓矢一技,至于剑枪则徒有其器,原无习用之法”[42],而《武备志》最早版本为明天启元年(1621)本的历史来看,“朝鲜势法”应出于1592-1621 年之间,与浙兵武艺东传朝鲜的时间正好吻合。又因其势法名称大多出于中国,故这套剑法毫无疑问汲取了浙兵武艺的精华。
宣祖三十七年(1604),朝鲜曾刊印《拳谱》一书,并训谕将士勤以习练。此后,拳法频现于朝鲜的阅武、试才等活动,闾巷儿童亦转相效则。在从军队向民间渗透的过程中,《纪效新书》“学拳要身法活便,手法便利,脚法轻固,进退得宜。腿可飞腾,而其妙也”[10]之精要则为民间流行的手搏所汲取,衍生为强调身法轻捷,突出腿脚技法的跆跟运动。《海东竹枝》曾于1921 年刊载过一首描绘跆跟的朝鲜汉诗,“剑术先后手术妙,戚将军已教兵材。三节鉤如差一节,拳锋一瞥落头来。”[52]“手术”即拳法,汉诗言其肇始于“戚将军”,更为直观地说明了拳法东传朝鲜后,对跆跟起源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5 结语
万历援朝战争的爆发,为中朝武艺的深入交流创造了历史契机。在社稷为墟的危急时刻,援朝浙兵所展现的技战术优势,使朝鲜明确了通过效仿浙兵技法强军固防的革新方向。戚继光围绕鸳鸯阵所创设的浙兵武艺亦为朝鲜所推崇。在中朝两国的共同努力下,朝鲜新设“训练都监”这一国家机构,选派浙兵将士为教官,依《纪效新书》规式,采用“同衣甲、同器械、同技艺”的方法操练浙兵武艺,打造了一支戚家军的海外嫡脉。万历援朝战争时期浙兵武艺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拉开了朝鲜系统学习与吸纳中国武术文化的历史序幕,推动了东洋武艺深入而又持久的交流。遗憾的是,中国武术传播史这段浓墨重彩的篇章鲜为国内学界关注,中朝武艺交流亦有许多未被呈现的历史,故期拙文能有抛砖引玉之效,吸引更多同仁关注于此,还原中朝武艺交流更多未知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