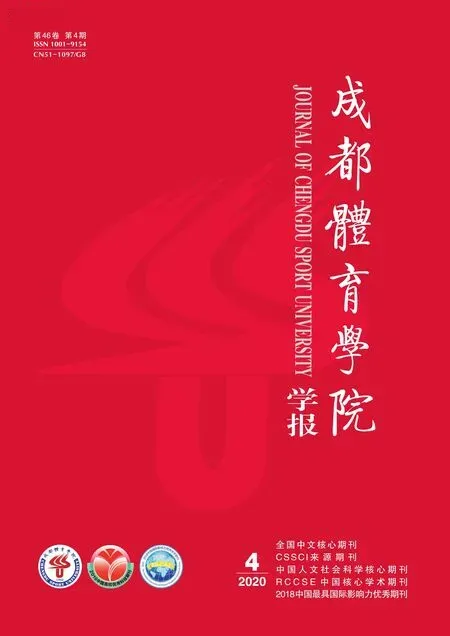人类学视角中的竞技体育:基于民族志洞见的启示与思考
2020-11-24潘天舒
潘天舒,何 潇
在人类学家看来,体育作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受制于规则的竞技活动,更是具有仪式性和游戏特征的集玩耍、工作和休闲为一体的社会实践模式[1]。对于球员和职业俱乐部老板来说,体育就是工作。同时体育比赛也是观看者(如球迷)与竞技者在个体和社会层面通过参与表达认同的重要场合。通过赛场这一精心设计和营造的幻想世界,球迷与他们所仰慕的英雄共同感受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沮丧。从表面上看,竞技体育的本质特征似乎就是对抗,或者说是为比赛而比赛。在全球化时代,伴随着实时赛事所展现出的不仅仅是攻防策略的高低、输赢比分的变动,更是从个人到国家层面的身份认同,以及一整套与运动员精神、领导力、性别和多元文化有关的价值观[2]。
那么,植根于社会秩序之中的竞技体育活动,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会受到文化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如何借助人类学的视角来审视和解读处在全球化和地方转型语境中的竞技体育赛事? 以参与式观察为特色的研究方法能否为我们带来接地气的田野发现和洞见? 本文力图通过论述和分析民族志案例,探讨田野体验、视角和策略选择与研究发现之间的关联性,同时就当代体育人类学的价值、功能和意义进行思考和总结。
1 竞技体育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功能与意义
田野视角中的体育实践是特定语境中社会关系和文化理想的折射和反映,与宗教节庆仪式一样充满表演张力。竞技体育不仅仅是成人的儿戏,而是一种社会生活隐喻和符号叙事。曾经在巴厘岛悉心阐释“斗鸡”文本的格尔兹(Geertz)就主张:田野工作者应该把任何竞技和嬉戏作为一种“属于现实”(of reality)的和“为了现实”(for reality)的文化素材来加以解读,同时阐释充溢各种符号的文本及其在传导价值观和核心理念的社会化过程中呈现的多层意义[3]。格尔兹的这一洞见为人类学者以文本阐释的方式来解读和破译包括橄榄球、篮球、板球和棒球在内的竞技体育实践,提供了足以激发灵感和创意的认识论框架。
如果将美式橄榄球视作美国文化的象征来进行浓描(thick description),我们就有可能通过“破译”隐藏在球赛程式中的符码来感知现代日常生活的本质特征。首先,在美式橄榄球竞赛过程中,美国文化所推崇的个人奋斗精神往往受制于强调团队合作的协调策略(这一点与英式足球尤为相似)。在跨文化比较的视角中,美国大学和职业橄榄球作为旨在加强男性纽带的集体竞技运动,类似于一种隔离两性的“男性成年礼”(male initiation rite)。已故著名民俗学和人类学家邓迪思(Dundes)在一篇题为“在达阵区触地得分”的论文中写道:“美式橄榄球可以视为一种两队男性通过穿越在对手的达阵区来表达男性气质的仪式”[4]。他将橄榄球视作一种具有“同性恋”行为特征的符号形式,与澳大利亚土著的“男性成年礼”做了饶有趣味的类比。处于两种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男性仪式,都有排斥女性的机制。当一位女记者出现在新英格兰爱国者队更衣室的时候,球员们表达了强烈不满的情绪。因为在他们看来,女记者侵入的是一个男性仪式的禁忌空间。除了性别身份表达这一维度之外,阐释人类学意义上的橄榄球赛还赋予我们深度阅读文化的机会,并由此领悟以专业化为基础的社会分工特征、在球场上攻城略地的商战隐喻以及贯穿其间的团队精神,从而获得解析北美企业文化模式的最佳视点。
就理念而言,体育竞赛始终映现出某种核心价值观,如:公平竞赛和运动员精神。在实践层面,竞技体育的开展本身又是在地方场景中一种制度文化的重新转译过程。如,当摩门教徒1940 年代把篮球引入印第安纳瓦霍部落居住区后,这项运动就很快被赋予新的不同含义并产生出在白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玩法。纳瓦霍人的篮球赛中看不出刻意的进攻性,而且球员喜欢把球传给自己的亲友,而不是处在有利位置的队员,毫不在意输赢。[5]比较棒球在美国和日本的不同玩法,亦可发现其中所显示出的与社会关系相关的核心价值观的差异,当美国球员加盟日本棒球队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那种强烈的个人主义作风和标新立异的打法。这与崇尚服从大局、自我牺牲和人际关系和睦的球队氛围显然格格不入,产生文化冲突在所难免。[6]近年来,不断有日本球手加盟美国职棒联盟赛,文化适应和制度安排也始终是影响选手临场表现的两大问题。
当一种竞技体育项目传入到不同文化区域时,必然会在输入地产生不同的象征意义。一个世纪前随着英国殖民主义的扩张,板球渐渐成为从加勒比海到太平洋和印度次大陆均广受欢迎的一项运动。日常表述用语中,“没有板球范儿”(not cricket)就有做事缺少绅士风格和擅改规则的意思,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在马林诺斯基进行过经典田野研究的特布里安群岛[7],板球这一源自英国的绅士游戏,亦在经历了极为戏剧化的本土化过程后,成为岛上的热门体育运动。20 世纪初,英国传教士把板球运动介绍给土著岛民的初衷,是想传授一种“文明人”的休闲和娱乐方式。然而随着这一运动的不断普及,20 世纪70 年代,在该地区,板球已经转型为一种高度地方化的村际比赛替代了原先的纷争斗殴,已基本上看不出太多的英国特色:首先,比赛双方球员们的着装不是白色球服,而是传统的部落战衣,而且每队最多可以上40 名球员(而正规赛只限11 名);其次,“球赛”成为“政治结盟”的一种方式,东道主永远是胜者,但赢的比分不能太大,以免使客队难堪,这在西方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此外,在比赛时队员们载歌载舞,不时使用巫术来辅助击球手和投手,而巫术一直是殖民当局屡禁不止的“落后”习俗。当投手在投球时,会念念有词,背诵咒语,似乎是为了让投出的长矛能击中目标。当地人还重新设计了板球拍,以提高投球的准确性;“球赛”还是当地人食物和其他物品进行仪式性交换的场合。当地人利用板球赛来表达他们拒绝殖民化的立场,同时显示出特布里安岛居民独特的文化创造力。在1974 年出品的民族志影片《特布里安岛的板球》(Trobriand Cricket)中,一位村民代表说道:“我们终于抛弃了白人的游戏;板球现在是我们自己的运动。”
《特布里安岛的板球》这部人类学民族志经典影片所展示的是一个体育“文化转译”后发生意外状况的案例,即:象征西方文明、理性和绅士精神的板球,原本是一项试图对“野蛮”他者进行规训和约束的竞技体育项目,在日常实践中却被“他者”拿来,并以村际比赛为平台,将白人视之为“落后”的魔法和迷信习俗发扬光大。此后体育人类学者渐渐将民族志凝视的目光,转向西方社会,用审视异族的猎奇心态来观察自己早已熟视无睹的高度仪式性的竞技赛事,希望能获得不俗洞见。人类学者格梅尔希(Gmelch)在马林诺斯基洞见启发之下,对美国“棒球巫术”所做的田野研究就是一部带有充满文化反思精神的民族志案例。[8]
格梅尔希在20 世纪60 年代效力于美国著名职业棒球俱乐部底特律老虎队(Detroit Tigers),司职一垒。这一难得的职业棒球人“过来人”经历使他在日后的人类学研究生专业学习和研究中受益匪浅。在选修“魔法、宗教和巫术”课程时,他以丰富的竞技体验为基础,在文化相对主义精神的引导下,对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理性思维和科学态度进行了反思和质疑。在格梅尔希看来,置身于现代文明大都市的职棒球员,在面临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情形时,也会求助魔法和巫术,以保持对自己技能和控制力的自信和镇静,与马林诺斯基笔下特布里安岛的渔民并无二致。这两类处在完全不同文化和社会语境中的“专业人士,”在面对非常人能控制的事件时,都会通过仪式、禁忌和吉祥物等“迷信”手段来管理自身的焦虑和紧张情绪。马林诺斯基发现:在渔产丰富的环礁湖捕鱼时,特布里安的岛民并不依靠巫术帮忙,因为他们凭借自身知识和技术已经绰绰有余了;但当特布里安人出海捕鱼时,他们就必须施行巫术和举行仪式,希望得到神助来保证安全和增收渔产。美国的职业棒球运动员为保证自己能够赢球,也会像世界各地的信徒一样,祈求超自然力量的保佑和帮助。
格梅尔希认为:对于美国职棒队员来说,棒球不是简单的比赛,而是实实在在的职业。球员能否保住饭碗,完全取决于平时的球场表现。职业棒球手会使用巫术来试图控制棒球赛的运气,从而显示出与特布里安岛渔民相似的行为特征。投球和击球是棒球比赛中常常会被运气或概率主宰的两个环节,投球手可谓是比赛中最没有办法控制结果的队员,击球通常也被认为是运动项目中最难完成的任务,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即投球手和击球手可以做足准备,并且全身心地投入比赛,但仍然无法影响球的最终去向和球赛的结局,就像在远海捕鱼的特布里安人一样会时常感到无助。
的确,职业棒球队员能够通过日常训练来获得一些看得见的成效,如在比赛中集中注意力等。然而,格梅尔希注意到职业棒球队员将日常训练以外的活动如吃、穿和驾车等仪式化,以期获得比赛胜利的运气。如“白袜队”的一位投球手会在比赛日听同一首歌;有的球员会在赛前吃固定的食物如鸡肉、火鸡和金枪鱼,赢球往往会催生出新的个人化的仪式性行为,表现出色的球员并不会把获胜仅仅归结于自己的球技,而是将输赢与自己在比赛当天吃了什么,做了什么联系起来,如是否要刮胡子或者洗头发都成了能影响比赛结果的因素。有时候,投手的太太或者女朋友都会主动做些支持自己心上人“迷信想法”的事情,如在第六局时吃冰淇淋,或者穿着粉色的球衫,披着棕色围巾或者戴着松软的帽子去观战助威;在比赛中处于下风的球员会选择不同的进场路线来改变运气,当队员没有击中球时,教练会摇动装着球棒箱子,似乎要“唤醒”状态不佳的球棒。击球手会不断地用手摩擦球棒,试图获得某种魔力。
职业棒球队员们的禁忌往往与临场表现失常有关。许多球员们的禁忌活动发生在场外,不在观赛者的视线之内。格梅尔希本人曾因连续两次在吃了馅饼之后输球,就决定在整个赛季不吃馅饼;另一位职业棒球选手的饮食禁忌却很形象化:他在吃了肉球(meatball)三明治之后,投球时大失水准,从此以后再也不吃肉球(肉圆)类食品。有的球员整个赛季都不会看一场电影;有的击球手在球赛当天不会看书,怕影响自己的视觉。“吉祥物”是球员认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物品。有些吉祥物已经是球员的标准装备,如钱币、链饰和十字架等;有的球员会戴着从大学时代就开始用的旧手套,因为它常常会带来好运;有位击球手在穿着从队友那里借来的棒球鞋后成功地投出了“无安打”(no hitter)之后,毫不犹豫地买下球鞋,并视其为恋物(fetish)。14,24,34 或者44 是球员们希望得到的印在球服吉祥数字。有些球员会忌讳数字13,有些却要求成为第13 号球员;有些球员希望得到退役队员的球号。有的球员会按照固定的程序穿球服。一位球员在连续击出两次本垒打之后,发现自己有一颗纽扣没有扣好。在此后的每次比赛时,他都会松开那颗纽扣。格梅尔希注意到:与职业棒球相关的仪式和禁忌并非一成不变,时代的变化也会影响到队员们对于吉祥物的选择。在街上捡到妇女的发针曾经被击球手视为吉兆,看到白马会使得球队获得神助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旧俗显然已被遗忘。
如果说《特布里安岛》是在后殖民批判的视角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处于蛮荒人之地的“他者”是如何改造象征西方“文明”的板球运动项目,颠覆白人游戏规则,并以调侃俏皮的方式来保护传统生活习俗的视觉民族志案例的话;而《棒球魔术》则是将惯常对“他者”进行田野凝视的目光,转向职业棒球手,对棒球这一北美人无比钟爱而又似乎是熟视无睹的体育项目进行审视和反思,可谓殊途同归。两者以不同的方式致敬马林诺斯基,同时充分展现了参与式观察法对于跨文化语境中竞技体育研究的价值和功能。
2 足球民族志棱镜中的“世界第一运动”
在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眼里,当今4 年一度的世界杯赛不但是一场牵动全球亿万球迷神经的超级赛事,更是研究民族和国家认同、世界公民想象、“殖民主义”历史记忆以及“金元足球”和竞技体育市场化等热门议题的大好契机。笔者认为,完成于不同时段的两部以狂热球迷为“凝视对象”的民族志作品《足球狂热》[9]和《一部有关英格兰足球迷的民族志》[10],在相当程度上展示了历时性田野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同时还为如何在田野实践中将球迷的热忱情感和人类学者的专业精神有机融合,做了成功的示范。
2.1 《足球狂热》[9]
《足球狂热》以巴西足球的社会和文化意涵为核心议题,作者利弗(Lever)为美国人,在上大学之前,从未听说过什么是世界杯,对足球一无所知。然而1966 年利弗作为大二学生在伦敦的暑期实习经历,使她大开眼界,亲身体验了足球作为世界第一竞技运动项目对于社会和个体的冲击力。当年作为现代足球发源地的英国(英格兰)终于第一次成为世界杯东道主,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获得雷米特杯。在利弗实习期间,世界杯几乎是她的英国同事和朋友唯一的聊天话题,她感受到了当地民众对于进入决赛的英格兰队所持有的乐观情绪,在经济和综合国际地位下降的背景下,英格兰队在世界足坛的上佳表现也在瞬间提升了国家形象。此外,世界各地尤其是拉美的球迷蜂拥至伦敦,众多巴西球迷搭乘远洋货轮而至,晚上就在甲板上过夜;很多人为了凑足旅费,往往积攒数年,就是为了能一睹巴西三连冠的盛况(巴西因三次获得冠军得以永久保存雷米特杯)。然而,当年巴西队出师不利,在先后输给匈牙利队和葡萄牙队及球星贝利因伤退赛的情况之下,无缘四分之一决赛。这一“噩耗”使巴西全国上下悲恸不已,里约街头痛苦的男女球迷,被黑布笼罩的大楼外悬挂着半旗致哀以及跳船自杀的球迷,焚烧球星和教练相片泄愤的“足球流氓”。(2014 年巴西世界杯期间巴西队惨败于德国队后也有类似情形),另一方面,则是欣喜若狂的英格兰球迷纷纷走上街头狂欢,城市交通不得不中断两天之久。
世界杯对于东道主、参赛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产生的这种富有传染力的狂热性,给来自于素有“世界第一体育大国”美国的利弗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促成了其把对世界杯和巴西足球的浓厚兴趣,转化为一种专业追求,一种学习运用社会学想象力来进行体育民族志研究的动力。在《足球狂热》里,利弗以足球为棱镜,以球迷为关注对象,提出其主要观点:在现代民族国家,足球作为一种高度制度化的运动能够使复杂多元的社会获得空前的凝聚力量。如,巴西每个城市至少有一支职业足球队。在大城市往往有几支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和团体的职业球队,在里约热内卢,富人、中产阶层、穷人、黑人、葡萄牙人后裔和街坊社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心仪球队。作为符号表征,这些球队代表不同球迷人群的兴趣、利益和身份认同;各个球队也借助于对足球的共同热爱把不同派系的球迷们联结起来;城市和全国范围内的冠军赛更是起到了统合巴西国内不同地域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多元团体的作用。
对于许多巴西人来说,支持某一支球队可能就是其一生中第一次表达超越地方社区的忠忱之情。如,里约的球迷在全国联赛时会支持里约的球队。但在国际赛事如世界杯举办期间,他们与所有来自不同地区的球迷一样成为国家队的坚强支持者,此时,足球使不同族裔和阶层的人们得以大大增强对于“巴西特性”(Brazillianness)的国家认同。利弗同时指出:作为全球大众体育代表的足球,在巴西实际上是一项将女性运动员排斥在外的“男人的竞技项目”(特指20 世纪70~80 年代)。该书透过社会性别的视角,显示出足球在巴西具有融合和分裂人群的双重特性。
利弗本人对巴西足球的喜好以及她与球王贝利的私交使得这部巴西足球民族志格外引人注目。女性和美国人的双重身份更使她获得了与贝利单独见面和访谈的机会。因为在那个年代,巴西人通常认为女性和美国人是不可能对足球如此着迷的。而利弗的专业精神,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人的文化偏见。通过对足球俱乐部老板、教练、球员、足协官员、体育专栏记者、球迷俱乐部负责人以及200名球迷的访谈,利弗以竞技体育为棱镜来研讨人群、文化和政治三者间的关联性,贡献了可资仿效的范本。
在《足球狂热》1995 年再版的序言里,利弗不失时机地蹭了1994 年美国世界杯的这一热点。她着重阐述了世界杯史上首次在没有持久足球传统的体育大国举行的历史意义。美国世界杯期间,多达188 个国家转播了赛事,在电视机前观看决赛直播的观众达到了创纪录的10 亿。利弗难掩对美国世界杯赛事的赞美之情。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心仪的巴西队重夺雷米特杯,更重要的是,世界杯让使得美国的少数族裔(尤其是拉美墨西哥裔)有了表达身份认同和宣泄民族自豪感的合理途径,同时该次世界杯对于职业足球,尤其是美国女子足球的成长壮大并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冠军,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利弗的研究表明,国际体育盛会在成为比赛对抗的戏剧化舞台的同时,也通过强化参与者(如球迷、赛事组织者和媒体等)对该项运动的共同喜好产生巨大的趋同效应。
2.2 《一部有关英格兰足球迷的民族志》[10]
上文提及的利弗是通过熟悉和研究巴西足球而成为球迷的,佩尔森(Pearson)不同,其在写作《一部有关英格兰足迷的民族志》之前就早已是一位资深球迷。他第一次随家人到曼彻斯特联队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时年仅3 岁,之后,逐渐成长为忠实的红魔球迷。虽然同为球迷,利弗和佩尔森的研究出发点和宗旨却有着显著差异。前者在开始着手研究时,对足球文化知之甚少;而后者却是在英国职业足球亚文化氛围中成长大的“内幕知情者”(cultural insider)。前者试图以民族志文本为载体,录写巴西足球这一“典型”案例,呈现全球化条件下竞技体育的持久魅力和文化成就,并弥补英语学界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后者除了真实还原田野图景之外,还有试图通过实证案例来消除公众对英格兰球迷的刻板印象,同时为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初衷。
顾名思义,《一部英格兰足球迷的民族志》的田野凝视对象就是以行为出格而闻名于世的英国球迷,该书副标题为——罐头(cans)、警察(cops) 和嘉年华(carnivals)3 个关键词,不仅仅是为了玩弄文字游戏,更是鲜明地指向了作者佩尔森在对球迷进行田野观察时的3 个聚焦点。佩尔森先后费时16年,以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对英国职业足球劲旅曼联、布莱克普尔(Blackpool)和英格兰国家队(1998年和2006 年世界杯期间)的球迷进行了长时间的田野追踪研究,系统地描述和解读了被他称之为“嘉年华球迷”(carnival fan)的行为特征和亚文化准则[11]。通过跟队随访,佩尔森对这比貌似狂放不羁的“嘉年华球迷”在国内和国际球场的表现方式有了真切的了解。其发现:创造嘉年华式的节庆氛围和现场效果是球迷观赛的主要动机所在:赛事阶段的嘉年华狂欢为他们暂时摆脱日常生活规范,以成群结队的方式“酗酒滋事”,从而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为达到这一目的,成群结队的球迷常常不由自主地挑衅或冲撞足球权威,卷入与球场管理方、警察和“足球流氓”的冲突与纷争中。佩尔森在书中对近年发生的一系列球迷寻衅和球场失序事件进行了较为中肯评述,同时也在参与式观察的基础上,对球迷的性别、性、种族态度以及球场管控技术对于球迷整体影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有着“足球流氓”之称的英格兰球迷一直是被大众媒体、警方和球场管理人员标签化的“特殊人群”。①本文作者不禁回忆起30 年前在英格兰北部利兹(Leeds)大学做交流生时,听朋友绘声绘色地描述过球迷是如何有组织有预谋地在赛场上滋事。在当地超市购物时还撞见一位据说是利兹联队“足球流氓”后台的小学校长,其步态和神情看上去还有点像黑社会的头目。地方特定语境中传媒和谣言刻意塑造的刻板印象,显然无益于消除人们对足球迷群体的文化偏见。然而这种,在地方特定语境中传媒和甚至于谣言所刻意塑造的刻板印象,显然无益于消除人们对足球迷群体的文化偏见。佩尔森力图从球迷的立场、用球迷的声音来解释他们的言行和动机,由此来反思和质疑被大众媒体过度渲染的“足球流氓主义”神话,也为如何更有效地维持球场秩序和控制人群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的资料。
作为曼彻斯特大学新近推出的“新民族志系列”(New Ethnographies Series)中的跨界趣作,《一部英格兰球迷的民族志》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曼彻斯特学派”一贯的作风,即:始终如一的跨学科田野视角和对专注于小范围社会和组织机构的细致案例分析。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佩尔森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管理学院任教,并非人类学科班出身,然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使他获得了比同行更加接地气的田野洞见,为犯罪学、社会学和体育学等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植根于现实世界的民族志案例,同时也为如何变通使用参与式观察手段研究体育文化实践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3 全球化与地方转型背景下的体育人类学研究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包括奥运会在内的国际体育赛事实际上已经成为各种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对抗和平衡的平台。竞技赛场所展现的除了选手高超的技能、运动员精神和以“公平竞赛”为准则的所谓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精粹之外,还有民族主义情感及利益集团的“贪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奥运会和国际锦标赛场为北约和华约两大敌对阵营意识形态的持久较量,提供了不见硝烟的阵地。在苏联和东欧,以军事化和“科学”手段培养尖子运动员的机构和制度安排造就了所谓的“体育工厂”,其产品就是一批批在国际大赛上掠金夺银的好手。他(她)们使欧美选手在田径、游泳和球类项目上的优势几乎荡然无存。对垒双方的运动员的身体几乎成了不同政体和团体表达极端爱国主义的工具。
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发挥人类学视角和方法在文化理念和实践经验两个层次上所占据的独特优势,将考察重心从地方道德世界中的单一场域转向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中多点和多地的体育实践过程,是一个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体育运动的“中国模式”也是学界内外的关注焦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 世纪60 年代开始,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实施使得一些源于西方的体育项目如乒乓球、羽毛球、体操和跳水等运动项目逐步崛起,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几乎成为中国力量的代名词。中国教练和运动员通过实践摸索出的一整套因地制宜的训练手段,在截然不同的制度文化语境中完善和丰富了这些项目的内涵,并使之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在北京和伦敦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傲人成绩唤起了全球华人民族主义情感,但也引发了西方媒体带有种族偏见的谬论。
从20 世纪80 年代起美国密苏里大学人类学教授包苏珊(Susan Brownell)就尝试使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手段,对中国女运动健将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对于中国的发展进行了从微观个体到宏观制度整体的描述、探讨和解析。在其专著《为中国锻炼身体》中[11],她解释了身体与文化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联,以及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对身体文化的影响。她通过观察1987 年全国运动会来分析新的社会变迁,如激励政策的引入。与“毛泽东时代”不计较奖牌得失不同,中国体育1980 年代开始鼓励竞争,赢得奖牌和奖金。在运动员激励动机层面,她比较了西方竞技体育强调的“公平竞争”与中国本土的“面子”之间的差异,与西方体育强调通过体育本身公平角逐出输赢不同,中国体育似乎更关注参与者的荣誉面子问题。在女性参与运动方面,她注意到,相对于西方社会,中国社会对女性参与运动持相对友好的态度,这也使得中国女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获得了相较于她们男同胞更好的成绩。
在《北京的赛会:奥运对于中国的意义》[12]一书中,包苏珊考察了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的相遇,并且更进一步将中国体育置于全球视野中进行分析。她分析了在西方竞技体育模式的引导下,中国武术如何被拒绝列入奥运会的正式项目及美国社会关于中国体育的很多偏见,如,所谓的国家支持对年轻运动员的“剥削”。奥运会是一场涉及全球观念,人员和科技流通的文化展演。包苏珊将人类学的分析单位从社区和群体扩展到大型事件和活动,后来她又将对大型活动的研究延伸到了上海世博会。在与Niko Besnier 合作撰写的体育人类学总结评论中,她继续指出未来的体育人类学不仅需要对大型赛事活动的组织进行人类学分析,还应该对这些大型活动的遗产和对举办地的影响进行分析[13]。
在关于中国体育的人类学分析中,包苏珊展现出了熟练运用理论工具却不拘泥于既定范式和分析框架的能力,以及通过中国经验反思欧美学界固有思维定式的创新意识。值得一提的是,她的曾祖父是美国第一位成功地为华工维权的州级大法官。1980 年她通过选拔赛,成为美国奥林匹克运动代表队七项全能选手。在此之前她连续三年参加充满政治意味的美苏田径对抗赛。然而由于美国发起的对莫斯科奥运会的抵制,她失去了展示才华的良机。1985 年她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留学生,并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大学生运动会,获得1 金2 银的成绩(她创造的全国纪录至今未被打破),对于实践中的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她有着比一般中国人还要真切的“局内人”的体验和感受。应该说,包苏珊堪称传奇的个人成长经历、在加州大学研究生院所受的学术训练、以运动员身份而进行的参与式观察以及她与包括何振梁在内的中国体育界人士结下的情谊,使她获得了令同行嫉羡的第一手资料,并且奠定了她体育人类学代表人物的地位。她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国竞争2000 年奥运会主办国之所以失利,其原因主要在于西方大国长久以来一直没有消除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傲慢心态。作为国际奥委会(瑞士洛桑)的顾问,她以学者和体育权威的双重身份,为维护中国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应有尊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包苏珊接受了数百家中外媒体的采访。在《何振梁与奥运五环梦》发行式上,包苏珊作为英译者发言[14]。
包苏珊的同道罗力波(Lozada)则以球市和球场为聚焦点,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对上海这座象征中国现代性的城市内足球职业化表象后隐匿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情绪的宣泄作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和分析[15]。他揭示,球迷们一方面对地方俱乐部和国家队的赛场表现极度不满和愤懑,另一方面又以观赏欧洲职业联赛的方式来想象和描绘异域文化的图景。以竞技体育为棱镜,罗力波通过运用田野民族志手段,揭示出全球性消费文化和地方转型这两股结构性力量所主导的体育产业化对于处在城市巨变中的普通民众的多重意义。同包苏珊一样,罗力波也是一位体育运动好手。除了在大卫森学院教授人类学,他还任该校男子网棒球队教练。
包苏珊和罗力波的前瞻性探索为后奥运时代的中国的体育人类学田野考察和反思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洞见。随着思想、人才和资本的流动,中国体育将不可避免地与世界相遇。正如包苏珊所言,大部分人都关心奥运会如何改变中国,也许我们同样可以问,中国将如何改变奥运会。①由于时间和篇幅限制,本文未能对耶鲁人类学家William Kelly 对日本职业棒球的不懈探索以及历史学家徐国琦以中国百年奥运梦为主题所做的开创性研究展开评述。
4 结语
作为公共领域的流行文化模式,体育是形塑个人与社区,社会与国家,以及地方与全球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动力;现代体育正是在这一系列的互动中形塑和发展的。现代西方社会在对非西方社会“殖民”的过程中发展出了许多现代竞技体育理念,并不断地应用“现代”竞技体育来文明化“非西方社会”。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在这一全球互动历史中理解为什么中国武术很难接纳为现代体育竞技项目。虽然现代竞技体育起源于全球互动,它的理念和组织形式被不断“翻译”到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发展出新的功能和意义。
注重实证、比较和细节的人类学方法为析察体育在社会语境和文化实践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工具。而人类学的文化观以及跨学科的思维路径,必将推动学者对当代中国体育实践进行卓有成效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16],发展出关于身体和组织的文化理论。体育人类学的研究同时会在应用层面帮助我们理解体育运动面对的难题(如兴奋剂和种族歧视)和帮助有效地改善体育制度设计[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