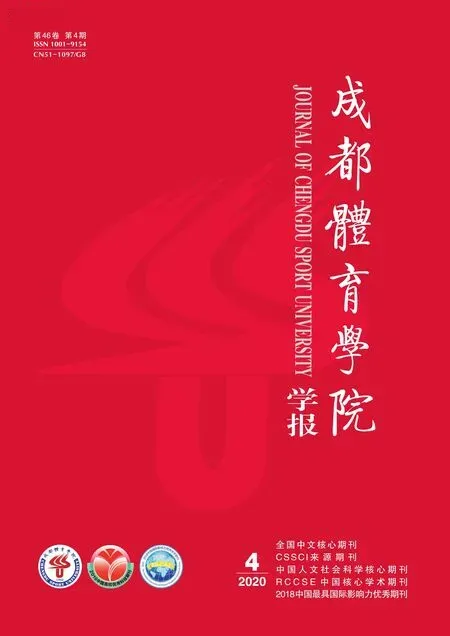节奏趋同:西方当代舞蹈与东方搏击类运动①的融合研究
2020-11-24塞尔吉奥雷蒙多王永顺
塞尔吉奥·雷蒙多,王永顺
1 什么是通用节奏效率
著名的汉学家马塞尔·格兰内特指出,阴阳理论所传达的世界观概念是基于通用的节奏效率。阴阳辩证法指出,事物与事物,事物与万物皆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相互影响。若不将事物看做整体,则任何事物都难以理解通透。阴阳辩证法并非逻辑体系,比如希腊哲学所形成的逻辑体系,而是借用于产生真实现象的标志。仅从理性角度研究阴阳辩证法,而且通过抽象概念与归类步骤区分反面事物的相互性与感官世界,这样的分析方法是错误的。更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则是通过实际体验与体认提高对变化的感知能力,且适当融合知识,在不放弃通用的节奏效率的前提下丰富实际体验。因此,人们可以进一步寻求有效方法,用以为人们一生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可以通过成熟且有意识的方式承担起对自己、对当下和将来社会与环境的责任,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人们认为阴阳两种力量作为一个整体始终不断地变化着。此外,阴阳并非固定的实体,但可被看作两个彼此竞争却又互补的实体的集合。阴阳交替出现,并始终变换,形成不同的组合,证实了万物合一的长久性。
人们通过维持身体和精神的灵活性,从而实现对对立且互补的阴阳之间的不断调节。此外,对阴阳不断调整的追求也是武术哲学的灵感来源。因此,阴阳调整发掘了每个人固有的可塑性,尤其是大脑的可塑性,故而像现代生物学所证明的那样,帮助个人拥有新的状态。实际上,节奏这一概念也被认为是新科学范式的基础。近几十年,这些科学范式被用以讨论复杂理论,旨在超越笛卡尔——牛顿简化论。笛卡尔——牛顿简化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已在化学,生物学和物理学领域引发了革命性变革,其表明进程与稳定性之间的动态关系事实上是生物体的固有特征。但是,阴阳两个极点仅在节奏模式下才能同时存在,例如在波动、振荡、振动,起伏时。因此节奏模式成为现实生活秩序的基础,换句话说,节奏模式发展出了有序结构。[1-2]而且,节奏这一概念可以很好的代表“调节人类行为的非社会原则”。阿兰·图林指出节奏可能化解工业装置、市场和国家对个人日益增长的影响。实际上,现代化进程需要变得更为合理,且需要找到能承担起对自身和社群责任的主体。[3]
2 本研究的基础
过程和稳定性之间持续的动态性产生了有序结构,而人体本身就是体现这一有序结构的最佳范例。米歇尔·福柯对这一话题有十分实际的认知。福柯建议人们把焦点转移到当代事物形态上,并认为它已经淘汰了形而上学问题和有关知识基础的相关问题。[4]从他的观点来看,事物并非稳定的固定的结构,而是可能性具象化。换句话说,事物并非物体,而是能够适应任何可能客观表现的现象。此外,尽管在当代社会中,各种变化接踵而至,但是任何人都很难将自身当做是持久的事物。现代性极大地促进了各类变化及变化的速度,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文明这一意识已经丧失或是很难维持。齐格蒙德·鲍曼在谈论当代人的多变的身份认知时便提及了这一论点。[5]
如果根据福柯的说法,人体则是一种社会结构,且一种潜在状态,那么我们可能将人体当做目录,认定只要通过勤奋密集的锻炼与练习就可获得特定的技能。且无论何种情况下,此类锻炼与练习都十分必要,因为即使人体展现出了适应周围环境条件的绝佳能力,但这类能力仍然有限:例如,像鱼一样游泳,像蟋蟀一样跳跃,像瞪羚一样奔跑,像老虎一样搏斗,像蜥蜴一样攀爬的能力…这些隐喻强调了人体结构的潜能与动物的特定能力之间的差距。动物的身体总是能立马展现其完美的某一特性,而人体则更像是许多潜能的集合体。但人体的潜能性并不完美,因此我们必须要有能够从人体中锻炼出某一特定能力的意志(理性的或有远见的)。人体被当做一项能帮助我们建立身份认知的项目,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心理生理技术来探寻我们的身份认知。在这项研究中,该技术成为了我们建立身份认知的工具,因为它能够同时兼顾到心理、身体与情感,且在使用该技术过程中,原始人类社群中比赛、戏剧、仪式之间的原始关系得以保存。
3 舞蹈与搏击类运动的原始关系
舞蹈与搏击类运动是大多数人能随节奏全身心投入的两种人类活动。在古代社会中,比赛、戏剧和仪式之间的原始关系是通过舞蹈表演与格斗技巧精准体现出来的,且常能从对自然的观察和感知中得到启发。[6-7]
这些对原始关系的展现可以从萨满巫师的表演中得以体现。萨满巫师将其身体当做一种交流工具,利用身体动作展现一些自然现象和动物语言。此类动作所展现的舞蹈场景与战斗场景之间几乎一致。此外,此种对原始关系的展现也可由集体表演体现。此种集体表演可被视作利用舞蹈的模仿能力,展现社群内部故事的典型运动,比如集体表演可以隐喻爱情或打斗场景。从该意义上讲,人们可以联想到新西兰毛利人的传统舞蹈——著名的哈咔舞。在每次比赛之前,著名的新西兰橄榄球队全黑队会表演哈咔舞“Ka Mate!”。哈咔舞在大众前的表演形式仍只是战舞,用以吓退对手。但实际上,哈咔舞出现的初衷是为了能通过舞蹈自由表达喜悦或痛苦。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舞龙”。这一民族传统体育形式经常出现在中国和越南武术的表演中。舞龙最初出现的目的在于某一社群想向其相邻的敌人展现其力量,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战争。[8]舞龙在宋朝时期就已经非常流行,如今在举行某些庆祝活动时,舞龙仍然存在。例如,在新年庆祝活动中,人们认为舞龙可以带来好运、和平与繁荣。但在武术场景下,舞龙常有“鼓舞战士”的传统含义。舞龙与武术界之间存在联系是因为舞龙这项活动仍有极大难度,因为舞龙需要表演者有强健的身体基础。
在现代社会,在都市化、生活富裕、工作久坐不动且经常过度饮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运动强化我们身体素质和安抚我们的身心。舞蹈和搏击类运动这两种身体活动都包括了能改善我们自身气度的所有要素。通过不断的试验,与试者通过将放松心境,控制情绪和提高身体效率结合起来,从而建立了强大的个人性格。
结合以上背景,在近几十年间,西方当代舞蹈与东方搏击类运动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这并不奇怪。相比于古代格斗学在战斗力上的体现,古代格斗学为心境平衡、传达能力和美学动作留下了更大的研究空间。同时,现代舞蹈受到了亚洲搏击类运动和亚洲传统戏剧和舞蹈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印度舞蹈和戏剧、日本戏剧和巴厘岛舞蹈的影响。对于舞蹈而言,这意味着古典芭蕾的原理被彻底重塑,从而得以创造出“独特并新颖的动作”。
4 西方当代舞蹈与搏击类运动的相遇
我们很难也几乎不可能精准确认西方现代舞蹈是何时何地接触到搏击类运动的。但有许多重点研究一致认为,19 世纪70 年代的纽约市是现代舞蹈与搏击类运动融合这一现象的发源地。[9-11]当然,自20 世纪初美国现代舞蹈创始以来,其形式与古典芭蕾舞截然不同,且其内容、角色、服装和体型塑造上都过于严格。美国现代舞蹈先驱伊莎多拉·邓肯、露丝·圣丹尼斯和泰德·肖恩都受到了法国音乐家弗朗索瓦·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塞里·德尔萨特的理论的影响。通过观察人类的社会关系,这位音乐家创造出一类表演风格,制定出一套动作和表情规则,以帮助演员和歌唱家更好地传达他们的感情。因此,很可能正如现存的少量美国和欧洲艺术家所写下的报道所言,在19 世纪西方舞者已经开始接触搏击类运动,即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搏击类运动和舞蹈的融合仅仅代表了个人表演的技巧,而非公开展现了两者的融合。
就此而言,尽管我们并未深入分析伊朗——亚美尼亚裔舞蹈家格兰特·穆拉多夫,但他的故事十分具有启发性,因为穆拉多夫有多重身份。起初在巴黎和纽约,他是一位著名的芭蕾舞演员,并在之后成为了一名老师和编舞者,而后成为一名太极拳大师。1935 年,他开始在巴黎练习瑜伽,且这一习惯持续到他去世。1944 年在纽约,他在冯家福①冯家福(Gia-fu Feng),1919 年出生于上海,先后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而后在美国传播道家文化。冯家福被认为是美国嬉皮运动的重要精神导师和支持者,重要的翻译著作是《道德经》和《庄子内七篇》。的指导下对太极拳也产生了兴趣。20 世纪70 年代初,他移居意大利,在那里他成为引入中国武术的先驱。他在罗马、佛罗伦萨、热那亚和都灵都教授过许多积极的学生。同时,我们应该铭记穆拉多夫,因为他最初出版了与太极拳有关的意大利语书籍,且建立了相关的编辑部,而且该编辑部近年来也逐渐得以壮大。
他是意大利太极拳的先驱,并深刻影响了公众舆论对太极拳的认识。实际上,太极拳(就字面意思可解释为至尊终极拳Supreme Ultimate Fist)是一种能致死的打斗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可帮助长寿和福祉的特别方法,此外太极拳还可作为一种表达途径。穆拉多夫移除了太极拳中的武术元素,原因可能是冯家福并未将太极拳中的武术元素教授于他。冯家福被誉为将《道德经》引入西方的最重要人物之一[12],因为他所翻译的道教的最重要的著作《道教经》,已售出超过100 万册。他还是艾伦·沃茨的同事,以及《垮掉的一代》的作者杰克·凯鲁亚克的朋友。同时,他也是创建了自我实现理论的心理学家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的朋友。冯家福被认为是20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加利福尼亚嬉皮反文化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考虑到这一背景,我们可以轻易地推断出,作为和平运动的推动者之一,冯家福很可能会忽略太极拳的武术元素,尤其是在他需要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一位专业的芭蕾舞演员的时候。因此,当下在意大利的太极拳学校中(其中一些学校由穆拉多夫的学生开创),如果有一些学校教授的太极拳没有武术的成分,而像舞蹈一样强调艺术的表现力,这并不足以为奇。
5 西方当代舞蹈与搏击类运动的融合
5.1 融合的开端:《镁》的引发
1972 年,在纽约,史蒂夫·帕克斯顿创作了一场名为《镁》的表演,至此搏击类运动与西方当代舞蹈终于得以融合。帕克斯顿和其他年轻的舞者开始练习合气道和太极拳,并最终创造了一种新的双人舞蹈形式,即所谓的“接触即兴”。“接触即兴”在欧洲也很快成为一种广为人知的新的艺术形式。
舞者的灵感来自大都市生活的日常姿势与日常情景,他们不断即兴创作,并通过触碰传递给舞伴。但是,舞者与舞伴之间的交流不仅仅只限于手,而在于整个身体的投入,从而发展出“一种涉及所有感官的身体对话”[13]。“接触即兴”的传播也促进了它的发展,因为它融合了其他不同舞种的技巧,比如卡泼卫勒舞。卡泼卫勒舞是舞蹈和格斗技巧的特别融合,它起源于巴西,最初由非洲奴隶表演,衍生出其中可致命的战斗技巧。表演者跳舞时就像在表演一种杂技桑巴舞,借助鼓和一种名为birimbao 的弦乐器产生的节奏来隐藏他们的战斗能力。在表演卡泼卫勒舞时,两个斗士(舞者)最先开始前后移动,从而表现出其非凡的灵敏程度。随后,他们便开始一系列极其快速如杂技般的进攻和防御技巧。归功于音乐和围绕着表演者的观众通过拍手和唱歌产生的节拍,这类运动更像是舞蹈而非战斗。
“跳舞能力”这一概念受到“接触即兴”核心主旨的启发,根据其主旨,“无论他们来自何处,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他们的优势和弱势是什么”,每个人都可以跳舞。[13]1987 年,美国舞蹈家兼编舞家阿里托·阿莱西开发了一种即兴表演技巧,得益于“一项基于个人生理和心理能力的相互联系的研究”,健壮的人和肢体残疾的人们可以一起跳舞。[13]
在1990 年代及随后的几十年间最初的这些试验中,搏击类运动和舞蹈之间的交流旨在促进即兴舞者的即兴表演,无论舞者是专业人士、身体强壮或残疾人士。在这些试验之后,出现的一些表演中,通过编舞、舞台表演和精良制作,搏击类运动的技巧、哲学、情景和典型场景得以体现。在此次研究中,我们将分析其中的五场表演,因为它们代表了当代舞蹈的不同流派。这五场表演的首映地点和时间分别为:1994 年中国台湾,2000 年瑞典斯德哥尔摩,2004 年意大利拉文纳,2008 年英国伦敦和以及2017 年意大利罗马。
5.2 融合的表现
(1)《流浪者之歌》。1994 年,在中国台湾省云门舞剧院上演了林怀民①林怀民,著名现代舞编舞大师,中国台湾第一个现代舞剧团“云门舞集”创始人,在玛莎·葛兰姆现代舞编舞理念的影响下开始接触现代舞,并进一步赴美深造,深受美国当代舞蹈理论与实践的影响。编舞的《流浪者之歌》。这支舞蹈的开幕式在台北大剧院举行,观众可以参与到时长90 min 的整场表演中,其舞蹈设计旨在展示一场盛大的净化仪式。该表演重现了作者前往印度菩提迦耶的旅程。按照宗教传说,印度菩提伽耶正是公元前530 年左右悉达多·豪达玛顿悟成佛的地方。
该剧院的24 名舞者不仅学习了古典芭蕾舞和现代舞,还学习了太极拳和其他搏击类运动,以及中国戏曲和书法的姿势和手势。通过这种方式,舞者获得了惊人的表现力,他们将中国戏曲的经典动作与太极拳缓慢但有力的动作以及其他搏击类运动融合在一起,因此舞者似乎在舞台上处于律动状态。这场表演旨在展现如何通过与世隔绝来寻找安宁这一主旨,并展现了神秘的轻微律动与阴阳和“五行”哲学概念的融合,而后者恰是武术和中医的基础。
(2)《两极》。多年以来,米利森特·霍德森和肯尼思·阿彻与一群居住在伦敦的舞者和插画家合作,旨在重新设计《春之祭》这一原始芭蕾表演,该作品于1913 年由伟大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编排。为展现这一作品,伦敦皇家芭蕾舞团编排了一场舞蹈并于1987 年演出。该舞蹈随后在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十二个国家上演。基于1900 年代俄罗斯芭蕾舞团与中国文化和武术的融合,霍德森和阿彻第二次创作了一个名为《两极》的当代舞蹈节目。《两极》这一舞蹈于2000年在斯德哥尔摩首次上映,展现了阴阳两极之间相斥但互补的力量。
该表演中,四对男女舞者在舞台上跳舞,通过身体接触,使每一极都向相反的方向滑动。舞者依据八卦这一中国传统八边形图案,沿着一个圆圈外部或沿着穿过圆圈内部的八条线移动。八位舞者都学习过古典芭蕾,但是为了该场演出,他们还学习了基于八卦的传统中国武术八卦掌。得益于八卦掌,编舞人得以创造出一种四对舞者能交织在一起的双人舞。实际上表演八卦掌是舞者展示出了脚底与地面之间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例如一个人应在泥泞中踏出一步,但是上半身为使手能够自由活动而仍扭转着。
(3)《佩剑舞》。2004 年,在意大利拉文纳音乐节上演了由著名的比利时编舞兼导演米沙·凡赫克创作的佩剑舞。他的剧团自1981 年成立以来在国际上广为人知。此次,他指导其剧团上演了一出将搏击类运动与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表演。这次表演中使用的配乐由乔尔·格雷、林英哲、灰野敬二和皮埃尔·亨利共同创造,此外演出中还使用了与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和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合称为最著名的苏联亚美尼亚作曲家阿拉姆·伊利奇·哈恰图良所创作的加贾尼音轨以及一些日本传统音乐。
该剧团表演的场面设计和舞蹈设计中都包含有搏击类运动成分。且在本次表演中,搏击类运动这一成分因为若林庆子和弗朗西斯科·德多纳托这两位格斗界重要人物的参演而更为突出。若林庆子出身于一个武士家庭,她精通柔术鹿岛神流,师从于此项运动最后一位传人。此外,她还师从合气道创始人植芝盛平,学习合气道。在首次参演时,她已经77 岁了。此外,她还是日本著名的歌剧家,自2001 年以来,她与身为米沙·凡赫克剧团一员的女儿洋子一起住在意大利切奇纳。她教授驻扎在里窝那的福尔戈尔旅(雷霆旅)的伞兵如何自卫,并在意大利多个地区举行关于柔术与合气道的讲座。另一位表演者,年轻的弗朗西斯科·德多纳托来自拉韦纳。他曾于1990 年获得欧洲拳击冠军,此外,他还教授泰拳和全接触运动。此次表演中舞蹈与搏击类运动之间的交织表演是由日本传统舞蹈家,舞团另一位成员三木的母亲松濑彩子完成的。
(4)《佛经》。西迪·拉尔比·沙尔卡维是一位拥有摩洛哥血统的比利时编舞家,他是现代舞蹈最著名的编舞家之一。2008 年在伦敦,他与来自少林寺的18 位僧侣共同合作表演了《佛经》这一节目,这18 位僧侣精通闻名世界的少林武功。
对少林武术的学习是这些僧侣遵循的严格宗教学说与生活的一部分。此外,少林武术包括了习得完美的、巧妙的技巧,要求小到毫米的动作精准度,这些由谢尔卡维于2007 年在少林寺学习和冥想时创作的动作对于此次表演的舞台影响巨大。由伦敦、雅典、巴塞罗那、阿维尼翁、卢森堡和布鲁塞尔的主要文化机构的共同制作的《佛经》,其场景展现了基于对自己身体尊重所取得的精神探究。这一精神探究可以通过结合冥想的艰苦身体训练来达到身心间的平衡,而达到这种身心的平衡也是这一舞蹈创作的初衷。
(5)《8x8=64》。《8x8=64》这一表演创作于2017 年,借鉴了数字8 扭转缠绕的表面含义。该表演是由本文作者塞尔吉奥·雷蒙多与意大利里特米·索特拉内伊舞团的领舞及编舞家阿莱西娅·加塔合作完成。阿莱西娅·加塔创作的作品通常与线条设计和几何有关,她的创作想象集中于空间、哲学和身体姿态间的关系。其所编的舞蹈汲取灵感自建筑和城市景观,并融合了视觉艺术、当代舞蹈、嘻哈和霹雳舞。本文作者塞尔吉奥·雷蒙多是一位历史学家,同时他还出版了有关武术历史和人类学的论文和书籍。雷蒙多师从陈式太极拳大师陈小旺先生,在研究历史与文化的同时还在卡西诺和南拉齐奥大学教授太极拳和气功。在历史比较法的指导下[14-16]他还在2015 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寻找无限》的文章。在其发表的《数字8 和武术》文章中,他也分析了该数字在不同文化中的多重含义。[17]
实际上自远古以来,在西方和东方数字8 都曾存在多种文化含义,在各个领域都有象征和具体意义。比如从宗教领域到数学领域、从哲学领域到风和太阳系的命名、从建筑到象棋、从慢跑到肢体表达,在肢体表达上体现的更为形象,例如肚皮舞、探戈、气功和各种搏击类运动。在表演《8x8=64》中,数字8 既体现了舞蹈设计,又体现了舞蹈动作。在舞台上,舞者表演出一系列场景,描绘了该数字的不同含义。例如:太极拳中模拟云流动的手部动作、将气功和打斗结合起来的棍棒表演、八风(八风统指四时气候变化或尘世间煽惑人心的八件事),以及无限。数字8 决定了所有舞蹈动作的顺序及舞者表演的“呼吸”。作为该表演的核心,呼吸会在舞台上转换为声音、时间和图像。在《8x8=64》这一表演中,舞者最初拿着扇子舞动,代表呼气;在表演中途,舞台上出现一个大型吸尘器,代表吸气,演出最后演奏者对着“雨”的气柱吹气代表再次呼气。该表演于2017 年在罗马举行的迪韦尼雷节中获得一等奖,并于2018 年和2019 年在上海上演。
6 结论
本文中所分析的搏击类运动与舞蹈融合的案例可以体现出表演、戏剧与仪式之间的原始关系,这是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18]这些表演展现出了当代大都市社会中的原始关系,这一原始关系可以艺术地为失落的地球村居民找到一种心理和生理平衡。在这种情况下,美学享受保留了对象的真实感,同时在主观行动的影响下,创造出将人体合而为一的艺术体验。亚洲搏击类运动基于通用的节奏效率,而节奏存在于相悖却互补的力量的传承中,因此很多现代舞蹈流派对武术产生极深的兴趣。舞蹈重现了搏击类运动中的艺术成分,由此再次开始追寻武术的哲学基础——和谐、美好与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