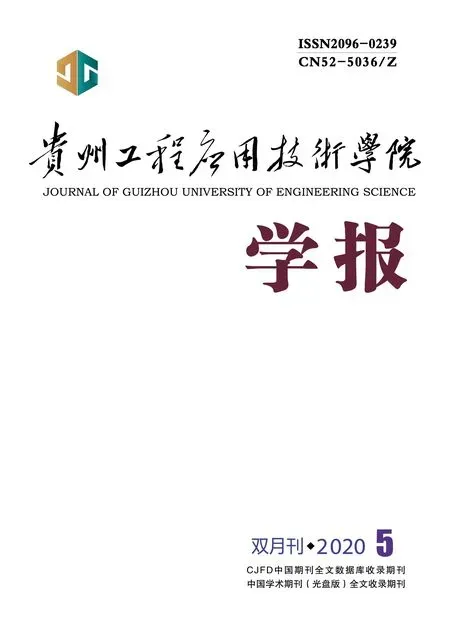凉山彝族关于麻风病的文化应对与社会构建
2020-11-23约其佐喜
约其佐喜,蔡 华
(西南民族大学哲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麻风病在中国,最早的记录可追溯到春秋时期[1],不少历史、哲学著作都有相关记载。由于麻风病在历史上的不可治性,人们对其尤为恐惧,凉山彝族也不例外。麻风病在凉山彝区被称为“癞病”,民国三十一年(1942)《康导月刊》第三卷第一、二合刊曾载:“夷人极忌癞疥。因此种病症传染性极大,每一处染病,必杀鸡犬弃道上,见者生畏则四周各地皆禁人往来。家有癞疥者,其家人必打猪羊或牛以饮之,迫其自死,否则易绳缚之掷之岩下或洞中,虽父母兄弟亦之不顾。”以前,在封建社会里,凉山彝族麻风病人轻则被隔离、除籍①,重则判以死刑。如今,生物医学的突破使得麻风病的不可战胜成为了历史,但在凉山彝族群体中,麻风病“无药可治”的观念依旧盛行,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笔者在凉山彝区考察“尼木撮毕”②大型民俗仪式时注意到,若仪式的祭祀对象中有患麻风病致死之人,则需为其单独举行特殊的仪式,彝语称作“粗尼木”。该仪式过程尤为宏大复杂,耗资堪称仪式之最,最终目的是为逝者之魂卸除“麻风病根”,以免此疾“遗传”给亲属、后代。麻风病是凉山彝族生时最为恐惧、避而不谈且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疾病,为何在患者死后却如此声势浩荡地为其举行“卸除病根”的仪式?生时无法治愈的疾病,逝后为何被认为是“可卸除的”、“可治愈的”?这看似矛盾的背后是否蕴藏着某种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本土逻辑?同时,麻风病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不会以基因遗传的形式传给下一代,但凉山彝族却将其视为“可遗传性”疾病并且极忌讳与此类患者及其亲属通婚,可见麻风病患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无法用单纯的生物性因素予以解释。
每个文化群体,对于疾病的认知与应对实践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凉山彝族也不例外,但目前学界关于凉山彝族麻风病相关的研究屈指可数,对其深层次社会文化因素挖掘与探讨的更是寥寥无几。
鉴于此,本文章将结合凉山彝族古籍文献与实地田野调查,除了关注地方性知识中麻风病之病因解释、治疗实践外,着重探讨麻风病“遗传性”的社会文化构建。
一、“无解”之源:一则关于“麻风病”的神话解读
一个社会群体创造并认同的集体表象作为一个群体客观化了的“知识”系统,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会以一种客观实在的巨大力量参与人类的生活。然而,神话作为集体表象的一种重要形式,是集体的传统或回忆,也是生活中对矛盾、困难、灾害、疾病的一种解释,通过这种解释,人类变得有承担现实痛苦与负担的能力。至于彝族至今依旧认为麻风病是“无解”之疾的观念为何,下述盛行的神话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远古时代,天上住着一位叫蒙直阿普的“雷”。他脾气暴躁、喜怒无常。不喜人耕种推磨,更不喜人生火做饭。旦凡听到人间有声响或闻到饭菜香,便立即打雷吓人、放电劈人。因此,人们不敢耕作推磨、生火做饭,饿得奄奄一息。支格阿龙知道后,决心惩治雷。他知铜可避雷,故身披铜蓑衣,手持铜网、铜绳、铜叉等工具。同时,又命人们做饭推磨以诱雷下凡与之较量,最终制服了骄横跋扈的雷。雷尽知药物,支格阿龙在降服雷后,还向他询问了治疗各种疾病的方法与相应的药方,雷尽告之,遂离去。待雷上天后,阿龙才想起竟忘了问麻风病的治疗之法。因此,麻风病在彝区便成了“不治之症”。
正如孟慧英所述“中国各民族神话有个显著的特点,即以不同的方式树立起具有权威地位的神祗,这些神祗构成了人们认识世界、解释各种疑难问题的最初或最终依据”[2]。在该神话传说中,彝族塑造了两位对比鲜明的人物“支格阿龙”与“双面雷”。
不难看出,“雷”是古时彝族先民生产生活中“严重破坏力”的象征,不仅指自然天气中“雷”本身,还暗指生活中会遭遇的各种灾难、困境。“雷”的“灾难之源”的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了古时彝族对“灾难”的恐惧、厌恶与无助。然而,“雷”的“知药”身份对应的是彝族生活中“疾病”之困,疾病是灾难的一种,疾病的性质就是灾难;其所掌握的权能又不得不使彝族先民敬之、拜之。神话传说中,人们对“雷”的矛盾情感实则为古时彝族先民面对灾难时的反映,既畏惧又想征服的矛盾心理。而“支格阿龙”,是彝族的英雄、领袖的象征。他制服“雷”的情节除了体现了彝族先辈积极面对困难的态度外,“铜可避雷”还暗示了不同的灾难亦有相应的解决之法。但在故事的最后,却以“遗忘”为由,解释了为何麻风病是“无法治愈”的疾病。
上述神话传说利用神圣象征突出了对彝族祖先的智慧和勇敢的敬仰,不仅强调战胜困难时彝族先民的基本态度,还解释了麻风病“无解之疾”的原因。随着该神话传说的世代相传,麻风病的“无药可治”,在彝族的传统社会中已然成为客观化了的“知识”系统,被人们所共享、交流,影响着其对自己生活环境的感知和判断。然而,彝族先民并没因其“无药可治”而选择逃避、消极应对,反而在长期的应对和“消灭”麻风病的实践中,通过与崇祖习俗、家支制度的融合,构建出了一套特殊的文化应对机制内化于彝族的传统社会之中。
二、病因与病症:麻风病的文化阐释
疾病是文化构建的,疾病通过解释形成,也只有通过解释才得以认识。[3]从人类学家的观点来看,人们对疾病病因的解释以及做出的反应都因文化而异,我们不应就疾病论疾病,而应该把它放在人们所处的文化场景中加以分析与理解。[4]因此,从本土文化和社会的角度说明疾病是必要的。
(一)病因阐释
引人致病的原因很多,病因观对医疗实践有着指导性作用。病因观不同,治疗的手段也有所不同。目前,传统医学将病因分为两类体系,“自然病因体系”与“非自然(或拟人)病因体系”。[5]“自然论”医学体系侧重从物质层面解释人体健康与不适,强调人体的平衡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和谐。换言之,“疾病”是一个客观化的实体,医生只需针对疾病本身进行治疗。然而“非自然论”或“拟人论”体系中,寻找疾病的“终极原因”是其特点,关于疾病的文化解读是必要的。对于病因的解释,凉山彝族的病因观当属“非自然论”体系一类,主要是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进行阐释的。
在传统的彝区社会,与防治疾病有关的仪式活动可分为“毕”③、“尼”④两大类[6];“毕”类,由毕摩主持,仪式种类繁多复杂且涉及到彝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祈福为主要形式;“尼”类,则由苏尼主持,无成书经文,主要以唱、跳、驱邪为主要形式进行治疗。对于“麻风病”的治疗,毕摩与苏尼各有所长,虽治疗仪式的形式不同,但两者对于麻风病的病因阐释却如出一辙。
麻风病,彝语称为“粗”、“奴”或“粗奴”。“粗”多为书面语,特指麻风病之病根,有“癞”之意;古彝语中“粗”有“光、电”之意,大地上的一切事物若接触到“粗”,便可能感染此病。[7]2“奴”多为口语,亦指麻风病,但更强调由麻风病导致的病症。在彝族观念中,麻风病的成因虽种类繁多,但仍可归为两大类:“自然型”与“社会型”。
1.自然型病因
自然型病因特指由自然界事物感染而致病的类型。这种类型的传播源有许多,主要包括“雷”、“电”、“雨”等自然天气以及“蛇”、“蛙”等动物,但麻风病的“病根”却是由天上的癞“粗”所致。彝族古籍《祛癞经》里载“粗之源流,起自上苍,降至人间”。[7]188《撮诺祭》⑤里亦叙述了“癞源于天”的情况,如“癞魔居天上,魔归至天际,你所有家业,全部在天上”[8]、“癞魔归天际,人们齐欢腾;癞魔回天庭,人们皆欢笑[9]”,等。至于癞魔“粗”降至人间后如何传播使人致病,经书中也有相关描述。《正义咒》中有“癞魔伴雷电,虹挂天空一,远在天际二,虹引癞魔三”、《癞土贫瘠咒》中也有“癞神所居处,癞神伴乌云,癞神随雨水,伴着那风云,伴着那雷电,降临沃土中,癞魔污沃土……”[10]等。同时,癞“粗”变化多端,经书中有大量相关篇,如《咒水癞》、《咒蛇癞》、《咒彩虹癞》、《咒雨癞》等。
可见,在彝族的观念中,癞“粗”源自上苍伴雷而生。同时雷与电相伴,同风、雨、云雾、雹、虹来到人间,所到之处便有“粗根”。雷击之处,“粗根”停留;蛇、蛙、鸟、兽等经过便会携带“粗根”散播到世界各地。人吃了带有“粗根”的食物便会得病,接近“粗根”所到之处也会得病;带有“粗根”的动物来到耕地或村寨也会得病;用了被雷劈过的树也会招此病。总之,“粗”来自于天,伴雷而生,大自然是“粗根”传播的媒介,人一旦接触到此类传染物便会得病。
2.社会型病因
社会型病因主要有两类:一为“直接接触麻风病患”型,二为“麻风病死者的纠缠”型。第一类社会型病因与现代生物医学类似,若家中或村寨中有人得了麻风病,周围的人就可能会被传染。第二种类型主要源于彝族的崇祖观念,万物有灵习俗,是彝族典型的文化习俗,而人的死因与死后的属性息息相关。虽然,死因并非死后属性的唯一条件[11]1:23,但麻风病作为彝族观念中极为恐惧、避而不及的一种疾病,因之而亡的人,其死后则极有可能变成“麻风病”。若某患麻风病者死后,其子孙或亲属也得了麻风病,则被认为极有可能是该患者的所致。
(二)病症阐释
在凉山彝族的传统观念中,不同传染源所致病症不同,麻风病的传染源主要有十二类:斯奴习奴、瓦霍吉奴、阿嘎扯奴、迪沃湿奴、迭托巴奴、义沃合奴、史奴纽奴、约木奴习、斯习沃奴、布乌习奴、其奴勒奴、吾呢措奴(如表一所示)。其中,布乌习奴、其奴勒奴、吾呢措奴被认为是具有“遗传性”的麻风病,原因在于其病症表现中有“骨髓发黑”、“肢体残缺”等人体结构、组织残缺情况。同时,以上三类患者与其他类型的患者相比,死后所变的“麻风病”更易作祟于后人。通常这类患者生前都被要求除去家支,家族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出资共同为其操举办一场浩大的“除籍”仪式,以防死后作祟于家族亲属。

表1 麻风病的主要传染源及种类
正如有学者提出疾病“是指某些症状和异常在不同时代和社会中被烙上文化特征的印记,这些特殊的症状和病痛种类因此带有强烈的文化涵义”。[12]疾病作为人类生活中“苦难”的象征,长久以来一直受到各个族群社会的防御和抵制。在医疗水平有限的年代,面对疾病带来的巨大恐惧,彝族先民选择寻求文化的力量,用其特殊的逻辑解释这一现象。由此可见,与生物医学将疾病看作个人生理事件不同,在凉山彝族的观念里,疾病存在于与更大的宇宙联系和更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
(三)麻风病的民俗预防和文化治疗。
“任何一种医疗文化都有观念知识和治疗经验两大领域,一方面是人们普遍认可的有关疾病与治疗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是文化治疗实践”。[13]9换言之,病因观指导着人们处理与解决疾病的方式和行为。由非自然因素引起的疾病,凉山彝族主要采用仪式文化的手段和方式来防治。通常,一个人若长期感到不适,便会实践其特有的文化习俗,即向毕摩或者苏尼处问卜以探病情;“确诊”后,则会根据其建议做相应的文化治疗。历史上,麻风病患也一样,在发觉自己可能得病后便会到毕摩或苏尼处问诊,确诊后,若可治,则会举行相应的仪式。
问诊占卜,是彝族传统社会中一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民俗现象。其中,鸡蛋卜、绵羊胛骨卜和库瑟(经书占)尤为普遍。同生物医学的医生类似,毕摩或苏尼首先会询问患者的情况,查看其病症表现,最后进行占卜。麻风病的占卜仪式通常是先用鸡蛋卜,看其病是否是麻风病,随后用羊肩胛骨卜占算是否能被治愈,若可,再用经书占算相应的吉时以举行适宜的治疗仪式。
1.鸡蛋卜
鸡蛋卜彝语称“沃其赫”,在凉山,鸡蛋卜是一种常见的判断疾病的方式。首先,患者会准备一个鲜鸡蛋和一碗清水,在鸡蛋较圆的一端扎一针头般大小的孔,并用嘴对此孔吹三次气。随后,手拿鸡蛋以顺时针方向在头顶绕三圈。接着就拿鸡蛋擦拭全身(痛处可多擦几遍),遂交给毕摩。毕摩接过鸡蛋后,会念诵《鸡蛋卜经》,念毕,在蛋身三分之一处将其分开,将蛋液倒入清水中,验看蛋黄与蛋白的呈相,不同的疾病呈现的表象不同,若蛋黄周围呈现出蛇形,则可确诊为麻风病。
2.绵羊胛骨卜
绵羊胛骨卜彝语称“约皮吉”。“绵羊胛骨卜”有两个过程,“烧骨念诵经文”和“验看胛骨纹路判断吉凶”。烧骨念诵经文时,毕摩会先将事先准备好的火绒草粘在羊胛骨的炙烤点上,随后一边念诵《羊胛骨卜经》⑥一边点燃火绒草。待经文念诵完毕,火绒草燃尽后,毕摩会将草灰抹去,翻至另一面验看灼烧纹路,若是吉卦,患者疾病可治;若是中吉,亦可治,但仪式较复杂。若是凶卦,患者疾病治愈困难,得另寻他法。
3.库瑟
库瑟:即“算吉时”。在举办治疗仪式的过程中,日期的选择尤为重要。与日常的“库瑟”不同,对于麻风病治疗仪式的举办日期往往按照彝族传统的“二十八星宿⑦”测日来定。其中第二十二星“瓦诺”日、二十三星“挖黑”日、二十四星“瓦斯堵”日、二十五星“瓦斯玛”日为治疗麻风病的吉日。除此之外,举行仪式会选择“冬季”或“非雨水”季节,以防动物、天气等因素使麻风病根扩散,危害他者。
(四)文化治疗
麻风病的文化治疗方式主要有两类:“粗吉”和“粗尼木”。两类仪式文化的举办条件不同,且规模、仪式所用经籍、牺牲、仪式道具也略有差异。
1.“粗吉”
“粗吉”。“吉”为彝语,有“驱除”、“送走”之意;故,“粗吉”仪式可理解为“送癞”或“驱癞”的仪式。该仪式既有以家庭为单位举行的,也有以村寨为单位举行的。举行该仪式的情况有两类:
一是当村中或离村寨不远处发生雷击事件后,以驱除“粗”根、预防感染“麻风病”为目的举行的;
二是“麻风病”患以“治疗”为目的“粗吉”仪式。做治疗类“粗吉”仪式时,毕摩会按照患者的严重程度举办不同的级别、规模的“粗吉”仪式,由轻到重依次为:“噶粗吉”、“粗曲吉”、“粗哲吉”、“粗诺吉”。
2.粗尼木
其为麻风病致死者举行的祭祖习俗。该仪式规模宏大、程式复杂、耗资之甚。举办仪式的目的有二:
一是为逝者卸除、驱赶“癞”,净化其死后可顺利归往“祖界⑧”;
二是为了预防“癞”再次作祟于该家支的子孙后代。[14]8
仪式需准备牛、公山羊、猪、鸡、猪油、酒、一口锅、一个铜盘、一把镰刀、一个铧口、一把斧子、一把尖刀与杨柳树枝与树杈(桃树、李树)数百根,并将所有物品带至屋外适宜之地,或山间、或田地。用杨柳树枝和树杈布置好道场,将祭牲摆至相应位置,待锅中油开始冒烟后,仪式便正式开始。
通常,“粗尼木”会由几位毕摩共同完成。但由于麻风病的“危害”广为人知,大多数毕摩都不愿意做该仪式,怕自己法力不够无法制服“癞”反而感染上绝症。但有两种情况例外:一种是长期为主人家举行仪式的毕摩;另一种是被占卜选中者有不可推辞的义务。
同时,举办该仪式,毕摩获得的报酬也是平日仪式报酬的数倍。[14]8
不论是“粗吉”仪式还是“粗尼木”仪式,仪式中“绘制”木板是必不可少的步骤。“木板”运用的是仪式中交感原则,用仪式祭牲的鲜血在木板上绘制“粗”的形象,目的是将“粗”附于木板之上,最后将木板埋进洞中,以起隔离疾病作用。在彝族的观念中,“粗”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既有动植物形的“粗”,也有人形“粗”。动植物形的“粗”是由天上降至人间的“粗癞”变化而成,人形“粗”则是由麻风病患者死后灵魂所变,而仪式木板上绘制的“粗”主要是人形“粗”,笔者在凉山做田野调查期间,一位名叫的惹阿拯的著名毕摩告诉笔者:
“我们在做粗吉或粗尼木的时候是一定要把麻风病画在板上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粗——九头‘粗卜’、七辫‘粗嫫’、断脚‘粗惹’、断臂‘粗么’。他们是一家人,‘粗卜’是爸爸,‘粗嫫’是妈妈,粗惹是儿子,粗么是女儿。麻风病人就和他们一样,是没手没脚的,他们是得病的主要原因,是以前麻风病患变的。”
简言之,在凉山彝族观念的中,“粗”家族有两个特性:
一个是“粗”的家庭中有“男”有“女”,以家庭为基础单位。
另一个是病症特点在“粗”的形象中有所体现,特别是肢体残缺的特点。
由此可见在历史上,彝族对于麻风病的认识是建立在其文化观念上的,“治疗”麻风病的方式也是建立在其文化观念之上的。虽然利用仪式进行治疗的实际效果是有限的,但它为处于困境、危机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超自然的避难所,使其在精神上得以安慰。
同时,在医疗技术有限的历史情况下,仪式的预防功能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麻风病“遗传性”生产机制:崇祖习俗与家支制度
不难发现,历史上彝族文化中的疾病观念并没有从其原生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内容中分化出来,疾病是彝族先民所遭遇的灾难中的一种,或与神灵、鬼怪相关,或与社会关系、道德相连。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利用文化观念解释疾病可以满足人们认知的需求。调研发现,凉山彝族常常通过文化来解释顺利与危急、疾病与康健、繁荣与衰弱、成功与失败、死亡与出生、现在与未来等各种矛盾与不确定性。“人们利用它来抵御困扰人类的那种强烈的、潜在的、势不可挡的焦虑,以便使其增长自身的承受能力,避免被焦虑、混乱所摧毁。”[13]56对于麻风病这类有着明显的身体表征和传染性的个体性疾病。彝族先民对其的解释更是不得不从文化出发。然而,这种文化观念的形成不是其本身衍化的结果,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在天上,而是在人间……”[15]
因此,要理解彝族对麻风病独特的认知以及彝族对其恐惧的真正原因,不仅要关注其信仰观念还得考虑其传统的社会制度。
灵魂观念是彝族信仰的基础,其崇祖习俗也是由此衍变而来的。在彝族的观念中,人死后灵魂犹存,形灭而灵魂不灭,灵魂之形虽与生前相同,但亡者灵魂的属性却有所不同。在彝族看来,无论是何种死亡方式(自然死亡、凶杀或特殊疾病致死),其灵魂都有可能变为善灵庇佑后代,也有可能变为恶灵作祟于亲属。决定其属性的条件多种多样,如生前的道德品行、死亡形式、死期之凶吉、后代是否献祭等。就死亡性质而言,正常死亡(自然死亡、或常见老年疾病致死)是变成善灵的条件之一;而非正常死亡却被认为是转变成恶灵最为的重要条件。在彝族生活中,非正常死亡主要包括凶死(凶杀、含毒自杀、坠崖、溺水、离奇死亡等)、麻风病致死与“猴瘟”致死。非正常死亡者需要举办特殊的送灵仪式,才能转变其亡灵属性以防其作祟于子孙。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何在彝族的观念中,麻风病患死后的形象中有“断手”或“断脚”的,以及必须为其举办“粗尼木”仪式的原因。
同时,祖灵的权能具有我向性和有限性的特点[11]48,这与彝区传统的社会制度息息相关。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以看出随着一夫一妻制的巩固和发展以及私有制的形成,个体家庭渐渐从家族公社中分化而出。但在彝区社会的历史发展中,个体家庭从未脱离家族或者家支血缘群体的脐带而成为独立的社会单位。[11]23在自然资源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彝族先民获取物资的数量极为有限,一旦遭遇天灾人祸,以个人或单个家庭的能力是很难抵御自然或社会风险的,此时基于血缘的家支群体固然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为了保存和延续这种集体力量,“保持家支利益至上”成了彝族先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生存法则。[16]44另外,凉山彝族实行家支家族外婚制,这种制度使得家支家族相互联姻,社会实力因其扩大。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在家支内部,基于血缘的家支关系清晰明朗,每个人对自身在团体中的位置有明确认知,并以自身为中心外推亲疏关系作为交往原则的基础。同时,家支团体之间的相互交往通过通婚和打冤家等形式体现出来,共同构建了凉山彝族地区多元共生的团体权力格局和社会政治生态”。[17]203-208凉山彝族的亲属关系正是建立在血缘家支与姻亲关系之上的,而祖灵信仰习俗也恰恰是彝族社会发展史实在文化中的投射。祖灵虽是亡者之灵,但始终与其亲属发生着各种联系。祖灵权能的我向性特点,使得“祖灵只保佑其亲属也只作祟于其亲属”是祖灵与生者之间的“交往”准则。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彝族为何不与“麻风病患”的家庭或家支联姻的原因。在彝区,男女双方结婚时,除了举办宴席、接受祝福外,还要举行“入赘仪式”。仪式在男方家举行,目的是为了告知其祖先,家中迎娶了新娘,愿祖先接纳此人。自此以后,新娘的灵魂便属夫家,夫妻双方家支的祖灵权能的有限性也随之扩大。可以设想,若双方家支中,任意一方有患麻风病致死之人,那么姻亲关系的建立也意味着“麻风病”危机的到来——姻亲双方亲属可能会被“癞魔”祖灵侵扰致病或子孙“被遗传”致病。然而,个体患得麻风病不仅意味着该社会成员降低或丧失了生产和生活的能力,其传染性还威胁着每个社会个体的生命健康,在往来密切的家支社会中传染几率大大加强,可能导致一人病数人病,甚至群体病的现象,这对于生产力低下的社会无疑是极大的打击。基于此,家支内部通过“夸大传染性”以隔离个体病患者。社会通过设立“遗传性”切断患者亲属的一切社会关系,拒绝与其通婚,更不会与其子孙通婚。为了使家支内部没患病者能够继续生存、繁衍,人们又采取将病患“开除家支”的手段,通过举办大型“除籍”仪式切断与患者的一切关系来恢复家支中其他亲属的社会关系,从而确保群体利益的最小损失。
在凉山彝区,与艾滋病等输入式传染性疾病不同,麻风病对彝族社会而言,其文化资源内部有着应对此病的机制和传统。由于古人的医疗水平有限,对麻风病的一无所知,人们并不理解为何有人会因之致残、任何药物都无法治疗。面对疾病的巨大恐惧,彝族先民选择寻求文化的力量,用其特有的逻辑解释这一现象,并通过家支制度与崇祖习俗的融合,在社会结构中为“麻风病”患设定了“可遗传”的亡魂属性,从而阐释了社会制度中“隔离”或“开除”麻风病患的合理性。一旦此类患者被“开除家支”,家支中的其余成员依旧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以常人的身份进行社会互动。由此,很好的解决了麻风病患给社会群体带来的隐性集体性危机。
四、结语
医疗与疾病并非单纯生物性的问题,除了其导致的重要社会影响外,疾病的文化意义是不容忽视的。[18]此外,疾病虽是一种个人化的生存体验,但在这种身体体验中却能映射出患者所处时代和社会结构的特征,特别是作为客观存在或文化概念的“疾病”,患者的日常生活实践是嵌合在多重层面的结构性社会文化因素当中的[17]202-205。在这方面,麻风病便是个很好的例子。在凉山彝族社会中,麻风病既是生理过程、文化意义和社会关系相互衔接之网中的事件,也是生理感觉与文化认知相互作用的结果。
第一,在医疗技术有限的历史条件下,彝族先辈将疾病与文化观念相结合,创造出了一套关于麻风病的解释体系,将麻风病对族群人口和生产力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以及疾病的“无法治疗”巧妙的融入神话中并代代相传,从而造成了彝族对此病的“先天性”恐惧与排斥。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认为的,人格特点与特定的行为类型是后天形成的,并非天生的、自然的,而是由文化决定的。[19]此外,对于超越人类存在的神圣对象和神圣领域的构建是彝族信仰文化的基本特点,也其疾病观念的基本特征。他们将人和自然环境、个人和群体神秘地结合起来。“当人们把疾病同具有神秘力量的存在物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些神秘对象就会转变成宗教崇拜对象,从而成为疾病实现自身恶化或转变的根源。”。[13]:2正如祖先和自然是彝族信仰的具体对象,他们也是造成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象征物。就麻风而言,自然型病因与社会型病因以及相应的病症解释就是自然崇拜与祖灵崇拜的具体表现。
第二,在面临麻风病带来的集体恐慌与传染,围绕着病因观展开的各种预防和实践体系应运而生。就个体患者而言,隔离是防治传染病的最基本、最有效的措施。[20]彝族传世经典《劝善经》载:“人得麻风病,会相互传染;要好好避讳……百姓亲戚有患此病者,如怜悯之,在不远处盖好麻风房,送好口粮,好好抚养。莫睡他的睡处,莫坐他的坐处……要注意忌避。”[21]。就仪式而言,前文所涉及的“粗吉”与“粗尼木”主要有两个功能,即治疗功能与预防功能。虽利用原生文化“治疗”麻风病的效果实际上是有限的[22],但“预防”效果却是明显的。群体性的预防仪式不仅可以增强族群对麻风病的防御意识,同时还能缓解群体焦虑。而对于个体性的治疗仪式而言,虽然患者病情会因此公之于众,极大可能成为“社会隔离”的对象,但仪式本身可为患者提供“一种力量与信心之威”,帮助他克服不得不面对的疾病痛苦[23]。
第三,麻风病对彝族先民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带来的影响既是解构性又是重构性的。新中国成前,彝族传统社会中人们的往来密切大大提高了麻风病的传染率,导致社会人口和生产力的严重破坏,社会恐慌因此而生。由于麻风病外部表征明显,又属个体性疾病,为了最大限度维护社会群体的利益,对患者和家庭甚至家支进行他者化区分和排斥的行为通过拒绝与患者及其亲属开亲的社会的形式进行着。当“家支现行权力不足以达到威慑效果的时候,需要神灵权威来作补充”[16]45。于是,当地制度与原生文化的结合,创生了“麻风病”的“可遗传性”,从而加固了“隔离”或“开除家支”的合理性。一旦患者被“开除家支”,家支中的其余成员便能重新得到社会认可,而“粗尼木”净化死者仪式的举行使得重构后的社会信任与关系再次巩固。换言之,麻风病的“遗传性”构建实则很好的解决了个体麻风病患给群体带来的信任与结构危机。
第四,每一种医疗文化的认知方式都有其历史语境,在新的认识方式产生后,原有的认知并不会立马消失。“医疗文化的历史并非仅仅是一种新的知识简单地替代传统知识的形式,随着时间的变化,他们之间还会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或相互竞争。”[13]237在凉山彝区也不例外,随着生物医学的发展,麻风病虽然已变成可防可治的普通疾病,但仍有部分彝族群众认为麻风病是“不可治的”、“可遗传的”。要想使现代生物医疗病因观在彝族地区全面接受,也许“化生为熟”是一条不错的路径[24]。
注释:
①除籍:指开除家支,与家支及亲属断绝一切关系。
②尼木撮毕:凉山彝族传统的大型祭祖送灵仪式,目的是使祖先之魂净化并将其送至“祖地”(类似于“天堂”)以享永福。该仪式规模宏大,程序复杂且气氛隆重,在彝族的传统观念中,它不仅关乎已逝先辈灵魂的最终归宿,同时还影响着子孙后代的繁衍发展。按举办仪式的时间长短分类,可分为大型(九天九夜)、中型(七天七夜)、小型(三天三夜)。选择何种规模的祭祀,主祭方可据其亡灵的情况与主人家经济条件而定。不论是何种规模的“尼木撮毕”,其基础的仪式过程是必不可缺的,包括咒鬼仪式、宴灵献牲仪式、祈福送灵仪式、遣返赎魂仪式。
③毕摩:从古至今都被彝族人民认为是“智者”,“知识渊博的人”。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社会现状下的彝族毕摩是专门从事宗教活动,处理人们信仰事务的神职人员。
④苏尼:彝族民间传统的巫师,人数甚少且社会地位不及毕摩,其主要职能为“治病”。
⑤《撮诺祭》是一套专针对“麻风病”进行祭祀活动,以求取物让病的经文祭祀古经。据传,该书为古代彝族毕摩伙毕史祖所在撰,在距今41代以前的阿堵尔普时已成册流传。后来,该书由吉克氏中吉补亚氏族的毕格尔布家所珍藏,目前在凉山已成孤本,知者甚少,用者更稀。
⑥《羊胛骨卜经》:彝语称“约皮吉”,执卜者在用绵羊胛骨举行占卜活动时念诵的经词。
⑦二十八星宿日(皆为音译):日霍、日纽、日克、日居、日黑、日姆、沙巴、北布、洛嘎、色卜、色莫、铁、姆以、勒克、塔姆、塔呗、霍居、吉额、吉洛、吉居、吉姆、瓦诺、瓦黑、瓦斯堵、瓦斯玛、尼石、者主、迪北。
⑧祖界:彝族观念中灵魂的终极归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