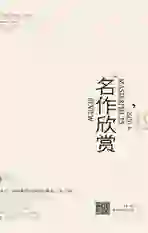流浪者的精神原乡
2020-11-19冯祉艾
摘要:蒋韵擅长书写在游离环境下的孤独个体,描写关于他们的出走与找寻,在诗性的语言之下,深入人物内心,探求其内心真实的自我选择,并将其外化于出走这一动作,讲述了个人在形成自我价值体系后与群体的反叛与对抗,以此展现凋零的悲剧之美。
关键词:蒋韵;母性;出走;精神家园;建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蒋韵自己就是一个中国文坛的流浪者。几十年的小说创作中,她是一个在不知不觉间被中国文坛“偏外”了的作家,虽然如此,在国内不断将作家群体化分类、作品也依照背景和风格依次命名成不同的时代潮流的当下,我认为蒋韵依然是其中个人风格最为鲜明的作家之一。而无论是在她个人的创作还是自我精神的建构中,女性主义都是其最为具象的风格。蒋韵毫不讳言她对苏珊·桑塔格的热爱。同为女性作家,蒋韵和她心仪的作家是如此的不同。作为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作家、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思想犀利、强悍,她不断发出的批评之声被广泛瞩目。而蒋韵却纤弱、敏感,充满紧张感,她在城市中走动的时候,她的身影是快速而飘动的,如她在《传说中》写过的那些远古的亡魂。
因此,对她笔下的男性角色,大多是以女性视角进行叙述。甚至有一部分成了流浪者,在普世中无法找寻个人价值,只能依附于女性角色而存在。女性在蒋韵的小说里,常常扮演着这样一种拯救者和信仰载体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天然带有了母性特征,也蕴含着人性的复杂和爱的无私伟大。本文就将以蒋韵小说集《完美的旅行》中《朗霞的西街》和《完美的旅行》这两篇为例,分析流浪者如何在女性的善良和纯净中找寻精神原乡,借此探讨蒋韵小说中母性形象的建构和异化。
男性流浪者的精神困境
在小说《朗霞的西街》中,有两个不同的流浪者形象。
第一个是陈宝印。在国军溃败之后,陈宝印原本可以踏上前往台湾的船只,但是对于他而言,唯有谷城,才是他的归途。陈宝印的流浪是天然地带有浪漫和神秘色彩的,他的流浪是自我价值观平衡之后的选择。换言之,他是为了心中存留的爱和家庭的圆满才放弃船票而跋涉万里的。但就结局而言,他究其一生追寻的精神家园更像是梦幻般的破碎影像,他只能在地窖中,借助偶尔投射下来的一抹阳光和隔着厚重土地的来自女儿的笑声追寻纯净的乐园。
陈宝印这一流浪者的形象带有传统中国男人的家国观念,然而这样的家国观念却是他精神困境的来源。陈宝印是一个典型的悲剧性人物,如果用一个词形容这个流浪者,应当是压抑。
地窖是压抑的,封闭的环境和长达十几年的自我囚禁将这个原本“还算排场”、粗通文墨的军官硬生生磨成了恐怖的“白毛鬼”。
压抑感是如影随形的,马兰花从始至终的克制和寡言,“守墓人”这一荒诞又精准的定义,无一不暗示着陈宝印如同困兽一般的压抑。
而有趣的是,我们能窥见的压抑感大多是从女性角色中呈现的,在对陈宝印的叙述中,作者似乎带着些梦幻的理想主义色彩。他永远温和平静,甚至反过头来安慰马兰花:“这比战壕里强一百倍呢。”从中可以窥见作者对于流浪者精神原乡这一意象的调度和刻画。
《朗霞的西街》中另一个流浪者,是谷城中学的美术老师周香涛。这个角色在故事中着墨不多,几乎是影子式的存在,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工具人物,作者试图用他来表现吴锦梅的天真和炽烈,表达对人性欲望的反思。
和陈宝印自己选择的流浪不同,周香涛的流浪是被迫的、沮丧的。如果说陈宝印的流浪是精神选择下的自我放逐,那么周香涛的流浪则是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体冲突。
和许多怀才不遇的文人一样,周香涛身上有着愤世嫉俗的孤独和失意。从大城市“分配”到小地方的挫败感,造就了他精神世界的沉重和孤寂。文人第一次意识到书本和知识的无用,精神的自由和宽广只能让他对现实中生活空间的狭小和俗气感到愈发逼仄。
年轻天真的文人面对这种落差,是无法再从書本中找寻精神归宿的,他迫切需要着精神家园的重构,而众所周知,重构的前提即是打破。他在文中出现的次数很少,我认为作者是有意对他的形象进行模糊化处理,并希望以此指代一整个群体,以唤起独属于那个年代和地点的精神共鸣。
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类似于周香涛这样的群体是非常多的。年轻人或由于时代所需要,或由于“建设农村”这样的鼓动,不少人在历史的转折点中也经历了属于他们个人发展历程的蜕变。当我们回看这一代人,他们内心的流离感和失措感是难以弥补的,与其说这是历史的阵痛,不如说是个体在群体导向下的狂欢落幕。他们的精神世界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而蒋韵就在这部作品中对这一代流浪者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周香涛和陈宝印恰恰相反,陈宝印是在国家的流放中颠沛,却完成了自我精神家园的建构;但周香涛则是在群体浪潮中被大浪裹挟,却丢失了精神原乡,必须依靠外界的相互取暖重新寻找生命的温度。
如果说《朗霞的西街》或多或少带着些时代反思,那么《完美的旅行》则不折不扣地描述着男孩成为男人历程上的阵痛。这样的阵痛无关政治文化,只关乎成长。
在小说最开始,作者对刘钢下的定义就很有意思:“刘钢是一对外省夫妇的孩子。”这句话拆解过后能够得到很多种解释。刘钢的父母在高原的城市中落脚,他们原本也属于城市的外来客。但成年人的适应总是超过孩子太多,不多久,他们就已然不习惯刘钢身上的气味——那是一种新鲜的羊奶养成的膻气和青草的香味儿。
奇怪的地方是,作为异乡人在这座城市定居的父母,并没能从儿子身上获得对家乡的怀念,正相反,母亲甚至对这气味感到不安和心烦。
“强烈的陌生感”,这是母亲对于这个亲生儿子的形容。毫无疑问,年纪尚小的刘钢是一个可怜的流浪者形象。如果说陈宝印的精神家园是“此心安处是吾乡”,周香涛的精神家园是自由的广博和驰骋。那么对于年幼的刘钢而言,他的精神原乡更像一个深沉的意象。
东京城,那个属于长白山地的小小林区,随着刘钢在城市中生活的愈发苦闷,它就愈发带上了回忆滤镜的暖光。
但作为流浪者,他是无法靠自己重建这个地方的,更何况他的流浪并不仅仅来自异乡的隔绝感,更来自自己母亲的愤怒。一个不被母亲接受的孩子是悲惨的,然而这种陌生感完全无法弥补。
“她从这个有异味儿的孩子身上找不到一点骨肉的感觉,亲人的感觉。她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去对待这个陌生的闯入者。她只有频频地往澡堂里轰他。”
兄弟们故作的快乐也在时时刻刻提醒着刘钢,于异乡的家庭而言,他是一个不规矩的闯入者,于远在天边的东京城而言,他是一个可怜的流浪者。他仿佛与世界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能够模糊地探听到他们的快乐,却无法感知,也被毛玻璃那头的人所屏蔽和隔绝。
女性作为信仰载体的必然性
蒋韵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在她的作品中,女性气息是非常强烈的。作者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有着尊重和矜贵感,这样笔触下所描绘的两性故事,女性角色几乎是天然地就带有了母性的光辉,必然地承担了作为信仰载体的功能。
《朗霞的西街》中,马兰花的母性形象是显而易见的。在对马兰花前情简单的交代过后,大半的篇幅中,马兰花都是作为朗霞的母亲这一形象出现的。就母亲身份而言,马兰花是非常合格的。她给女儿朗霞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在生活中,也尽己所能地保护着朗霞。“人人都说,朗霞养得很娇。”就是最好的佐证。
当然,她的母性光辉绝不仅仅是在于对自己的孩子。恰如中国古代朴素的哲学理论中强调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马兰花的良善和温和覆盖了西街上的另一户人家,也就是吴锦梅和引娣姊妹二人。当然,她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
对于引娣,更像是对待一个天真的孩子,和朗霞一样。年幼的老幺需要被照料,而原生家庭的困苦又深重地打击着她。引娣和朗霞差不多大,因此,马兰花像包容自己的孩子一样包容着引娣。而对吴家的长女吴锦梅,她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少女已长成一朵清丽的花,有着对家庭默然的愁怨和羞怯的失意感。她的女性特质较引娣更为明显。因此,马兰花对吴锦梅,是一种近乎疼惜的温和。
她改了自己的衣裳给吴锦梅穿,心如明镜似地包容着她不可见人的秘密,收留吴锦梅软弱甚至是不堪的一面。在马兰花身上,真正诠释了中国传统女性如水的特质——云淡风轻,却又铿锵有力。
她的力量感就体现在她对陈宝印长达十几年的藏匿中。“这个女人,这个马兰花,真厉害呀!平日里,出来进去,看上去那么绵善,那么清秀,弱不禁风,却谁知,心里藏了这么大的事,一藏,藏了这么些年!她竟然藏着这样的秘密,和整个时代,也和整个谷城,挑衅。”
她身上馨香的、热烘烘的气息,是陈宝印归来的全部动力,对于陈宝印而言,马兰花身上承载的远不仅是一个妻子的身份,更是白昼似的光明、清甜的稻谷香气和世间极乐的缠绵。
马兰花身上代表的是几千年中国女性最为朴素又旺盛的生命力,她们的存在让人相信,只要拥有了她们,精神原乡就能被找寻和安放。
吴锦梅则是另一种母性形象的光辉投射。马兰花的形象是大地般广博而伟大的,而吴锦梅代表着世间极致缥缈的美丽和虚无。
吴锦梅的出场就是美丽的。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吴锦梅的美丽就是羞怯而脆弱的。比起对两人爱情历程的描述,作者用了更多的笔墨来描绘吴锦梅的美丽。
四季中变幻的树木和庄稼,黄昏中少女柔软的天蓝色的腰际,如同丁香花般哀婉又凄清的美丽。
因此,周香涛与吴锦梅的爱最初就是一场懵懂的自我追溯。周香涛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美术老师,对于美学有着天然且具象的认知。在这个逼仄平庸的小城里,吴锦梅毫无疑问地代表着美,当读者被带入这种美学架构之后,却能够发现,周香涛这个流浪者对美的姿态是高高在上的。
这一点从他给画取的名字中就能看出——刑场边的花朵。是一种带有血腥气和对立性的美丽,相较于马兰花身上朴素的母性气质,吴锦梅在周香涛的生命里是一个需要被摧毁的美丽形象。
这令人想到西方神话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弑父恋母,这种对美的找寻天然地带有侵略性,而作为平庸生活中的美学力量所存在的吴锦梅,也就成了周香涛逃离俗世的精神原乡。
《朗霞的西街》中的母性都是作为象征意义存在的,其反映的更多是男性力量下对于女性的架构和解读。而在《完美的旅行》中,陈忆珠几乎是完完全全按照一个完美母亲的形象来构建的。
刘钢作为流浪者在生身母亲那里无法得到认同和接受,转而在迷途中寻找下一株鲜活的植物,他找到了,就是陈忆珠。
陈忆珠无疑是所有青春期男生心中的完美母亲,或者更直白一些,完美情人。她乐观温和,亲切明亮,宁静有趣。她擅长消解一切糟糕情绪,转而将天真外化成为对抗世界的表达。在《完美的旅行》中,几乎处处可见陈忆珠与刘钢生身母亲李淑的对比。
“他和这个女人相遇了。就像——灰姑娘遇到了仙女。”众所周知,在灰姑娘的童话里,仙女是作為教母出现的。在遇到陈忆珠之前,刘钢的身体和心灵都属于流浪状态,他是被自己母亲亲自放逐的可悲者,是不小心闯入钢铁森林的外来者。但在陈忆珠这里,他得到了共鸣,与光明和拯救相遇。
小说在前半部分用了大量梦幻的笔触描绘着两人浪漫的相处。公路两旁的风光、柔软妩媚的泉水以及那个在梦中的东京城。
打破这一梦幻景象的是冷冰冰的生身母亲,这不能不让人叹息,当流浪者刘钢无法在陌生隔绝的母亲身上找寻到归属感时,对精神原乡的渴盼使他不得已扑向了另一个女性的怀抱。
当然,这怀抱最后的破碎是惨烈的,以死亡告终,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永恒呢?
陈忆珠死的绝美,她留下一封仍然温和亲切的信,带着明亮的爱意上路,和世间庸俗丑陋的一切告别。相信陈忆珠的死亡给刘钢的打击是巨大的,但这也帮助刘钢完成了精神原乡的最后归属。刘钢终究会寻找到那个带着青草香气的故土,而这一次,他的精神原乡被安放在陈忆珠的母性形象上。
作者对于母性形象的建构
也许是出于对女性身份的尊崇和热爱,在蒋韵的笔下,女性角色大多是美的。即使是因自己的利益告发马兰花的吴锦梅,作者也近乎同情地替她编织了一套自我开解的理由,并用细腻温和的笔触表现着她脆弱的美丽。
而间接毁掉儿子精神寄托的李淑,刚一出场时,作者不惜用大量笔墨为她辩解,读到最后,并不会觉得李淑是个十恶不赦的人;相反,我们能感受到,在时代更替间,母亲这一角色转变的困境和挣扎。
在流浪者被放逐的历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受着来自外部世界的攻击和打压,也在面对着自我精神原乡崩溃的困境。蒋韵笔下的男性流浪者,有的对精神原乡矢志不渝,历尽千辛万苦也要寻找家园,有的则在懵懂中不断地重塑自我,进行自我认知和对精神原乡的建构。但无论是哪一种,他们都需要一个母性角色对他们进行引导和帮助,从而追寻到迷失的精神原乡。
这也就是蒋韵对女性角色的观照。她们往往乐观、坚强、明亮、美丽。有着在任何时刻都不放弃挣扎的斗志,也有着打破一切视死如归的勇敢,她们的形象往往比男性角色更为高大,并且在两性关系中扮演着保护和引导的一方。
蒋韵用她独有的温情脉脉和梦幻的笔触建构了一个属于女性的诗意世界。和现下的女权主义所不同的是,在她的笔下,女性并非是仅仅强调权力和斗争的冷硬角色,而是能以温柔和爱打败一切的主导力量。这,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史诗。
作者:冯祉艾,青年批论家。作品散见于《西湖》《湖南文学》《文艺评论》《名作欣赏》《山西文学》《文艺报》等报刊。现供职于湖南省文联《湘江文艺》杂志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