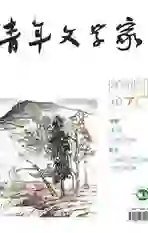广西侗族作家创作审美文化的生态研究
2020-11-18覃健
摘 要:侗族作家张泽忠小说集《蜂巢界》描绘了二十世纪中国南疆侗乡,描画了一个神奇瑰丽的聚居地,构建了独特侗族审美文化。本文以此为切入口,尝试结合生态美学理论分析了侗家人的生态空间叙事,后现代焦虑和侗族作家审美文化之核。本文认为张的边缘创作和地方性书写蕴涵有了一种生态美学观念,其意义也在参与多元文化对话中得到凸显。
关键词:《蜂巢界》;审美文化;生态美学
作者简介:覃健(1981-),男,博士,广西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多元文化与多元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0-0-04
引言:
在提倡多元文化的当代世界里,侗族——这个偏居于湘、黔、桂三省比邻地带,怀抱山水的族群也为外界所知。特别随着多元文化的意识自觉,侗族文化也进入到公众视野。广西侗族作家创作审美文化的生态研究是一个宏大的题目,限于学识本文不能就事论事。[1]而选择一位深具代表性的侗族作家来切入此话题的讨论或许不失为较好的尝试。
侗族学者作家张泽忠与小说集《蜂巢界》进入了研读的视野。张泽忠,侗家的儿子,在三江这块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的侗族作家与学者。与当下广西文坛上作家相比,他似乎“抱残守缺”,他是紧紧“抱”着侗族乡土。
而同时他的小说却显现出惊人的“文化自觉”。正如他在《蜂巢界》里“友人致作者信及作者复友人信(代自序)”中谈到“侗族是一个善良柔弱的民族……这样一个先祖用肉团做成的唯有善良的民族……它与环境相处那么的和谐,对生命存在的理解那么的独特。”[2]在他的创作里,他是主动承担起侗族审美文化写作者的身份的,记录侗族文化故乡人事变迁,描绘那方水土中孕育的灵魂祈求。
以下,本文进入到张泽忠小说集《蜂巢界》所描述表现的审美文化之中,尝试结合生态美学的理论做一些分析研究。
一、侗家人的生态空间叙事
首先,在《蜂巢界》里吸引大家注意的是,关于侗乡特有的风物风情的叙说。谁说南疆之地是穷山恶水,在作家神奇的笔端,我们分明感觉到这是乐土。
鼓楼,是侗族最有特色的建筑之一,它位于侗寨的中心,其位置正是“诸山来朝,势若星拱。”鳞次栉比的吊角楼簇拥其周围,正如百鸟朝凤。而鼓楼作为侗家人的精神与理想,凝聚着侗家人的精神。鼓楼里供奉的是侗乡团寨先祖母萨神娘娘。侗家人说,团寨也像细脖子阳人,有头有手也有脚,鼓楼坐落地方就是细脖子阳人的肚脐窝。且看《蜂巢界》是这样描绘的:
古榕寨位于都柳江的下游。一座酷似千年巨杉的鼓楼,坐落在山寨中间;鳞次栉比,参差错落的吊角楼,好象密密匝匝的星颗,簇拥在鼓楼的四周。这是个远近闻名的大寨子,有九百多户人家,大概为了铺排日子,不管晴天雨天,九百多户人家数千口人丁像蜂而觅食四的整天纷纷攘攘,进进出出。凡到过古榕寨的远方客都说,隔着老远,就能听见九百古榕寨闹腾腾地酷似深山野地里的大蜂巢。[3]
九百里古榕寨在盗匪侵犯,风雨飘摇之时,侗家人聚集到鼓楼里。巴隆格老带领侗家人唱耶歌,跳耶舞,请萨神娘娘,唤起侗家人团结一致的精神对抗苦难。侗族在历史上是没有“国王”的族群,侗家人过着一种“有款无官”的生活。[4]而鼓楼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它的精神凝聚力与向心力,它就是“蜂巢里的蜂皇”。
走进侗乡,那里山青水秀,流水潺潺。有水必有桥,几乎每道河流上都有一两道飞虹横跃水面。在侗乡,“桥”是最难忘的。而在张泽忠的笔下,即使是故乡里一道不起眼的小木桥都蕴涵着侗家人的生命情怀与脉脉温情。《我们寨的小木桥》里追叙了童年时与小木桥朝夕相对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小木桥是寨子里的乡亲们一起建起来的。从选木,伐木,抬木,喊号子,唱号歌,抬水,筛木,建桥,寨里每个人都出了好大的力气。于是桥修好的那天,全寨子男女老少都到桥上饱饱坐了一整天。坐桥,白天听故事,看水牛打架。夏秋之夕,看银河,数星星。
在作家笔下,小木桥内蕴极为丰富。
首先,桥是生命的桥。侗寨祭桥的习俗。侗族认为阳世间人人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生命桥。这桥是灵魂投胎时候由阳间到阴间的必经之路,死后又由这桥回到阴间。桥最古朴的民俗含义,在于让阴间的灵魂转世投胎,以及让人的灵魂在阳世间得到安宁。[5]“桥”是与侗人的生命血肉相连的。从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更深层次地阐释“细脖子阳人坐桥”的内在生命情感意义。文中说“我”求学山外,乡亲们在木桥上送行与祈福。山外归来,乡亲们木桥守候。知道“我”读书有成,三毛公把我抱起来放在小木桥的最高一层。坐桥在此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命仪式。
再者,桥是“交往”之桥。桥是全寨的乡亲的心血,是“千秋桥”。坐桥时候都要讲究“规矩”,孩子坐下面一层,大人坐靠外一层。而平日小伙子坐桥时候的姿势,说话的声音,长辈都要管。客人过桥要主动帮助,打招呼。这里包含这质朴的伦理价值——人与人之间交往必须要懂得互相尊重和关怀。
最重要的是,从哲学意义而言——桥是“存在”之桥。从以上论述可知,橋在侗家人心理是内化了的生命情感之桥。“桥”已经不是一个纯然的外在于生命情感意义之外的科学思维下的“物”。侗家人的桥“与生俱来”的具有了超越现实生活实用价值的品质,而物化为赐人幸福,吉祥的神圣的“灵体”。要对此阐释加以深化,不妨借用二十世纪哲人海德格尔的入思之路与生态美学思想进行分析。[6]海氏后期的思想表述了“天,地,神,人”的“世界游戏”这一命题。他提出,“物”的意义存在于它能在“物化”之际聚集“天,地,神,人”之“四方”。[7]在张泽忠先生的笔下,桥正如神圣之灵体聚集了“天,地,神,人”之“四方”。小木桥筑建大地之上,河流滋润大地,细脖子阳人在桥上,看日月运行,群星闪耀,与四时季节同在,感受昼之光明和阴晦,夜之暗沉和启明。
二、侗家人的后现代焦虑
在作家深情的细语呢喃中,侗家人在大山的褶皱岁月的悠悠里固守着宁静的家园。而同时《蜂巢界》也写出了作者对侗家人现实处境的焦虑。
偏居西南一隅的侗族并未在现代历史之外,那“化外”之地的融融和和,生机盎然的景象也发生了变化。在《树爷爷》中那棵替行人遮风挡雨乐善好施的香樟古树,那棵全寨人亲热地喊“树爷爷”保佑一方水土一方村寨平安的香樟古木,那棵与奶奶终身相依不离不弃的香樟古树,在“高山造平原”喊声中轰然倒下,只留下了一块“癞头疤”。“奶奶”也阖然而逝。面对着这一切 ,诗人借笔下人物之口来表达——“遭遇劫难后,山与水形容枯槁,天旱地龟水枯竭,天雨洪涝如猛兽;而山寨鼓楼,前人木建筑的智慧结晶,于今却常年失修,斑驳陆离,模样寒傪”(《蜂巢界·婄婵》)。侗家小姑娘用心灵的画笔描绘了家乡,鼓楼旁边月色漫漫笙歌阵阵,山青青水盈盈竖笛禀冽。而她父亲杨力却惟恐现实的丑陋侵坏了孩子“心灵的净土”。而现实中家园净土何处寻呢?
随着传统地域文化或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时代衰落,而人文意义的家园所倚凭的切身环境——家乡也频于消失。在张泽忠诗意的笔端,我们倾听到他的轻叹。“山林是主,人是客”这是侗家人的质朴的生命观,而家园的园与故乡之乡就是旅居大地之人所栖居的自然。侗家人家园与故乡观念所直接关联的是蓝天,大地,流水,青山,古木,吊腳楼,鼓楼,风雨桥。这种关联并非偶然的,而是历史的进入了侗家人的情感生命里,自然(涵盖了侗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也成为人文意义的家园血肉相连的一部分。上世纪后二十年市场化的经济浪潮下,侗乡经历了不可避免的变迁。为了经济利益,人们无视传统,开山伐木办工厂,导致生态的恶化和风俗的淡化。作家不仅意识到自然生态恶化带来对人类物质生存环境的恶果,他更敏锐而清醒洞悉——生态危机从更深层次上毁坏了作为人文家园与故乡精神的自然依托。当昔日那青山绿水,鼓楼花桥的侗乡变成了缺失雀鸟啼鸣的死一般寂静的穷山恶水时,毁坏的不仅是自然环境的故里,也是作为精神象征的家园。这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无家可归的焦虑感。作家是在执着探询人类存在的精神根基——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精神家园何在。
于是,我们听见《望融洲》里老阿公的呼嚎声。融州大火烧掉老人的家,老阿公背井离乡,从融州“流落”到宜阳,住在儿子工作的武装部招待所的大间里。阿公年迈,他背躬如弓,天天隔着窗望着对门坡,如孤身一人站在荒野上,无助而无奈。大火如噩梦萦绕在他的脑海深处,他至死不忘回融州。
但是阿公至死也回不去了,回不去的不仅是记忆里融州的老家,还有亲情伦理的家。阿公的儿子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侗家人。儿子和老父隔阂太深,以致两人已经没有了对话的空间。儿媳的霸道也让阿公感受不到“家”应有的温暖。
如果我们拿《望融州》和《蜂巢界》里其他的篇章作一番“互文性”的阐释,文章的深意不难体会。《我们寨的小木桥》里的三毛公是一个孤寡老汉却不孤独。他生活在人伦和谐的侗寨里。他发动侗胞们修桥,他教导年轻人和照看孩子,他弹唱琵琶歌与人同乐。他深受乡亲们的爱戴,侗人把老人的名字刻在“寨首”栏里。谈到此,作家的悲哀凸显出来了——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侗乡,传统的伦理亲情在淡化,老一辈人珍惜重视的价值也在失落。
《曾波老师》一文中,作家用“第一人称”满怀深情的叙说了曾波老师的往事, “我”把曾波老师与“我”相处的细节勾勒出来了。曾波老师声音嘶哑,教学认真严格,待学生视同己出,一着急“他头上,额上,鼻尖汗水淋漓”。而在结尾,“我”在尴尬场景中重遇曾波老师:
……珍藏心底里那点美好的东西不敢再损坏了,于是造访曾波老师的勇气再也提不起来了。旅店到是清静,窗外都柳江上渔歌咿呀,浆声唉乃。夜里睡时,迷糊想起,天地君亲师,师乃在世人敬重之列,况且过些日就是教师节呢。于是宽了心,拥着被子睡著去。[8]
感情在文章结尾渐渐克制,叙述者欲言又止。“我”深知人世之粗糙不堪,细脖子阳人在尘世的脆弱。只是内心所珍藏坚守在现实中破损的无奈之情同样也流露于文字间。在“窗外都柳江上渔歌咿呀,浆声唉乃”中留下了问题。作家的心真能平静下来吗?而那些曾经不为现实压倒,在质朴侗乡里为真情所系“亲人们”还在吗?
《曾波老师》一文流露出来的苦涩之情,与《蜂巢界》里描述侗乡风土人情时的喜悦形成鲜明对比。比如《我们寨里的小木桥》的秋夜坐桥看天上银河与桥下小河并向而流;或是《山崖上,树蒙蒙》里描画了侗味十足的花街图。阿萨们和儿孙在花街上摇纺车,转绞纱架,折筒裙,摆酸宴,讲苦情歌,其乐融融;《“扑哧”一声山水绿》塑造了明快如山涧的培也姐姐和温厚如山的郎腊个哥,两人爱情荡漾于青山绿水间。从深层来说,这种苦涩是来自于对古朴的侗族精神失落的体验,还包含着一种超越了个人意义的担忧。这种担忧是对现代文明历史进程中侗民族品德的消失和人性的堕落,侗民族“不可知的命运”的忧患意识。
三、侗族作家审美文化之核
以上可以看到在张的作品里,自觉地流露出了对侗族文化在现代境遇下的反思。也许我们要继续追问。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同时又以侗家人身份自居的张泽忠先生,在作品里他是如何探询自我和侗族的现代价值意义的?
进入《蜂巢界》文本,张泽忠先生的笔下人人物,特别是在那些用第一人称叙说的小说,叙事者总会在柔弱地退让着。《望融州》里结尾是意味深长的,“我”重遇阿公儿子,听到了阿公过世的消息。在楼上灯火通明,人生鼎沸,骨牌声如鼓鸣中,我“扯起一床被子,把自己整个儿蒙了起来”,闭上眼就看见了阿公。在彼时彼刻“我”“无力”的,只能无言地面对这些人世的不堪。《曾波老师》的结尾,“我”也是遭遇了如许境地。在粗暴的现实面前,“我”反而安静下来。但是,如果读者体会到这两个小说结尾包含无限的深情与关怀,自然也就能理解诗人的对侗族审美文化价值的坚守。作者深知,现代文明的强大和侗家人的柔弱,也深知人事的变更在这冷漠的年代里是如此之“习以为常”。但是,他在“无声的呼喊”侗家人用质朴的“坚忍柔和”去坚守世界。
于是,诗人的笔下出现一系列侗家的女性形象,女性形象成了诗人价值意义的载体。如《扑哧一声山水绿》里善良活泼的“蓓也”,《美娘》里的纯真羞涩的丫姐,《我们家的妈妈》里的可敬可亲,坚韧不屈的妈妈。在《爱也混沌》 里,诗人用流水一样的文笔,叙述了“我”与“前妻”,“妻子”两个美丽女性的故事。妻子她为了报答女友相救之恩,默默地承擔起照顾女友遗夫遗子的义务,而后感情升华成为了我的妻子。她的沉静让我一直觉得妻子缺少些什么。特别是让我这个受现代文明冲击,内心波动不已的“知识人”觉得妻子的欠缺。终于,在妻子大山般温厚,溪水般不息的情感的感应下,“我”发现妻子的宁静之美。而这份宁静超越现代文明的喧嚣,给“我”这游子予故乡的召唤(已经有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这些诗篇,这些人物都是来自“月亮文化”,是月地里最美丽的歌谣[9])。妻子用爱意滋润“我”疲倦的灵魂。有研究者对张泽忠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研究,认为“这一系列的女性形象侗族的生命力和灵性美,是侗民族的象征,但其实是作家对起民族的审美期盼的结晶或承载……是作家审美理想的形象表达。”[10]进一步说,张用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来表达一种存在意义价值的坚守态度。
无论是月亮文化或者是“肉团式”的民族,都是一种审美文化的表述。这里包含了侗民族积淀形成的历史经验,情感方式与内在价值。这一种价值观正如朱慧珍(2005)在总结侗族审美生存特征时候所指出的,侗民族以歌唱为乐生手段,以和谐共生为审美理想,以柔性美为审美追求。[11]
四、结语
曾繁仁(2005)明确提出了“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他认为生态美学是“在后现代语境下,以崭新的生态世界观为指导,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审美为出发点,涉及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以及人与自身等多重关系,最后落脚到改善人类当下非美状态。”[12]本文尝试结合生态美学核心理念去分析了侗族作家张泽忠的创作。
《蜂巢界》里构建了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圣(超自然存在)和谐共生的乐土。作家用诗意的文字书写侗家人质朴自足的生活,悠远宁静的家园。张先生并不是个“单纯”的童话诗人,他同时也是现代文明的审视者。在他对侗族家园的叙事中,还蕴涵了他内心的无尽的忧思,哀痛,无奈——那个他深爱的历尽磨难的侗民族,还能在现代性的困境里进行“自我的救赎”吗?或者侗民族那份柔韧忍耐亲和的品质在现代社会中坚持守护下去吗?张泽忠先生的写作留下的是巨大的疑问和他那深切的关怀。
注释:
[1]“审美文化”一词是由法兰克福学派首先提出来的概念。朱立元认为,“审美文化”可以表述为具有一定审美特性和价值的文化形态。他指出,审美文化涵盖中、西乃至全世界古代文化中的有审美价值的部分,即古今中外以文学艺术为核心的一切具有审美特性与价值的文化产品或形态。参见朱立元. “审美文化”概念小议 [J].浙江学刊.1997年,第5期.
[2]张泽忠. 蜂巢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页.
[3]张泽忠. 蜂巢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9页.
[4]关于侗族的“合款”制度参见邓敏文,吴浩. 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1页.
[5]参见朱慧珍,张泽忠,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第142页.
[6]关于海德格尔思想与生态美学的联系,曾繁仁先生曾提出,生态美学最重要的理论原则是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主义,这是一种新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生态美学包含生态本真美、生态存在美、生态自然美、生态理想美与审美批判的生态维度等内涵。在西方则以海德格尔的“四方游戏说”为其典范表述,因此生态美学必将开创中西美学对话交流的新时代。参见曾繁仁.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J].文学评论,2005年07期,第48-55页.
[7]相关的思想参见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M].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年,第230-243 页.
[8]张泽忠. 蜂巢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66页.
[9]廖开顺,石佳能,侗族“月亮文化”的语言诠释,理性的曙光[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
[10]刘长荣,女性形象的民族文化表达——读张泽忠先生的小说集《蜂巢界》[J]. 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
[11]参见朱慧珍,张泽忠,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第8-39页.
[12]曾繁仁.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03期,第5页.
参考文献:
[1]张泽忠. 蜂巢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2]邓敏文,吴浩. 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朱慧珍,张泽忠.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4]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M].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
[5]廖开顺,石佳能,侗族“月亮文化”的语言诠释,理性的曙光[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6]刘长荣,女性形象的民族文化表达——读张泽忠先生的小说集《蜂巢界》[J]. 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
[7] 曾繁仁.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