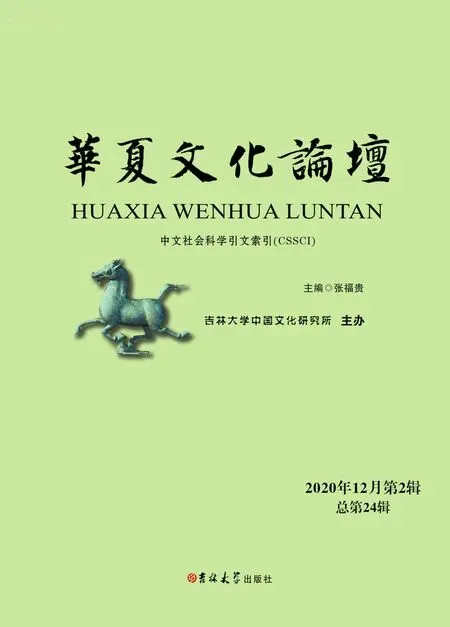作为索引的感性影像: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对作家血地根性的聚焦方式
2020-11-18
【内容提要】张同道先生的人文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深度聚焦了中国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六位作家,很好地体现了新时代、新经典与大众传播新经验的探索和尝试。通过纪实影像寻找文学的萌芽和顿挫的节点,观众可从中能够感受到作家的写作原乡为他们带来的原始力量,读者则能够从中还原小说文本中的种种独特的形象和背景,寻到在阅读中产生怀疑和揣度的历史证据。作为索引的感性影像,《文学的故乡》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了生动的、真实的、感性的存储指南,可令更为广大的观众和读者从中找到当代文学的根性与原乡。
贾平凹、阿来、迟子建、毕飞宇、刘震云和莫言——窃以为,张同道先生选择这六位作家作为采访对象,并非仅因为他们的创作代表着国内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更为深刻的缘由是他们的故乡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的故乡、精神的故乡、美学的故乡,各有着地理和人文的代表性、独特性和典型性。从零下42摄氏度的北极村到海拔4300米的四川巴郎山,从横卧中国腹地的千里秦岭到天开地阔红高粱无尽头的平川高密,从苏北悠悠水乡的乌篷船到中原老庄雨后的大水坑……在中国当代的文学地图中,张同道统观全局选取了六个有典型特征和意义的点。所以,这部人文纪录片更像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索引”,观众能够从中感受到作家的写作原乡为他们带来的原始力量,读者则能够从中还原小说文本中的种种独特的形象和背景,寻到在阅读中产生怀疑和揣度的历史证据。作为索引的感性影像,《文学的故乡》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了生动的、真实的、感性的存储指南,可令更广大的观众和读者从中找到当代文学的根性与原乡。
索引的逻辑、结构和表达的翔实程度,是极为重要的。纪录片深度聚焦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以纪实影像为载体寻找文学的萌芽和顿挫的节点,为中国当代文学存像,成为丰满的纪实的索引册。这六位作家,几乎每一位都在如今的文坛牵领着一脉或是一派的书写风潮,其间有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其后有诸多的崇拜者、追随者、模仿者。故而,作为索引,此后的当代文学研究者也能从这部纪录片中更快、更好、更准确地搜索出对应值和原生孔口。然而需要承认的是,影像始终是浅显的,真正要了解一部作品、一位作家,这部纪录片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还是需要沉下心来,去真正阅读他们的作品。所以,这部纪录片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播放的影响力,更在于它在后续“被检索”的过程中产生的巨大价值功能。
故乡是一个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宝藏和资源,作家对故乡的情感和态度也是复杂隐秘的。对于故乡,作家们离去再归来,回想着故乡的历史和自己的曾经,反观自己现在的时代和生活,故乡在无声无息中赋予了作家充分的滋养和洗涤。
一、念兹在兹:“血地”文化传统的存续与断裂
童年的经历能够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一个人的一生,尤其是对于作家这一类敏感的人来说。毕飞宇至今对人生第一个陀螺玩具念念不忘,迟子建对童年每天睡醒时姥爷早饭的鱼香和酒香记忆犹新,所以,作家童年所接触和经历的人和事,所产生的情绪,以各种形态出现在他日后所创作的文字中,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纪录片为这种“自然而然”寻到了线索,并将其衔接了起来。
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阐述了影响艺术家产生及其艺术风格和美学气质形成的三种决定性因素——种族、环境和时代。与沈从文的“湘西”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等文学叙事场域一样,“文学的故乡”象征着一方独特的风土和人情,在文学叙事空间和文化指代上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创新性,赋予了作家空前的叙述想象自由。以莫言为例,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县境属古齐国故地,是兵家文化的发祥地。兵家文化崇尚大开大合、雄奇壮丽,民间故事多涉神鬼狐怪,想象丰富大胆,这些民间文艺风气都是莫言文学成长的文化血地。片中那些舒缓、平和、真实、生活化的长镜头,对作家体验式地聚焦、回忆、再失焦,描述了人与人、人与故乡的关系,提炼出了最核心的文化元素和逻辑关系,实现了纪实性与艺术性的充分融合。在纪录片的莫言部分,戏曲多次出现,无论是民间茂腔、2017年《人民文学》的戏剧剧本《锦衣》,还是意大利歌剧《蛙》、民族歌剧《檀香刑》,都嵌入了莫言与戏曲的密切联系,为莫言诸多作品都有茂腔的影子而提供了依据。莫言从小接触茂腔,他的道德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的雏形都来自于茂腔。“茂腔是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剧种,流传的范围局限在我的故乡高密一带……公道地说,茂腔实在是不好听。但就是这一个不好听的剧种,曾经让我们高密人废寝忘食,魂绕梦牵,个中的道理,比较难以说清。”①莫言:《茂腔与戏迷》,《故事会》2012年第22期。然而,就是这个并不好听的剧种,却在莫言的几十个作品中出现过,可见,它在莫言枯燥困窘的童年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个小戏唱腔悲凉,尤其是旦角的唱腔,简直就是受压迫妇女的泣血哭诉。高密东北乡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够哼唱猫腔(茂腔),那婉转凄切的旋律,几乎可以说是通过遗传而不是通过学习让一辈辈的高密东北乡人掌握的。”②莫言:《檀香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后记”。不断地强调并借用茂腔(在文本中称为“猫腔”),也是莫言纾解乡愁的一种方式。从文艺理论的角度讲,这就是文学地理学的现实表现。地理基因是客观物质世界中的地理环境与人类文化发生碰撞的结果,也是对文学发生基础与文学生存形态的哲学思考,它们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发挥力量。“对于作家而言,地理基因是一个丰富而多变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并不是说它在作家的童年时代就已经全部完成了。作家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下出生与成长,家人、家族、社区、地域、经历和所接受到的教育等,都会对作家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所以地理基因是在综合条件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①屈伶萤、邹建军:《“地理基因”的形态、内涵及其产生根源》,《当代文坛》2020年第4期。在高密贫穷的乡野中,莫言用耳朵纪录了故乡的童年和民间的艺术,记录了茂腔的苍凉与情趣,这也为莫言善于动用听觉感官参与叙事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依据。
莫言以民间的身份描写中国北方农村的生存之艰难和生命之野性,用老百姓的视角、语言甚至是思维方式去丈量历史的宽度、深度和长度。这是对高密民间文化传统的存续。但同时,莫言也在《檀香刑》《红高粱家族》《丰富肥臀》中写出了中国北方农村的生存之艰难,用悲戚的茂腔控诉故乡这块土地的落后、闭塞和故乡人的愚昧。莫言在《超越故乡》中写道:“十八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比牛马付出的还要多,得到的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凄凉生活。夏天我们在酷热中煎熬,冬天我们在寒风中颤栗。一切都看厌了,岁月在麻木中流逝着,那些低矮、破旧的草屋,那条干涸的河流,那些土木偶像般的乡亲……当时我曾幻想着,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②莫言:《超越故乡》,《会唱歌的墙》,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233-234页。因此,“血地”不仅是母亲生育流血的地方,不仅是作家度过童年乃至青年的熟悉的地方,更有一层含义,它是有复杂的、难以名数的情感积淀的地方。它的复杂在于,这个地方并不是全都包裹着爱,还有令人心生痛苦、欢愉、泣血的现实图景,而当找不到出路倍感迷茫的时候,又能够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找到情感的归属寄托。当作家能够把这种复杂的情感融入创作的意境,肉体的故乡也就演化为了文化的故乡、精神的原乡。
大多数成熟的作家对故乡的情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热爱,而是存在着由顿挫衍生出的理性转变。纪录片很客观也很坦诚地叙述了这一点,例如经历《废都》遭遇的贾平凹,再如想看看还有没有比家乡更坏地方的阿来,还有想逃脱饥饿去当兵的莫言。他们表达乡愁,表达对故乡落后、贫穷的审视,表达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反思。莫言曾说:“高密东北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高密东北乡是在我童年经验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一个文学的幻境,我努力地要使它成为中国的缩影,我努力地想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③莫言:《莫言讲演新篇》,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121页。
纪录片仿佛一把铲土的铁锹,一点点挖开土层,露出作家和他所成长的土地之间始终牵引着的隐秘绳索。作家的血地是对“地理故乡”的诗意想象与审美扩张,是无限开放的,可以不断生成新的时空意义。作品中关于自然,关于生命,关于故乡,都是作家给故乡的一个交代。作家尽可能地还原故乡历史的厚重,同时从民间生活的乡土根性回溯文学创作的诗性与神性。如此一来,与其说“寻根”,不如说是在历史中坦诚地、反思性地、赤裸裸地叩问:“我究竟是谁?”即便是要打破重建,也需要找到那个基点,而故乡就是那个基点。作家们在故乡找到了原始而野性的力量,也找到了最为淳朴的、不加修饰的赤裸的曾经。
二、分享秘密:在蒙太奇中诉说困惑与执念
刘震云在纪录片中讲:“故乡对人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最重要的层面——语言、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肉体的故乡如何转变为文学的故乡,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对方言的应用和理解。也是通过语言,故乡血地的文化传统和风土人情才得以存续。所以,这是一番从语言开始、最后超越语言的诗意流动。既谈到方言,便必定要说说纪录片中偏不讲方言的毕飞宇。
毕飞宇有意识地在纪录片全程使用普通话表达,即便是在苏北农村,村民们用方言同他聊天,他也用普通话回应。无需多言,这样的言语对话是带有明显疏离感的,他是游离于乡土之外的。故而,无论是一般的观众还是文学研究者,都会有所猜想:随着纪录片叙述的推进,在毕飞宇的普通话背后或许会有更多隐秘深邃的东西逐层揭开。对于大众来说,在毕飞宇这一集,“秘密”成为关键词。
首先是他的姓氏。“我是家族缺失的人,因为父亲来路不明,父亲由姓陆改为姓毕,所以我就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这对毕飞宇来说,没有故乡、没有祖先都是巨大的遗憾。毕飞宇在小说《祖宗》中渗透着不同浓度的黑色,那不是一种确定的颜色,笼统来说就是没有光。这就表明了作家对祖宗的态度,以及对人与祖宗关系的怀疑。在毕飞宇的笔下,祖宗不仅是祸的象征,也是文明的咒语。
他对故乡的定位是第二个“秘密”。“来路不明”四个字,充满了自嘲和遗憾,而“我作为一个来路不明的后代,又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而不停地漂泊”。纪录片用了倒叙和插叙混杂的方法,从扬州起,至南京求学,再回溯到中堡镇,而后又到了毕飞宇出生的地方杨家庄,最后一站则是1979年到达的兴化。生活因为各种现实的原因辗转,给毕飞宇最直观的感受是自己被连根拔起,一敲,根上的土都掉了。继而,他的故土究竟是哪里也成为了“秘密”。实际上,毕飞宇在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就对自己的身世有所表露,毕飞宇诚恳面对过去,但还是遮蔽了一部分人生的秘密。有一些生活体验是悄然进入心理动因和转换机制的,在潜移默化间成为了作家艺术创作的文化资源,而没有出现明显的标注。显然,毕飞宇本人是认同这一点的,所以他才想在自己的虚拟文学创作中回过头来写写那块土地和他的祖辈——“再怎么说你没有故乡,你什么都没有,我相信,只要我在那片大地书写过,我就有理由把它看成我的故乡。”
毕飞宇部分是纪录片中写意成分最多的一集,舞蹈家王亚彬在水乡花田中演绎《青衣》片段,正是一种蒙太奇式的诉说:美的、写意的、虚构的、令人不断产生好奇心的东西,就是毕飞宇热爱写作、热爱虚构的原因。张同道通过王亚彬的白衣水袖向观众分享了毕飞宇的“秘密”。
第三个“秘密”最为动人,是关于树生长的姿态,是属于自然的,也是属于美的。“告诉你一个我内心的秘密:我特别喜欢仰着头看树。其实,任何一棵树都长得没规矩,它想怎么长就怎么长,跟写作非常像。一棵树枝决定向哪儿延伸,它都是对的,怎么长都是对的,它永远不会长错。这个发现为我的写作带来了巨大的勇气和自由。”毕飞宇半架着眼镜,抬到脑门上——他标志性的戴法,他站在南京茂密繁盛的古树下,仰拍的镜头不停地旋转。镜头仰望着作家,作家仰望着天。这其中有迷惑,有不确定性,同时也有力量感。在诗意的蒙太奇镜头中,毕飞宇对高耸云天的古树也表达出了敬意。这是对自然的敬意,以及作家所受到的启蒙。
随着时间的流逝与亲人的故去,作家们寻找的是一种痕迹,既是自己生活过的证据,也是如今的自己从何处来、又将往何处去的答案。作家的返乡是真诚的、虔诚的。毕飞宇的两次情难自禁都发生在杨家庄,一次是找到了刚到杨家庄的那个场景画面,镜头中他的背影耸动;另一次是和毕飞宇“舅舅”夏雨田抱养的哑巴儿网存相逢。尤其有意味的是,网存无法说话,他与毕飞宇的交流已经完全超越了语言,所有的所谓“艺术性证据”与“哲学性思考”都融化在童年回忆中。这也令毕飞宇在杨家庄实现了对故土的物我相遇、物我相融、物我相忘。
每一集纪录片的丰富性和美学风格各有不同,这与作家的经历、性格、面对镜头的感受,理解生活、认识世界、触摸乡土的姿态,都有关系,与作家写作的潜意识驱使、本质、精神诉求也有密切的联系。张同道导演向观众分享作家的秘密,以及作家在人生中发现的秘密,并在蒙太奇镜头中展露了作家在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执念。纪录片中表达了许多令人惊诧的反转性——不识字的乡人、外祖母、小舅等成为了人生哲学家和启蒙者,对生活有着透彻的体悟;而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对这种原始的认知世界的能力与胸怀表达了无限的崇拜,反转了常规路径的身份感,打破重构、颠覆了知识分子探索的路径。
刘震云外祖母割麦子能赢过满村庄的大汉,这是刘震云从小就想探究的“秘密”。外祖母说:“割麦子,我只要扎下腰,就从来不直腰。因为你只要直第一回,你就想直第二回和第二十回。这样趁着别人直腰的时候,我就比别人割得快。”它是秘密,是生活的诀窍,也是为人的根本。对于观众来说,看完这部纪录片,在了解作家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执念之余,内心会有一种新的东西在生长;对于作家来说,拍摄完这部纪录,亦会有新的东西生长。
作家的“秘密”,实际上就是作家在文本中存留的空白,也就是阿尔都塞所谓的“症候式阅读”的条件。在当今的文学作品中,单单依靠问题式阅读很难完成有深度的解读了,必然要依赖症候式阅读,从作者所留下的“空白”“沉默”“症候”来读出文本中字面语句所没有表达出的深层含义,即是小说中没有清明言说,却又影响了创作的因子,关于精神内核、美学路径选择、命运的安置等。这部纪录片就是对作家症候阅读的辅助,将隐秘的、缺席的东西和文学接受过程中被忽视的部分都分享给受众。因此,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次具有典型意义的、带有普遍性的、关于乡土与启蒙的艺术生产。
三、影像的修辞学:作家的离去与归来
张同道创作纪录片尽量保持着学者姿态,坚持创作的独立性;在内容的传达上,追求真实、严谨;在形式表达上又保持着开放的心态,艺术手法多变。在非虚构的前提下,力求使纪录片更具观赏价值,这一点是难度所在。在《文学的故乡》中,这六位作家作为一个意识开放的采访对象,并不是被完全限制于一个封闭的叙事时空中,它不断地行进,不断地流动,这让叙事的时空也不断进行延展。接受美学代表人物伊瑟尔认为:“文学文本具有两极,即艺术极与审美极。艺术极是作者的文本,审美极是由读者来完成的一种实现。”①[德]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金元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9页。纪录片面对受众,同样经受着接受美学的考验。艺术级和审美级不可偏废一方,所以,有效地使用影像的修辞学,能够将六位作家的情感和意志用更有共情力的方式表现出来,将作家的离去和归来用更为多维的历史观照呈现出来。
张同道导演选用一个农民锄地的背光影作为整部纪录片的第一个镜头,是颇有深意的。观众看不清农民的脸,只有剪影——正是因为看不清农民的脸,所以他可以是每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也可以是作家认识的、了解的农民形象,当然也可以是作家自己。农民,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中国的大地上,是极为重要的国民群体存在。对于这几位作家来说,农民与血地是一对富有震撼力和感染力的意象,打开了他们的书写大门。这第一个镜头为这部人文纪录片奠定了美学基调,呈现了一种辽阔的意境和人文精神的魅力。
贾平凹先生在第一集开篇无不骄傲地、用浓重的陕西方言说道:“秦岭是中国的一条龙脉,它横卧在中国的腹地,它是提携了长江和黄河的,统领了北方和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也是最有中国味的一座山。”贾平凹一生都围绕在秦岭,秦岭厚重绵延的历史赋予了他丰富的创作资源和灵感,当他寻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感到苦闷的时候,他只想到他熟悉的地方。秦岭这片土地是神秘的、崇高的,充满了灵性,联结着神明和鬼神。他在小说中不断用原始意象和巫鬼文化来书写乡土中国,最终将一切人与事又回归到乡土中,这是他对现代文明代替传统文化的隐忧和不满。从寻根文学到改革文学,贾平凹看似一直在围绕着秦岭来写作,但是创作的内核早已突破了现实的空间感。张同道用大广角镜头远眺秦岭,将作家的心境与自然景观同等相栖,这才抓住了贾平凹创作的全息性特征。他时时都在此空间之中,却又超越了地方性。张学昕教授曾评价:“他在构建一种人伦关系的时候,既不背离生活本身的逻辑,不随波逐流,同时又不忘记在写作中反思人的处境、人性的变化。尤其是他对于人性、欲望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其间发生的裂变和错位所做出的超越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的思索,更有其审视灵魂的力度和力量。”②张学昕、贺与诤:《简洁而浩瀚的“商州美学”——贾平凹短篇小说阅读札记》,《当代文坛》2020年第2期。贾平凹将他雄浑悲悯的精神气度和乡土经验弥漫在字里行间,张同道给贾平凹的镜头修辞也是粗粝的,聚实焦的。
迟子建一集的开篇,雪在光影中映衬着这个冰雪国长大的天真自由的女儿。雪的浪漫折射着光,抚摸着迟子建一路成长的痕迹。对于迟子建丈夫意外离世的一段采访,导演给了迟子建一个中景长镜头,陪伴着她回忆讲述丈夫的离世和自我修复的那段时光:“幸福不能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哪一个冬天会没有尽头呢?”每一句话、每一个语词,都温柔平和中带着力量和执着。不加修饰的镜头抒发了已达不惑之年的女性直面人生的旷达,还原了这位女性作家的感性与理性,应答了读者的揣测,也是作家同自己和解,对自己创作的交待。
相比表现迟子建的平直镜头,阿来一集的镜头十分复杂多变,充满了修辞的张力和寓意。在卓克基土司官寨——被《尘埃落定》蒙上神秘色彩的地方,张同道突破了纪录片的常规方式,同时运用平行蒙太奇和抒情蒙太奇的手法,加入了艺术想象的实体转换:在官寨楼上,阿来端起单反相机,镜头成为一个隧道,在镜头中即出现了书中虚化的土司二儿子和塔娜。参考阿来的文学创作特质,仅仅依靠纪实的影像镜头是很难表现其丰富性的,需要借助其他感性的艺术表现形式。正如埃德加·卡里特所说:“在一切美的东西之中,都存在着始终是表现感觉的形式。不表现和无形式的激情,是带有动物性野蛮特点的新酒;优雅而无激情的诗句,则是艺术在文化的旧瓶中所残留的沉淀物。”①[英]埃德加·卡里特:《走向表现主义的美学》,苏晓离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220页。阿来一集中所有场景都回到了真正的文学现场,镜头表现很有仪式感。他站在梭磨河畔谈诗集《梭磨河》,在原始森林回望他的《空山》,踏上草原吟诵《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在卓克基土司官寨回顾《尘埃落定》。镜头中的爬山也是他文学创作历程的象征。阿来正在创作一部关于植物猎人的小说,所以纪录片中出现了大量的阿来拍摄植物的镜头,他跪下去、他趴在草丛、他仰面躺下,只为记录一朵花开的姿态。每一个花朵都是它所处的自然环境中特别精巧的一种设计。因此,在阿来的笔下,生命既是简单的事情,也是具有震撼力的存在。
《文学的故乡》每一集纪录片都为作家作品在国外的翻译、出版和研究现状留有相当的篇幅,展现翻译本在国外的传播效果,以及作品被国外学者、翻译家接受、认同和共情的情况。对于作家创作来说,这是具有普适性的重要评价。这也证明了,作家的创作本质精神已经超越了故乡、民族、国家而产生了人类普世性的共鸣和巨大的影响力。正如刘震云所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被遗忘的角落,恰恰是这些被遗忘的角落藏着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学像一束光,它能照亮这些被民族遗忘的地方。”同时,对“文学的故乡”的坚守也能拒绝遗忘。诗意的流动、神性的敬畏和淳朴震撼的血地,在张同道的影像中有了更为感性的聚焦方式,超越了语言的限制而成为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索引。
纪录片用新的角度去观察有结论的认知,证实和纾解了可能产生的怀疑或共鸣,呼应了某种特定群体、特定对象的诉求,但仍在传播中保留了一部分“未完待续”的朦胧模糊。它的索引特征成为一个做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使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在追求历史性的同时,也具有延展性和社会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