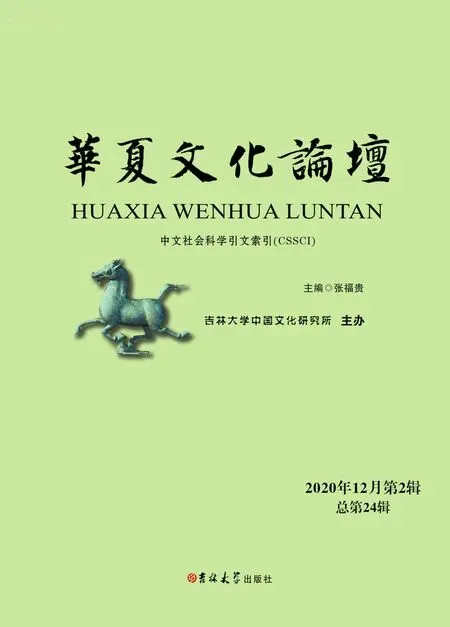论帕慕克小说《白色城堡》中的颜色隐喻与文化象征
2020-11-18
【内容提要】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是土耳其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白色城堡》构建了一种东西方精神文明交融与稳定的状态,试图通过镜中孪生兄弟对调身份的方式找寻东西方对话的途径。帕慕克以色彩为线索的一系列代表作品不断实践着对土耳其民族身份归属问题的认知与追寻,创造出了土耳其文化归属意义上的“帕慕克宇宙”。本篇论文将从帕慕克在文学创作的背景出发,以一部经典文学作品《白色城堡》为例证,探究其小说中的颜色意象隐喻,并充分发掘故乡对作者创作心理、文化身份与主体意识的影响。
屈原《哀郢》诗云:“狐死必首丘。”故乡不仅是一个作家成长的摇篮,亦是灵魂和回忆栖息的地方,它对作家的创作习惯、思想倾向以及审美心理结构都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2006年,一位来自土耳其的作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就是奥尔罕·帕慕克。奥尔罕·帕慕克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其父亲天性热爱文学艺术,父亲的鼓励与殷切希望形成了幼年帕慕克关于文学创作的启蒙。六岁起,帕慕克开始学习西式绘画艺术,推崇莫奈、毕沙罗、尤特里罗等人。成年后他将所习得的绘画艺术融入文学创作中,使绘画为创作提供了灵感来源与文学素材。
帕慕克在小说创作中将颜色的铺陈与渲染达到了极致,这与古代诗人王维在某些维度是具有某种相似性的,王维与帕慕克都身兼作家与画师的双重身份,他们的妙手丹青使文学与绘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融合。帕慕克穿梭在光怪陆离的色彩世界,不断实践着对土耳其民族身份的认知与追寻,塑造了瑰丽的色彩与奇情的帝国。以其故乡伊斯坦布尔为中心,帕慕克尝试打破人们传统认知中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僵局,构筑了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的东西方文明交融互通的文学桥梁。《白色城堡》构建了一种东西方精神文明交融与稳定的状态,试图通过镜中孪生兄弟对调身份的方式找寻东西方对话的途径。帕慕克以色彩为线索的一系列代表作品不断实践着对土耳其民族身份归属问题的认知与追寻,创造出了土耳其文化归属意义上的“帕慕克宇宙”。
一、白——无法抵达的梦境
奥尔罕·帕慕克是色彩帝国孤独的守望者,出色的绘画功底使他对于颜色的敏感程度超乎于一般作家,这与他幼年学习绘画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他深刻通晓颜色的表现力。他赋予颜色以生命力,用画笔徜徉在17世纪君士坦丁堡的大街小巷,娴熟地运用西方透视画法与土耳其细密画法的绘画技巧,将颜色意象自如地穿插在多声部叙事语言之中,把文学艺术与绘画艺术巧妙地结合起来,创作出了语言美与颜色美共具的小说。《白色城堡》中的两种对比色彩——白色与黑色,象征着作者在东西方身份之间的犹疑、徘徊与彷徨。
《白色城堡》是帕慕克第一部历史小说,于1985年出版发行。作品主要讲述了一段东西方文明相遇融合、离奇曲折的故事: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正处于由盛转衰的时代,威尼斯学者“我”被海盗俘虏至伊斯坦布尔,苏丹把“我”引荐给土耳其人霍加,“我”成为了他的奴隶。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二人拥有极度相似的面孔。“我”与霍加阻止了土耳其一场灾难性的大瘟疫,苏丹对霍加赞赏有加,并晋升他为皇室星相家。“我们”为苏丹发明了一件用来攻打“白色城堡”的武器“黑色污点”,最终这场战役以失败结束,寂静的浓雾之中,“我”与霍加在白色城堡遥不可及的梦境下实现了身份的交换,“我们”作为彼此的影子重新开始新的命运。霍加离开故乡,奔向了他梦想中的西方城市威尼斯,而“我”则取代他留在东方伊斯坦布尔,任职皇室星相家,娶妻生子。
在《白色城堡》中,关于“白色城堡”的描写仅出现过一次,将其摘录如下:“它(指白色城堡)位于一个高丘的丘项,落日的些微余辉照在旗帜飘扬的塔楼上,堡身是白色的,白白的,很漂亮。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如此美丽且难以到达的地方……想要赶到山丘顶上明亮的白色建筑物那里去……有着你所不想错过的幸福。”①[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白色城堡》,沈志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0页。作者通过一系列比喻句抒发对这座城堡的向往之情,这是他对“白色城堡”寄寓着深厚个人情感的集中流露。对白色城堡充满期待的原因是那里拥有作者不想失去的幸福,所以他渴望抵达。但是在本体和这些喻体之间,却相隔着梦一般虚幻的距离。
那么“白色城堡”这一意象,究竟隐喻着作者的何种情感?它是否也如同帕慕克想象中的幻梦一场,事实上并不存在呢?
(一)命运的隐喻
“白色城堡”隐喻命运的神秘性与未知性。白色城堡是人类永远无法抵达的精神彼岸,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的代名词,充满着神秘感和未知性。冥冥中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带领着人们走向它,这与卡夫卡在《城堡》中所想传达的思想主题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无限趋近、循环往复的命运怪圈。我们时常对人生未知的前途和命运心怀疑惑:这个世界上会不会存在着另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的命运又会如何呢?帕慕克借助白色城堡的意象塑造,对这一问题的答案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
“我”与霍加在伊斯坦布尔的相遇绝非偶然,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土耳其的高速发展进程中,宿命论观念支配下两人跨越国界相遇的必然,是命运将这对东西方的“孪生兄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我们”的相遇也是东方与西方文明在伊斯坦布尔这个“十字路口”命运产生交集的必然。
帕慕克认为过去的民族传统大部分是祖先遗留下来的美好财富,但是人们不应该对它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自由的人类灵魂应该选择把各种文化身份结合起来,或者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文化身份。与此同时他也并不认为存在一个独立国家的概念,我们都是世界公民,并不存在纯粹的国别,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身份更加不需要肩负道义上的责任感。尽管这种“中间人”①窦波:《奥尔罕的钟摆——帕慕克的小说艺术与文化认知发微》,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39页。的文化身份在现有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但它为土耳其人提供了文化身份的第三种选择,定位了自由主义的文化认知,证实了解构东西方文化冲突理论上的可能性。《白色城堡》小说中结局的开放性与模糊性给予了后来者更多关于东西方前途命运想象的空间,也为中西方文明交融构建话语体系赋予了无限的想象。
(二)土耳其文明的象征
“白色城堡”也是土耳其民族文明的象征。白色城堡作为土耳其国家的军事堡垒,自古以来就扮演着保卫土耳其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守夜人角色。“白色城堡”是“我”与霍加进攻的对象,但它并没有被现代高科技武器所摧毁,依旧作为物质文明的地标性建筑守护着土耳其这片土地,这也是作者帕慕克对故乡伊斯坦布尔文明坚定信仰的体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东西方交流更加密切,然而由于政治背景、民族情感、历史环境和宗教信仰所持立场不同,人类的思想文化在频繁的对话中难免产生冲突与隔阂,而土耳其因为其位于东西方的十字路口,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这个矛盾更为显而易见。作者希望能够借助白色城堡这个象征土耳其文化的意象,找到东西方文明共同的归属感和落脚点,使东西方人民都能进入一个真正意义上精神文明的国度,也希望自己的故乡土耳其可以远离破败与孤立、迷惘与哀伤。
1925年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开始进行西化改革,使土耳其成为了一个现代化世俗国家。但是他理想中的民族国家在土耳其的实践中,面临着缺乏根基、水土不服的问题,加之改革措施缺乏变通,无视多元性和差异性,使得国民在民族认同构建的过程中,存在抵触心理,最终效果不理想。②甄华杰:《现代土耳其社会分层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97页。
西化过程带给土耳其人难以言喻的失落感与恐惧感,他们开始陷入自我迷失和混乱,逐渐失去了本民族的身份认同感。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民族身份认同的长期缺失感会带来凝聚力的丧失,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凝聚力和向心力,将会导致整个国家精神信仰的坍塌,将会带来致命性的打击,这也是身为土耳其人民的帕慕克所不想看到的。因此他塑造出“白色城堡”的意象,希望帮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寻找到身份认同的归属感,重新构建集体性的精神信仰。
(三)人类精神故土的象征
“白色城堡”还象征着人类共同追寻的精神故土。在沈从文《边城》一书中,守护着茶峒百年兴废的白塔在风雨之夕轰然倒塌,象征着充满人情美的湘西世界在城市文明的侵蚀下土崩瓦解,结尾处重新修葺坍圮的白塔也象征着凤凰人对原始故乡文明的追忆与重拾。威尼斯学者长期在异乡漂泊流浪,白色城堡正是隐喻威尼斯学者永远无法返回的梦中故乡。
大雾是小说中的核心意象,象征着迷失自我的困境。①周宁:《小说家的思想——重读帕慕克〈白色城堡〉》,《读书》,2015(04),第103页。在威尼斯学者看到白色城堡的那一刻,他明白自己已经逐渐习惯了伊斯坦布尔的生活,梦里的故乡是不可能重返的,只能由霍加代替自己完成未能成为现实的梦境。他不得不独自一人留在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威尼斯,继续着无法摆脱却不得不坦然接受的命运,面对着困难重重的人生。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一文中这样形容城市:“城市生活者那如同举行某种年度仪式般地陷入的、像日常熟悉的浑浊的咖啡果冻一般的精神幽暗再次笼罩了我。脏兮兮的楼宇,芸芸众生的群体,永不中顿的噪音,挤得寸步难移的车列,铺天盖地的广告牌,野心与失望与焦躁与亢奋——其中有无数选择无数可能,但同时又是零。我们拥有这一切,而又一切都不拥有。这就是城市。”②[日]村上春树:《去中国的小船》,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31页。足以见得飞速发展的现代化都市似囚笼一般禁锢着人们的肉体,束缚着人们的精神。而那遥远的“白色城堡”则与压抑、脏乱的伊斯坦布尔城市相对照,成为了人类精神世界中的理想栖息地。
生活在现代大都市中的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着威尼斯学者的影子。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时常处于一种紧张而焦灼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而冷漠。我们似蝼蚁般在大都市精心包装的外壳下苟延残喘,灵魂深处保留着一丝对故乡温存的向往,挣扎在对过去的苦苦追忆与无法回到过去的痛苦泥沼中寸步难行,在残酷的现实中割裂自我,无奈地寻求心灵的解脱和救赎。
二、黑——窒息绝望的荒原
与“白色城堡”形成一组对比意象的是“我”与霍加运用机械科技知识共同制造出的武器“黑色污点”,它是一个由钢铁打造的重型机械大炮。作者在小说中并未对这一武器进行具体的细节描绘,而只是运用比喻的写作手法,将它比喻为“猪、黑崽、巨兽、魔鬼撒旦、大家伙、大虫子、庞然大物、独眼巨人、蓝色眼睛的怪物、黑色的铁堆、移动的城堡、带轮子的锅、带弓箭的乌龟”,使读者可以赋予“黑色污点”这个意象更多隐喻意义。
(一)战争的隐喻
“黑色污点”隐喻奥斯曼帝国战争的冷酷性。黑色象征着黑暗、冰冷、死亡与战争,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是一部衰落史,更是一部战争史。书中进攻白色城堡的战争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真实存在,它代表着土耳其战争史上的一场浩劫,1529年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苏莱曼一世率领十万人攻打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冬季的寒冷逼退了土耳其军队,这场战役以土耳其人的战败结束,史称“维也纳之围”。这一次战争也成为了奥斯曼帝国止步西欧的历史转折点,此后西方成为了土耳其人无法抵达的远方。
战争的隐痛与阴翳是土耳其人记忆里挥之不去的“黑色污点”。人类贪婪地对文明和文化的血腥暴力征服,大量人力、财力的浪费拖垮了国家经济。当整个国家被笼罩在战争的“黑色污点”下时,人间就如同恶魔撒旦统治下的炼狱一般,人民的生活充满着苦难与绝望。战争对于一个民族所带来的黑色创伤是难以愈合的,那段历史中的黑色记忆也是难以忘怀的。城市已不再有城市的容貌,废墟成为随处可见的风景。当现代科技被滥用,变成肆意杀戮、破坏和平的武器时,世界必然走向毁灭与失败。两种文明在交流中产生碰撞是难免的,但是彼此可以理解冲突、消解崇高,以求达到互惠共存的状态。在中东文明与欧洲文明历史语境与现代书写下,帕慕克渴望通过小说创作引起读者对于二者关系的重新审视与思考,从而跨越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藩篱。
(二)现代西方文明的象征
“黑色污点”也是现代西方文明的象征。当土耳其人初次接触“黑色污点”时,过于沉重的大炮使得行军速度变缓,军人们都认为它是邪灵的象征,会为军队带来灾祸,纷纷不敢靠近。最终它陷入沼泽而不能前进,也反映出了土耳其人与现代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之间深度的隔阂。
土耳其是一个中东地区的国家,土耳其国土面积为769604平方公里,其中97%属于亚洲,3%位于欧洲。尽管土耳其大部分领土位于亚洲,但它始终坚持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近代历届土耳其政府都非常推崇西方文化,共计开展了三次西化运动。但是土耳其融入欧洲的过程却是非常艰难的。面对着西方“黑色污点”不断进攻下的伊斯坦布尔,精美独特的奥斯曼风格建筑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西式混凝土建筑。帕慕克极度厌恶过度西化下的故乡,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他发泄着对城市的不满:“这确实是个朝两方推进的城市,所有的一切都是半成形、粗制滥造、肮脏污损的。”①[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8页。咖啡、汉堡、大型商场、雪佛兰汽车、好莱坞电影这些西式的生活方式进入了土耳其人的日常生活,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古老文明的绝迹带给土耳其人强烈的时空断裂感,造成了民族归属感的丧失,也使整个国家和城市丧失了个性。
现如今帕慕克这样描述他内心中对于故乡的忧郁与哀伤:“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帕慕克与故乡伊斯坦布尔构成了一组“在”而“不属于”的依存关系,当城市与故乡都无法作为知识分子安放心灵的家园和精神寄托,知识分子便成为了城市的边缘人和故乡的流浪者。
(三)土耳其民族忧伤的象征
“黑色污点”象征着一种由知识分子个人蔓延到整个土耳其民族的失落感与挫败感,是一种被称之为“呼愁”的集体性忧伤。
“呼愁”是整座伊斯坦布尔城市的灵魂。它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的忧伤情绪,是整个伊斯坦布尔人的忧伤。“呼愁”既是源于奥斯曼帝国辉煌历史的优越感,又是源于奥斯曼帝国如今衰落的耻辱感。土耳其民族位于欧洲的边缘却生活在贫困之中,于是整个民族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处世哲学:土耳其人永远不会富有,不会成功,贫困和挫败感被当作命运被他们所接受。
土耳其在西化进程中,种族冲突问题、土耳其现代化改革问题的接踵而至,保守派与西化派之间喋喋不休的论争,这些都促使帕慕克将视角转向了那个记忆中的“黄金时代”。
沉睡的宗教信仰与历史遗迹在帕慕克的作品中复活,怀旧的危机冲淡了土耳其人精神上黑色的绝望感和荒原感。帕慕克使用历史语境下的书写来修复剧烈社会裂变带给国民心灵的戕害,“黑色污点”是隐藏在民族灵魂深处无意识的创伤,它包含着土耳其人对奥斯曼帝国昔日辉煌的留恋和沉湎,对帝国衰落命运不可挽回的哀叹,对土耳其现代化改革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的焦虑。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一段尘封的历史、难以忘却的隐痛,如何治愈民族创伤、走出记忆的阴霾、积极面对未来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而帕慕克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三、白与黑的艰难抉择——文化身份认同的追寻
在《白色城堡》这部小说中,从威尼斯学者和霍加最初的冲突对立到最后的和解交融,两人的身份也一直处于不断的互换之中。他们作为“自我”的时候代表本身的固有属性,作为“他者”时分别代表东方和西方文明。二者在精神和灵魂层面的完全契合,是作为“他者”时两种文明交融与稳定的状态,而冲突则代表着“他者”外壳下两种文明的对立。小说结尾处霍加选择离开,以威尼斯学者的身份前往梦中的西方世界,威尼斯学者留在伊斯坦布尔继续霍加皇室星相家的事业,则是他们各自对“自我”身份的最后消解,他们转化为东西方世界联结的纽带,即“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带给我们丰富的哲理性思考。
帕慕克从对个人身份的追问上升到对国家文化身份的追问具有极其鲜明的现实意义。帕慕克提出了当今世界令人焦虑的民族文化身份问题:一个国家应当如何正视过去的历史与未来的命运?若过分偏激地追求“文化自我论”,就会陷入种族主义的怪圈,无疑会排斥世界文化,不利于文化的融合;如果过度追求“文化他者论”,将会在世界文化的漩涡中迷失自我,丧失民族身份。
站在文化身份观的选择角度分析,《白色城堡》中关于两种呈现对立状态的颜色“白”与“黑”的选择,二者不是意指某种东西方文明,而是两种文明形态的选择。“白”象征着文明的融合,“黑”则象征着文明的冲突,最终“白”战胜了“黑”,“黑”不攻自破。而事实上帕慕克也并非执着于“黑”与“白”的对立,二者必须分出胜负,选择非黑即白的状态,他更想在白与黑之间达到一个平衡点,因此小说最后以一团迷雾收尾,作者放弃做出“黑”与“白”的抉择。
帕慕克创造性地找到了一条脱离传统意义上东西方二元对立格局的道路,土耳其具有双重的身份认知,既可以是东方的,也可以是西方的。两位主角的身份互换象征着作者寻求“双重身份”的价值判断——我们既可以是东方人,也可以是西方人。他既没有将西方文化视作神明,也没有将其弃之如敝屣,而是博采众长、兼容并蓄、文化杂糅、东西共存,以一种开放、包容、折中的文化立场对待西方文化。帕慕克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重新审视土耳其民族文化的概念,重建了失落的故乡伊斯坦布尔民族文明。
《白色城堡》中,在威尼斯学者与霍加相遇之初,在他们相互学习沟通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对彼此的不信任以及批判怀疑,这也是对自身所属文明的维护。进攻“白色城堡”的战役失败后,霍加和威尼斯学者在浓浓大雾中互换身份,一人逃离原有的故乡,一人留在充满新生的城市。从思想情感层面而言,东西方各有的价值观没有被分裂,也不会失去归属感;从文明的角度来说,这使人类没有失去东西方任何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二人在看似对立的文化身份中实现了文化的兼容并蓄。帕慕克的小说创作表现出了他对东西方文化关系问题的深切关照,揭示了冲突和对立对发展本民族文化是没有益处的,只有站在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以包容、开放、折中的态度,积极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与碰撞,架起一座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在坚守本民族文化的根基上,对西方先进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才能找回土耳其人遗失的民族身份归属感与认同感。
颜色意象在帕慕克的作品中占据大量篇幅,幼年的学习绘画艺术的经历使他在创作中无意识地将色彩与文字交融。《白色城堡》中,他以“白”与“黑”的艰难抉择表现自己对于个人身份认知的追寻、东西方文明关系问题的态度,给读者独特的视觉审美体验。帕慕克的作品以故乡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东方文化为背景,借鉴效仿西方文学的写作技巧,将东方的神秘题材与西方的叙事结构完美结合。他使得东西方文化在流变中依旧坚持灵魂对话,达到了精神上的深层契合。也正是因为阅读他的小说,我们得以窥见一隅土耳其的历史、文学、宗教、民族心理与文化身份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