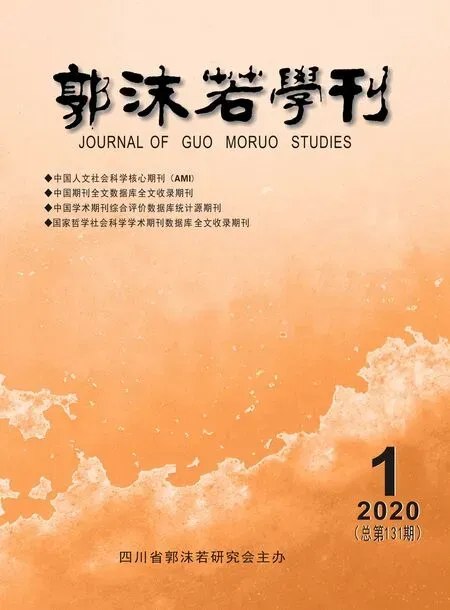挥洒自如写“女神”
——评李斌著《女神之光——郭沫若传》
2020-11-18廖久明
廖久明
(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四川 乐山 614000)
通读完《女神之光——郭沫若传》(作家出版社,2018年,以下简写为《女神之光》)后,认为李斌挥洒自如地写出了他心目中的“女神”郭沫若。
姑且不论规模更为庞大的郭沫若研究资料,单就郭沫若自己的作品而言便很多很多:已经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有38卷,未收入《郭沫若全集》的诗词、文章、翻译、书信、古籍整理等多达27卷,还有《郭沫若书法全集》10卷(李斌:《〈女神之光:郭沫若传〉的写作与出版》,《郭沫若学刊》2019年第1期,以下简写为《写作与出版》)。据版权页,《女神之光》的字数为49万字。要想在49万字的篇幅中“完整而简洁地描述郭沫若的生平、思想及性格”(《写作与出版》),没有高度的概括能力是不行的。阅读一下《女神之光》便会发现,李斌具有很强的概括能力。单就自传作品而言,郭沫若便写作了不少,李斌却将其高度浓缩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浓缩在《忆昔我曾出嘉州》一章中,将《初出夔门》《我的学生时代》《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编》《今津纪游》《水平线下》浓缩在《负笈远道去国游》《创造当年曾共社》两章中,将《北伐途次》《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脱离蒋介石之后》《海涛集》浓缩在《马列真诠赖火传》中,将《洪波曲》浓缩在《鸡鸣风雨际天闻》中。在这些篇章中,除郭沫若自传外,还浓缩了其他内容,篇幅却只有172页,占全书537页的32%。
李斌在具有很强的概括能力的同时,还具有广博的知识面和开阔的视野。在述及郭沫若1917年8月14日致父母信时,李斌如此写道:“这信描述日本人情风俗,明丽可喜,比诸后世推崇的周作人等人的散文,直在伯仲间耳”(第53页);在述及郭沫若的打油诗“权把梨儿作炸弹,妄将沫若叫潘安”时,李斌引用了《世说新语·容止》及刘孝标注引《语林》中的文字,有力地说明了郭沫若打油诗的价值:“郭沫若用‘掷果盈车’的典故,显得淡然而幽默”(第195页);在述及郭沫若与陈寅恪的关系时,李斌不但介绍了韩愈的《平淮西碑》、李商隐的《韩碑》,还介绍了郭沫若19岁时对李商隐《韩碑》诗的评点、皖南事变后写作的《咏史》(第376-377页)等。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李斌是不可能做到由此及彼的。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仅有广博的知识面还不行,还必须有开阔的视野,否则便只能局限于自己写作的核心内容,而不能将相关内容写进去。《女神之光》每章的标题大都取自郭沫若诗词,实际上也体现了这一特点:要想在郭沫若大量作品中选择符合每章内容的诗词作为标题,只有在对郭沫若作品相当熟悉并且具有开阔视野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尽管《女神之光》的内容相当丰富,全书却脉络清晰。全书以郭沫若的生平为经,以重要事迹为纬,有条不紊地写出了“郭沫若的生平、思想及性格”(《写作与出版》)。除上面已介绍的篇章外,作者用两章71页的篇幅写作了郭沫若流亡十年的情况:《爰将金玉励坚贞》主要写1928-1930年流亡日本初期从事自传写作、学术研究、翻译及参与国内文坛论争等情况,《渊深默默走惊雷》主要写1931-1937年流亡日本后期从事学术研究、写作自传、参加东京左联活动等情况,两章都写到了郭沫若在流亡时期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活动,前一章侧重于写在容庚帮助下进行研究,后一章侧重于写在田中庆太郎帮助下进行研究;用两章86页的篇幅写作了郭沫若在三厅和文工会的情况:《鸡鸣风雨际天闻》主要写1937年回国至1941年在三厅、文工会及为郭沫若祝寿的情况,《誓把忠贞取次传》主要写郭沫若创作抗战历史剧和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过程和观点;用两章53页的篇幅写作了1945-1949年参与民主斗争的情况:《域中潮浪争民主》主要写郭沫若在重庆的情况,《民之喉舌发黄钟》主要写郭沫若在上海、香港的情况;用5章188页的篇幅写作了郭沫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情况:《敷扬文教为人民》主要写郭沫若1949年2月从香港北上到1953年的情况,《争鸣方好咏新诗》主要写郭沫若1954到1959年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及参与百家争鸣的情况,《文章翻案有新篇》集中写郭沫若1960年前后创作《蔡文姬》《武则天》、研究和点校《再生缘》、写作《读随园诗话札记》的过程,《歌颂东风走天涯》主要写1961-1965年到全国各地巡游及写作、研究情况,《彩练横空舞夕阳》主要写文革及文革结束后的情况。
《女神之光》语言的特点是平实畅达。如果通过引文说明该特点需要较多篇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阅读原著,笔者在此仅分析一下具有该特点的原因。语言平实应该与作者采取“零度写作”的方式有关:“作者不发议论不抒情,只是从大量资料中选择那些最有意味、最生动的细节,从这些细节中凸显郭沫若的个性、追求和思想。至于郭沫若的个性完美还是有缺陷,他的追求合理还是不合理,他的思想偏激、驳杂还是纯粹,他人生道路的选择对还是不对,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我都不评判。”(《写作与出版》)语言畅达应该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一、作者具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能够自如地选择合适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二、作者对所写内容相当熟悉,因此写得相当顺手。
笔者前面之所以姑且不论规模更为庞大的郭沫若研究资料,是由于《女神之光》较少引用它们。在通读全书后,笔者回头统计了《女神之光》引用21世纪郭沫若研究成果的情况,其结果为:《郭沫若〈我的幼年〉的双重叙事与读者接受》(陈俐,第13页)、《郭沫若在冈山》(名和悦子,第48页)、《郭沫若年谱长编》(林甘泉、蔡震主编,第76、495页)、《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蔡震,第117、163、223、234 页)、《在“两个口号”论争中被茅盾遗忘了的一些事》(蔡震,第197页)、《四时佳气永如春》(蔡震,第411页)、《郭沫若的最后29年》(贾振勇,第495页)、《时代的反讽人生的反思——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刘海洲,第495页)。根据所写内容可以知道,少部分属于引用却未注明出处,多部分属于没有引用。出现第一种情况的原因也许是为了节省字数,并且应该与传记的写作方式有关——不能像学术论文那样掉书袋。不过在笔者看来,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时交代出处有以下好处:一、符合学术规范,二、能够说明自己写作的内容言之有据,三、能够显示出自己对研究现状的熟悉程度,四、能够为他人查找相关文献提供线索,五,如果对字数没有限制,还可增加作品的字数。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即使缩减正文字数也有必要交代引用观点的出处,建议《女神之光》再版时能够在注释中交代。出现第二种情况既有可能是看见了却没有引用,也有可能是没有看见。如果看见了未引用属于确实没有必要引用,说明作者具有史识,能够准确判断其没有价值;如果有必要引用却未引用,说明作者的史德和史识有待加强,要么固执己见、要么未能准确判断其价值。笔者无法根据未引用情况判断作者在该方面的史德和史识,却可以肯定存在没有看见的情况:在写作时,作者如果看过《1936年郁达夫访日史实新考》(武继平,《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第1期)、《郁达夫1936年访日新史料——近年日本外务省解密官方档案考》(李丽君,《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5期),并愿意将第201页的“1936年11月,郁达夫造访日本”增改为“1936年11月,在日本国1936年度‘对支文化事业’项目资助下,郁达夫造访日本”,并注明引用内容出处,至少会让读者对流行于学界的郁达夫1936年底赴日目的是“奉蒋介石之命”敦请郭沫若归国的说法感到怀疑,当根据引用内容出处阅读这两篇文章后便会发现流行于学界的说法是错误的。由此可知,作者对研究现状的把握有待加强。
当然,造成该情况应该与以下两方面原因密不可分:首先,需要阅读的资料实在太多,有的还很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出生的作者,为了能够“比较全面地呈现郭沫若的精神和学术世界”,“仗着自己年轻,将《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共8卷)和《郭沫若全集·考古编》(共10卷)一字一字啃下来了,也读了不少他的同时代人的相关研究,以及学界有关他的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著述”(《写作与出版》),用于阅读郭沫若作品的时间多了,无疑会占用阅读郭沫若研究成果的时间;其次,时间紧迫:“中国作家协会于2012年初作出决定,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文学界和文化界的精兵强将,创作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出版说明》),作者2014年才在曾任郭沫若纪念馆副馆长的李晓虹带领下写作《郭沫若传》的申报书。在郭沫若本人作品如此众多且有的还很难、时间如此紧迫、郭沫若大部分研究资料又未进行系统收集整理的情况下,无法较全面地阅读郭沫若研究资料是很正常的。在方便引用的时候,李斌还是愿意引用的:《女神之光》便在第267、284、285、385页引用了杨胜宽、蔡震担任总主编的14卷本《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1920-2008)》收录的相关文献。
作者在写作这部传记时为自己确定了一个“首要任务”:“希望阅读过它的读者,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于郭沫若形成一些基本的共识。”由于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很难,作者的这一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很难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作者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并注意平衡各方面内容之间的关系,以下目的应该已经达到:“我这本传记有意平衡作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的郭沫若和作为古文字学、历史学专家的郭沫若之间的叙述比例,以弥补以前的郭沫若传记或偏于文学,或偏于史学的不足,比较全面地呈现郭沫若的精神和学术世界。”(《写作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