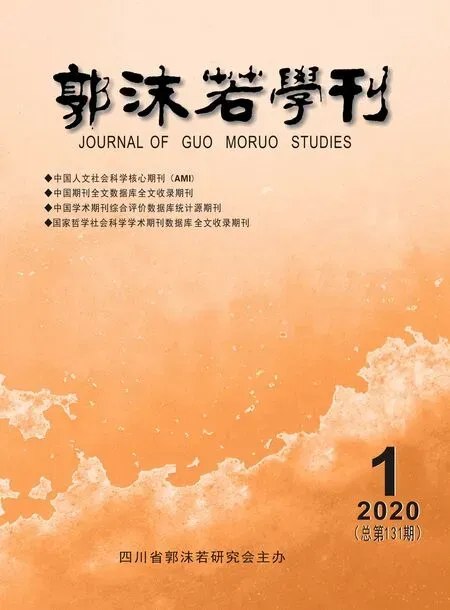《郭沫若年谱》订补二则
2020-11-18李红薇
李红薇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9)
一
龚济民、方仁念编著《郭沫若年谱》①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增订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1930年4月23日:
作《“矢令簋”考释》,并附《追记》。考定此为“周初之器”,其制作年代“必在成王之世”。收《文集》十四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
5月:
发表《明保之又一证》,以“新出一卣”复证明保确系“周公之子”。……收《文集》十四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②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增订版)增“现收《全集》历史编一卷”。
王继权、童炜钢编著《郭沫若年谱》③王继权,童炜钢编:《郭沫若年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1930年4月23日:
作《“矢令簋”考释》,并作《追记》。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又收《沫若文集》第14卷。
5月:
发表《明保之又一证》……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上海图书馆编《郭沫若著译系年》④王训昭等编:《郭沫若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矢令簋考释 附追记(论文)”注:
1930年4月23日补志;初收1930年5月20日上海联合书店三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再版书后》;又收《沫若文集》第14卷。
“明保之又一证(论著)”注:
初收1930年5月20日上海联合书店三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再版书后》;又收《沫若文集》。
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①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930年4月23日:
作《“矢令簋”考释》《追记》,考释成王时一尊一卣。
两种《年谱》《郭沫若著译系年》及《年谱长编》均将《“夨令簋”考释》②多误成“矢令簋”。的写作日期定于1930年4月23日,即《“夨令簋”考释》文末“追记”部分的“补志”时间。《明保之又一证》归入是年5月,是由于该文未注明写作时间,即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三版的出版月份为准。
蔡震先生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夨令簋考释》《明保之又一证》等6篇文章,“著者于第6篇《夏禹的问题》文末署‘1930年二月七日补志’。这个日期当然应该是全部6篇补遗文章最终完稿的时间。”③蔡震:《〈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写作与出版》,收入《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也就是说,蔡先生认为《夨令簋考释》《明保之又一证》皆作于1930年2月7日之前。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看法都是有问题的。
《夨令簋考释》开篇即言:
与《夨彝》同出之《令簋》,近蒙容君希白以拓墨见示,与《令彝》确系一人之器,并饶有相互发明之处。
《明保之又一证》言:
《令彝》之“周公子明保”,余以为乃周公之子名明保。近新出一卣,复得一证。其铭云:“隹明保殷成周年,公锡作册鬯贝,扬公休,用作父乙宝尊彝。□”
由上可知,《夨令簋考释》的写作,缘于容庚(字希白)寄赠的《令簋》(即夨令簋)铭文拓本,《明保之又一证》亦由于见到一件铸有“隹明保殷成周年”的卣。也就是说,两篇文章的写作一定晚于郭沫若见到二器拓本之后。《郭沫若致容庚书简》1930年2月16日记:
如南宫中鼎……,其文例为“隹+subject+predicate+年”此之“隹明保殷成周年”,正当以明保为名词主格,殷为动词,成周为宾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三版的《三版书后》有一则“按语”,“这本是《再版书后》,因寄回国时没有赶及,只好改成《三版书后》了。”“按语”写于“四月十日”。《夨令簋考释》《明保之又一证》等6篇文章,本作为《再版书后》,后收入联合三版,故这6篇的写作时间不会晚于4月10日。④蔡震:《〈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写作与出版》,收入《郭沫若着译作品版本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
揆诸上述细节,《夨令簋考释》《明保之又一证》的写作时间当在1930年2月9日之后,且不晚于4月10日,其中《夨令簋考释》追记部分标明“1930年4月23日补志”自当与正文非同时所作,应是“再版书后”改为“三版书后”时另加。
二
王继权、童炜钢编著的《郭沫若年谱》1947年“初秋”记有为郭墨林题跋事:
文中所谓“郭若愚未刊稿”,已于1990年正式发表于《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五期,该文首次公布了郭沫若为樊季氏孙中鼎所作题跋的手稿照片。②郭若愚:《郭沫若佚文〈樊季氏鼎〉跋小记》,《上海博物館集刊》(第5期),1990年,第103-107页。《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六卷《金文丛考补录》亦收录了这篇题跋。③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六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6页。此事龚济民、方仁念编撰《郭沫若年谱》,上海图书馆编《郭沫若著译系年》,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皆失载。
郭若愚在《郭沫若佚文〈樊季氏鼎〉跋小记》一文中对郭沫若《樊季氏鼎跋》的手稿作了释文,落款时间记作“民纪卅六年初秋”,即1947年。文章开头云:
一九四六年至四七年,郭沫若先生旅居沪上,他写了《诅楚文考释》《行气铭释文》等研究古文字的文章,已为郭老学术思想研究者所注意。就我所知,他还写过《樊季氏鼎跋》,文字不多,但对于研究樊季氏鼎及樊国地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可以看出,郭若愚认定该文乃1946-1947年郭沫若旅居上海时所作。值得注意的是,郭若愚漏引了跋文末“墨林先生嘱题”六字,却称“我曾手拓全形墨本,郭沫若先生跋云……”,全文对“墨林”只字未提,这很容易让读者误以为此跋是为郭若愚所作。《郭沫若全集·考古编》收录这篇题跋时,亦脱“墨林先生嘱题”一行,落款时间也作“民纪卅六年初秋”。
细审题跋手迹,笔者认为所谓的“民纪卅六年”,实应作“民纪廿六年”,即1937年。
跋文中“墨林”即郭墨林(1906-1986),嘉兴人,回族,抗日战争前,子承父业,随父经营“听涛山房”古玩店,④葛壮主编:《长三角都市流动穆斯林与伊斯兰教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196页。曾收藏过甲骨,⑤严一萍:《甲骨学》(上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8 年,第 230 页。对文物颇有研究。1986年任上海文史馆馆员,擅长文物鉴定。曾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⑥嘉兴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兴市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第2259页。郑国贤:《历代嘉兴书画名人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4页。不少史料均记载了郭沫若曾为郭墨林收藏的《樊季氏铜鼎拓文》题跋注释的经过。⑦苏菲:《郭老与回民的一段情》,收入《成都少数民族》编委会编:《成都文史资料第三十辑:成都少数民族》,1997年。中华文化通志委员会编:《中华文化通志第3典民族文化:回族文化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史》(修订本),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
郭沫若为郭墨林题跋的具体时间,《中国回族文献库》“郭墨林”条称:
民国二十六年,郭沫若在沪时曾为他所藏的《樊季氏铜鼎拓文》题词注释。⑧参中国回族文献库http://www.huizu360.com/huizu/news_view.asp?tid=16&id=1554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网站“郭墨林自传”,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郭沫若曾为其藏战国时代铜鼎拓片题字注释。1937年7月29日,郭沫若自日本归国抵沪后的第三天,墨林携《樊季氏孙中鼎》拓片去沧州饭店请教,郭沫若题字如下:“此鼎有铭盖文,凡廿一字,曰:‘佳⑨“佳”当为“隹”的误字。正月初吉乙亥,樊季氏孙屯中鼎鼎共告金,自乍石池’。古鼎铭有自名石池者,如大师锤,伯侯鼎即其例。其石字稍沮力但固无可疑也。文尚未着①“着”当为“著”。录,而盖纹取制与寿春楚器颇相似,时代当属于战国。樊季氏如细考之,或当有得。墨林先生嘱题。民国廿六年初秋,郭沫若”。数十年来,墨林将其收藏身边,1990年,其次子良能与北京郭沫若故居纪念馆联系,同年9月,该馆馆长,郭沫若之女郭平英信称:“能在《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的《金文丛考》卷发稿前增补这一遗散题跋,可谓意外收获”。②参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网站http://www.shwsg.net/d/96/78.html
郭沫若归国日期,见诸当时报刊,如《申报周刊》“时事一周”辟有专栏报导“郭沫若返国”一事:“于七月二十五日自神户乘日本皇后号轮返国,于二十七日下午安抵上海”。③参《申报周刊》1937年第2卷第31期。“1937年7月29日”确为“郭沫若自日本归国抵沪后的第三天”。王继权、童炜钢编著《郭沫若年谱》1937年7月27日记“下午,船抵上海……到达上海后,由党组织给他安排了住所,暂住沧州饭店”,龚济民、方仁念编《郭沫若年谱》则记1937年7月27日“下午,抵达上海。……然后由郁达夫作东,在来喜饭店设宴洗尘,直到深夜。”1937年7月28日“搬至沧州饭店。”两种记载虽略有差异,但至少可以肯定,7月29日郭沫若已下榻沧州饭店了。另郭成美在《回族学者金祖同》一文中称“1937年7月底金祖同带两个妹妹德娟、淑娟和侄女金颐拜见郭氏。……祖同还带回族表兄郭墨林携一古鼎访郭氏。”④郭成美:《回族学者金祖同》,《回族研究》,2008年第2期,第138-144页。郭成美《国学大师致回族学者金祖同之书函、为其著作序文》亦有类似说法,“1937年秋祖同还带回族表兄郭墨林携‘樊季氏孙中口鼎’拓片拜访郭老,郭老题字如下:‘此鼎有铭盖文……民纪廿六年初秋,郭沫若’。”⑤郭成美:《国学大师致回族学者金祖同之书函、为其著作序文》,《甘肃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第22-29页。
揆诸上述史料,可以肯定:樊季氏鼎拓本的主人是郭墨林,郭沫若为之题跋时间当是“民纪廿六年初秋”。是年郭若愚仅16岁,而据文献记载,郭若愚与郭沫若相识当始于1947年6月,⑥郭伟亭编著:《文博专家郭若愚》,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第14页。故可肯定此事与郭若愚无关。
王继权、童炜钢编著《郭沫若年谱》对此事记载有误,应将郭沫若“为郭墨林所藏樊季氏孙中鼎题辞”这一事件移至1937年。龚济民、方仁念所著《郭沫若年谱》《郭沫若著译系年》《郭沫若年谱长编》等也应补收此事。《郭沫若佚文〈樊季氏鼎〉跋小记》误夺“墨林先生嘱题”,将题跋时间错识为“民纪卅六年初秋”。《郭沫若全集·考古编》因袭了这一错误。为体现题跋原貌,释文当补入“墨林先生嘱题”一行,且落款时间应订正为“民纪廿六年初秋”。《郭沫若全集》若有机会再版,应修订这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