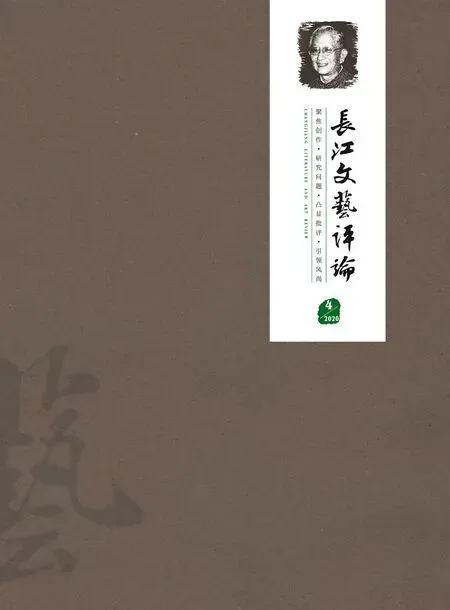在日常生活里创造诗性空间
——余述平诗歌印象
2020-11-17◆熊均
◆熊 均
一
在中国,孟子最早发现了诗歌文本的不可靠性,于是提出了“知人论世”的口号,对诗歌的解读,从董仲舒开始有“诗无达诂”之说。然而,要了解一个陌生的诗人,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甚至是相识多年的熟人,我们也并不一定真正了解对方。因此,后人又发现“知人论世”免不了“心画心声总失真”的危险。总而言之,对诗歌的解读是难的。从根本上来说,读者的阅读和解读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误读。因此,对于诗歌,我一向只读不解。所以,下面的文字并非是系统的研究和专业的评论,仅仅是我个人在阅读余述平诗歌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和感悟。
在我看来,余述平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个时代的生活节奏形成了一定的偏离。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生活对“慢”或者说“轻”的诗意快要消解殆尽的当下,他决定用笔来记录自己的某些感悟和时代的某些情绪;在物质世界不断挤压精神空间的今天,他给自己营造了一方小小的天地,安放他源源不断的诗思和感悟。在这里,他在现实生活的奇观化和魔幻化的映射下,用轻巧的笔触,记录下了一个永恒的、慢的诗性空间。
余述平笔下的诗歌,已经不再是《尚书·尧典》“诗言志”传统上的一朵花了,也不是屈原意义上的“发愤抒情”,而是一种日常生活化的情绪和思索,不再受“载道”“明志”的束缚,成为了供他自己消遣的“玩意儿”。因此,日常生活的一切,在他这里都可以入诗,成为他的喃喃自语。这一点,以他成百上千首的“翠柳街”系列诗和“自言自语”系列诗最为典型:泥土、树叶、嘈杂的声音、过往的路人、变换的四季、此起彼伏的言谈、飘浮不定的云彩、一只流浪狗……都在他笔下穿上了“诗”的外衣。
众所周知,古人有“诗言志”的口号,也有“诗缘情”的传统。而且纵观古往今来的很多文学作品,的确绝大部分难逃这“言志”或“抒情”的藩篱。但是也有例外,比如玄言诗、哲理诗,喜好以诗谈玄,在诗中讨论玄妙的哲思。言志、抒情、思辨的诗歌常常占据历朝综合诗歌选本的绝大半江山,它们三峰并峙,几乎没有留下太多的空间给其他类型的诗歌。因此,诸如宫体诗、应制诗等往往是在一些专辑别录中保留,当然,这跟它们本身不太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也紧密相关——不可能得到广泛认可及流传。至于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琐事的诗歌,除了禅宗打机锋一类的偈语,似乎就更不值一提了。“小我”及“小确幸”或“小缺憾”被认为是可以忽略的、不重要的东西。我们的文化历来讲究先国后家,先集体再个人,除非个体经验和感受能被上升为一种普遍性的经验和情感,超拔于个人的牢笼之时,它才被认为是有价值和值得被关注的。因此,我们的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缺乏“个体”和具体个人生命经验的文学史,是抽象的“我们”的文学史。
但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逐渐意识到这种“个我”的缺失,也是一种极大的遗憾。因此,很多作家出于对自我或他人的独特生命经验的感悟,开始去描绘、刻画一大群神态各异的个体,也更加愿意书写出带有个人性的独特体验和感悟——由于小说需要刻画情节、形象,篇幅较长,因此还尚为不易——所以,用诗歌来呈现“我”生命、日常中的点滴情感和诸多情绪,更加“可能”。余述平便是这样一位用诗歌来记录他个人日常生活的感悟和情绪的能手。他的诗没有沉重或高昂的“志”,也没有绮靡或泛滥的“情”,他把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细琐感悟都绵密地织进了他诗思的江流当中,源源不断、不绝如缕——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几乎每天都能写出近十首诗歌。据他自己的统计,自他2016年重新开始写诗以来,截至目前已创作了六千余首诗歌,几乎每天从不间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诗歌源于生活,生活不止,他写作的灵感就不会枯竭。他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创作:在大街上,在高铁上,在商场里,在饭店中,在开会的间隙……写诗既是他对生活的表现和记录,更是他的生活。他的生活和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现代生活节奏很快”已是老生常谈,但也的确是这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给了我们一个需要去认真解读余述平诗歌的路径。如何在这快节奏的时代保持一颗向“慢”的心以及细致的诗思,是每个创作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余述平的诗歌都来源于生活的激发,但又与生活绝不相同,这是由于经过了诗人之笔的雕琢、渲染、升华、改造。以他的《旧事物》组诗为例,整组诗都以老、旧的事物为意象,诗人从“今天”对“昨日”的事物投去审视的目光,在诗人的审视中,旧事物重现了往昔片段的历史,也呈现出它们各自独一无二的特征。在诗人的审视中,昨日与今天相联,而这联结又不是事实上的连接,而是在诗人思维上的碰撞。不可重现的昨日之光,借助诗人的诗句得以重见天日,但它们的面貌却难以称得上“真实”或者说“真相”。旧事物不过是借了诗人的意识活动,作为诗人印象的投射而已。而对于我们(读者)来说,虽无缘于真实或真相,但亦能借诗人的营造,去感受旧事物的某些片段,如旧爱情之不可得,老照片之朦胧美,旧抽屉之执着,古莲子之坚韧……这一切感受的产生和获得,既与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同样也离不开诗人的提醒,他将生活之旧物,生活之点滴凝练成诗句,凝结成光,点醒了在混浊中昏沉的人,让这些昏沉的灵魂为之一瞥,也许,就会发现更多的光,就像《古莲子》浴火重生一般:
把苦汁和甜水都挤干了
你才发现你命硬了
硬得让别人即使咬牙切齿,也崩溃
你已顽固不化
或者像石头立地成佛
其实你依然心软
只要那些泥水的亲人来了
你即使过了一万年
你还是会打出一把绿伞
余述平的很多诗歌,都来自于对生活现象的仔细观察和敏锐感悟。而对生活现象的仔细观察和敏锐感悟,离不开一颗诗心。只有拥有一颗诗心的人,才愿意在眼花缭乱的大千世界里,安静且缓慢地立在那儿,去审视生活、时间、事物乃至于自身。余述平,应该是这类人当中的一个。他在《平手》中,看见了生活的别样奥秘:
生活,就像不幸买了一支股票
从交易开始到交易结束
总是涨一分跌一分
白白忙乎了一天,还是一个开盘价
就像织布机
上一下,下一下
热闹非凡
但它织出来的
只是一块布
多么宽广也只是一块布
再花花绿绿也只是一块布
生活不是一块布
而是衣服
诗人通过股票的涨跌、织布机织布的形象事例,来论证生活与它们之间的不同:生活不是简单的1+1=2,也不是2-1=1。生活在这些加减乘除中,丰富了自己,也沉淀了生活在其中的人。生活的得失,不以成败论英雄。而生活的成败,就像衣服一样,不一定最华美、最艳丽、最富贵的就是最好的,唯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在所有人都忙于积累财富、获取财富、投机取巧的时候,他们也许忘记了升职、加薪、买大房子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当然,诗人也并未告诉我们最终目的是什么,毕竟,每个人的追求都不尽相同,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好的归宿。
二
按照世俗的标准来看,余述平应该算是一个成功的人了:生活稳定,事业有成。他完全可以在日常生活的确幸和平淡中,躺在一把藤椅或沙发上摇晃度日。但他没有,他一直在这波澜不惊的稳定生活中,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他写小说,先后发表过十余篇中短篇小说,出版过两部小说集;写剧本——这可能还跟工作稍微搭一点边,毕竟他还身兼湖北省电影家协会主席这一职务,剧本也曾多次获奖;他还写诗歌,而且大量地写诗歌——他有很多诗歌在《红豆》《星星》《新诗别裁》《中国作家》《西湖》《飞天》《草堂》等刊物上发表,多次被《诗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转载,还有诗歌入选了《湖北省百年新诗选》。
写诗于他而言,不是为“别有幽愁暗恨生”而作,纯粹是出于一种热爱——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我写诗并不是为了发表和稿酬,如果是为了稿费,那我还不如写小说。”的确,作为一个已然有着成熟的小说创作经验的作家而言,转型并非易事。但也正是他的小说和剧本创作经验,为他的诗歌写作提供了一种别样的风格支撑。他的诗歌具有较强的个人风格,主要表现为:意象丰富、故事性强、极具画面感。这三者不是各自分散于他的某一首诗歌中,而常常统一于他的诗歌创作里,难以割裂开来进行分析。以他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白日梦》为例:
宇宙内外全是雪片
向日葵们撒下的碎片
大海举起的沙子
我已被空置
眼睛游离出了身体
他们像宇宙飞船
在自我焚烧
短短的7行诗中,出现了宇宙、雪片、向日葵、碎片、大海、沙子、眼睛、宇宙飞船等诸多意象,这些意象来自于宇宙、大海,囊括了无限渺远的时间和空间,我们不用去揣测诗人为何如此营设,因为他早已在题目《白日梦》中给予了回答。诗人,不仅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更是生活在白日梦中的人,他在梦中被酒神狄奥尼索斯赋予灵感,让他一窥上帝和天界的奥秘和神奇,从而创造出普通人难以想象的事件,让生活在凡俗中的人们诧异、惊奇。在白日梦中,幻想得以实现,奇幻得以呈现,虚假与真实被模糊了边界,一时间“不知蝴蝶之为周,周之为蝴蝶也”。而这所有的意象既富有色彩,又充满画面感,仿佛是一个极其壮观的影视片段。再来看他的短诗《救命》:
一个人报警
他喊救命
结果警察来了
救护车来了
人民群众也来了
他呢
却失踪了
他在笑
他给上帝搭了一个能下的梯子
他很能干
他做的
但面对面校访、家访,其作用是网络、电话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所不能替代的。教师只有亲自接触家长,看到学生生活的家庭环境,才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学生的情况,家长只有亲自到学校才能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孩子成长的环境和学习情况。
是把风往天上赶
这首诗仿佛一篇微型悬疑小说,讲述了一个报警求救的人,等警察、救护车和人群都到来的时候,作为主角的“他”却离奇地“失踪”了。他到底是失踪了,还是不在了?诗人没有告诉我们。紧接着,诗人又说“他在笑”,但我们却不知道他在哪里笑,以及他为什么笑。直到诗人告诉我们,“他给上帝搭了一个能下的梯子”,这个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已经不在人间,他已经在为上帝服务了。最后,诗人告诉我们,“他很能干”,他在“把风往天上赶”。但至于“他”为什么要把风往天上赶,赶的是什么风,把这个风赶上去有什么意义?诗人都没有说,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我不清楚这首诗是否也同样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事件,但其中的确有着许多似曾相识的情节和要素让人思索。
余述平十分擅长在诗歌中营造一个个极具电影镜头般的画面,这营造画面的功力,应该与他剧本创作和电影拍摄经历颇有关联。当然,一个成熟的诗人,总会有着属于他自己的意象群、词汇库、凿句谋篇的独特痕迹,我们刚才简要分析了余述平诗歌的一些特点,这些具有标识性的个人特质,赋予了余述平的诗歌属于他自己的独特风格。而这种独特的个人风格,也预示着他在诗歌创作的路上,已经走向成熟了。
三
但在成熟的同时,可能也还有一些小缺憾。我们在前文提到,从世俗的标准来看,余述平是成功的,他有着成功的事业,有不俗的创作成绩;不用为工作烦恼,也不为衣食发愁。因此,他可能会较难意识到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切肤之痛存在。因此,他的诗歌读起来是轻松的、闲适的,不会带给你苦恼、怨憎和负担。比如,前段时间他在朋友圈一连发了好几首短诗,《灯》《寄生虫》(似乎是在吐槽当下人们赠书的现象和尴尬)《救命》《自言自语》(似乎又是在调侃别人对他诗歌的评价)《动力》《野心》《情怀》《真相》《命运》《人生》《死亡》《玫瑰也有疼的时候》《我确信,我可以靠风养活自己》等等,多达13首,这些诗无一例外都是借日常生活事件来凸显他的感悟,乃至寄寓某种戏谑抑或反讽。它们的优点,如上所述:轻松、机智、幽默、闲适,是采撷了日常生活这个万花筒中的一片,同时也是对日常生活的锦上添花。但这同时也可能给他的创作带来另一方面的缺憾:不够震撼和深刻。
智者言,生活的苦难(磨炼)是一笔可贵的财富。苦难,虽然是人人唯恐被其选中的恶煞,但对于艺术家来说,也许切身、深刻的苦难,会帮助他深入到创作的另一个维度,穿透另一堵墙,抵达另一个空间。惟其如此,他才更有可能创作出从芸芸众作中凸显出来、熠熠生辉的作品。正如司马迁历数先贤创作的经历那般: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无不源于生活的困厄和苦难。
当然,并不是要妄论余述平意识不到社会的黑暗或者不公平。他的诗歌《棋子》,就仿佛是一个寓言或者讽刺社会不平的故事:
棋子每一步都是按规矩走的
但有的幸存了
但有的牺牲了
由此可见
规矩不重要
重要的
是如何玩弄这些规矩
这首诗似乎隐喻着某些人,某些制度,某些场合,某些关系,某些事件……在隐喻之余,诗人隐约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棋子每一步都是按规矩走的”,就仿佛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普通人,都是按照规章制度、道德法律行事的,“但有的幸存了,有的牺牲了”,同样是按规矩在走,却有成功有失败。诗人由此得出结论“规矩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玩弄这些规矩”。这不正是当下某些乱象丛生的原因所在吗?老老实实的人到最后成了垫脚石和铺路者,而会玩弄规矩的人却飞黄腾达,呼风唤雨。比如《暴裂无声》,按规矩走的保民、磊子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像羊一样;而能玩弄规矩的昌万年和徐文杰却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多金有势。对那些玩弄手段的人,余述平的讽刺和不屑,在诗中一眼即见。在《麋鹿》中,他同样表达了自己对于某种现象的不满:
麋鹿个子不小
但它们见到了生人就很害怕
它一直就在荆州石首的沼泽地里
躲躲藏藏
它现在人多势众,变成了广大的人民群众
也依然在躲躲闪闪
它们偶尔流窜到过岳阳洞庭湖
那是因为长江的洪水
究竟是因为什么
它们恐惧和人做朋友
你有那么健壮的体格
为什么对我们,不能保有一个动物的傲慢
虽然并不清楚他所写的“麋鹿”有何深意,但却很容易在诗句中读出他对于怯懦、平凡和恐惧的拒绝和排斥。对于健壮而躲闪的麋鹿,他有恨铁不成钢的叹息甚至是批评,而这恰恰是他骄傲与自信的体现。但在自信和对“麋鹿”失望的同时,却少了一分《棋子》那般一针见血的批判:健壮的麋鹿本不用害怕、躲闪、恐惧、流窜。可为什么它们会害怕,会躲闪,会恐惧,会流窜?这也许是更值得被诘问的关键。
如今,的确是一个艺术自由的时代,文学艺术被卸下了许多沉重的包袱,甚至被鼓励成为娱乐的方式之一,成为娱乐的载体。而面对一首诗、一篇文章或者一个其他什么作品,在阅读或者说观看完它之后,无论它的语感、观感如何,我都会禁不住去追问:“作者为何要写/画/拍下它?”我想起刘勰《文心雕龙·序志》“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哪怕时隔千年之久,读来仍是令人动容的。纵观那些能够打动人心的作品,无不有着深刻的关怀所在——无论是现实关怀还是终极关怀。惟其如此,它们方能像黑夜中闪烁着的灯塔,为艺术和文明的发展,为困厄中挣扎着的不幸的人们,指出一条条可以通往救赎、深刻、高尚乃至不朽的道路。
余述平用他的诗歌努力地弥合着如今人们身体与灵魂之间渐行渐远的距离,试图在这个灵光消失的时代,为自己,也为旁人搭建一个诗意的小小天堂,他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但我们仍然期待着他能更进一步,进一步用他勤奋的诗笔,去探索一个更加艰难,更加高远,更加深邃的世界和空间,去那里发现尚未被其他人开发的领域,在那里镌刻下属于他的名字。
另外,T.S.艾略特在《批评的功能》中说:“一个作家在创作中的一大部分劳动可能是批评活动;是筛虑,组合,构建,抹擦,校正,检验。”瓦雷里在《诗学第一课》里也说:“一部作品是长久用心的成果,它包含了大量的尝试、反复、删减和选择。”因为余述平的诗歌数量太多,内容也过于庞杂,所以不可避免会存在着某些意境、技巧乃至内容相似的作品,在集结成册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些修改和选择,以使作品更加精炼、独特。我们期待他笔下的一花一树、一人一事最后能相互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它们各在其位又互相契合,共同创造出一个属于余述平诗歌的“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