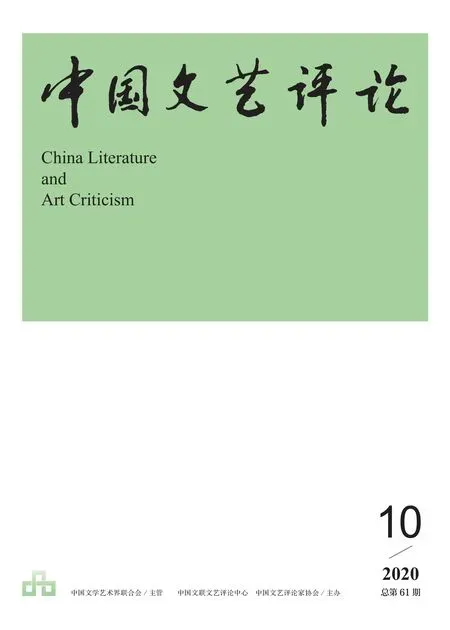中国早期类型电影的创新探索及启示:以武侠神怪电影为例
2020-11-17赵春晓
赵春晓
王德威在谈到晚清小说的“谑仿”问题时说,相较于写实,“谑仿”在形式及观念上都形成了一个论述的自由区域,“一旦文学对生命的铭刻‘再现’转化为修辞的演出,或仅是形式想象的展示而非逻辑推演的结果,那么随之而来的自由就使文学创作者充满了创新自觉,不管这些创新有多少令人发窘的结果”。[1]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4页。这句话在中国早期类型电影的创新中同样适用。在20世纪20年代众多电影类型中,武侠神怪电影以奇观化的身体展呈与视觉体验,突破了观众对于“真实”的认知,从而使一种以通俗文化的审美惯习为支撑、以通俗文化资源文本为基础、以民族文化理想为潜在结构的民族文化创新,将类型电影的民族文化想象推至巅峰。直至今日,这种对传统通俗文化资源的想象性改编,以及基于传统文化的通俗化表达策略,仍被当下电影人所延用,给当代电影类型化发展带来许多启发。
一、回应民族表达冲动的努力
1920年代的古装、武侠、神怪电影类型创作,有着完整性与独立性兼具的标本意义。从精英文化的立场来看,这一阶段的类型风潮或被诟病为“封建小市民文艺”,比如茅盾批评“武侠小说和影片是纯粹的封建思想的文艺”[2]茅盾:《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第3号,转引自芮和师、范伯群、郑学弢等编:《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774页。,至于那些神怪片“还说什么改良风俗破除迷信,那简直是败坏良好的风俗,促进人们的迷信”[1]文殊:《中国电影漫谈》,《白幔》1931年第6期。。但在通俗文化的立场看,它仍反映了市民观众的所思、所想、所爱,它所蕴含的复杂文化内涵,远非封建思想可以概括。
通俗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中贴近大众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改造大众审美惯习的文化,自有其文化逻辑并已成为世俗化的游戏、疏解压抑的方式,并具有与民族性格相关的文化载体与表达形态。相对于此一时期不稳定的商业资本市场,包括民间传说、稗史弹词、演义小说、神话故事、戏曲等在内的、与市民喜好惯习密切相关的通俗文化资源,以其在审美接受层面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为国产电影实现商业竞争提供了文化来源和表达支撑。1912年至1926年,上海近代工业发展迅速,民族工业在与外资工业的对峙中获得较快增长,但民族资本并未逃脱帝国主义列强经济以及本土封建经济的双重压迫,无法真正实现对电影业的巨额投入。“欧美制片、其工程大者一片动辄费数十百万元、而中国影戏公司、资本至百十万者固绝无仅有、数十万者亦寥若晨星”[2]春愁:《中国电影事业之前途》,见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第700页。,反而是一些闲散的社会游资以及大量小股资金的注入,给当时的民族电影产业带来了异常喧闹的竞争图景。在1927年逐渐回落的公司热潮中,持续五年之久的商业类型片竞争格局渐次打开,中国电影市场迎来了本土第一波商业类型电影。市场虽在大小电影公司的激活中不断膨胀,但喧哗的背后忧患重重,牟利与投机商业心态的掺杂给电影工业持续良性发展埋下了巨大的市场隐忧。
欧美电影的强势姿态及其中对中国人形象的歪曲塑造,将民族类型表达的需要推至时代舞台的前景。“西人摄中国剧。其辱华人者。已令人目眦欲裂。”[3]瓠犀:《纪空前古装片〈美人计〉》(一),《申报》1926年10月31日。英美烟草公司“影片部”在五卅运动之后仍拍摄辱华意味的中国滑稽喜剧,如《慢慢的跑》《名利两难》,将中国人描写得不堪入目。美国电影大行其道,占据着上海电影院的半壁江山,即便抛开那些激起民族认同焦虑的丑化华人形象的作品不谈,《罗宫秘史》《乱世孤雏》《党同伐异》《海上英雄》《斩龙遇仙记》《三剑客》《宾汉》等历史题材作品在中国市场的成功,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着中国电影人。
1925年末,呼应前一段时间的“整理国故运动”[4]1919年1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名为《新思潮的意义》的文章,首倡“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提出要通过重新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研究,促进中国现代文明的建设。,报刊上开始陆续出现关于“历史影片”的讨论,与之呼应的还有郑正秋、周剑云、汪煦昌等人发表的关于国产电影前途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电影现状的焦虑。中国电影如何实现主体性表达、如何振奋民族精神、如何对内提升影戏事业、对外塑造国际形象,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促使电影人纷纷将目光投向中国自己的通俗文化资源,希冀从中获得新的民族表达可能。《中国电影年鉴》刊载的《天一公司十年经历史》这样描写道:“那时中国新文坛上正在提倡民间文学,邵先生也以为民间文学是中国真正的平民文艺,那些记载在史册上的大文章,都是御用学者对当时朝廷的一些歌功颂德之词,真正能代表平民说话,能呐喊出平民心底的血和泪来的,惟一只有这些生长在民间流传在民间的通俗故事。天一同人根据这一点,便采取了不少民间故事改编电影,这一年里完成了《梁山伯祝英台》《唐伯虎》等八部片子,比第一年度的产量加了一倍。”[1]《天一公司十年经历史》,见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电影年鉴》,南京:正中书局,1934年。天一公司在初期的创作中,的确有严肃的艺术态度,《梁祝痛史》《孟姜女》《珍珠塔》都取得了不错的艺术反响。从这段彰显初心的话中,也可看到邵醉翁等电影人从文化层面对于电影转型的现实需求作出的回应和努力。
通俗文化与市场的特殊关系,又决定了传统通俗文化资源在为电影所用的同时,也必然不断深化电影作为大众通俗文化的特质。郁达夫说,“电影成立的最大根据,就是要通俗,要Popular。因为太高深了,太艺术化了,恐怕曲高和寡,销不出去。所以从Commercial point of view 讲起来,愈通俗越好,愈能照一定的形式做出来愈好。”但他并不赞同刻板化的通俗化,因为过度依赖类型成功的模板必然丧失个性尤其是民族个性,“哪里还可以讲得上创造,讲得上艺术呢?”[2]郁达夫:《如何的救度中国的电影》,《银星》1927年第13期,转引自丁亚平主编:《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1897-2001)》(上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18-19页。在类型的系统中,缺乏艺术的良好氛围、健全的法制以及规范的产业环境、市场环境的情况下,通俗文化很容易从民族表达的迫切冲动滑向流俗、媚俗,这一点在民族商业类型兴衰往复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在那些受商业意图限制的类型化创作中,又无法完全摆脱中国观众文化基因中的世俗观念,比如武侠电影中超凡入神而又有着世俗神秘色的“神”延伸着大众对于世俗生活的理想,绝不同于西方“三位一体”的“神”的超越性内涵。因此,民族化表达的迫切与民族化表达的困窘总是相伴相随,尽管它们充斥着猎奇、艳情、夸张、臆想、非驴非马、不土不洋等不合时宜的现象,却不可否认地担当了20世纪20年代对抗外片保全市场、矫正欧化发扬传统的任务,在民族主义立场上传承与延续着中国电影民族化的文化要求与想象空间。
二、通俗文化资源的转化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矛盾复杂丛生,激烈的政治斗争不断,民国虽成立,却并非人们所期待的“理想国”。满清政权解体,“王权旁落诸侯家”,随之而来的是军阀长年混战、苛捐重税、匪乱天灾。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共双方达成合作,征讨军阀,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给人民带来希望的曙光。但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使战争阴影再次降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民众对战争深恶痛绝,对公平正义的新世界心怀希望,现实世界的矛盾、压抑和无奈,更让他们渴望一处实现精神快慰的世外桃源。匈牙利学者阿诺德·豪泽尔认为:“通俗艺术的目的是安抚,是使人们从痛苦之中解脱出来而获得自我满足。”[1][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233页。其在游戏性之上“提供了逃避现实的方法,这种逃避不是往返某个地方的逃避,而是乌托邦式的自我精神逃避”[2][美] 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13页。。武侠神怪电影在当时正担当了这一功能。
从1921年平襟亚主编的《武侠世界》月刊创刊、1922年包天笑主编的《星期》周刊开办“武侠号”开始,近代报刊为武侠小说提供了集体狂欢的大众舆论空间,将这一通俗文化艺术推向公共空间,大放异彩,“武侠小说风起云涌,几乎占了小说出版数量的大部分”[3]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料》,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312页。。向恺然(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江湖大侠传》《江湖异人传》,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奇侠精忠传续集》《大侠殷一官轶事》,开言情武侠小说之端的顾明道的《荒江女侠》,被视为“冠绝武林”文坛巨制的李寿民(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一同掀起了近代武侠小说的第一个浪潮。“日常生活的‘亚空间’,包括大众媒体空间等,总存在着逃避控制或与控制机制协谈和争斗的趋向”[4]孙绍谊:《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将现实问题改头换面,再以大众(弱者)的立场营造想象世界的“真实感”,以此获得大众青睐与信任,从而使观众的民族想象、现实期待在想象中得到完整的释放。换言之,通俗文化是以观众心理为中心构建的一个理想世界,这一现实和想象的转换机制在文学和在电影中的运作十分相似。武侠热进入电影领域后,使古装电影尤其是武侠片以及其后的武侠神怪片成为寄予民族文化理想的又一镜像和载体。以演员的服装、布景摆设等跳脱时空的假定性,给观众营造出向市民开放的、可塑造的话语空间以及认同方式。
相较于以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母题为基本内容的古装历史题材影片,武侠类型因为江湖这一与家国有着明显同构性的虚构空间的存在,而在民族想象层面上走得更远,武侠神怪片更是将传统文化系统中的“奇幻”因素利用到极致。明星公司拍摄的《火烧红莲寺》是中国神怪传奇武侠电影开宗立派之作,1928年5月13日在上海中央大戏院首映后迅速引起轰动,“每集开映时,到处都是万人空巷”,“各戏院开映此片时,都能突破以前最佳的卖座纪录”,可谓“誉满东方,人人欢迎”。[5]蕙陶:《〈火烧红莲寺〉人人欢迎的几种原因》,《新银星》1929年第1卷第11期。而电影所改编的正是当时武侠小说南派代表平江不肖生连载六年洋洋洒洒一百三十四回的《江湖奇侠传》。该小说在《红杂志》连载之初,世界书局便在《申报》做广告,称作者平江不肖生就是“身怀绝技的剑侠”,小说中的那些“剑仙侠客,都是他的师友”,“神怪的事实,都是他亲身经历的”“实情实事”。[1]参见汤哲声:《中国现代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学三十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9页。以虚构取胜的小说之所以不断以“真实”二字予以强调,正是存在于幻象之中的通俗文化想象奥秘。对于《火烧红莲寺》的成功,连茅盾都评论说,在那些痴迷的观众眼中,电影艺术本身已不再重要,于他们,“影戏不复是‘戏’,而是真实!如果说国产影片而有对于广告的群众感情起作用的,那就得首推《火烧红莲寺》了”。[2]茅盾:《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第3号。米歇尔·德·塞尔托在《日常生活实践:实践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大众在日常大众中如何游戏般地在日常生活中采用“策略”“战术”,潜在反抗现实中的支配力量,抵制权力的规训,创造自己的空间。所谓“策略”,塞尔托解释为一种行动,“该行动受益于某个能力场所(特有场所的属性)的假设而建立了一些理论场所(全面的体系和话语),这些理论场所能够对力量进行统筹安排的全部物质场所联系起来。策略将这三类场所组合在一起并试图利用它们互相控制。因此,它们给场所之间的关系赋予特权”。[3][法]米歇尔·德·塞尔托:《日常生活实践: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9页。他以自己熟读的中国的《孙子兵法》为例指出,在具体情境中具有即时性的“策略”类似战争中的谋略,对弱者扭转劣势有重要意义,体现着大众隐秘的创造力量。在电影中,这种策略首先表现为从现实到想象不着痕迹的置换,电影镜头技法使想象的真实感得到大大提升,使人们从现实到理想的出走与逃离隐去踪迹,实现了真实而又自然的想象性置换。
辫线能抵挡数万利刃,人能顷刻间行万里之远、上天遁地无所不能,死人复活、鱼解人言,这些超能力经由电影镜头语言以及特技处理得以在电影中真实存在,虚构与真实之间的距离通过电影语言的提升被消解,“或驾云腾空,凭虚御风,或隐遁无形,稍纵即逝,或则虹光贯日,大显神通,或则剑气凌云,小施身手,举凡书中所有,银幕俱能使之一一实现”。[4]青苹:《从武侠电影说到〈火烧红莲寺〉和〈水浒〉》,《影戏生活》1931年第1卷第3期。这种“真实的想象”与“想象的真实”在古装类型中有许多极具代表性的探索与尝试。比如《西厢记》中,创作者在张生与孙飞虎对垒近四分钟的梦境段落中,利用电影镜头的艺术魔力,将毛笔变粗变长,被张生骑着飞上蓝天,将原剧中“笔尖横扫五千人”的唱词形象生动地呈现在银幕之上,彰显了知识分子“以文克武”的幻想。到武侠片风行时,一些演员因精湛的身手和表演被观众熟识,电影公司都有一批叫座的“侠星”,个个身怀绝技。被称为“银坛霸王”的王元龙剑术精良矫健灵活,“那一片寒光,缓时如白云出岫,急时如风雨骤至,危险处,更能令人失声惊呼”。[1]绿竹:《谈荒唐剑客》,《电影月报》1928年第3期。圆熟的电影技术不断升华着人物的“无所不能”,满足着民众对于逞强除恶除暴安良的英雄的期待。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摄影技巧不断涌现,更令想象空间的真实性在艺术性提升的同时得到最大的发挥。《火烧红莲寺》摄影师董克毅为拍剑侠飞行的镜头,学习美国杂志上类似摄影法,循着书上的化学名词,“凭着想象用土法子试验,终于想出了空中飞人的拍摄法”。[2]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第229页。空中飞人技法成为当时武侠以及神怪电影中最常使用的经典技法,饰演红姑的胡蝶腰系铁丝,在巨型风扇吹出的大风吹拂下,翩然而起,摄影机前笼一薄纱,画面呈现出朦胧的仙气。
那些一度在小说文本中引起观众阅读想象的离奇武功、奇异之事,在电影中得到了奇观化的视觉呈现。电影影像所努力营造的“真实”,迎合了民众对民族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憧憬与想象,这便是“电影幻象”所呈现的似真本质,“幻想”与“真实”,以一种全新的视觉感官体验,将这种基于传统文化的想象进行演绎,予观者以沉浸式的情感互动。
三、市民美学口味的满足
武侠神怪类型在叙事上以充满俗世趣味的通俗剧为蓝本,将世俗话语的影像表达实践扎根于平民视角之中,迎合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市民阶层强烈的精神需求。即使创作态度严肃、投资高达15万元创下空前电影制作纪录的《美人计》,也只是从《三国志》中选出了表现“忠孝节义,并且既悲壮又香艳”[3]张碧栖:《对于〈美人计〉的感想》,《美人计特刊》,大中华百合公司,1927年5月25日。的五十四、五十五回,在严肃的制作中不乏对“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趣味性主题演绎。耗时一年多时间拍摄的电影《盘丝洞》,并非取自《西游记》中最精彩的章节,而是着力表现神秘洞穴里的蜘蛛精等更加“性感”的内容。《火烧红莲寺》也同样只节选了单行本中第八十回“游郊野中途逢贼秃,入佛寺半夜会淫魔”到第九十八回“红莲寺和尚述情由,浏阳县妖人说实话”等最具有视觉发挥空间的章节变成电影剧本,并且从文学到电影的转化中都做了相应的改动,加以对观众更有吸引力的英雄美人、艳闻逸事、采奇擒怪等不乏油滑的噱头。
但在人物塑造层面,贴近平民立场的世俗趣味并非毫无原则的迎合,而是将世俗的话语与通俗文化想象植入人物的想象性胜利之中,使人物获致一种理想性的民族性格。《火烧红莲寺》里,不仅有众侠客惩奸除恶,还有私访民间疾苦的清官与义士一同大败恶僧;《关东大侠》中男女主人公与无穷无尽的恶霸、盗贼、邪教进行斗争,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荒村怪侠》中备受恶霸欺凌的乡村青年,学成武艺满载归来,不仅除掉恶霸伸张了正义,还收获爱情,实现了普通百姓的圆满的生活梦想。更有一些夸张荒诞的剧情,比如《航空大侠》中驾驶飞机到处行侠仗义的主人公,“懦弱者遇到被强暴者压迫的时候,只要一听到空中机声轧轧,那懦弱者宛如表现影戏般的,顿时将愁容不展的面孔,一变而为笑逐颜开,这原来是救星航空大侠来了,那强暴者也早已溜之大吉,逃之夭夭了”。[1]鹃红:《航空大侠》(电影小说),《电影月报》1928年第7期,转引自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在具有假定性的故事和人物设置中,与现实有关的内容被重新组织编排布局,一个保护弱者平衡劣势的理想世界被建立,通过电影的众多策略性技巧,不幸的人获得特权赢得胜利,通过这种想象性的胜利完成对现实的反抗。
可以看到,无论是情节还是人物塑造,隐含于类型中的通俗文化想象,一定程度上暗合了转型社会关于世界“应该如何”的迷思,“这种实然与应然间的对照、对立,使人们对未来产生强烈的希望感,从而推动人们去追求更合理的生存状态”。[2]耿传明:《清末民初“乌托邦”文学综论》,《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177页。正如电影《大侠甘凤池》上映后,有评论文章就道出观众的心声,“我处在今日强权压迫之下,这片真可当作救时的良药了。我看完之后,不觉发出一种新希望,希望甘凤池再来;因为他在字幕中告诉我,说人们如果有急难时,他会再来帮忙啊!”[3]文湘:《大侠甘凤池》,《中国电影杂志》1928年第13期,转引自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3页。虽然隐晦地表达了对现实的思索,并给出了想象性的解决,但必须看到,这种理想的“麻醉”作用明显盖过了它“推动人们去追求更合理的生存状态”的积极意义,对于英雄以及其给出的解决路径过于理想主义的表达,使得对许多问题的思考浅尝辄止无法深入,人物描写流于表面而缺乏性格和心理的深度揣摩。以至于到后期极致地走向消极遁世、蛮门仙妖等为奇而奇、为怪而怪的技巧和叙事的探索,理想世界被人妖莫辨、混沌无序的不可知世界所取代。对此,学者陆弘石总结为“消极浪漫主义的极端化发展,使20年代商业片创作走入了最后的歧途”[4]陆弘石:《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48页。。
虽然,这一时期的武侠神怪类型有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类型独特性,但当下一些魔幻片、奇幻片、玄幻片等神怪类型的种种尝试,仍能够从其中找到源头活水。同样是基于超现实幻想的类型题材,好莱坞从20世纪30年代恐怖片到70年代科幻魔幻类型,到《侏罗纪公园》《指环王》《哈利·波特》等一系列电影风靡全球,除了极强的技术依赖的共性,其在民族类型的发展角度上仍与中国神怪奇幻类型大有不同。在中国的民族电影发展历史上,无论《倩女幽魂》《青蛇》还是《画皮》《西游·降魔篇》《钟馗伏魔:雪妖魔灵》《捉妖记》《寻龙诀》《九层妖塔》,这些21世纪现象级神怪类型片都与20年代末的武侠神怪类型隐隐呼应。中国武侠神怪所特有的对武术动作身体展示的倚重,成为不同于西方魔幻类型的独特民族表达优势,其对于传统通俗文化资源的重视与改编,使文化想象各有出处,经典传说、神话、文学故事等焕发出新的民族文化活力,让人感到民族的通俗文化资源持续饱有世界影响力与市场号召力。比如,唐朝名相狄仁杰因清廉自守、敢于犯颜直谏、整肃朝纲而名垂青史,后世对于狄仁杰一生的传奇经历以及历史功绩评说不断。然虽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在先,徐克的《狄仁杰》系列仍能基于神怪类型拍出别具一格、不落俗套的新意。骇人听闻的怪力乱神,民俗的奇观展示,不仅能够为观众带来神秘诡谲的感官体验,也能为影片的历史怀旧蒙上别具一格的东方魔幻气质。既有古装历史、侦探推理,又有奇谈神怪度人耳目,其《狄仁杰之神都龙王》对民间巫术、水怪进行极具想象力的吊诡呈现,狄仁杰解救花魁、搭救元稹、朝中解蛊、大战龙王,少了徐克以往武侠人物萧飒独行的江湖之气,多了心系庙堂捍卫威权的道义精神,“东洋蛊毒”的植入使大唐悬案扑朔迷离,狄仁杰断案如神的形象也因此更加丰满生动,焕发出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无不表现出当下电影创作者对早期武侠神怪类型电影的通俗文化想象传统的自觉承续与发扬。
应该看到,在20年代末商业电影浪潮所涉及的这道关于世界的思考题中,无论是对于未来世界的想象,还是对于过去时代的想象,都以“现时”为基点,并隐晦地指向现代性的问题。用本雅明的话来说:“恰是现代可以唤起远古,每一个时代都梦想将来的另一个时代,而在梦想的同时也借此修正了过去的那一个时代。”[1]转引自万传法:《想象与建构“现代性”视野下的早期中国电影叙事结构研究》,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年,第8页。在今天看来,通俗文化想象本质使过去、现在、未来在民族想象的穿梭中实现完美的置换,并达成统一与和解。相对于时装电影对社会、爱情、伦理等现实问题的思考,具有传统、古典、东方蕴味的宽袍阔带更贴近中国的民族品格。在电影营造的理想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勇武和伦理美德的确认,以及自由、正义、忠诚、爱情等的价值诉说,在虚幻迷狂的想象外衣之下,悄然完成了现代性的本土转译或者说传统的现代性转换。因此,无论站在历史角度还是现实角度,早期武侠神怪类型对传统和现代、民族性和当代性的种种反馈与探索都是独一无二的,无不彰显着民族影像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