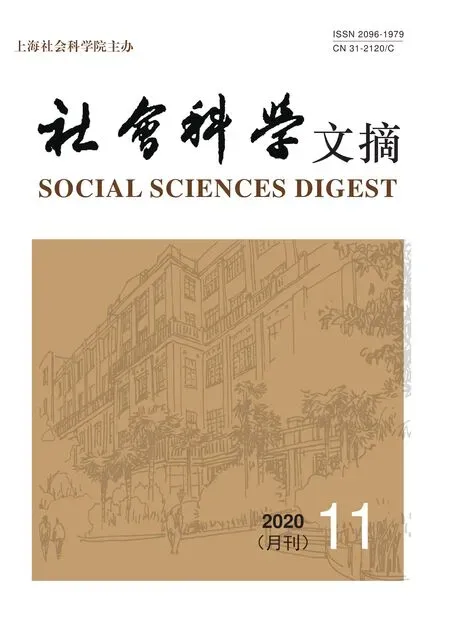论物质性人格权的性质与立法原则
2020-11-17
引言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的上位概念是物质性人格权。梁慧星教授等认定物质性人格权是“防御性人格权”,不能积极利用。王利明教授等主张物质性人格权既具有防御性,也可积极利用。物质性人格权究竟有无积极利用的属性以及如何积极利用?这是人格权研究和立法必须清晰和解决的核心问题。
防御性权利之说的由来和依据
人格权出现于1986年的《民法通则》。但尹田教授认为人格权与自然人本身不可分离,是“人之本体”的权利,不能由民法赋予。梁慧星教授在批评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人格权编草案》一文中强调:人格权不存在权利变动的可能,也无法对其进行使用、收益和处分,人格权是一种防御性的权利,不可以积极利用。李培林教授、陈甦教授在《民法典编纂中的人格权法立法争议问题》一文中提出,“人格权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其存在本身即为目的”,以康德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名言为依据。
王利明教授等对康德名言未作正面回应,只是引用拉伦茨等“归属效能”的论述说明人格权可以积极利用。但拉伦茨等所言的生命、健康等人体法益的积极利用只适用于人体受侵害的场合,其积极利用依然具有消极防御的意义,其论述的公信力也不能与康德的名言相提并论。“人格权是防御性权利”和“人格权也可积极利用”,前者绝对排除后者,后者也是对前者的否定。民事权利都有积极利用性,如果人格权只有防御性,自然不能成为独立的民事权利。因而,“人格权也可积极利用”之说的成立,首先需正面回应“人格权是防御性权利”之说及其依据。
康德的名言被后人冠之为“目的公式”:“对待每一个理性存在者(无论是你自己或是他人),你应如此行动,以至于在你的原则中,每一个理性存在者在其自身即是目的”。人本身作为一个“目的性”的存在,在任何时候,行为都是以追求人的“目的性”为其目标。所谓“目的”,是指自由的对象,是被主体所欲求的对象,由此,人能够进行自我满足和自我发展。与“目的”相对的是“手段”,所谓“手段”是实现特定“目的”的中介或者工具。人在任何时候只能作为满足自己自由发展的目标,不能作为他人或者自己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可作为手段的只能是外在对象,不包括人自身。
以康德的名言证明人格权是防御性权利,符合德国民法理论的法律关系结构。法律关系三要素中,权利和权利客体泾渭分明,权利是主观意志的,客体是客观实在的。人格权与人格权客体需要主观意志与客观实在的区分,才能符合法律关系的基本原理,这就有了人格要素是人格权客体的认识。但是,人格要素恰恰是人自身的组成部分,与自然人的人格须臾不可分离,将人格要素作为客体容易混同于将人自身当成客体,因而,萨维尼不承认人对于自身的“原权”,德国民法典只肯将某些人格要素的权利置于总则编中的民事主体部分。
然而,符合德国民法理论并不能证明人格权是防御性权利之说的正确,更不能证明梁慧星教授等真正理解了康德的目的公式。
如何理解“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康德的目的公式简洁有力地表述了其所处时代的主流伦理。在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旗帜下,近代社会以来的主流伦理拒绝人类个体被国家和他人奴役,也拒绝人类个体摧残自己。如果康德的本意是人只能绝对地作为目的,任何情形下都不能作为手段,以康德的目的公式证明人格权是防御性权利,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是,如果康德的本意不是如此,对梁慧星等教授而言,这是一个不当的论据。
在《道德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说:“理性的存在者则被叫做‘人’,因为,他们的本性就指出,他们本身就是目的,也就是说,是不可能仅仅被当作手段使用的某种东西”;“在对每一个的目的所使用的手段中,我应该把我的准则限制在那对每一个主体都是作为一个规律性的普遍有效性的条件上,即,同时被当作一个目的来对待”。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也这样说:“正是由于自由的缘故,每个意志,甚至每个人格自己特有的、针对他自己的意志,都被限制在与理性存在者的自律相一致这个条件上,这个存在者绝不可以仅仅被用作手段,而是同时本身也用作目的。”由此可见,康德反对的是“只将人作为手段,不将人作为目的”,主张的是“如果将人作为手段,必须同时将人作为目的”。
康德将人的“目的”分为“客观目的”和“主观目的”。“主观目的”是指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人类个体某种行动的动机,即我想如何,“主观目的”具有个体性。“客观目的”是指“人性”,所谓“人性”,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这样解释:“一个人可以是其自己的主人,但是并非其所有者,因为其要为存在于其本身中的人性负责,由于它是属于人性本身的权利,而并非属于其个人的权利”,即人类整体的理性和尊严。康德的“主观目的”着眼于人类个体,“客观目的”着眼于人类整体,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这一目的公式中,目的是指客观目的,手段是指主观目的——“我想如何”,主观目的对于客观目的而言是一种事关人类文明发展的手段。因此,康德的目的公式应解读为人类个体的任何行为都不能违背人类的理性和尊严,不能“将人仅仅作为手段,而不同时将其作为目的”。
与之相似,康德反对人在“非理性”状态下的自杀行为,因为允许人类的这一行为演化成一项“普遍法则”,将损害人类群体的人性尊严。但是,康德并非无条件地反对自杀行为,而是认可为国家利益或者保护他人的生命健康而放弃自己生命。康德指出:“在很多情形下,生命必须被牺牲,尤其当自我保存的义务同那些义务相互冲突时,我必须去牺牲。”康德提出生命可以为特定义务而自我牺牲,就是因为特定义务属于“客观目的”。
在康德目的公式的基础上,黑格尔明确提出具体的人本身就是目的,每一个特殊的人都通过他人的中介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他如果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不仅如此,黑格尔还提出“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的观点,人是一切价值的源泉,自然界因为人而获得其存在的意义。只要出于人自身的理性和意志自律,即便是具体的人也可以将自己作为一种手段。
马克思进一步修正了康德的“目的公式”,提出人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马克思肯定了人作为手段的现实可能性:“每一个人的利益、福利和幸福同他人的福利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事实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不言而喻的真理。”马克思明确提出:“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的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人的价值体现了人作为目的和手段的动态统一,没有只作为目的的人,也没有只作为手段的人。
由此而言,梁慧星教授等均误读了康德的目的公式,也没有注意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康德目的公式中所谓的“目的”,转化为权利的话语毋宁说是具有普适性和道义性的“人权”,而不是私法意义上具有自治性和个体性的“人格权”。以康德的“目的公式”证明人格权只具有防御性是一个鲜明的错误。除了康德的名言,梁慧星教授等再无其他理据,人格权是防御性权利之说因而不能成立。
积极利用是物质性人格权的固有属性之一
关于人格权的积极利用属性,王利明等教授作了不少的论述。其中,人格权的伦理性是解读人格权积极利用的节点,这是争论双方唯一的价值共识和争议准则。
伦理性是人格权的本质属性,人的伦理价值包括个人价值和群体价值,是人格权的核心价值,决定着人格利益、具体人格权的权利义务、人格权保护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伦理性不是一种抽象的道德信仰,而是人类自我认识、自我定位形成的具体价值取向,是人类文明逐渐进化的产物和表现。生而平等、天赋人权是现代国家公认的伦理价值,但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以后才形成的人类共识。一部分自然人不是法律意义的人,这在现代国家绝对不可思议,但在古罗马理所当然,伦理性从来是世俗的、时代的、地域的。
更为重要的是,伦理性离不开人的生物性。人是万物之灵,其首先是一种生物。伦理性共识淡化了生物性在人格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彷佛生物性仅有自然科学的意义,事实上,生物性是人格权的构成要素,同样具有法的意义。争论双方都以人格要素或人格利益作为载体或媒介,而人格要素或人格利益都是基于人的生物性形成的概念和分类。生命、健康、自由、名誉、隐私等,首先是人的某一生物属性,进而才赋予相应的伦理属性,组合为人格权。罗马法将奴隶当成物品,同时保护身体、贞操、声誉、身份,伦理性不过是生物性社会化的结果,尽管这种社会化因立法者的价值倾向而表现出强烈的选择性。人格权的生物性和伦理性不可分离,伦理性源于生物性同时决定生物性的社会意义,生物性产生伦理性的同时制约伦理性的内容和倾向。自杀或安乐死的伦理争议源于死亡这一生物现象,使得死亡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而死亡的生物意义对伦理的利弊又是不同伦理价值立论的基础。
人格权的伦理性是生物性的社会反应。生物性是一种自然属性,属于客观范畴。所有的客观事物都可以被支配和利用,区别只在于人有无支配和利用的意愿和能力。古代社会有合法的奴隶,现代社会有非法的劳工,人的被支配和利用是一个生物事实,问题只在于社会是否允许。人格要素的支配和利用不是一种创意,而是生物性所决定的客观存在。悬梁刺股是以自然方式积极利用人格要素的故事;基因编程是以科学方式积极利用人格要素的现实。人格权积极利用的本源是生物性。人格要素被支配和利用是客观事实,是否允许人格要素被支配和利用是主观选择,两者不可混淆。社会可以不允许某一人格要素的支配和利用,或者不允许以某种方式支配和利用人格要素,但改变不了人格要素被支配和利用的生物事实,这是非法支配和利用人格要素屡禁不止的原因。由此而言,积极利用是人格权的固有属性,正如消极防御一样。
梁慧星教授等的失误就在这里。人格要素的支配和利用与人被支配和利用不是同一概念,将人格要素的支配和利用解读为不把人当人显属逻辑错误。人格要素的支配和利用,既可能损害人的主体价值,也可能为人的主体价值增光添彩,这取决与立法对人格要素生物性的认识和应对。所谓积极利用,当然仅指有益于人的主体价值的情形。
物质性人格权积极利用的立法原则
在现代社会,人格要素的生物性有了崭新的意义。现代生命科学技术不断发掘和改良人格要素,拓展人格要素的利用范围,提升人格要素的利用价值,极大改变了人格要素的自然状态。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大大减少人类生老病死的痛苦,显著提升人类生命、健康、尊严的质量,促使人体资源有益于人的主体价值,为人格权的积极利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志愿者和无偿捐献一直是生命科学技术的人体资源来源,但是,这是一种有限的人体资源供应,阻碍着生命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大规模应用,人类因而面临守成或革新的选择。美国是生命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也是母乳、卵子和血液等人体资源可以交易的国家。斯旺森教授从制度史的角度论证了人体资源衍生财产利益的正当性。有条件地允许人体资源市场化,是现代社会实现人的主体价值的路径之一。同时,生命科学技术具有两面性,既可能开发人的生物性潜能,也可能危害人的生命、健康、尊严。因而,人体资源市场化也具有两面性。
为此,“伦理价值优先兼顾经济利益”应为物质性人格权的立法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人的主体价值是物质性人格权积极利用的最高目的和准则,为充分实现人的主体价值,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可以允许某些人体资源市场化。具体而言:
积极利用必须立足于人格要素的生物性。生物性是人的主体价值的生理基础,只有生物意义上有益于人的主体价值,才有积极利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在现代社会,生物性主要依赖生命科学技术,其对人的主体价值的积极或消极影响通过一定的技术分析和指标加以确定。对供体者不产生永久性伤害的人体资源可以积极利用,反之则否。
积极利用必须评估人格要素的伦理性。有益于人的主体价值,不仅需要生物性证明,而且需要伦理性证明。人格要素的伦理性是一定社会主流伦理对人体资源的道德评价,不同的评价赋予人格要素不同的伦理价值。主流伦理是一个社会多数人的道德共识和行为准则,由历史、文化、信仰、利益、制度等各种因素融合而成,具有短期难以改变的社会支配力,是人格要素生物性社会化的向导。伦理性是积极利用的决定性指标。
积极利用必须确立人格要素的自主权。自我决定是人的主体价值的本质和核心,自主支配和利用自己身体是自我决定权的最低要求。在符合生物性和伦理性要求的前提下,人体资源是否利用、如何利用由人格权人自行决定,因为只有本人才能切身体会其中的利弊,只有本人才能承担各种可能伴随一生的后果和风险。人体资源的利用,绝不能适用以当事人利益平衡为支点的法律规则,包括代理、实际履行、强制执行等。
积极利用必须建立严格有效的监管制度。人体资源依赖普通人难以掌握的生命科学技术,其资源价值、技术成本、利用效益的信息难以对称,极易沦为中介牟利的“工具”。人体资源的研究和应用大多具有个体试验的意义,极易出现突破主流伦理底线的情形。人体资源绝大多数严重短缺,市场化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黑市交易几乎是全球性的问题。可以说,没有严格有效的监管制度就无所谓人体资源的积极利用。因而,应设立专业的机构主管人体资源的利用,审查个案的生物性、伦理性,批准和登记审查通过的个案,动态监管个案的实施过程。对可以市场化的人体资源,应指定交易场所、统一交易程序、管制交易价格、打击违规交易,确保交易的透明和公平。
结语
《人格权编》肯定物质性人格权的积极利用性质,是民法典现代化、中国化的重大成就。但这只是一个开端,物质性人格权的积极利用需要更为清晰的法理、更为明确的方向、更多合理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