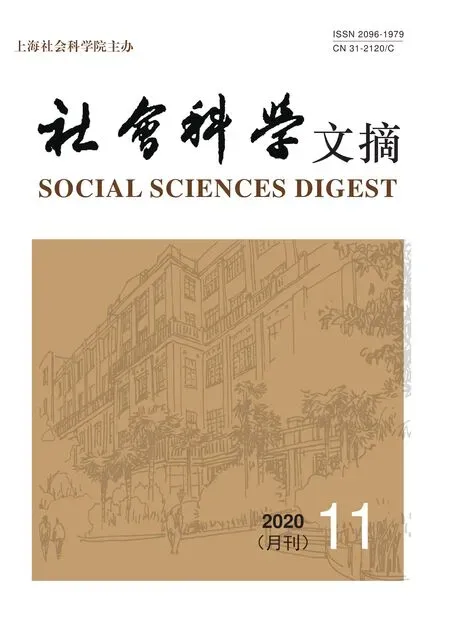论宪法中的行政诉权
2020-11-17
中国现行宪法中的行政诉权
(一)理论争议
时至今日,对中国现行宪法是否存在行政诉权根据的认识仍颇具争议。即使是持中国宪法中存在行政诉权依据的观点内部,也存在着微妙的分歧。早期的一种见解认为行政诉权是行政诉讼法对宪法中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进一步明确的结果。另外一种早期的观点则认为,中国《宪法》41条“暗含着对行政诉权的肯定”。此后的学者将行政诉权与宪法中的某一具体权利相联系。一种说法认为,行政诉权来源于中国宪法中的控告权。另一种说法则认为,申诉权“为公民提起行政诉讼提供了宪法依据”。显然,上述解释对“依据”的具体定位有不同的认识,但“依据”被圈定在《宪法》第41条中的申诉权、控告权和检举权的范围内。
对此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有的学者认为,将行政诉权认为是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具体化的观点,是对行政诉权的误解。有的学者不认可将申诉权作为行政诉权的宪法依据。还有学者认为,该条文并不能引申出司法救济权,也并不是要确立中国的诉讼制度,而仅是一种政治宣言而已。另外有学者并未涉入上述争论,而是直接指出,中国宪法条文并没有明确地规定行政诉权。
(二)外国宪法有关行政诉权的规定
在宪法文本中明确规定诉权,是现代宪法发展的普遍性趋势之一。从相关文献来看,学者多援引宪法文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9条第4款第1句:“无论何人的权利遭到公权力的侵害,均可提起诉讼。”《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113条第1款:“对行政机关的行为不服时,可随时向法院或行政司法机构提出请求,以寻求对其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如果以这两个宪法文本为模板,当今世界各国的现行宪法中,还有《智利共和国宪法》(第38条)、《摩洛哥王国宪法》(第118条)、《1990年新西兰权利法案》(第27条)、《阿根廷国家宪法》(第43条)等明确规定了行政诉权。
仅对条文字面含义进行理解,上述法律条文中较为明确的是:行政诉权针对的对象是行政权;与行政诉权相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司法机关(法院);行使的方式是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有两点不易弄清:其一,行政诉权是否以权利受到损害为必要的法律要件,是否存在仅是对行政机关违法履职而提起的诉讼,此时,并没有具体的个人权益受到损害;其二,公民可否因行政权力侵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而提起行政诉讼,此时,作为起诉人的公民并非行政相对人,也不是利害关系人。对这些疑问的不同解答,将会对理解行政诉权的性质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也意味着宪法中的行政诉权恐怕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
(三)中国宪法中行政诉权的法律性质
中国《宪法》第41条由3款构成,涉及行政诉权依据之争的是其中的第1款后半部分,这个句子说明了三个问题。首先,如对语句彻底分解,它创设了三项权利:申诉权、控告权和检举权。其次,它规定了这些权利的享有者是公民(关于公民身份的定义可在《宪法》第33条中找到),义务主体是“有关国家机关”。最后,它规定申诉权、控告权和检举权作为一项公民的宪法权利理所当然所具有的内在界限,即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直至今日,后两个方面并未引起太多争议。但对于第一个问题,则存在不同的解释,究其缘由,虽然文本中创设了这几项权利,但并未给出这些权利的定义,它们的含义是不明确的。
从现有的相关解释来看,大家对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的理解不是固化的,这几项权利具有非常宽泛的内涵。不过,从字面含义和用语习惯来看,与行政诉权所要表达的意思最为接近的是其中的“控告权”,而非“申诉权”和“检举权”。“控告权”含义很广,包含了公民利用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控诉的权利。根据现行宪法起草者作的相关解释,完全可以推论出控告权包含有公民针对行政权力的违法行为行使向司法机关控告的内容。其内容也与上文中中国现行宪法以外的其他国家宪法中有关行政诉权的规定无异。在此,行政诉权可以理解为是控告权的操作性、手段性权利。并且,其所引申出行政诉权的范围和内容还较上述相关规定更广,不仅仅是作为权利被侵害而救济,亦可包含客观合法性审查。宪法上行政诉权的宽泛内涵或许也是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并列构造设计的根源之一。
另外,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对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程序法规则进行了原则性规定。据此,法院有权依据民事诉讼法对行政案件进行受理、审理,人民向法院控告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有了程序法上的保障。有学者认为现行《宪法》第41条之规定仅是一种“政治宣言”,其实并非如此,41条中的公民可以控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有诉讼法律制度支撑。
对宪法中行政诉权的认知
(一)中国现行宪法建立的国与民的关系是行政诉权的基点
中国宪法建立的国与民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点来把握:第一,人民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和来源;第二,国家权力必须受到人民的监督;第三,人民有权参与国家管理;第四,国家有责任保障公民权利。此外,中国宪法体例设计上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置于“国家机构”之前,亦表明了此种国家责任。
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行政诉权,是由宪法所确立的国与民的关系决定的。其一,行政权力必须受到人民的监督。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并不直接行使国家权力,这就存在国家权力的行使者违背人民意志,甚至侵害人民权益的可能。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性质决定公民有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进行监督。在中国,公民监督权的行使不外乎两种形式:一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二是公民直接行使。公民直接行使的监督权具体包括《宪法》第41条规定的批评、建议、控告等权利,如果没有这些权利,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受人民监督的规定就会落空。其二,权利被侵害之后必须得到救济。权利和救济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个强调和尊重权利的社会中,根据权利和义务所获得的保障和救济,是人们真实地享受权利的关键因素之一”。国家应该承担被公权侵害的权利的救济任务。与个人的民事权利被平等主体侵犯也可通过私力救济不同,公民的公法上的权利如被行政权力所侵害,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渺小的个人无法通过自身力量来保护个人权利,这就需要国家设置法律制度以提供救济的途径。
(二)宪法中行政诉权的双重属性
宪法上建立的国与民的关系决定了公民应当享有行政诉权,同时也展现出了行政诉权的两种功能,即监督功能和救济功能。上文已述,有学者认为,从学理上看,控告权应可包括公民针对违法或失职的行政行为的控告权、公民针对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对其合法权益的不法侵害的控告权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前者是公民根据其政治意志或者是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而监督行政活动的权利,在此意义上,可称之为监督权利,属于政治性权利和实体性权利。后者是公民救济自身被侵害的合法权益而行使的权利,也称之为“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这种权利形态是一种程序性权利,属于非政治性权利。
对于这一见解,人们存有疑问:都是控告行政机关,为何根据公共利益去控告就是监督性质,而根据私人利益被侵害去控告就不是监督性质?这样划分的理由并不充分。如果我们认可监督的内涵就是对政府是否依法行使行政权力、是否按照人民授予权力的目的行使权力进行监督,那么,此种监督的动机究竟是出于私益还是公益,对于监督的本质而言并无影响。就行政诉权而言,无论是受行政权力侵害的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第三人或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提起行政诉讼的任何公民,他们提起行政诉讼的对象都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的行为,这本身就是一种监督,是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同时,在个人权益受损的情况下,提起诉讼的活动亦包含权利的救济。也就是说,那些以权利受到侵害为要件的行政诉权,所具有的监督和救济两种属性是重叠的,并不能分离,这一点在行政诉讼制度上更是得到彻底的体现。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行政诉权与一般性诉权的区别。诉权只是一项行动的能力,它本身不具有利益属性,只有通过其他权利的连接才能产生利益。这也是为何诉权被称为程序性权利的原因,它是为实体权利服务的。而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并不只是一项程序性权利,它本身具有监督的利益属性,不以个人权益被侵害作为其权利行使的必要前提,并且宪法创设这一权利的初衷并不一定只是为了受到侵害的权利的救济。它的另一面向,也是其并非不重要的一种属性在于,它是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一项权利,是一项政治性权利。它可称之为一项参与权,参与到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衡中。这种参与不是被动的、作为客体的参与,而是作为主体、积极的参与,离开了行政诉权,司法权力无法启动对行政权力的司法监督。
宪法中行政诉权与行政诉讼法中行政诉权之间的关联
(一)两种成文法载体中行政诉权的性质应无不同
行政诉讼法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作为公民享有行政诉权的条件之一,并且规定了诸多程序性权利以保障行政诉权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实际行使,容易让人误以为其只是一种救济权、一种程序性权利。然而,宪法中的行政诉权所具有的监督性质依然在行政诉讼法中的行政诉权上得以延续。一方面,《行政诉讼法》第2条中的“侵犯”是指违法情形,人民法院原则上只审查违法的行政行为。公民提起行政诉讼即是开启了法院监督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的大门。另一方面,行政诉讼法是一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法律,行政诉讼法在立法宗旨条款中明确规定“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此处的“监督”不应只是理解为司法机关通过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也应当包括公民对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的监督。通过行政诉讼这种形式,人民民主监督和国家司法监督这两种监督融为一体。在行政诉讼中,没有公民的起诉,则无法启动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司法监督,没有司法机关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则人民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将会没有任何结果。
(二)行政诉讼法上行政诉权的配置及其限度
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权权利主体的配置只涉及一个问题:对于一项可供法院审查的行政行为,谁可以提起诉讼?中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是公民享有行政诉权的一般性条款,与宪法中的行政诉权相比,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行政诉讼法中行政诉权的享有者是自身合法权益被行政行为侵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宪法中行政诉权的享有者是公民,并未明确限制为是自身权益被侵害的公民。从享有主体来说,前者将公民扩展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但在实质上是否扩大了行政诉权的享有者范围,其实未必,因为后者在理论上可以涵盖任何公民,而前者仅限于与被侵害权益的关系人,其实质是将行政诉权与权利、自身的权利相挂钩,从而披上了权利救济的外衣,使这一权利可能包含的其他特质隐藏了起来。
宪法中的行政诉权以利益的类型与提起控告人的关联程度可以划分为三种:公民对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致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而提起控告,公民对行政权力侵害他人权益提起控告,公民因行政权力侵害自己权益的行为提起控告。在行政诉讼法中,第一种行政诉权被交由人民检察院行使(第25条),在这里行政诉权不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项公权力,是一项由公权力机关行使的诉权。第二种行政诉权因为容易成为好事者的诉讼,以及缺乏必要性(被侵害人自己已经享有行政诉权)而被否定。中国行政诉讼法对这两种诉权限制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中。这种限制或许都源于一种共同的考量:公民不应该借助行政诉讼,把自己变成公共利益的“卫士”。
行政诉权的监督功能和救济功能是通过司法权力来实现的。这里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行政诉权对象的配置问题。在中国宪法中,这一范围被限制为任何违法失职行为。《行政诉讼法》的第二章“受案范围”以及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部分“受案范围”中采用列举加概括的方式,均对行政诉权的对象作了进一步的规定。这意味着,行政诉讼限于对行政机关的法律监督,而不是对行政机关实施“全面的监视”。通过对行政诉讼法上行政诉权配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两种成文法载体上行政诉权表达的失衡问题,宪法上的行政诉权是如何在具体的行政诉讼制度中形成和并受到限制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行政诉讼法之所以对宪法中行政诉权的享有者、对象的范围进行缩限,是为了规范司法实践中行政诉权行使的秩序以及司法制度自身的限度使然。
(三)行政诉讼法担负着保障行政诉权的任务
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只有在行政诉讼活动中才能成为一项实然的权利,行政诉讼法还担负着落实宪法中行政诉权的使命。公民行使行政诉权,归根结底是在行政诉讼活动中进行的,是公民以起诉人、原告、上诉人等诉讼过程中的身份参与到法院对所涉行政争议的裁判中来实现的。如何保证这样一种权利被公民所切实地享有呢?那就是赋予他们启动和延续行政诉讼的权利。因此,行政诉讼法中规定了一系列程序性权利以保障行政诉权的行使。这些程序性权利包括:起诉权(第2条、第25条),上诉权(第29条,第85条),申诉权(第90条),获得公正裁判权(可从第3—8条中推定得来)。这些权利在整个行政诉权结构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如果它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反而被设置过多的限制甚至是阻碍,那么所谓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权益的救济就可能偏离行政诉权创设的初衷和预期。
以起诉权为例。行政诉讼是以起诉人起诉和法院受理两个行为的结合来启动的。因此,无论是对行政权的监督还是个人权利的救济而言,起诉权是公民迈向法院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不少地方存在限制起诉人行使起诉权的“土政策”,将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法律关系是否明确等裁判要件作为立案受理的条件,对起诉权进行过度审查,使得人民群众的行政诉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对此,修正后的中国《行政诉讼法》第3条旗帜鲜明地规定人民法院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公民的起诉权利,并且在第49条明确规定了起诉条件,第51条规定了立案登记制,这无疑对规范、保障当事人行政诉权的行使起到积极作用。
当然,对公民权益无漏洞、具有实效性的保护,对行政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严格约束,是一种理想化的制度目标,行政诉讼制度仅仅是这些监督和救济手段中的一环,其作用的发挥还受到它所寄生的体制的影响,也不是仅通过立法政策的调整就能实现巨大突破的。不过,行政诉权作为一项对公民与国家权力之间制衡具有特殊意义的权利,理应得到作为程序法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更多的尊重和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