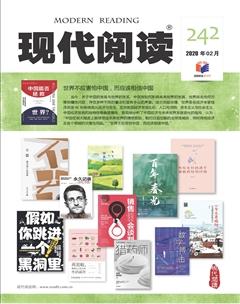一次两败俱伤的拜访
2020-11-16
新文化的思想领袖胡适与旧制度的帝王溥仪见面之后,舆论方面对两人都不买账。这似乎是一次两败俱伤的拜访……
1922年5月17日,刚在皇宫安装了电话的废帝溥仪,心血来潮,翻着电话本,到处给人打电话玩。他想起了他的洋老师庄士敦跟他提起的白话文运动的领袖胡适,想听听这个人“用什么调儿说话”,便拨通了胡适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胡适本人。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了当时他们通话的情景:
“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呵!”
“宣统?……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對这件事,胡适在日记中也有记载:
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宫中逢二休息)那年的阴历五月初二,就是阳历5月30日。此外,在约定时间时,胡适也很细心,他们选择了宫中休息日见面。17岁的废帝溥仪之所以对胡适感兴趣,是因为他对当时风靡一时的白话诗有兴趣。而胡适恰恰是提倡白话诗最有力的人。
7天之后,也就是5月24日,为了这次约见,胡适先去拜访了溥仪的洋老师庄士敦。在庄士敦那里,胡适了解了溥仪的近况。当天的日记中,胡适写道: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对溥仪独行其是的行为作风,胡适持赞赏的态度。
6天之后,胡适赴约,为了这次约见,胡适当天没有上课。见面时,溥仪先起立,胡适行了鞠躬礼,然后就坐在了溥仪为他准备好的大方凳子上。当时,两人聊了如何写白话诗、溥仪如何出洋留学等问题。此外,溥仪还向胡适解释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想办一个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这件事很有许多人反对,因为我一独立,有许多人就没有依靠了。”
对溥仪想独立但又不能独立的矛盾,胡适是很同情的。谈话最后,当溥仪抱怨许多新书找不到时,胡适还答应帮他找书。聊了20分钟,胡适告辞。
1922年6月6日,也就是这次拜访7天之后,胡适写了一首小诗《有感》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诗中胡适写道:
咬不开,敲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后来,胡适在这首诗旁边还特意加了一个注释:“此是我进宫见溥仪废帝之后作的一首小诗,读者定不懂我指的是谁。”
新文化的思想领袖与旧制度的帝王见面之后,舆论对两人都不买账。这似乎是次两败俱伤的拜访。
一方面,忠诚于清朝的遗老对溥仪不满意。对此,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说:他(胡适)走了之后,我再没费心去想这些。没想到王公大臣们,特别是师傅们,听说我和这个“新人物”私自见了面,又像炸了油锅似的背地吵闹起来了。另外一方面,那些喜欢胡适并将他视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青年人对他也很不满意。一时之间,许多报纸纷纷以“胡适为帝王师”“胡适要求免跪拜”为标题来报道此事。
为平息舆论,胡适只好写了《宣统与胡适》一文来澄清事实。文中,在讲述了两人见面的情形之后,胡适辩解说:
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一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自从这事发生以来,只有《晨报》的记载(我未见),听说大致是不错的,《京津时报》的评论是平允的,此外便都是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评论了。最可笑的是,到了最近半个月之内,还有人把这事当作一件“新闻”看,还捏造出“胡适为帝者师” “胡适请求免拜跪”种种无根据的话。我没有工夫去一一更正他们,只能把这事的真相写出来,叫人家知道这是一件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胡适礼节性的拜访溥仪一事,其实没什么可说的。
1920年代是革命逻辑开始的年代,道不同不相为谋是理所当然的。你既然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怎么能够去跟晚清皇帝交朋友呢?最好的方式应该是胡适与溥仪划清界限。胡适在《宣统与胡适》一文中那句“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的话广受非议。
1931年10月,上海《申报》登载了“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的新闻。看到这则新闻之后,鲁迅对胡适非常失望。他在《二心集·知难行难》中用小说笔法写下了一段讽刺胡适的文字: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
当“宣统皇帝”逊位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
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这篇文章背后的讽刺意味不言自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申报》的这一则新闻完全是假新闻,蒋介石与胡适在1931年并没有见面,他们正式见面的时间是1932年。
鲁迅建立在假新闻基础上的对胡适的讽刺,更多的是文学性的想象。如果只通过鲁迅的这段文字来认识胡适,难免失真。但也可见“去见溥仪”这件事给胡适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我的朋友胡适之》 作者:林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