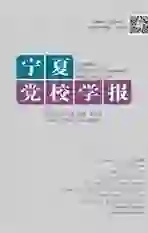论行政训诫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规制
2020-11-16易明佳
易明佳
摘要:当下关于行政训诫行为的法律性质判断尚存争议。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裁定,在确定行政训诫行为是行政事实行为的基础上,将其界定为综合性的行政指导行为。针对行政训诫在实务中所产生的问题,提出厘清行政训诫主体和适用范围、完善相关程序制度并准许一定程度的事后救济等措施。
关键词:行政训诫;行政事实行为;行政指导;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D63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0)05-122-007
2020年初的热点“李文亮医生事件”,使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誡书进入到公众视野,也使学界关于训诫行为的法律性质争议及规制被再度点燃。
训诫,从字面上看含有教导、劝告的意思。作为法律术语的训诫,其规定散见于《刑法》《民事诉讼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由此可见,训诫遍布于多个法律领域,其法律性质具有多重性。本文仅讨论行政法领域的训诫行为,下文简称为行政训诫。行政训诫,原本见于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九条,该条规定:“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八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处罚;不满十四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免予处罚,但是可以予以训诫,并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该条文规定的行政训诫本是一项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措施。而在2005年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则删去了这一规定,也没有将行政训诫纳入第十条所规定的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然而行政机关在执法实践中依然广泛使用行政训诫且逐渐突破原有释义,甚至出现于法无据的行政训诫行为,如对李文亮医生的训诫。故此,行政训诫应如何定性并予以法律规制,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行政训诫法律性质之争议
(一)学理分歧:“行政法律行为”抑或“行政事实行为”
学界关于行政训诫的法律性质争议颇多,对行政训诫也存在一定的共识。行政训诫,是由行政机关基于一定的管理目的,以训诫书的方式告知行政相对人相关权利义务或者让行政相对人知晓某一行为或某一事件的行政行为。在此基础之上,可将学界关于行政训诫的法律性质争议分为“行政法律行为说”与“行政事实行为说”。该分类以行政训诫行为对外是否发生法律上的效力作为分类标准,属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行为的典型分类之一。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的区别在于,前者不能产生、变更或者消灭行政法律关系。[1]
“行政法律行为说”认为行政训诫是对行政相对人直接产生法律效力,引起法律关系变动的具体行政行为。持该观点的学者大多认为行政训诫是一种行政处罚。王学辉教授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认为训诫是行政处罚中警告的书面形式,其符合行政处罚的特征和构成要件。一是行为基础与警告相对一致,同样具备应罚性和可罚性。二是训诫与警告的性质一样,同样是一种声誉罚或者警告罚。[2]
“行政事实行为说”认为行政训诫是对行政相对人不产生法律效力的事实行政行为。姬亚平教授认为,行政训诫类似于一种批评教育,未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是行政法中“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具体应用。[3]《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行政处罚法》第五条同样也规定了这一原则。
(二)当前司法裁判中的行政训诫
对于行政训诫的法律性质的学理争论,应当在结合当今司法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界定,如此既能实现对行政训诫行为的合理定位,亦可完成理论与实践的架接。通常情况下,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训诫行为时,会对行政相对人出具训诫书,而在司法裁判中围绕行政训诫行为进行的诉讼无一不涉及到训诫书,训诫书成为目前司法裁判中行政训诫相关案件的焦点。例如训诫书是否有法律上的强制力,是否侵犯到了行政相对人的具体权利等等。截止到2020年3月3日,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所检索到与训诫书有关的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案件裁判文书共计30份,其中涉及到行政训诫行为法律性质认定的裁判文书一共9份1,笔者通过对这9份文书的梳理归纳得出以下结论。
1. 最高人民法院并未明确行政训诫行为的法律性质。而对于案件本身,最高人民法院都援引了《行政复议法》第六条或《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认为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训诫行为,未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亦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2. 对于训诫书,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训诫书内容是公安机关在履行治安管理职责过程中对行政相对人所作出的指导、劝阻、批评、教育,该训诫行为并不具有强制力,对其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2最高人民法院目前并未对训诫书内容作出实质性审查,但训诫书本身可能存在违法情形,例如可能出现引用事实不清,援引法条不明确的情形。而这可能是当前行政训诫相关案件的司法盲点。
二、行政训诫法律性质之界定
(一)对行政法律行为说之辩驳
首先,从行政法律行为的定义来看,行政法律行为追求的是对当事人形成法律上权利义务的影响。通过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裁定可发现,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行政训诫行为未对当事人产生法律效果,未对当事人造成权利义务的实际影响,实质上否定了行政训诫行为是一种行政法律行为的说法。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行政裁定书中载明“所受训诫行为不是行政处罚措施,而是现场劝诫措施”3。这也否定了行政训诫是一种行政处罚的观点。
其次,行政训诫等同于行政处罚中警告的书面形式这种说法并不成立。警告作为法定的行政处罚措施,具有严格的批准程序。需要将案件信息录入公安机关的办案系统,与公民的个人信息相关联,且无法消除。相比之下,训诫行为所开具的训诫书,看似具备声誉罚或者警告罚的特性,但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显然不能等同于行政警告。当然,本文否定行政训诫是一种行政法律行为的依据主要基于实践,这并不妨碍我国后续通过完善相关立法使其成为一种新的行政处罚措施并予以规制。
最后,诚如学者所言,“法律行为是立法者精心设计的结果,是法技术的创造物”[4]。当前缺乏精细法律规定的行政训诫,不应将其界定为一种行政法律行为。
(二)行政训诫的基础定位:行政事实行为
行政事实行为的概念首创于德国行政法学者瓦尔特·耶利内克。[5]虽然学界关于行政事实行为的定义还存在争议和模糊之处,但一般认为,行政事实行为的通常定义即是:它并非旨在追求一种法律效果,而旨在产生一种事实效果。王锴教授认为,行政事实行为可能会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但这并非行政机关的意图所致。直接产生事实效果才是行政事实行为的特征。[1]
首先,行政训诫符合行政事实行为的概念。即行政机关作出的訓诫行为通过训诫书的形式,旨在产生一种制止行政相对人继续进行违法活动,并使行政相对人认识到自身行为违法性的事实效果。其次,行政训诫的作出主体缺乏就该训诫行为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事实上,如果行政机关意图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法律上的效果,根本不必采取行政训诫行为,直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行政处罚法》作出处罚便可。由此可见,行政训诫本就是行政机关为了避免对行政相对人直接产生法律效果所采取的行政行为。故行政训诫应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
(三)行政训诫的具体定位:行政指导行为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在确定行政训诫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的基础上,将行政训诫具体定位为一种综合性的行政指导行为。
1. 行政训诫符合行政指导的内涵
行政指导,是指行政机关旨在达成特定之目的,采取非强制性方式促使行政相对人作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行政活动。行政训诫符合行政指导的概念。行政训诫是行政机关基于社会管理目的,以训诫书的方式使行政相对人为或不为某种行为。此外,行政指导作为现代服务型政府背景下的一种柔性行政方式,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以形式上的灵活性来弥补法律上的僵硬性。行政训诫在实践之中即针对违法情节轻微,尚不足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行政处罚法》进行处罚的行为。
2. 行政训诫具备行政指导的非强制性与权力性
行政训诫在实践之中,表现为行政机关以训诫书的形式作出的指导、劝阻、批评、教育,体现出了行政指导的非强制性,即该行为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并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即使行政相对人拒绝接受该行政行为,也不会因此而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行政指导的权力性又会使行政相对人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该行为。由于“行政机关自设立之初就不同程度地享有一定的行政权”[6],行政机关因行使行政职权进行社会管理活动而处于强势地位,因此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训诫行为会给行政相对人带来事实上的压迫力,行政相对人一般会选择接受该行政行为。
3. 行政训诫属于综合性的行政指导
学界通识认为,行政指导以其功能性来划分,可分为规制性行政指导、调整性行政指导以及助成性行政指导。其中规制性行政指导是指行政机关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对妨碍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加以预防和规制的行政指导,而助成性行政指导是指行政机关为行政相对方出主意以保护和帮助行政相对方利益的行政指导。[7]结合实践来看,训诫属于综合性的行政指导,其兼具规制性行政指导与助成性行政指导的特征,例如在一些非法上访的行政案件中,训诫书的内容不仅包括对非法上访的行为人进行批评教育,还包括告知行为人相关法律规定及正确的信访途径。
三、行政训诫的法律规制:必要性与具体措施
(一)行政训诫规制之必要
1. 违反合法行政原则
合法行政原则作为行政法治的核心原则之一,要求“法无规定不可为”,即行政机关作出一项行政行为,必须拥有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现阶段行政法领域缺乏对行政训诫的明确法律规定。如前所述,如果要为行政训诫找一个法律依据,现阶段的《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大概只有“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符合。但是,原则作为法律之准则,除特别情况外不应作为法律规定直接引用。虽然前述将行政训诫定位为行政指导行为,行政指导行为被允许存在一定的灵活性。但正如英国行政法学家韦德所说:“法治并不要求消除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是应使法律能够控制它的行使。”[8]我们仍应对行政训诫的权力来源作出最低限度的基础性规定。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依法行政,首先要职权法定。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9]实践中没有明确法律依据却被广泛运用的行政训诫,无疑违反了合法行政原则,应当受到法律规制。
2. 扩大化应用放大执法标准差异
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行政权力的边界突破传统的物理空间,进一步扩张至无形的网络空间。行政训诫在实践中也呈现出适用范围越来越广的趋势,例如“李文亮医生事件”中,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行为即是旨在规范网络言论。再如在2020年2月14日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公安机关称就新冠疫情防控已开具180余份训诫书,对违反疫情防控者按照“第一次训诫、第二次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依法予以查处。4行政训诫在实践中有其灵活性的一面,但这也意味着其同时存在随意性,因而在实践中存在执法标准差异等问题。例如,相似的违法情节,行政机关对一部分行政相对人作出训诫,而对另一部分行政相对人作出处罚;或是对一部分行政相对人作出训诫,而对另一部分行政相对人不作出训诫,执法标准不明。再如,一些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训诫时,经常不考虑相关因素或考虑不相关因素。这些问题显然不利于行政训诫的正确应用,并且极易随着行政训诫在实践中的扩大化应用倾向而被放大。
3. 存在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可能
虽然行政训诫并不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但是在特定情况下,行政训诫存在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可能。例如,由于程序规制的缺位,行政训诫行为作出后,是否要将训诫书发送至行政相对人所在单位,目前在实践中做法不一。一些行政机关将训诫书发送至行政相对人所在单位,导致行政相对人被所在单位通报批评或者影响其绩效考核待遇。在这种情况下,或许行政机关并非出于故意,但已经间接影响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并且,当行政训诫行为出现诸如作出训诫书内容违法或者训诫书引用法条不明等情况时,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也可能受到损害。“李文亮医生事件”中公安机关的训诫书之所以饱受诟病,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训诫书的内容出现诸多问题,例如训诫书称该医生“行为已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5,该处便存在援引事实不清的问题,而该医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⑤,又存在引用法律不明确的问题。
4. 规制缺位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文将行政训诫行为认定为行政指导行为,行政指导行为应有一定的灵活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训诫行为不应当受到规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10]须知在实践中,即使是公安机关的基层组织派出所,也拥有行使行政训诫的权力,那么可以试想,如若使用行政训诫既不需要法律依据,也无明确的行政程序,甚至能够随时随地随意决定行政训诫的对象,这样的权力是否过大?这样的权力即使是派出所也能够行使,是否合理?并且这样的训诫在当前完全无法在实质上得到法律的救济。如若保持当下行政训诫规制缺位的现状,则行政训诫行为的尺度及边界完全掌握在行政机关的手中。或许当下行政机关对于行使行政训诫的态度还是审慎的,但在持续缺乏规制的情况下,我们就无法保证隐患会在何时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不合理的行政训诫,也许会在一次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后沉寂,但也可能会像“李文亮医生事件”中的行政训诫,在疫情暴发期间暴露于大众的视野之下,因其内容与形式的不合法引来公众舆论的声讨,极大地破坏了行政机关与公民间的信任。故而当前行政训诫行为的规制缺位,既不利于现代行政法所要求的行政机关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也不符合当下我国依法治国,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
(二)行政训诫行为的规制措施
虽然本文将行政训诫行为定位为行政指导行为,但是对行政训诫的法律规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对行政指导的普适性法律规制。理由如下:其一,并非所有的行政指导都如行政训诫这般被广泛和频繁地适用,其规制在我国尚不具有迫切性。其二,针对行政指导的法律规制应当是具体的、区别性的。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指导都受到行政程序法的严格限制,由于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因而对一些适用广泛的,有可能间接影响公民权利义务的行政指导行为应当优先进行规制。
1. 厘清行政训诫主体与适用范围
对行政法领域中的训诫进行法律上的规制,首先应当厘清做出行政训诫的主体。实践中经常出现其他行政机关如政府信访部门出具训诫书,造成训诫的做出主体混乱。行政指导具有行政性,所以指导内容应当属于指导机关的法定职权职责范围,否则指导主体便是违法的。行政训诫是一种批评教育,依据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凡是享有处罚权的机关都享有教育权,反之,没有处罚权也就没有教育权。[3]另外,在适用范围上应予以合理限制。应当看到,训诫与其他行政行为相比,具有柔性与灵活性等特点,如果过分缩限行政训诫的适用范围,恐怕会限制训诫行为的灵活与活力,失去其应有的作用,因而行政训诫的适用范围应当是概括性和宽泛的,明确行政训诫是行政机关在进行社会管理过程中,告知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或者让行政相对人知晓某一行为或某一事件的行政指导行为,并可以考虑将其规定为对于违法情节轻微,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或治安管理处罚的前置性措施。
2. 完善行政训诫相关程序制度
关保英教授认为,行政程序“关涉到一国行政法治的质量。”[11]现阶段,鉴于行政训诫在实践中的扩大化应用倾向,解决训诫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过分强调训诫的依据,而在于将训诫行为在操作层面上予以规范,完善行政训诫的相关程序制度,从而进一步使行政训诫沿着法治的轨道前进。
第一,建立行政训诫的执行规则和审查机制。行政程序的价值追求在于效率和公正。[12]程序上的公正在许多情况下能够促进并保障实体的公正。有必要制定关于行政训诫行为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例如行政训诫行为的实施准则和执行手册。在执行的过程中应当明确行政训诫行为的实效保障与违法性边界,防止行政训诫行为的适用不当、滥用现象。行政训诫的灵活性在实践中极易导致滥用现象,并且行政训诫的不当使用可能会造成极坏的社会及舆论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强行政训诫行为的程序规范,消除可能造成行政训诫行为滥用的因素,保证行政行为的公正、恰当。
第二,完善行政训诫的听取意见制度。在现代行政法中,告知与说明理由制度是行政法的基本制度,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要求。[13]目前我国行政机关听取意见的形式具有多样化,但行政训诫并未制定听取意见制度,在实践中极易造成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沟通缺失,并易使行政相对人产生对抗情绪。基于此种情况,有必要在行政训诫中建立听取意见制度。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训诫行为前,若其训诫内容涉及相关专业机构的业务时,应当听取相关机构的意见,必要时可协商处理。在实践中,基于行政训诫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在程序上给予行政相对人陈述意见的机会,对其保护自身权益十分有利,也会减少不当的行政训诫,同时能提高行政训诫行为的质量。
第三,训诫书应制定统一的文书格式。统一的文书格式可以大大减少实务中行政训诫行为内容违法的可能性。由于行政训诫行为在法律上的缺失,各地行政机关的训诫书格式不一。应制定统一的训诫书格式,训诫书至少应包括行政训诫行为的目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相关机构论证意见等内容,并且引用的法律依据应当具体而精准。
3. 明确一定限度内的事后救济
当前我国的行政救济体系是围绕具体行政行为而设计的,行政指导行为被排除在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范围之外。但应当注意的是,行政审判的重点应当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训诫虽然是行政指导行为,不产生法律效果,但仍存在是否合法的问题。对于内容及程序违法的行政训诫,应当考虑给予一定程度的事后救济。通过前述行政训诫相关判决及裁定,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行政训诫行为的内容是否合法并不进行审查。有学者指出,如果行政指导的内容确有违法之处,例如违反比例原则或者考虑不相关因素,就应当赋予当事人通过行政诉讼来救济的途径。[14]对于诸如作出程序违法、援引法条不清等存在内容违法的行政训诫,应当考虑适用行政诉讼的确认判决。此外,行政机关也应当对内容违法的行政训诫采取改正或者撤销的方式进行自我纠错。“李文亮医生事件”中,虽然公安机关因内容违法最终撤销了行政训诫行为,但这在很大程度是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也即是说,至少对于行政训诫行为,行政机关在大多数情况下缺乏主动纠错的意愿。故而有學者认为,只要行政机关在行政指导时存在故意或过失、错误或违法,就应对行政相对人予以行政赔偿。[15]在行政训诫行为中,因行政机关违法造成行政相对人相关权益受到侵害的,应当给予一定的行政赔偿。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行政机关主动纠错的意愿,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对行政相对人的事后救济。
四、结论
此次因热点事件而暴露出我国有关行政训诫方面的行政立法与执法漏洞,并且从该行为所引申出来的问题是:如何规制类似行政训诫在内的、无法律明文规定的行政行为,应是我国行政法学界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本文探讨了行政训诫在学理与实践上的分歧,尝试在不推翻已有行政裁定结论的情况下,将行政训诫行为的法律性质确定为行政指导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规制,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嫁接。它或许不能成为对于该行为的理想解决方案,但对于我国如何划分并规制类似的行政行为可提供有益的借鉴及思考。此外,对于行政训诫的法律性质界定,行政指导行为并非唯一的答案。但无论做何种界定,都应对行政训诫行为的规制进行严肃深入的审视。
参考文献:
[1] 王 锴.论行政事实行为的界定[J].法学家,2018(04).
[2] 王学辉.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的“训诫”行为的行政法分析[Z/OL].微信公众号“公法之声”,2020-02-08.[2020-03-01].https://mp.weixin.qq.com/s/J_jAib3WXorD1o2J31RBVg.
[3] 姬亚平.训诫的法律分析[Z/OL].微信公众号“西北公法学”,2020-02-14.[2020-03-03].https: // mp.weixin.qq.com / s /aECUbCITxPas66R6Zjv9jQ.
[4] 汪渊智.论民法上的事实行为[J].山西大学学报,2003(03).
[5] 翁岳生.行政法(下册)[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887.
[6] 應松年.行政行为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
[7] 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8] H.W.R.Wade,Administrative Law[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388.
[9]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06.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35-136.
[11] 关保英.论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J].社会科学,2009(07).
[12] 卢华锋,崔晓文.公正 效率——行政程序立法目的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06).
[13] 姜明安.实施《行政许可法》规范行政许可行为[J].法学杂志,2004(03).
[14] 曾 哲,郑兴华.行政指导的诉讼救济理论探析——以相对人权益保障为分析视角[J].荆楚学刊,2018(03).
[15] 吴 华.论行政指导的性质及其法律控制[J].行政法学研究,2001(02).
Discussion on the Legal Nature and Regulation for Administrative Admonition
Yi Mingjia
(School of Cyber Security and Information Law,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Abstract: Presently there is still an argument about the legal nature of administrative admonition. 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verdicts from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the basis of determining that the act of administrative admonition is an act based on administrative facts, it is therefore defined as a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act. Practically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arising from practicingadministrativeadmonitions it needs to clarify both key subject and scope in practice for practicingadministrativeadmonitions, improve relevant procedures management and allow using after-event relief measures.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Admonition; Administrative Factual Acts;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Legal Regulation
责任编辑:步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