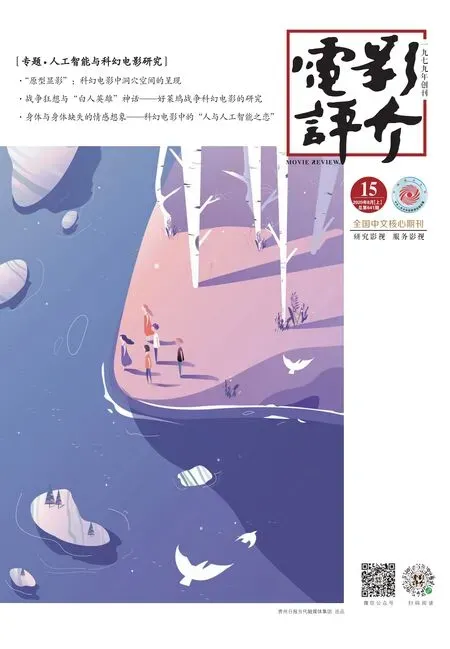面对黑镜:人工智能科幻影视剧中的“现实纹理”
2020-11-14郭晓丹
郭晓丹
人类社会中科技发展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技术进步本身,它还进一步缔造着新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伦理,即重塑着新的现实世界。科幻电影来源于当下现实也超越了当下现实,关涉到对于未来现实的遐想,具有寓言性质。正如英剧《黑镜》中的台词所说:“当你关掉手中的电子设备后,那逐渐黯淡的屏幕就像一面黑色的镜子,看见的只有你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幻电影这扇窗中所发生的事件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来自于人们对当下现实的审视与思考,以及对未来现实的推理与想象。所以科幻电影中不仅有单纯的“技术幻境”,还有丰富的现实纹理。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引发的一系列讨论不断进入民众的视野。伴随着“图灵测试”“人机大战”“奇点问题”等概念与事件的传播,人工智能技术从使人惊奇发展为使人惊诧甚至于使人忧虑。人们的忧虑分为两个层次:较为浅层次的忧虑表现为将人类与人工智能进行简单的善与恶、强与弱的二元对立,并因而担忧人类是否会被取代或毁灭;较为深层次的忧虑表现为,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将面临新的欲望追求、生活伦理与精神焦虑。针对深层次的忧虑,近几年的《阿丽塔》《她》《西部世界》《黑镜》《超体》等人工智能科幻影视剧都作出了讨论。正是由于这类影视剧中所呈现的近景与中景想象。使剧情牢牢扎根人性与生活,映射当下现实问题并呈现未来现实中的种种景象。
一、未来景观:现实世界的欲望追求
人工智能科幻影视剧与现实生活最直白、最浅显的关联就在于对普通人欲望追求的袒露,其中包含大快人心的决斗、复仇、抗争与自我实现。这些角色设置与剧情安排都是来自于人性中最容易被唤起的冲动,从这些现实冲动入手,能够寻找到激发观众观影快感的捷径。在不同时代,人们将这类欲望寄托于各种类型的“爽剧”中,如武侠剧中的快意恩仇,宫斗剧中的角色黑化等。在这类影视剧设置了更加新奇的情境——在空间布局上与现代城市截然不同的“未来城”,并在体能与智能上都提升了角色的上限阈值后,观众可以获得一种源出于生活但远远超越于生活的体验。人们将自己现实中想要达成却无法达成的欲望追求与理想抱负投射在这类影视剧中,如《阿丽塔》《西部世界》等。在这类影视剧中,人工智能是一种外在的“装备”,或智能上的“武装”,是更加偏向于工具性质的。这类表露普通人欲望追求的人工智能影视剧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奇观化的未来景观、“类人”的人工智能主体、被消费的欲望追求以及微观的现实主题。
首先,影视剧常常会缔造非常新奇的“未来城”景象。其中有一部分是极具科技感与未来感的景观,如《阿丽塔》中高阶层群体居住的悬浮的空间站,与当下人们所处的现实世界在视觉上有较大距离感;另一部分则是与现实较为接近的景观,甚至复制和还原了历史中的场景,如《西部世界》中的高科技实景乐园,人工智能的觉醒以及权力的较量是在这片古老的西部热土中,既有时代上的相互反衬又有精神上的相互呼应。《阿丽塔》中建构场景的元素主要是钢铁和水泥,营造了未来城市冷漠萧瑟、阶层分明的景象,反衬出阿丽塔在钢铁城市中追求爱情、勇敢奋战等一系列行为的动情与热血。《西部世界》中建构场景的元素主要是黄沙和树木,营造了一个弱肉强食、暗藏危机的西部景象,为之后人工智能的觉醒、反抗与血腥屠杀埋下了伏笔。影视剧中的“未来城”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又一个的想象空间,但这些奇观化的未来景观却充满了对现实的隐喻和对照,其目的也在于衬托主人公追求爱与自由或反抗强权暴力的现实精神。
其次,影视剧中的行动主体,是与人的外观或思想非常接近的赛博人或人工智能。在这类人工智能影视剧中,为了展示人的各种欲望追求并使观众获得共鸣感,行动主体在外形上或在情感上都非常接近人类,并且可以分为“机身人心”和“人身机心”两类。这两种银幕形象都是基于人类的外形或心智进行部分强化与改造后的结果,与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阿丽塔》中,主人公阿丽塔拥有半机械的身体,但在心智上同普通少女一样,充满了对生活的好奇与热情。《西部世界》中,主人公具有完美的人类外形,但是在智能上却远远超越人类。《阿丽塔》中“机身人心”的赛博人是钢铁构筑的未来城中的“人性之光”,而《西部世界》中“人身机心”的人工智能是具有超级大脑的“完美的人”。正如沙兹所说:“首创性只有在这样的程度上,以及当它只是加强了所期待的体验而不是根本改变它时才是受欢迎的。”通过“类人”的人工智能主体,观众可以联系和审视自身。
再次,这类影视剧中所展示的人类欲望与追求是非常能够唤起观众的一般情感的,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且迎合消费市场。这其中包含积极抗争、自我实现等追求,也包括逃离樊笼、以少胜多、激情复仇等在当下社会中被禁止的欲望,观众可以通过观影宣泄压力。阿丽塔因为机械身体而具有超强的战斗能力,阿丽塔甚至不需要成长过程,其超能力在生活娱乐和日常战斗的过程中不断显现,伴随着伙伴的惊叹、敌人的臣服,“天赋异禀”的阿丽塔满足了人们在短时间内获得个人成就的快感。《西部世界》中的人工智能则具有超越人类的思考能力,人工智能的觉醒与复仇,满足了人们的抗争诉求,这种抗争诉求在历史中可以找到许多印记,如黑人运动、女权运动等。无论是个人成就的满足还是抗争诉求的表达,都是来自于人们在现实中的欲望追求的折射。正如王峰所说:“科幻人工智能叙事中的未来其实深深地打上了当代文化烙印,因为这里的‘未来’不是真正的时间维度上的未来,而是经由文本想象的概念性的存在。在这样的‘未来’中,隐藏着当下科技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文化欲望,它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未来,而是包裹着多种元素的形式化的复杂的未来的显像。”扎根于现实中人的欲望追求,并赋予其得以实现的捷径,这类人工智能影视剧因而拥有较好的消费市场。
最后,这类影视剧关注的都是微观的现实主题,即相比于政治、经济、宗教等重大话题,它们更关注人的处境。《阿丽塔》中的主人公身处揭开个人身世谜团、对抗庞大利益集团、为所爱之人复仇等多重线索编织的故事中。《西部世界》中的主人公则身处在被限制、被奴役的游戏情景中。对照当下人们的生活,繁忙生活的困局与个人价值的迷思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症结,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淡漠与人的生活价值选择也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这类人工智能影视剧在建构炫目未来世界的同时,还揭露了人们在当代生活中所面临的细致而微的问题。
如《阿丽塔》《西部世界》这样的人工智能影视剧,虽然都搭建了奇观式的未来景象,但表现的仍旧是当下人们的欲望追求。影视剧中的主人公都不是经过了“彻底改造”的人工智能主体,即没有彻底脱离人类的身体与心智特征,也不像人们所预测的那样具有极端的不确定性。人工智能并非是深不可测的,也并没有带来真正的颠覆伦理的社会变革。这类影视剧是具有科幻魅力的,但是人工智能只能是一种装饰人物、修饰剧情的手段。在这里,技术是一种外在的工具,而非变革性的、决定性的力量。面对这类影视剧,人们不仅看到了自己,还将自己置于这个“梦空间”中宣泄压力、释放想象。
二、情感交往:人工智能时代的生活伦理
詹姆逊曾这样评价科幻小说:“科幻小说作为形式的一个重要可能性正是为我们自己的经验宇宙提供实验性变种的能力。”这段话揭示了科幻作品所具有的预测未来的功能。相比于呈现一些契合消费市场的较浅显的欲望追求,一部分人工智能影视剧将视线聚焦于新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生活伦理问题,如《黑镜》系列等。在这些影视剧中,人工智能的发展溢出了社会原有的伦理架构,开始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因而急需建立一套新的秩序来对一系列想法和行为进行协调和规范。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人工智能技术不再仅仅是一种“装备”了,技术本身也具有了表达的功能,并具有重塑世界的能力。技术也不再是辅助性工具,而是暗藏着推动社会生活转型的变革性力量。如《黑镜》系列中的《马上回来》《白色圣诞》以及《她》等。这类电影中的人工智能包含纯粹由算法创造的线上主体,也包含由科技创造的人的“身体副本”或“意识副本”。《马上回来》讲述的是女主角的男友在车祸中丧生,女主角购买了一个在外形上与男友完全一样的人工智能替代品,但最终发现这个人工智能“身体副本”在精神上的匮乏。《白色圣诞》则是由两个故事交织串联构成,其中包含完全脱离身体而存在的人工智能“意识副本”等元素。《她》则细致展现了人类与云端人工智能的情感交往。这些作品都反映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的道德法律、人伦情感的探索与思考。
(一)道德与律法之罚
这类影视剧中,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道德和法律惩戒的方式变多了,而这些惩戒方式脱离了现代法律的理念与框架,以人工智能科技为手段,在给人耳目一新感受的同时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道义上的惩罚”。如在《白色圣诞》中,波特犯下杀人罪且不愿供认,警察在他的脑中取出“意识副本”,并由谈判专家在线上的虚拟房间中与“意识副本”进行对话,“意识副本”的坦白使波特本人在不知情以及保持沉默的情况下依旧被判有罪。因而值得思考的是,“意识副本”是否能代表波特本人在审讯中发言,即在人工智能时代,当个人的意识与身体可以剥离,意识可以被计算机复制和改造后,法律的惩戒对象究竟是自然人,还是人的意识甚至是“意识副本”,甚至需要进一步思考这种线上的“意识副本”是否能够成为独立的法律主体。此外,波特本人在受到了法律审判的同时,他的“意识副本”将在线上的虚拟房间中受到囚禁,且在无需进食和睡眠的情况下,在播放着震耳欲聋的歌曲且无法逃脱的虚拟房间内受到无尽的折磨。警察在出门之前随意地摁下了1分钟1000年的时间设定,并将虚拟房间中收音机的声音调到最大值,面对这种“随性”的惩罚方式,一部分观众感到大快人心,另一部分观众则感到十分惊恐。惊恐的是相比伦理制度的完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先行一步,科技的惩罚手段朝着“道义”的甚至是“泄愤”的方向发展。
(二)身体与精神之爱
这类人工智能影视剧讨论了人类情感新的可能性,如《她》探讨了剥离了肉体的爱情,而《马上回来》则探讨了脱离了精神的爱情。人类感情被人工智能技术解剖了,影视剧探索了情感被解剖后所产生的多种可能的结果。《马上回来》对于缺失了人类精神复杂性的人工智能“身体副本”明显抱有悲观的态度,女主角在看到几乎是过世男友翻版的人工智能“身体副本”后表现出了惊诧与兴奋,但在深入交往后,发现这个副本只有人类的外形,没有回忆、情绪和思想,缺失了个体的独特性,仅仅是一个与人类在形象上完全一致,但内在依旧机械呆板的科技产品。在这部剧中潜藏着一个更加深刻的内涵,即将社会经验和思想情感界定为人的本质核心,由此,人工智能是无法替代人类的,更无法填补人类情感的空缺。而《她》则对脱离了身体而开展的虚拟爱情抱有部分认可的态度。影片呈现了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发生在男主角身上的,他对人工智能产生爱情的过程,揭示了人类爱情的发生所依托的熟悉、亲密、依赖、了解等精神阶段,另一条主线发生在人工智能(剧中性别为女性)身上,揭示了人工智能通过不断认知与学习所获得的知识积累、思考判断甚至是嫉妒与缺失。通过这两条主线,影片探索和发掘了人工智能与人类在情感交往过程中可能迸发的火花以及将要遭遇的问题。当人工智能升级换代,没有身体作为依托的人工智能迅速下线,瞬息万变的信息更迭给已然积累起的深厚情感留下了一片空白。
(三)社交与独处之境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们会趋向于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人们在生活中的兴趣爱好与价值取向是否会发生改变?在人工智能影视剧中,呈现出的是科技高度发达的背景下越来越私密的生活空间和越来越个人化的兴趣爱好。网络时代,线上社交取代见面交往已经使人们警惕,人们思考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否会因为网络技术、社交媒体的发展而变得淡漠。影视剧对人工智能时代人们生活方式的推测则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面对面社交进一步减少,线上社交进一步增加,人们甚至不需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人机互动成为了新的重要社交形式;另一方面,人们的情感需求变得更大,并通过人工智能的具身性和高度智慧来满足未来生活中越发凸显的情感缺失等问题。《马上回来》中,女主角与亲人、朋友之间的交往很少,影片以孤独冷清和与世隔绝作为未来生活的主要基调。《她》中,大街上每个人都通过耳机与自己定制的人工智能聊天对话,形成了一个个热闹但独立的城市孤岛。在未来世界的情感荒漠中,人工智能的声音甚至是更具有人情味的,与人工智能的独处成为了许多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回来》中的女主角与手机中过世男友的“意识副本”进行交谈甚至一同旅行。《她》中男主角则与人工智能发展为恋爱关系。在与人工智能的交往中,人们愈发缩小自己的生活交往范围,并更加深入地体察自己的内心世界。
三、精神牢笼:未来世界的时空搭建
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在《心灵、大脑与程序》一文中将人工智能分为“强AI”和“弱AI”,认为弱AI的主要价值是“为我们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而强AI主要是“带有正确程序的计算机确实可被认为具有理解和其他认知状态”。例如,《她》《黑镜》《超体》等人工智能影视剧中的强AI,不仅是智能工具,更是与人类在意识上接近,并拥有超常思维能力的新型主体,给人类世界带来的冲击不仅是现实的,更是精神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技术的发展不仅将改变现实世界的生活伦理,还将引发新的精神问题。而这个精神层面的问题指的不仅仅是对于人工智能战胜与毁灭人类的恐慌,在人工智能与人类强与弱、善与恶、输与赢的简单二元对立关系之上,还有人们对于未来自身精神世界的进一步聚焦,以及对未来人类精神困境的哲学思考。在这类影视剧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身体与意识彻底分离,促使人们进一步审视纯粹的精神问题。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异化时间与空间制造的一个个未来世界的“精神牢笼”,增加了人们的担忧与恐惧。这些都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精神世界笼罩了一层迷雾。在迷雾中,人们面临的是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的科技产品、无法把控未来社会的情感关系、无法预料意识抽离身体后所要面临的问题等一系列焦虑。
为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精神世界,这类人工智能影视剧做的第一步工作是将意识与身体分离,创造了一个个无需以身体作为依托的新型人工智能主体。正如张咏絮总结的那样:“在AI的形象上,经历了‘人形/有形——无形’的蜕变过程。”《她》中,萨曼莎是寄居在OS系统中的人工智能(剧中性别为女性),影片仅仅通过展示声音的方式勾勒出了一个鲜活的女性形象,萨曼莎带给男主角的交往体验和亲密感甚至超过了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马上回来》中,女主通过手机与过世男友的“意识副本”进行交流,并将其完全当成了过世男友的“替身”,这一点从女主摔坏手机后的情绪失控可以看出。《白色圣诞》中,人的意识被抽取复制,并被制作成人工智能保姆,一个不需要身体且仅存在于线上的复制的“我”。《超体》中,女主角在进化的最后阶段脱离了实体的存在,成为了弥散在空间中的“无所不在”的超体。由此,在彻底剥除了身体之后,精神与思维可以独立地存在,而观众的目光和思考也进一步地被聚焦到了纯粹的精神层面。
第二步工作,则在于通过异化时间与空间制造未来世界的“精神牢笼”,深化人们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恐惧感。这其中包含三种形式:
(一)无止境的时间
在《白色圣诞》中,一名女性接受了一项手术,她被提取并复制了一个永远存在于线上的“意识副本”,这个复制的“她”将被安装在意识存储器中,作为生活管家为实体空间中的她提供服务。“意识副本”具有线上的虚拟身体,但是在精神上不能接受自己永远被囚禁在虚拟空间这个事实。研发者为了与“她”谈判并使“她”妥协,实施了为期三周的虚拟空间“关禁闭”处罚,即让“她”在一片虚无的房间内无所事事地度过三周(现实世界中的一瞬)。因为精神驯服效果不理想,研发者又将“关禁闭”设置为6个月,在空虚中度过6个月的精神濒临崩溃的“她”不禁请求“请给我点事情做”。这样一个通过设置线上时间来驯化“意识副本”的过程,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恐惧。这种精神恐惧中包含脱离身体的恐惧,如“她”大声疾呼的:“把我放回自己的身体!”,也包含对无止境的时间的恐惧。影片最后,警察给杀人犯的“意识副本”设置了1分钟1000年的刑期,则将这种对无止境时间的恐惧推向了极致。
(二)戛然而止的时间
在《她》中,男主角里奥对人工智能萨曼莎产生了爱情。在这种纯精神的恋爱中,包含着亲密、依赖、担忧等复杂情感,当情感不断升温和加固,萨曼莎却要因为系统更新换代而下线。在交往过程中,萨曼莎的思维与感情淡化了其作为代码的本质属性,强化了其人性。但在系统更新换代的节点,它却作为一种科技产品而必不可免地面临被替换、被更新的命运,使里奥面对猝不及防的失去。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算法的产物,与人类精神存在着某种契合,甚至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并行、延续。但当人们如同以往一样期待长久的友情、爱情时,它却显露出其作为商业产品的属性,在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浪潮中被淘汰,而被培养出来的感情也戛然而止了。康德认为:时间不过是内部感官的形式,即我们自己的直观活动和我们内部状态的形式。在人生的长河中,一段段高度依赖的感情被擦除,时间仿佛失去了积累,一次次清零。人们在城市丛林中复归孤独,是又一重精神焦虑。
(三)没有边界/出口的空间
影片中,人工智能时代的“意识副本”所滞留的空间与现实世界有所不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居住的空间都是由特定的地理或物质边界来划定的,而《超体》中的女主角露西在不断进化后,身体消失了,弥漫的意识超越了空间的边界发展为“无所不在”的状态。现实世界中被划定的各种不同的功能性空间变得无意义。另一类给人造成精神焦虑的空间则是没有出口的空间。如《白色圣诞》中,被复制的“意识副本”都是寄居在线上的虚拟房间中,房间中或是一片空白,或是装饰得如同现实生活场景一般,如家庭厨房,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没有出口、无法逃脱。“意识副本”们在经由人工设定的空间里受到不定时的精神惩罚。在这样封闭的虚拟空间中,“意识副本”只能坐以待毙,接受审判的降临,且无从进行反抗,个体的无力感被强化和放大了。
结语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社会秩序及人的精神世界将面临一系列的改变。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谈到:“据说每一种文明自身就携带着自我毁灭的种子。这个种子可能就是那些引进新的社会形态、送走旧的社会形态的技术设备……技术设备自然要改变人们的习惯,并且必然改变社会的结构和功能。”在风暴之前,人们观看人工智能影视剧的过程即是面对黑镜的过程。在镜像中,人们思考和探索当下现实与未来现实。无论是体察人们的欲望追求、分析人工智能时代的生活伦理、预测未来世界的精神焦虑,都是在关注绚丽的科技发展之外那片现实的土壤中已经产生的或将要遭遇的变革,为眼前的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作出充分的社会、伦理、人文方面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