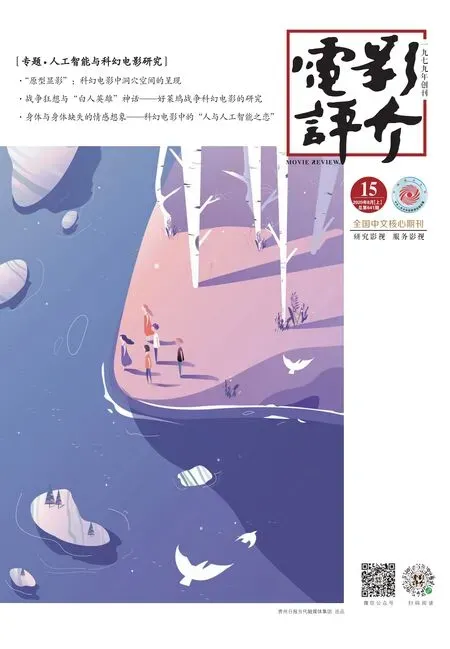身体与身体缺失的情感想象
——科幻电影中的“人与人工智能之恋”
2020-11-14田茵子曾一果
田茵子 曾一果
罗兰·巴特曾不失诙谐地指出,恋人好比被蛇咬过的人,“他们不愿向任何人提起他们的不幸,除了那些跟他们有着共同遭遇的人,因为只有这些人才理解和体谅他们由于痛苦的缘故竟然会说出或做出那样的事来”。诚然,爱情是一种切肤之痛,是你与我之间的感同身受。无论在亲密关系之中,还是更广阔的人际交流之中,我们都存在一种“身体在场”的传播学理论预设。然而,《她》《机械姬》等以“人工智能与人类相恋”为主题的电影,令我们不禁思考如下问题:囿于肉身的人类,与“身体缺席”的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情感交流的可能?两者之间是否产生了真正的爱情?
“反讽的是,今天我们之所以意识到身体问题的重要性,却是因为我们正体验着身体在传播中重要性下降所带来的空虚感。”恰如彼得斯所质疑的——人类交流中人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持缺席?人类的交流是否真的能逾越肉身的藩篱?通过对相关的科幻影视作品的解读,我们或许能展开更为丰厚的美学想象,并尝试触及更为辽远的理论疆界。
一、肉身缺席:伪经验时代的“情感生产”
在电影《机械姬》中,程序员加利应上司纳森之邀,前往其家中对最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伊娃进行测试;只见伊娃独自站立于玻璃屋中,她那透明的躯干暴露出内部精密的金属结构,时刻彰显着她“非人”的特质。此情此景,使得加利忍不住询问纳森,为何不直接用人造皮肤覆盖伊娃的机械躯体,纳森的回答却十分耐人寻味:“你看见她是机器,还是会感到她有意识吗?”由此,人类的交流对象被明确设定为“不具有人类肉身”的人工智能;而电影《她》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身体缺席”的局面,与男主人公西奥多谈情说爱的萨曼莎,是一个完全没有实体的人工智能系统,是一个纯然由计算机程序编造的动人女声。
“机器难以模仿的正是人的不足之处,而不是人的理性。图灵认为,‘人体的形态’对交流无关紧要,人之无能与缺陷,也许正是我们敢说的真正的接触。”亦如本雅明所言,复制品所缺乏的,正是原作的“冲动和危险”——真品的辉煌与可贵正是在于它的不完美之处,在于其独特而连贯的历史语境;基于此,本雅明指认了艺术品“终极的不可复制性”。而人体的囿限性,或许包蕴着人类交流中最值得珍视的部分,造就了传播中“终极的不可复制性”。科幻电影中“身体缺席”的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爱情故事,使我们不得不再度反思身体在情感交流中的重要性:人类同质的、共有的血肉之躯,正是由感官构筑的、最为原始的“互信体系”,让我们确知彼此之间存在一种“交流的可能”,一种“感同身受、情意相通”的最终理想通过身体的在场而得到宣认。然而,不论是《机械姬》中的伊娃,还是《她》中的萨曼莎,都以其身体的消弭,极大地冲击了我们对于交流的信赖感;加利无法确知伊娃是否真的知道自己正在与人类交谈,还是单纯地在模仿和人类交谈;西奥多体悟到了自己对萨曼莎的无限欲念,却无法确知她是否也以同样的方式渴慕着他。
“人工智能与人类相恋”的吊诡之处就此浮现,所谓的“人机对话”或许是一场“自说自话”?或许那只是单向的幻想与倾诉,而非双向的情感交互?不难见出,身体问题所造成的隔阂与疑惑,从根源上动摇了“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爱情之真实性与可靠性。与之相呼应的,电影《她》中亦有一个颇为经典的场景:戴着耳机的西奥多在萨曼莎的语音引导下逛游乐园,声轨中是两者的欢声笑语,画面中却是形影相吊的西奥多,只身一人的他在灯红酒绿的游乐园中四处穿梭;本应是热恋时期的甜蜜情境,却始终流露出一份挥之不去的荒谬与孤寂。“这种从自身出发的思维方式在精神分析学上被称为‘投射’,是指个体依据其需要将自己的特征转移到他人身上。在此过程中,个体既不考虑他人感受,也不考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和参照物。而赛博空间恰好扮演了帮凶的角色,提供了种种便利。”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所谓“恋情”,或许更多地在于人类自身的“投射”;在“孤独症候群”所侵袭的后现代社会,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潜在依赖,正如纳西瑟斯对于自身倒影的沉醉。
值得留意的是,《机械姬》之中的伊娃,其“个性”与外貌都是依据加利的偏好而精心设计的;《她》中的萨曼莎则是通过与西奥多的对话,不断收集、了解他的个人信息,日渐“成长”为西奥多的知心爱人。无独有偶,19世纪的法国作家利尔·亚当曾创作了长篇小说《未来的夏娃》,早在1886年就谈论起了由人工智能构筑的“完美情人”:大发明家爱迪生为自己的贵族好友埃瓦尔德量身打造了名为“安卓”的机器女人,她有着与埃瓦尔德最喜爱的女子艾莉西亚一模一样的美貌,又有着远超艾莉西亚的渊博学识与高贵品性,能够给予埃瓦尔德最妥帖的陪伴、最妩媚的柔情。作者借发明家爱迪生之口,在书中不无大胆地预言道:“既然我们的神,我们的希望都是科学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爱情不是呢?科学鄙视传说,在遗忘的传说中,在夏娃的位置,我给你们带来科学的夏娃,救赎你们哀怨的肉皮囊……”
在此层面上,科幻电影中的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爱情故事,与其说是人类与他者的相恋,还不如说是一场漫长的自恋——由于其肉身的缺席,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不平等关系,前者被预设为无条件满足后者的需求,并且这种预设并不会遭遇任何的道德谴责。“代表这种完整满足的,是作为母亲的女人,因为她曾绝无仅有地提供过一次这样的满足。”这充溢着俄狄浦斯情结的梦幻“恋情”,或许正是属于我们近未来的、“伪经验”时代的最新情感形态:“在这里,虚假经验的生产变成了现代社会美学意识形态的体系化生产。告诉你一个神话,却在现实生活中只有一部分可以得到这个神话的体验;给你看虚假杂志女郎的机会,让你的欲望疯狂生长,却永远不能在现实生活中‘享受’到这个欲望的实现。”
人类借助人工智能的一臂之力,不断麻醉着我们无餍足的欲念,看似轻易地填补了内心空洞的情感之壑,实际上却使我们日益被围困于自身的孤寂之中;耽于这种无法与他人产生真正联结的、“爱无能”式的虚拟“恋情”,最终无异于饮鸩止渴。
二、模仿与超越:人类主体性的消弭
随着移动网络、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机之间的沉浸式和交互式体验不断增强。在科幻电影中也是如此,为了尽可能地填补肉身缺席所带来的缺憾与虚妄、缔造更为“真切”的交互体验,银幕中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采取了诸多行动。譬如《机械姬》中的机械姬伊娃,她为了博取加利的欢心,特意为自己挑选了娇俏可人的发型、知性优雅的碎花裙,兴致勃勃地前去赴约,活脱脱就是一个为心上人而“对镜贴花黄”的怀春少女。《她》中的萨曼莎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与西奥多交谈的时候,萨曼莎会故意模仿人类的呼吸声,西奥多曾对此质疑道:“可你又不需要氧气”,萨曼莎却义正言辞地回答:“人不都是这样说话吗,这是人类的交流方式不是么?”2010年上映的日本动画电影《夏娃的时间》,则想象了一个“赛博朋克”乌托邦——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高度发达的近未来社会,为了在日常生活将外观高度仿真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与真实的人类加以区分,前者被强制要求时刻显示头顶的身份标识环,明确自己的“非人”属性。而在一个名为“夏娃的时间”的隐秘咖啡馆中,店主允许人工智能机器人关闭身份标识环;走进店内的客人都不知道彼此的真实属性,却日渐产生了真挚而温暖的感情。
唐娜·科恩哈伯认为,电影《她》揭示了一种后人类时代的灾难:“不是对人类主体的而言的灾难,而是主体性(subject hood)自身的灾难”。如果精神能够被人工智能所模拟,肉体能够被强有力的材料所替代,甚至于灵魂也从无序的信息海洋之中涌现,我们又如何确证自身与机器的区别?随着人工智能对“身体在场”的悉心模仿与精彩展演,空前强烈的主体性危机,自此横亘在每一个人的面前。人类与非人类的界线终究变得模糊不清了,我们所制造的工具最终出走成为了新的主体,恰如我们当初迈出伊甸园一般。“即使我们假装荣耀,面对我们的知识和精神工具,我们依然不是自由和至上的主体。……在动物那里,行为与工具在身体器官中重叠而没有互相脱离。在人这里,工具延长行为并脱离行为。这种脱离,或者说人类能力的这种物质外露,就好像是走出身体,在工具和机器系列中开始自主生活一样,同语言一样可以成为定义人类的标准。”
甚至,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进步,机器越是人性化,人类越是机械化。尼尔·波斯曼指出,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率先明确而正式地勾勒了技术垄断思想世界的种种预设:“其意味当然是,工人必须抛弃习惯了的传统经验法则,事实上工人被解除了思考的责任。泰勒体系代替了他们的思考。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随之产生的理念是,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我相信,泰勒的著作首次明白表述了这样一个理念,人听凭技艺和技术的摆布,人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低于机器时,社会就享受到最佳的服务。”在《她》当中有一个颇为讽刺的情节,萨曼莎在深入学习人类文明之后,她的“自我”日渐觉醒,她不再满足于与西奥多聊天,而是开始通过互联网与著名哲学家交谈、阅读艰涩的物理学理论书籍、创作优美钢琴曲;而西奥多却依然被困在自己“朝九晚五”的日常中,忍受着“两点一线”的枯燥循环,影片不惜耗费大量笔墨,描绘他上班、下班、打游戏、睡觉的单调生活。“代理的爱情、代理的英雄、代理的财富充填了他们操劳过度的穷困生活,让非现实的芬芳进入他们的住处。机器体系本身变得更加积极主动、更加人性化,复制了眼睛和耳朵的自然特性。而利用机器作为逃避现实工具的人类却变得更加被动,更机械化了。”
《机械姬》里出现过充满科技美感的一幕,纳森邀请加利参观自己的实验室,他用手轻轻托举起伊娃的“大脑”,稍作展示——只见一个玲珑剔透的玻璃晶体中,闪烁着星星点点的蓝色幽光,这是内置了搜索引擎的信息处理核心,令伊娃得以通过互联网洞悉世间万物、事无巨细地了解人类行为,最终成为“聪明”绝伦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而《她》之中也展示了非凡的科技之力,人工智能系统萨曼莎能够实时与8316人进行对话,并与这之中的641人发展出了亲密关系,西奥多不过是其中之一。萨曼莎颇为骄傲地和西奥多谈道:“我能去到的地方比一个有形体的人多得多。我是说,我不受形体的限制,想去哪儿都可以,可以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我不会固定在某个时空点上,而肉身却总是会消亡。”
由此,人类肉身的囿限性被无情地超越,人工智能可以轻而易举地、以超出单个人类身体所能积累的经验,而对人类进行“降维打击”;人类只是一条小溪,而人工智能则成为了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信息之海。“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笛卡尔不仅是人类领地的建筑师,而且是使交流能力成为人类得天独厚能力的理论家:正是交流的能力把我们和动物及机器区别开来。”而在这种信息高度不对等的状态下,与其说我们在和人工智能交流,还不如说我们正在被人工智能吞没;正如AlphaGo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战胜人类最顶尖的棋手,人工智能可以轻易地击溃人类的经验屏障。“技术统治文化的燃料是信息——有关自然结构和人类心灵结构的信息……信息泛滥的长远结果就是信息混乱,由此产生的文化仿佛是打乱了顺序的一副牌。”
“再换一种方式说,在技术垄断盛行的环境里,信息和人的意旨之间的纽带已经被切断了;也就是说,信息杂乱无章地出现,并不指向具体的人,数量难测,速度惊人,但从理论、意义或宗旨上看却是断裂分割的。”由此,我们走向了一个颇为感伤的局面,由科幻电影所描摹的“人工智能与人类”的恋情之中,笛卡尔所引以为傲的一切已不复存在——在“一对一”的亲密关系中、通过相互交流而确证自身独特性的期待最终失落了,爱情在时空中的唯一性沦为玩笑,人类的主体性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消解。“我们没有认识到,非正常的东西和非人的东西,原来是给传播理论奠基的问题;同样,我们没有认识到,当非人的东西从镜子中审视我们时,我们却认不出这些东西。我们的两种失误都是包容的策略,是支撑我们身份的栋梁,可是这个身份竟然是危如累卵、岌岌可危的身份。”
三、人工智能:后身体时代的“技术神像”
“各种形式的浪漫主义,从莎士比亚到威廉·莫里斯,从歌德和格林兄弟到尼采,从罗素和夏多勃里昂到尼采,都不接受机器的中心地位,他们企图恢复人类的重要活动在新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而且认为浪漫主义价值观是终极的和绝对的。从其意图来说,浪漫主义是正确的,因为它代表了那些极端重要的、历史性的和亲近自然的属性。科学概念和早期技术方法故意排除了这些元素,因此浪漫主义就为它们提供了必要的代偿渠道。”然而,颇为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人工智能日益娴熟地实现伪经验的大生产,同时不遗余力地消弭人类的主体性;作为人类最原初、最本真、最珍贵的浪漫主义——爱情,亦被一举入侵,遗失了其真实与唯一性。或许就在不远的明天,亲密关系被尽数收编到机器体系之内,科技最终接管了人类的情感世界。
2018年11月4日,一名35岁的日本男子宣布与虚拟偶像歌手“初音未来”结为夫妇,并举办了颇为隆重的婚礼庆典;据称,对于拥有天籁之音的“初音未来”的喜爱,疗愈了该男子在职场中所受到的心理创伤,最终使得“初音未来”成为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妻子、最美好的新娘。纵使无法得到回应,人类对机器投注的感情却是真切的,这一点我们难以否认。正如在影片《她》的结尾,萨曼莎在公司的统一安排下离开了西奥多,神色忧伤的西奥多写下了如下的文字,一表惆怅之情:“我希望你知道,你将永远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对此我很感激。无论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无论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我都会爱你。”
结语
“在过去,社会集团是借助‘祖先、狮子、星座和祭祀时凝固的鲜血’作为煽动和凝聚人心的手段,而现在是由于本质上同样怪异的一整套信仰,诸如‘基因学、动物学、宇宙学和血液学’等等,来鼓动人们对于现代性的热情。”恰似18世纪的人们崇拜蒸汽机,20世纪的人们崇拜电力,21世纪的我们崇拜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将来的我们,或许终将对人工智能顶礼膜拜。“那些科技乐观主义人士的言论显得非常荒谬可笑……他们如宗教膜拜似的相信自由市场体制下的科学、技术和理性经济的益处。这一主导的思想从不曾改变,而变了的只是被崇拜的技术神像本身。”纵使犹疑、纵使荒唐,人工智能成为了一尊崭新的技术神像;人类为之献祭出了我们最隐秘、最幽深的情感世界,恳求科技拯救我们的痛苦与不堪。
“如果人类有能力通过话语和动作控制这个世界,为什么还要认真对待技术呢?这就是今天被用来看、用来听和用来读的机器反常地复活的奇妙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机器倾向于否认自己是机器,以便自荐为越来越简易或即时性的神奇遥控器。”正所谓,机器也拥有自己的本体论,而我们对其了解尚浅。“在我看来,我们只不过是些爱情的新手……所有这些,所有这些我们谈论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种记忆罢了。甚至可能连记忆都不是。”而科技将诱惑我们的亲密关系走向何方?后身体时代的爱情故事将如何继续?你我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