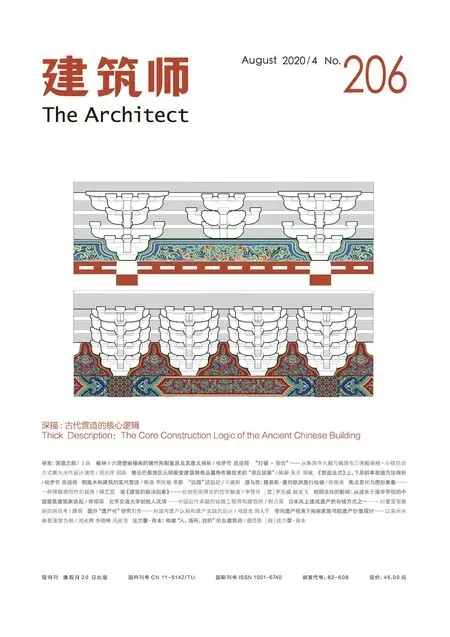日本风土建成遗产的存续方式之一
——对妻笼宿案例的再思考
2020-11-09潘玥
潘玥
日本自明治维新至1960 年代,逐渐新建为亚洲西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自柯布西耶提出“住宅是居住的机器”,住宅作为工业产品在日本到处泛滥,日本国民渐生“故乡失落感”。随着现代主义危机真正到来,后现代主义兴起,日本学者开始就本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反思。京都大学教授西川幸治在《日本都市思想》中提出“保存修景计划”,提倡以传统街区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将原来的环境印象保存下来传给后世,例如1970 年代日本爱知县五箇山的传统民居“合掌造” 的保存,对于风土建筑标本保存和修复的投入已等同于文物的标准。[1]
日本长野县木曾町妻笼宿是传统村落保护[2]的优秀案例,改造周期长达15 年。1955 年时,妻笼的观光化因毗邻马笼宿的发展一并触发,两者作为旧中山道的宿场町,也被并称为“妻笼·马笼”(图1、图2)。[3][4]
1967 年,当地政府谋求对妻笼宿进行观光开发规划,邀请到东京大学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太田博太郎加入观光计划制订。太田教授经过仔细调研后认为,妻笼宿遗留的江户时代即幕府末期的古宿场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年代价值,应当对妻笼宿进行完整保护,以保护来带动观光开发。[5][6]学者和当地政府以及民间组织三方在紧密的配合下,进行了第一、第二次保护运动,妻笼宿渐渐出名。至第三次保护运动时,也就是在1975 年,日本政府受到妻笼宿地方团体立法的促动,修正全国的《文化财保护法》,将类似于妻笼宿这样的古老聚落和街区追加为文化遗产保护对象之一,将这一类型称之为“传统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区”。南木曾町借此获得国家补助金,将妻笼宿第三次保护计划顺利地进行了下去。
与毗邻的马笼宿相比,妻笼宿的保护与再生计划耗费了大量时间和人力、财力,但是成效极好。1986 年以来,妻笼的观光人数和收入均大于马笼,营业收入远超支出。1968 年妻笼有22000 名观光客,至1969 年达5100 人,至1970 年达到146000 人。1972 年以后,每年达到50万~60 万人。现在的妻笼已经成为日本乡愁的代表。NHK 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不停走在街道上的旅行》(街道テクテク旅)记录了原短道速滑选手河原郁恵踏破铁鞋寻找母亲小时候所见的街道,终于找到妻笼宿,将在街道上拍回来的照片递给母亲时,母亲说道:“我有一张一样的老照片,正是在生你之前拍的”,此景让观众大为感动,妻笼的美名传遍了天下(图3、图4)。

图1:日本妻笼宿寺下地区上嵯峨屋附近

图2:日本马笼宿

图3:妻笼宿每年11月举行的“文化文政风俗绘卷之行列”

图4:“文化文政风俗绘卷之行列”中的嫁女队伍行走在中山道上
回顾妻笼宿的保存运动始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保护过程中伴随着一项社群民主进程下催生的遗产自我教育制度,起着主导作用,并注意到其实质是最终搭建产生的社群风土建成遗产的“照管体制”,这一系统至今仍然在妻笼宿的保护中发挥着很强的作用。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完全由妻笼当地自发形成的遗产保护性社群,其中融入了住民意识,形成了“妻笼共同体生态系”。这一遗产“照管体制”对于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具有丰富的意义。首先,这是有机的遗产保护体系,能够应对日常各种不利于遗产保护的变化因素。作为保护机制多样性的呈现,以及一种更有潜力的遗产保护的可能性,民间社群自发组织引领下的社会价值的实现,将是NGO(非政府组织)进一步发展的借鉴。其次,这种社群参与保护的程度是极深刻的,保护过程是紧密联系当地社群的。因为社群的原住民自发构建保护系统,所以体现着当地人的思维特点,被附着了很强的感情依赖和传承习惯。再次,是更为人性化的保护举措,原住民不会因为保护的实施被迁出,而是作为保护的主体,参与遗产保护,参与乡村发展的进程,社群住民的积极性得到最大限度发挥。最后,这种保护也是可持续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原则中着重指出在城乡可持续发展中“平等”这一原则所蕴含的文化权利,即支持社群全体公民对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的所有感。社群参与风土建成遗产的保护过程,同时伴随社会文化与经济的转型,也伴随人这一主体的自我教育和社会性成长。
以下,本文将基于原有的案例调查,再次考察妻笼宿从1960 年代起所经历的保护演进阶段中的社群保护运动发展进程,包括江户时代遗存——妻笼宿的历史、遗产保护政策评价、原住民参与度、社群构建遗产自我教育体系等方面的内容。笔者试图在新的文化政治语境下再思考日本风土建成遗产延续和发展方式的条件、问题与适应性,以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当代风土建筑遗产保护和进化阶段提供有益的参考;同时将揭示当地社群和社会的特殊性所在,这些社群具有的能动性为何,以及为何这一保护运动中由当地人承担风土建成遗产延续和建设的主体,社群主体的能动性又如何发挥更大的建设作用。
一、社群遗产教育制度的萌芽:住民意识与妻笼共同体的组织内发展
1960 年代,由于日本政府推行《国土综合开发法》,造成乡村过疏化。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带来的后果则包括通货膨胀、两极分化、大都市人口过密化和农村人口过疏化等。日本尽力推行的高度经济增长政策下,实际鼓励第二产业,农村的劳动力外流到都市,自然环境受到很大破坏,各地公害频发,都市集中了过量的人口。在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下,人们对于这样的生活逐渐开始反思,重获人在生活和文化中的主体性在日本各地初露端倪,而妻笼的动向就是这一浪潮中最集中的体现。妻笼共同体的逐渐形成与妻笼的文化有着非常切近的关系,考察妻笼宿保存的运动源流可知,住民意识的思想基础恰恰是从战后妻笼文化——演剧——研究的发展开始的。演剧研究肇始,妻笼宿保护中两个显著的产物——住民宪章和相互扶助原则,在社群参与保护全过程中起了极大作用。
妻笼地方体在一种较为特殊的条件下生成,有其个性。在1948 年,妻笼公民馆成立演剧研究会。妻笼公民馆被认为要培育民主主义社会的人,其“谈话守则”是这些活动的产物。战后初期演剧活动的主体是妻笼的年轻人,比较有名的曲目如《王者与预言者》,将王者(权利阶层)和预言家(庶民)的关系进行了戏剧化的阐释,庶民的智慧得到自身的认同,而“谈话守则”便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并被认为是民主主义的遗产,谈话守则对于后续的妻笼宿保护运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每一栋妻笼宿的建筑,并非只是住户个人的问题,而是全体住民所共同面对的问题 (图5、图6)。

图5:1980年(保存运动后)妻笼宿航空摄影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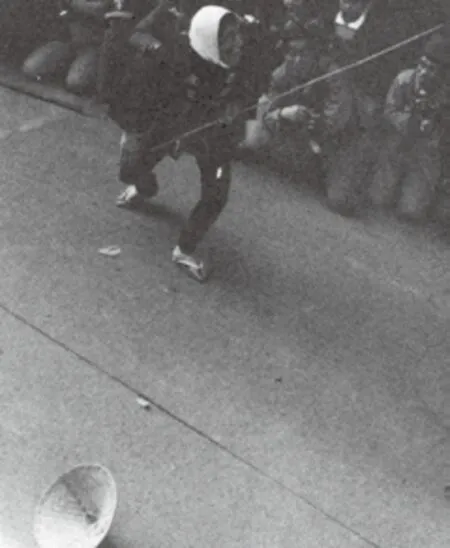
图6:妻笼宿演剧研究会的演员
1950 年,为了反对战前的封建支配层,妻笼御料林解放加速了地方民主化的进程。1955 年,妻笼宿成立制茶工厂,发展农业。但与此同时,妻笼町村合并,形成更极端的乡村过疏化,农业不振。政府颁布的《六割农民切拾》,规定林山属于皇家,使得妻笼农业不振加剧,1960~1966 年,国道19 号线开通,人口大量外流导致总人口数剧减。妻笼公民馆活动的积极分子,意识到爱乡的重要性,自1964 年起自发收集乡土资料,1965 年组构了“妻笼宿场资料保护会”,在结成意趣书《妻笼宿场资料保护会》中指出:“在我们的妻笼,每家均有继承自祖先,对于日常生活没有用处但却非常宝贵的民俗资料和文化遗产仍处于沉睡之中……为了保存这些大量的乡土资料,我们结成这一妻笼宿场资料保护会。在组织上,作为妻笼分馆的小组活动的一环,进行组织和运营,以发现、保存、整理资料为主要目的。将来,设立资料博物馆,给很多的学生和一般的游客,以及宿场研究者的学术研究和观光提供参考和便利。”这一资料保护会继续吸纳了公民馆、妇人会、青年会的很多组织,一直得以延续。在妻笼的战后发展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在随后的妻笼宿保护运动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个组织完成的第一件比较大的事件,即对于奥谷胁本阵的保护(图7)。经历了这次成功的保护活动之后,保护会人员得出共识:“活用宿场遗迹,是地方的人们生存之道”。随后组成第二个重要的地方体保护组织“爱妻笼会”,通过了《住民宪章》,提出著名的“不售”“不借”“不拆”三大规定(图8),随后开展了15 年的妻笼宿保护运动,吸纳了妻笼全体住户参与保护运动,形成罕见成功之举。[7]
可以发现,妻笼这一地域在经历剧烈变动之前(变动指的是妻笼宿场自昭和初期停止其机能),其住民的主体性危机经历了再次确认。而这是因为二战后妻笼有了公民馆进行文化活动,对于战后乡土再建主体性的发现有奠基的作用。但是,正如妻笼宿保存运动的报告书中陈述的,“在高度的经济发展政策下,提到所谓的日本人的故乡时,可以解读出近代文明冲击下人们共同感受到的压抑。1970 年代时,在妻笼的运动,实际上给全国范围内的保护运动带来了很大的益处,其价值被充分肯定。这样的运动的连带化被得到认识。但是,并不意味着妻笼的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地域化运动。其本质并不是‘地域中心主义’,只适用于一个地域。而是从地域出发,推而广之,从全日本历史和社会的维度上进行的一种创造。社群民主进程的成果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地域自我主义,而有着其在推动地方传统和文化遗产保护上的普遍意义。”[8]

图7:奥谷胁本阵住宅修复后

图8:1970 年代《住民宪章》写有“不卖”“不租”“不拆”
到了1970 年,爱友会成立,继续进行文化推广活动。从妻笼公民馆建立,至1970 年代完成保护运动,期间妻笼社群建立乡土资料保存会和爱妻笼会,形成互助原则和住民宪章,基本可以视作社群参与妻笼保护运动下形成遗产自我教育体系的标志。
二、乡村保护运动和地方社会发展进程中妻笼宿社群的推动作用
战后至1955 年,妻笼宿附近的马笼宿因岛崎藤村的文学作品而兴起观光热潮。1952 年,在马笼本阵的藤村宅迹建立了藤村纪念馆,为岐阜县指定文化财。因被诟病“马笼宿已落入俗套”,“像妻笼宿这样保持下去更好罢”这类声音随之出现,引发木曾郡向妻笼引流观光客的探讨,妻笼的保护意识随之萌芽。[9]
1961 年,吾妻村、读书村、田立村合并,南木曾町诞生。7 年后,妻笼地区人口从1757 人减至1347 人。为了发展南木曾町,町长片山亮喜制定了《南木曾町主要政策五年计划》(后文称“五年计划”)[10],计划包括道路整备计划、教育振兴计划与观光开发计划几个部分。计划自1964 年起执行了5 年。片山亮喜町长针对国家的“广域行政”提出“狭域行政”,以应对国家经济高速成长期。观光开发计划指出,南木曾町的自然环境是一大观光资源,而旧中山道的开发,可设计古道漫游线路、妻笼乡土馆、国民宿舍等进行开发。教育振兴计划强调基于乡土民俗资料的保存和文化财的保护,并公开保存于妻笼乡土馆的资料。这一计划是妻笼当地初次结合观光与文化财保护的尝试,町长又在1961 年8 月成立了南木曾町观光协会,与1965 年所成立的乡土资料保存会和1968 年成立的爱妻笼会一同,为观光进行调查和准备工作。
其中,乡土资料保存会一直试图继续扩大保护活动的范围,构想着宿场的町并保存[11],适逢“长野县明治百年行事”,住民曾自发拍下妻笼宿的照片进行投选。1968 年,新的住民组织爱妻笼会构建后,定下“三不”原则,至1971 年形成了重要的约束条款《住民宪章》。事实上,所谓的爱妻笼会是一个需要全体住民参加的组织,这种全户加入的实现,对于保护运动的顺利开展有很大的促进。
《爱妻笼会会则》第4 条,写明的该会活动内容如下:
1.妻笼地区的文化遗产(有形、无形、民俗资料,纪念物)的“补完”运动;
2.保护宿场;
3.保护风致;
4.区民的学习活动(讲演会、讲习会、展示会、先进地考察学习等);
5.其他必要的获得认可的事业。[12]
爱妻笼会实行的是妻笼全体住户都需加入的组织,在具体组织上,每四户出一位代表参与,共60 人,组成代表议员会议进行对话,并确立关于妻笼的从保护到再生的原则。那么为何爱妻笼会决定妻笼全户加入?原因在于:
1.妻笼的住民本是江户时期中山道的木曾道部分宿场的旧户,为了使得再生计划有效实施,需要全体住户参与。
2.街区的特殊形态决定了需要从点到线面的统一保护,因此需要全体参与。
巧合的是,妻笼自发形成的共同体所具有的保护理念与中央文化引领人物的意见方向一致。1967 年11 月至次年2 月,南木曾町政府委托东京大学建筑史研究专家太田博太郎先生对妻笼进行了保护调查,在调查报告中,太田先生向长野县提出关于妻笼观光开发的重要方针——整体集落保护。[13]
长野县和南木曾町政府后续主导的保护计划实际上都是基于太田先生这次提出的保护理念而展开的。长野县于1968 年提出的《旧中山道妻笼宿调查报告》,对构成宿内景观的各要素进了具体的评价。区别于仅将妻笼视作近代宿场町景观的角度,此报告对自然景观给予了重视。宿内的道路恢复旧路面石砌铺装,对侧沟、水流进行复原,下埋电缆等基础设施,将围墙作为景观要素进行考虑,统一新旧围墙的观感。[14]1968 年3 月,长野县向町政府提出《妻笼宿保存计划基本构想》(以下简称《构想》)报告书,再次重申观光开发不能对妻笼宿的保护计划造成影响。同时,对妻笼宿历史景观的保护将以更多地向公众开放为目的,且保护和观光不能以牺牲原住民的生活便利为代价。妻笼宿的保护不是完全的历史复原,而是考虑了复原的“传统生活空间再构成”。也就是说,人们感受到的旧街道的氛围主要来自于建筑立面,街道立面后的建筑,如果不妨碍历史景观,可大胆筹划创造具有历史感的景观氛围。在“保护整备构想”一节中, 《构想》对建筑物进行了保护阶段的划分:
历史的、景观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具有复原可能性的:尽量使其公有化,进行复原保护。
纳入经若干整修维持历史景观的建筑(允许内部变更);
纳入经大幅修复维持历史景观的建筑(允许内部变更);
不显示历史景观,但并未扰乱氛围的,以一定规律维持历史景观的建筑;

图9:妻笼宿历次保护实施情况
对历史景观造成明显不和谐的需拆除的建筑。[15]
后续问世的三次保护计划以及各类报告书虽对上述《构想》有所改动,但基本以其为基本方针。南木曾町政府则于1968年8 月发表《观光开发的基本构想》,按照太田先生的方针与长野县的《构想》,确立对旧中山道的三留野、妻笼、马笼三处集落进行整体保存。由此,对于妻笼宿场的保护成为观光开发计划中的核心部分。
至此,妻笼宿保护计划中最为重要的“全体保护”的构想成形,这一理念并不来自国家层面的推动,而首先是妻笼地方社群、町政府与县政府、专家学者三方在制订观光开发的计划过程中的自发产物,这在日本也从未有过先例。
从1968 年开始,妻笼宿保护和再生计划前后共进行了三次(图9),历经15年结束。三次保护计划耗资5.77 亿日元,用于建筑物保护修缮的费用为1.59 亿日元,单栋耗资约112.8 万日元(1.59 亿/ 141 栋),按照1970 年代汇率,折合人民币33800 元左右,考虑1970 年代人民币购买力,大约相当于现在的450 万人民币,单栋建筑的修缮花费可谓不菲。而5.77亿日元的大部分则花销于基础设施的改进上,包括修路、消防、停车场等,总额4.18亿日元,大大超过了在修缮建筑上的花销。再看其资金来源,政府2.79 亿日元与地方自治体2.98 亿日元的份额,投入比对半开。
妻笼宿第一次保护计划的实施耗资3600 万 日 元,持续了5 年,于1968—1970 年实施,以寺下地区为主,被称作“第一次妻笼保护事业”。这次保护计划基于太田先生的基础调查而成,共完成26 栋建筑的整修与复原。其中解体复原3 栋,大规模修理12 栋,中等规模修理6 栋,小规模修理5 栋。这一次的保护计划成果体现为妻笼乡土馆入馆人数的快速增加。1968 年的入馆人数是3500 人,1970 年则达到93000 人,增加了近30 倍。
1971—1975 年期间,町政府独立进行了新一次的保存计划,被称作“第二次妻笼保存事业”。这次计划的实施范围较第一次扩大,对妻笼的恋野、上町、中町、下町、尾又地区共58 栋建筑进行了保存和修复工作。同时也对消防设施、宿内道路(石铺)、公共设施进行了改修。

图10:妻笼宿寺下地区光德寺附近图

图11:妻笼宿寺下地区修复的建筑“出梁造”细部
1971 年由爱妻笼会举行的妻笼住民大会,通过了《住民宪章》(《妻笼宿守护住民宪章》),提出以保存为优先的原则,遵守“不卖”“不租”“不拆”三大规定,以及保存优先的原则,排除来自住民以外的外部资金进入。值得注意的是其强调的三不原则,相对于南木曾町政府《旧中山道妻笼宿保存和调和》(1968 年2 月)而言,前两个“不”显示出妻笼共同体更为强调抵抗外部资本和抵抗俗化。南木曾町的修正十分及时,基于《住民宪章》,在2 年后即1973 年制定的另一部地方性法规《妻笼宿保存条例》提出,在妻笼的宿场景观区域、在乡景观区域、自然景观区域中进行任何的新建与改建活动都需获得町长的确认和许可才能进行,并针对濒危建筑形成补助金制度。
自下而上的保存运动和活跃的地方自治体保存立法,也推动了日本国家立法的完善。1975 年,日本文化厅对于古老集落与街区的保存立法进入新一轮修改,并于同年7 月修正颁布新版《文化财保护法》,追加了新的保护对象——传统的建筑物群保存地区,将其纳入文化财保护对象名录,提供国家补助金。以此为契机,1976 年4月,南木曾町将1973 年制定的《妻笼宿保存条例》进行了一次修改,同年6 月确定新的保存计划,将妻笼宿的保存面积扩大到1245hm2;同年9 月,妻笼宿入选日本第一批“国家级重要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并完成“第三次妻笼保存事业”。这次保存计划将国家补助金首先用于较为重要的消防设施的改造,并对宿场共计57栋建筑进行保存和修复(图10、图11)。[16][17]
三、城市化进程中社群参与乡村风土建成遗产保护的积极因素和亟待优化的空间
历经15 年的妻笼宿保存计划,逐渐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肯定,获得了“日本建筑学会奖”“日本设计协会奖”等奖项,并受到社会各界肯定。其中,日本建筑学会公布的评议总结了妻笼宿保存得以成功的原因:得到作为地方自治体的事业、当地住民协力的保护、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学者的三方推动;在保存与观光开放一直以来的对立中,妻笼宿很好地融合了这些矛盾;不仅限于单栋建筑物,而是将集落周边广大的自然区域作为保存事业的一部分。[18]
正如日本建筑学会总结的,妻笼宿保存的成功来自地方自治体的执行力、当地住民被激发的热情,以及学者对科学保护理念的固守。除这三方面的助力外,尚得益于媒体的宣传和国家政策的跟进。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妻笼的保存运动是自下而上进行的,民间的保护组织,即妻笼共同体,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形成一种遗产照管体制。在保护开展的运作机制上,这种照管体制有制衡“利益一边倒”的关键作用。
小林俊彦先生深刻道出了不同价值诉求如何平衡的原委:“利益组织(观光协会)与保护组织(爱妻笼会)中,保护组织防止了以经济利益为先导的决定,保护组织所不能完成的调用资金,由观光协会承担。因此,即使是观光化保护,也可以在预想到其结果之前就进行地方组织的搭建,进行较好的平衡。”[19]
另外,这一社群形成的遗产教育和照管体制仍然在发挥作用。自1970 年起,妻笼的观光客一直在持续增加。1971 年间39 万人,1972 年达到54 万人。自此以后,每年观光客数量均达到60 万人以上。伴随着观光客的增加,妻笼彻底摆脱了贫困,但是也处于新的种种矛盾之中。随着观光客的增加,需要在利益和理智之间取得平衡。在1974 年的时候发生了住民拒绝观光客到来的现象,原因在于,由于观光客的增加,住民每日忙于接待,生活上受到很大压力,无暇照顾儿童与老人的问题也逐渐严重。为了更好地应对,爱妻笼会在1977 年组织了妻笼冬期大学讲座,并每年举行一次,对妻笼保护和观光现状进行反省。爱妻笼会提出今后保护妻笼宿的方针:基于地域振兴的目标,需继续坚持保存优先的原则,即“不忘初心”;遵守《妻笼宿守护住民宪章》与《妻笼宿保存条例》;尊重地域个性,妻笼宿的自然与历史环境属于全体住民,继续整体和活态地保存物质环境与住民生活[20];坚持住民、行政、学者三位一体的保护模式[21]。从更大的区域范围来说,需在以传统形式保存下来的木曾十一宿里的马笼宿、妻笼宿以及奈良井宿的街道中,赋予木曾谷再生的可能,以此挖掘这一区域的新价值所在。[22]
综合对妻笼宿的历史、遗产保护政策评价、原住民参与度、社群构建遗产自我教育体系的考察,在学习日本风土建成遗产延续和发展的条件、问题与适应性等方面尝试进行如下的反思和探讨:
第一,相对于其他类型的遗产,对于风土建成遗产的延续和发展来说,要尤其重视社群参与的问题。由于物质实体表面的材料已经形成了所有者的分野,风土建成遗产中最难以进行保护的恐怕是木质遗产,多体现为风土民居,其所有者对应的人是广大的老百姓。即使专业人士认为这一类型的遗产需要延续和发展,但是因为其量尤大,维护状况不佳,单纯依靠国家力量和专业人士的力量,都很难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只能更多依靠这些遗产自身的所有者才能进行可持续的保护。但是目前大多数老百姓的遗产意识非常薄弱,妻笼宿因为有着极强的社群驱动力成为例外。因此,要研究这种独特的社群遗产自我教育体系是如何构建的,保护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影响体现在何处?从妻笼宿的例子中可以注意到,木曾处于长野县[23]山野之中,妻笼更是在深山之中,相互扶助原则下的共同体的生存方式是妻笼独有的。这种共同体,是在当时的时代下和体制下,根据自身的生存需要产生的自我保护方式,这种共同体反对强权,是在民众与旧权力阶层对抗的过程中产生的组织。在妻笼的演剧和流行的诗歌,譬如《木曾诗集》(解放诗集)中,充满了这种“弱者连带”的意识,因此妻笼共同体的自立基础来自于地方社会的独立体本质,这便被称为“妻笼文化”。再加上战后,妻笼二次受到中央文化的影响:第一次是关口存男和米林富男进行的文化教育活动;第二次是以太田博太郎为中心的妻笼宿保护运动的开展。妻笼文化继续发展成了一种感性、内向、与共同体的基础根源联系紧密的思想,而这恰好是遗产教育和照管制度的主体性基础。
第二,社群逐渐形成的遗产自我教育体系还有可能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不仅将建成遗产的壳保护下来,其看不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可能一同有机而自然地保护下来,这就将包括节庆、礼仪、风俗等活态形式的遗产内容在内。比如妻笼宿在11 月23 日的文化文政风俗绘卷的保 留[24],万人欣赏,居民获得自我认同和文化的尊严,这是一种可贵的看待风土建成遗产保护的整体维度,给予保护人士的提示便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将可见的与不可见的遗产一同保留下来,不仅仅在立法上,还需要在社群中体现一种更健康、更可持续的遗产保护方向(图12)。进一步看,妻笼宿的演剧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在这种遗产教育的引领下,对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反向的促进表明,这两者本就是不能分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充分结合,使得遗产的保护是活态的,人们真正有了拥有此物的感觉。

图12:1980年间妻笼宿的文化文政风俗画卷
第三,就日本的经验来看,妻笼宿(高山、金泽等山村)的保护并非是由日本的历史街区价值和保护理念在当时就已经成熟而产生的结果,而是这些特殊地域有着“爱乡运动”这一历史背景,还要进一步考虑到由于国家政策下壬申户籍和町村合并共同导致的结果:伴随着战后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乡村人口逐渐减少(图13)。1961 年,吾妻村、读书村、田立村合并,南木曾町诞生。村合并当日,乡村人口数10771 人,至7 年后,人口减为8264 人;妻笼地区人口则从1757 人减至1347 人。町长片山亮喜制定了“五年计划”,正是地方苦恼于“过疏化”的问题,于是地方自治体和社群自发将希望寄托在观光策划上。类似的例子还有日本古川町濑户川的农村改造,1968 年起,以饲养3000 条锦鲤为契机治理污水。经过几年的坚持,河流变干净了,锦鲤图案也成了当地的代言。除了改造自然环境之外,新建筑改造都以传统风格为首选,并在此基础上复原传统工艺,使用榫卯衔接,在出檐、隔栅、斗栱上保存木造工法,斗栱上的“云”装饰作为当地工匠的名片,提振了工匠热爱传统工艺的信心,并且兴建“木匠文化馆”(图14),展示当地木匠文化。在这些基础上,复兴民俗活动,譬如每年1月举行的三寺参拜等。而以上这些行动并非是官方行为,而是由该村的村民自发进行。政府的出资以及在这些推动下进行的立法活动,是由这些地方的民间力量进行的。
第四,妻笼宿所包含的时代综合因素与风土建成遗产面对的现实问题与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情况多少有些类似。通过对于妻笼宿基本保护过程的回顾,日本在1960 年代兴起的历史町并保护运动,包括其对于町并的调查方法,对于文化遗产价值认识,是伴随着想要振兴本地区的“造町”思想,解决城乡传统流失问题的迫切需要被构筑起来的。保护町并成为地方公共团体制定条例的对象,被认定为文化遗产。这些运动最后得到的成果是1975 年修正《文化财保护法》,最终导入了传统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区制度。可以说,地方自治体和社群的遗产教育制度在保护中自始至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这些较为成功的案例,并没有遏制日本农村过疏化的总体趋势,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以妻笼为例,1970 年代妻笼完成改造以来,尽管名声大振,其人口仍在持续减少。目前依然面对着人口持续减少的问题。教育制度是否只是上一代的文化癖好和传统惯性?年轻人为何不愿意留在乡村?笔者在实地考察妻笼宿时,对比毗邻的马笼宿发现,马笼宿虽然是一个没有如妻笼宿般严格管控进行标本式保护的例子,但是生活气息较妻笼宿浓厚,具有一定的活力,这也在提示我们,风土建成遗产的延续和发展不能完全等同于维修文物建筑,其成功与否是存有多种评价机制的。
最后,作为中国的保护工作者,学习日本风土建成遗产延续和发展方式时还需要注意,相关问题需在一种缩小城乡资源差别的情况下讨论。日本乡村过疏化是其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后果。但是其城乡资源的差别并不非常严重。即使到了最偏僻的长野县境内深山里的妻笼、马笼等地,依然有十分便捷的交通设施,最为明显的是覆盖度极广的铁路网。而在其乡村比如妻笼村,有着完备的市政设施,包括警察局、邮电局、学校、公园、医院,以及干净的公厕。在妻笼宿的保护再生计划中,日本国铁长野铁道管理局也参与到观光企划的制订中,1966年11 月长野铁道管理局长小泉卓雄发表《关于南木曾町的观光开发——寻找自然与浪漫的故乡》,提出观光的形态应当为“文化型”“休养型”,开发须权衡对风光的保护与观光的需求。而国铁部门对于妻笼的支持还表现在,1968 年春季观光季期间,特发名古屋至三留野的“木曾路号”列车。在8 月,又将妻笼、马笼、田立指定为“周游地”,“夏山急行列车”在此设站。借此,全国兴起南木曾路的观光宣传,这对妻笼宿的保存计划的推进带来了很大的刺激。而在中国的大部分还未通公路铁路并且还在使用旱厕的乡村,这些基础设施尚未建成,在这样一种不成熟的条件下学习,中国乡村补课的力度将十分巨大,这种补课不仅是金钱、人力上的大量投入,还有即便投入,短期也看不到产出的时间成本。这意味着,学习日本乡村改造经验,即使拉近了城乡资源差别,我们也可能同日本一样,无法遏制自身的乡村过疏化,因此这将是一场长期和艰苦的战斗。

图13:南木曾町与妻笼宿1965—1987年间人口变化

图14:日本古川町濑户川的“木匠文化馆”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二届全体大会于1999 年10 月在墨西哥通过的《风土建成遗产宪章》指出:“风土建成遗产是重要的;它是一个社群的文化,以及与其所处地域关系的基本表现,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表现……风土建成遗产的保护必须在认识变化和发展的必然性和认识尊重社群已建立的文化身份的必要性时,借由多学科的专门知识来实行……为了与可接受的生活水平相协调而适应化和再利用风土建成物时,应该尊重其结构、特色和形式的完整性。在风土形式不间断地连续使用的地方,存在于社群中的道德准则可以作为干预的手段……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一些变化,应作为风土建筑的重要方面得到人们的欣赏和理解。风土建成物干预工作的目标,并不是把一幢建筑的所有部分修复得像同一时期的产物。”[25]作为对这一宪章的补充及更新,2017 年12月在印度德里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九届全体大会通过了《木质建成遗产保护准则》,再次强调社群对于这一遗产类型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性:“认识到木构建筑遗产保护中社区参与的相关性,保护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关系,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26]在城市化过程中,遗产照管的当地化、社群化是一种多样性的保护构建,其带来的积极因素很多,也有需要优化的空间。日本妻笼宿案例是很多乡村在面对城市化进程中如何选取合理的保护与发展模式的缩影,因此其经验与持续至今的探索也值得我国新一代的遗产保护者和乡村振兴建设者再思考和审慎实践。
注释
[1] 西川幸治. 都市の思想:保存修景への指標[M]. 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73.
[2]本文在涉及日本相关文件、制度、法律用语时,使用“保存”这一日语原文。正文以中文语境讨论的时候,使用“保护”这一现代用语。日语中的“保存”本是中国汉语内的一个词语,意思是使事物、性质、意义、作风等继续存在,不受损失或不发生变化,相当于英文的preservation,在日文语境里对于文化遗产的处置多使用“保存”而不使用“保护”,一方面是语言习惯,一方面也传达出日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强调“维持原样”。因此,日语的“保存”的辨析处于中文、英文语境的“保存”(preservation)与“保护”(conservation)的精细差别之中。
[3] 南木曽町誌編さん委員会.南木曽町誌·通史編[M].南木曾町:南木曽町誌編さん委員会,1982.
[4] 今津芳清,加藤亜紀子,小宮三辰,林金之.木曾路を行く[J].建築と社会,2007,1020(03):44-49.遠山高志.妻籠宿-その保存の事例について[J].建築と社会,2007,1020(03):40-41.
[5] 太田博太郎,小寺武久.妻篭宿:その保存と再生[M].東京:彰國社,1984.
[6] 太田博太郎.妻籠宿の保存計画[J].建築と社会,1969(10).
[7] 南木曾町.木曽妻籠宿保存計画の再構築のために——妻籠宿見直し調査報告[R].長野:南木曾町,1989:9-22.
[8] 同上。
[9] 澤村明. 街並み保存の経済分析手法とその適用——木曽妻籠宿の40 年を事例に[J]. 新潟大学経済論集,2009,88(2):19-32.
[10]同[5]。
[11]日本对于风土建筑的保护并没有按照行政区划有城乡之别,基本上都是以“历史性环境”范畴的用语“町并”来覆盖日本市、町、村这样的既存在于城市,也存在于乡村的特征性风土建筑及聚落环境,并以此作为重要的保护对象。“町并”这一和文汉译词首先指的是日本风土民居的一种具体形式,即日本具有代表性的风土民居“町家”这种原型不断重复和衍化所构成的大大小小的城、 镇、乡间的街道立面和建筑肌理,以及由这些街道和建筑纵横交错形成的整体的风土聚落环境。换言之,“町并”是对日本传统民居“町家”所构成的连续的街道景观和建筑肌理的一种统称以及外延,直接沿用“町并”这一说法指代的是日本典型的风土聚落地区。
[12]同[7]。
[13]同[5]。
[14]同[7]。
[15]同[7]。
[16]小寺武久,川村力男,佐藤彰,上野邦一.旧中山道妻籠宿の民家について[C]//日本建築学会大会学術講演梗概.日本建築学会,1968.865-866.
[17] 川村力男,上野邦一.旧中山道妻籠宿嵯峨隆一氏宅の解体復原[C]//日本建築学会東海支部研究報告.日本建築学会,1970:259-262.
[18] 長野県南木曽町商工観光課. 46 年度学会賞受賞業績——妻籠宿保存復元工事の経過概要[J]. 建築雑誌,1972(8):831-833.
[19] 小林俊彦. 妻籠が保存すべきもの[C]//長野県南木曽町&財団法人妻籠を愛する会. 妻籠宿保存のあゆみ. 長野:長野県,1998:4-8.
[20] 南木曾町.木曽妻籠宿保存計画の再構築のために——妻籠宿見直し調査報告[R].長野:南木曾町,1989:9-22.
[21] 今津芳清,加藤亜紀子,小宮三辰,林金之. 木曾路を行く[J]. 建築と社会,2007,1020(03):44-49.
[22] 遠山高志.妻籠宿-その保存の事例について[J].建築と社会,2007,1020(03):40-41.
[23] 長野県.長野県史·近世資料編·第六巻中信地方[M].長野:長野県史刊行会,1979.
[24]藤原義則.南木曽町妻籠宿伝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区:妻籠宿の文化文政風俗絵巻之行列.文化庁月報2011(4).
[25] ICOMOS. CHARTER ON THE BUILT VERNACULAR HERITAGE (1999)Ratified by the ICOMOS 12th General Assembly. Mexico:1999.
[26] ICOMOS. PRINCIPLE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WOODEN BUILT HERITAGE. Final draft for distribution to the ICOMOS membership in view of submission to the 19th ICOMOS General Assembly. Delhi: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