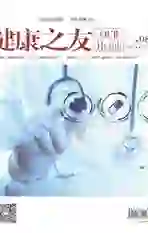脾胃学说与脾虚证临床研究进展
2020-10-21黄钰萍朱方石
黄钰萍 朱方石
【摘 要】脾、胃皆为消化器官,脾胃学说在各中医学著作中均有提及。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脾虚证的诊断标准已逐渐准确。对于脾虚证的治疗除了现代医学的对症治疗外,应用传统医学脾胃学说的理念可以进一步巩固治疗效果,帮助患者调理脾胃。
【关键词】脾胃学说;脾虚证;临床研究
【中图分类号】R223.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8714(2020)04-0274-02
脾胃学说在中医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全面理解脾胃学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脾胃病,脾虚证在脾胃病中较为常见。脾虚证的治疗大多依据脾胃学说的观点调治脾胃,脾胃学说认为调理脾胃应顺其升降,调其阴阳,以达到脾胃调和的状态[1]。关于脾虚证的治疗现大多提倡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众多研究认为应注意现代研究结果并兼顾中医传统理念,中西医结合,共同调理。
1 脾虚证的临床诊断
1.1脾虚证的实验室指标
通过现代实验室研究手段,脾虚证的本质已经基本清楚。大多研究表明,脾虚证的本质是患者胃肠功能障碍导致免疫功能和营养状态失调,从而引起一系列的临床症状[2]。虽然脾虚证在生理、病理形态、生化指标等方面都有较多的特异性表现,但公认最具特异性的客观指标为唾液淀粉酶活性实验和木糖吸收实验。且严巧锋等[3]的研究认为尿木糖的排泄率与患者的症状组合之间存在一定联系。
1.2 脾虚证的中医诊断标准
早在20世纪70年代,已有一个脾虚证的诊断标准,主要内容为:舌胖嫩或淡、有齿印,纳差、脉搏细弱,肢体倦怠,食后饱胀,大便时溏时硬或溏,以上症状为主症,有时患者还伴有一些次症,一般有2-3个主症并伴有2个次症即可诊断为脾虚证。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诊断标准也不断细化,后逐步将脾虚证分为气虚证和脾虚证,且将实验室指标作为辅助诊断参考。2002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了相应的疗效诊断标准,脾虚证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更加规范[4]。而国内诸多学者则认为同一诊断标准在实施方面可能有些困难,有些学者提出了“脾虚综合观”的观点,希望进一步统一脾虚证的诊断。
2 脾虚证的研究现状
脾脏不但是消化器官,在免疫系统、循环系统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有较多研究认为脾虚是多种疾病的原因。在脾主运化方面,脾虚证多为功能性消化不良,治疗时应注意健脾和胃。而危北海等[5]的研究认为,虽然溃疡病的发生主要与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有关,但其本质也是由于脾胃失调,在治疗时应治其根本,注意健脾温胃,可选择黄连汤、四君子汤等。此外,在脾统血方面,有不少学者认为脾不统血症的出现与血小板的功能障碍有关,由于此症发病急,因此首先应及时应用现代医学的方式治其标,再辅以四物汤、四君子汤等治其根本。关于脾虚证的临床研究还再不断的深入,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脾虚证的重要性,正在从不同角度和层次认识脾虚证。
3 脾虚证的治疗
3.1脾胃学说的临床应用
脾虚证累及患者肠胃,影响患者营养代谢的免疫功能,由于其病程长、复发率高的特点,导致临床治疗效果不佳。明代张景岳《景岳全书》中将“脾胃有病,自宜治脾,然脾为土脏,灌溉四旁,是以五脏中皆有脾气,而脾胃中亦皆有五脏之气,此其互为相使,故善治脾者能调五脏即所以治脾胃也,能治脾胃而使食进胃强即所以安五脏也”。脾胃学说作为重要的传统中医理论,在调治脾胃方面有较好的应用效果。依据脾胃学说,调理脾胃应顺其升降、辨其阴阳,达术柔肝。邱海云等[6]的研究认为调理脾胃首先应解决中焦痞结的问题,加强运动机制,可选用中经创半夏泻下汤进行治疗,紧抓心下痞这一特征进行治疗。脾胃功能的协调应是脾阴脾阳、胃阴胃阳的相互调和,脾阳伤则易出现津枯便燥之证,而脾阴伤则易出现便溏、腹胀等症,面对脾阳伤应注意淡味滋养,脾阴伤则应温补
脾阳。
3.2脾虚证的辨别
孔令彪等[7]的研究认为脾虚证依据临床表现可辨证分为相对脾虚证和绝对脾虚证,脾虚证的患者大多纳差、倦怠无力,但体型瘦小者与体型肥胖者之间还存在一定差异。相对于体型正常者而言,瘦小者为绝对脾虚证,而肥胖者则是虚实混杂,其脾胃功能与正常体型者相比是正常的,因此是相对性脾虚证。对于绝对性脾虚证应以健脾为主,而对于相对性脾虚证患者则应仔细辨别,化痰降浊和健脾同时进行[8]。对于脾虚证的鉴别在临床治疗中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相對脾虚证,由于其虚实夹杂,正虚邪实,因此应注意辨别,分清主要矛盾,对症下药。
3.3 脾虚证的用药
用药如兵,孔令彪等[9]的研究认为治疗脾胃病在于调控中州,医者用药正如战场点兵,治疗脾胃正如逐鹿中原。对于脾虚证的治疗多在于健脾扶正,健脾益气,鼓舞中州为治疗之上策,而驱邪则为下策,而中医方剂六君子汤、黄芪建中汤等皆可用于脾虚证的治疗。清代林佩琴 《类证治裁·脾胃论治》中亦提及脾胃调治之方法:“脾胃论莫详于东垣,其补中益气、调中益气、升阳益胃诸汤,以劳倦内伤为主,故用人参黄芪以补中,白术苍术以温燥,升麻柴胡升下陷之清阳,陈皮木香理中宫之气滞”。现代医学研究认为脾虚证的临床表现与胃肠功能障碍、胆汁反流的情况相似,可以选择理气药和促进胃肠分泌的药物。药理学研究证明佛手、陈皮等药物均可促进胃肠分泌,仓木、草豆蔻等药物可促进胃肠蠕动,适当添加此类药物均可达到治疗的效果。
参考文献
陈凯华. 脾虚证微观指标同步检测及其与症状相关性研究[D].广州中医药大学,2017.
周滔,申青艳,牛柯敏.危北海——中西医结合消化病学的开拓者[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6,36(02):146-148.
严巧锋. 尿木糖排泄率与脾虚患者症状组合关系的研究[D].广州中医药大学,2015.
胡玲,陈冠林,陈蔚文.脾虚理论及其应用——脾胃学说传承与应用专题系列(4)[J].中医杂志,2012,53(14):1174-1177.
张万岱,周福生.广东中西医结合脾胃学说研究的回顾和展望[C].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全国中西医结合发展战略研讨会暨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论文汇编.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2011:209-217.
邱海云.中医脾胃概论及脾胃学说的临床应用[C].甘肃省中医药学会.甘肃省中医药学会2010年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论文汇编.甘肃省中医药学会:甘肃省中医药学会,2010:419-421.
孔令彪,陈阳,李颖.绝对脾虚与相对脾虚的探讨[J].北京中医药,2011,30(11):832-833.
郑军,李敏,胡锦丽.温振英论中医脾胃学说在儿科临床的应用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2011,3(04):300-302.
孔令彪,江琪,董明霞,陈阳,李颖,葛楠,危北海.中医脾虚证研究的现状和展望[J].北京中医药,2008(09):738-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