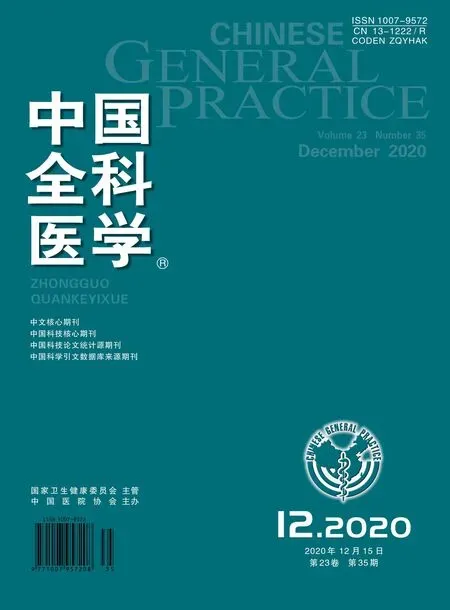中国大学生抑郁影响因素的Meta分析
2020-10-12张芮杨晨韵张耀东
张芮,杨晨韵,张耀东
抑郁是一类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思维迟缓、认知功能损害、意志活动减退和躯体症状为主要临床特征的心境障碍[1]。轻度抑郁对生活、学习没有长期影响,但重度抑郁可对生理、情绪造成长期严重威胁。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统计的全球抑郁症和恶劣心境者患病率达12.8%,并预测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全球第2位的医疗疾患[2]。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大学生群体的抑郁发生率高于一般人群,这与大学生处于青年期,心理状态不成熟,同时面对生活环境、人际关系的巨大改变,学业压力和就业形势严峻等多种因素有关[3]。国内外研究均表明,大学生的抑郁发生率高于一般人群[3-4]。我国大学生抑郁发生率在13.25%~79.90%,而一般人群仅为5%~6%[3]。长期处于抑郁情绪中会使大学生的学习效率下降,人际交往出现障碍,严重者甚至会退学、出现自杀意念或行为[5]。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大学生抑郁影响因素的认识不断深入,但研究结果还有不明确或不一致的地方,仍需进一步探讨。目前尚未发现有关中国大学生抑郁影响因素的Meta分析,因此本研究采用Meta分析的方法对国内外近年来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国大学生抑郁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探讨中国大学生抑郁发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为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检索策略 采用主题词和关键词相结合的方法,计算机检索 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VIP)等数据库,搜集关于中国大学生抑郁影响因素分析的相关研究,检索时限为1998—2018年。同时追溯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以补充获取相关文献。英文检索词包括:university students、college students、depression、influence factors、China;中文检索词包括:高校、大学生、抑郁、影响因素。
1.2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1)1998—2018年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描述性流行病学研究的文献;(2)文献的主要内容涉及中国大学生的抑郁影响因素分析,且有清楚准确的统计数据;(3)对于同一人群的研究,选用最优的1篇纳入;(4)抑郁的筛查使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或流调用抑郁量表(CES-D)。
1.2.2 排除标准 (1)综述类文献;(2)与研究目的无关的文献;(3)重复发表或疑似重复发表的文献;(4)无法获取有效数据的文献;(5)所用的评定量表是除SDS及CES-D之外的文献。
1.3 资料提取 由2名研究人员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交叉核对,如遇分歧,则咨询第三方协助判断,缺乏的资料尽量与原作者联系予以补充。资料提取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作者、发表时间、研究设计类型、调查地区、抑郁检测量表、样本量、抑郁检出率。
1.4 方法学质量评价 使用美国卫生保健质量和研究机构(AHRQ)推荐的横断面研究评价标准进行评价[6]。该评价共11个条目,分别用“是”“否”“不清楚”作答并赋分,选“是”得1分,“否”或“不清楚”得0分,其中第5条为反向计分。各条目总分越高说明文献的质量越高,其中≥8分为高质量,6~7分为中等质量,≤5分为低质量,低于7分的研究不纳入最后的Meta分析。文献质量评价和筛选过程由2名研究人员独立完成,意见不统一时,通过讨论达成一致。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RevMan 5.3和R软件进行统计分析。(1)根据Meta分析的要求对纳入文献进行资料提取,并整理数据,建立数据库。(2)效应量采用中国大学生抑郁影响因素OR值及其95% CI进行描述,同时绘制森林图。(3)采用I2值和Q检验对纳入文献进行异质性检验,当I2<50%且P>0.100时,无统计学异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即Mantel-Haensel方法(M-H法);反之若存在统计学异质性首先分析异质性来源,排除存在较大偏倚的低质量文献后重新计算合并效应量,若经上述处理后多项研究结果仍不具同质性,则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即Dersimonian-Laird法(D-L法)。(4)通过比较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效应合并值的差异分析研究结果的敏感性。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纳入文献基本情况 按照检索策略共检索到相关文献584篇,初筛及去重后,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得到21篇文献。再根据横断面研究评价标准进行文献评价,最终19篇文献[7-25]纳入Meta分析(见图1),均为中文文献。有效样本量共27 437例,纳入文献基本情况及质量评价得分见表1。
2.2 大学生抑郁影响因素的Meta分析 对纳入文献的研究结果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性别、户籍类型、是否独生子女、家庭形式、恋爱状态、年级、家庭经济状况各因素相关文献间均存在统计学异质性(I2>50%,P<0.05),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户籍类型、是否独生子女、恋爱状态、年级与大学生抑郁的发生不存在关联(P>0.05);家庭形式、家庭经济状况是大学生抑郁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2、图2~3)。
2.3 敏感性分析 对纳入分析的7个因素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两种模型合并OR值及其95% CI结果较接近(见表3),表明本研究的Meta分析结果稳定性较高。

表1 纳入文献基本情况及质量评价得分Table 1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included studies

表2 中国大学生抑郁影响因素的Meta分析Table 2 Meta-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pression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3 讨论
抑郁症是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情感障碍疾病,其病理机制迄今尚未彻底阐明。近年来国内外开展了大量流行病学研究以探讨抑郁发病的危险因素,但研究结果间存在不一致。抑郁不但与多种危害健康行为相关,而且是大学生休学、退学及自杀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26]。本研究在整理以往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运用循证医学方法,对大学生群体中抑郁发病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系统评价。纳入了国内13个省(市、地区)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好的覆盖面。通过严格的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文献并进行质量评价,提高了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本研究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双亲生活、家庭经济状况较好是大学生抑郁的保护因素。

表3 敏感性分析Table 3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图Figure 1 Flow chart of literature screening process

图2 不同家庭形式大学生抑郁发生情况的森林图Figure 2 Forest plot of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between different living arrangement

图3 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大学生抑郁发生情况的森林图Figure 3 Forest plot of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between different family economic status
本研究对大学生群体的性别因素与抑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共纳入19篇文献,结果表明女性并不是大学生抑郁的危险因素,这与既往的一些研究不一致[27-28],这些研究认为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更容易发生抑郁。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抑郁在不同性别大学生中的检出率并无差异[29-30]。在年级因素方面,有 11 篇文献[7-8,10-11,13-17,20,25]提供了详细数据,Meta分析结果显示,年级不是大学生抑郁的影响因素。
家庭环境对个体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又是个人社会支持系统的核心部分,影响着个体的应对方式,家庭冲突和破裂均会增加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的危险。本研究选取的家庭因素主要包括户籍类型(生源地)、是否与双亲共同生活、是否独生子女以及家庭经济状况。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双亲生活、家庭经济状况较好是大学生抑郁的保护因素。
一些研究也发现农村大学生总体抑郁情况较为严重,其抑郁检出率高于生源地为城市的大学生[31-32],单亲家庭的大学生抑郁检出率也明显高于完整家庭[8,33-34]。这可能与农村整体经济状况、教育程度普遍低于城镇有关。农村大学生来到城市,对城市环境的不适应以及学习生活的压力所导致的多重心理冲突,易使其产生抑郁等负向情绪。但本研究结果显示,尚不能认为户籍类型是大学生抑郁的影响因素,这可能与近年来国家大力建设农村,持续深化农村改革,缩小城乡差距等多种背景因素有关。不容忽视的是,未成年人与父母中一方或隔代亲属共同生活导致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父母在情感上的关注与呵护,父母对孩子在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上的引导与帮助不够合理。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容易导致青年学生在认知和价值观上产生偏离,若心理发展缺乏恰当引导,则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抑郁心理,甚至产生自杀意念。
从本研究Meta分析的结果来看,我国大学生抑郁研究对象包括了各地区各类型的高校和各年级学生,具有较好的覆盖性。采用较为权威的抑郁检测量表进行影响因素的研究,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可信度。但由于研究因素复杂,且国内缺少对相关研究因素的汇总分析,导致大部分研究仍然偏向于大学生基础情况的调查,缺乏更深层次影响因素的发掘研究。同时,对于研究人员来说,不同量表的选择,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的差异,因此也有必要设计一份影响因素更为全面的抑郁检测量表,有助于研究人员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开展测评,在抑郁检出后及时采取干预措施,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
本研究共纳入19篇文献,同时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敏感性分析,比较两种模型的结果发现,本研究中的所有因素在两种模型中计算的OR值相差不大,说明本研究的合并结果基本可靠。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本研究仅纳入了国人公开发表的中英文期刊文献,资料的全面性受到了一定限制;(2)纳入的研究均为描述性研究,含有大量的不确定性混杂因素;(3)纳入因素中涉及是否与双亲生活、恋爱状态、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况的文献只有4~8篇,导致Meta分析可能存在一定偏倚,影响分析的结果及本研究所得结论的推广,因此还需要更多针对大学生抑郁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论证。尽管存在上述局限性,但本研究克服了单个研究样本量小、地区局限的不足,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大学生相关状况与抑郁之间的真实联系。
综上所述,与双亲生活、家庭经济状况较好是大学生抑郁的保护因素。因此,要缓解和改善大学生的抑郁状况,应从多方面加以考虑。首先,大学生应及早发现抑郁情绪并主动寻求帮助,积极面对自己的负面情绪。其次,家长对子女需加以关心,经常交流和沟通,以舒缓和排解子女心中的苦恼。再次,高校应成立专业性较强的心理咨询队伍,为大学生服务,定期对大学生进行心理测评,针对测评情况及时开展干预措施,有效缓解和改善大学生抑郁状况。
作者贡献:张芮、杨晨韵、张耀东进行文章的构思与设计,撰写论文,对文章整体负责,监督管理;张芮、杨晨韵进行研究的实施与可行性分析,数据收集、整理,统计学处理,结果的分析与解释;张芮、张耀东进行论文的修订;张耀东负责文章的质量控制及审校。
本文无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