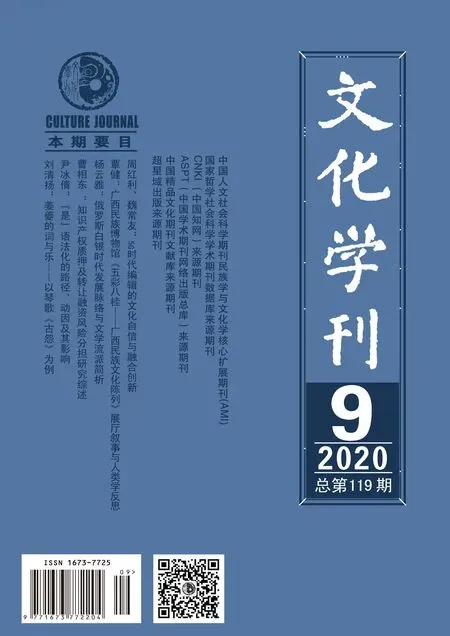《乐论》与《声无哀乐论》比较探究
2020-09-27宋佳佳
宋佳佳
阮籍与嵇康是魏晋时期名门士族,阮籍的《乐论》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对中国的音乐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阮籍的《乐论》通过刘子的问题,陈述了自己的音乐观。在《声无哀乐论》中,通过秦客与东野主人两人的辩驳,嵇康逐次表明自己的音乐思想。两人在音乐自然观、乐与情、和乐思想与音乐社会功能观方面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一、音乐自然观
阮籍《乐论》:“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1]“乐”的本质是天地之自然本体,万物之根本。阮籍认为古代圣贤制乐是按照世间万物本有的自然规律。这与儒家说讲的“大乐与天地同和”是相通的,音乐的本质应符合自然之和的属性。“体”与“性”虽没有明确的含义,但他在《乐论》中随即谈到:“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2]由此便可大致推断出,“体”“性”可以理解为自然万物本有的秩序。阮籍认为,音乐符合天地自然之规律与秩序,则天下平和;如果违背,便会出现乖离。这样的音乐使男女自然的位置不会改变,君臣之间的关系不会产生悖逆,不用惩罚奖赏制度,国家也长治久安。
嵇康认为音乐是“夫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3]。音乐是自然产生的,五色、五音产生于天地自然之间,并且不具备任何属性,但却有“善”与“不善”之分;音乐并不因环境而改变,音乐是客观存在的,不受外在环境影响而改变。
阮籍与嵇康二人把音乐的产生归因于自然之道,但阮籍带有明显的儒家礼乐思想,音乐的自然产生却可以使万事万物之间本有的秩序和顺,认为音乐自然就具有功用性。嵇康对礼乐的束缚一直持反抗的态度,认为音乐的本体是客观存在,有自己的规律。
二、乐与情之关系
阮籍在《乐论》中谈到:“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开群生万物之情气。”[4]圣人制作符合中和规律的音乐,调和自然万物,使自然与万物相和谐。他还提出“至乐使人无欲”的命题,他认为“乐”产生于“自然之道”,《乐论》中的“无欲”“道”与道家追求自然平和的思想相通,阮籍所言的“圣人之乐和而已”也就是道家的平和之气。阮籍《乐论》认为音乐具有多样性,他倡导先秦两汉“平和之乐”的观念,对悲乐持否定态度。阮籍还认为,儒家雅乐涉及礼制,礼与乐结合,是有效治理国家、统治百姓的工具。乐感化内心,礼是制度约束,礼乐相结合,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这与《乐记》中的“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5]思想相通,以乐感化人心,使人内心和顺,以礼为行为规范,使人去遵守,这样政治才会平和稳定。

秦 葵纹 咸阳窑店一号宫殿遗址出土
嵇康提出“声无哀乐论”,即认为声音哀乐与人的情感并没有关系。“及宫商集比,声音克谐,此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钟。”[6]音乐是乐器按照宫商客观排列而成的,并不是人的情感所赋予音乐情感色彩。“然则心之于声,明为二物。”[7]心之情感与声音是截然分明的两种事物。情感的喜怒哀乐早已隐藏在心中,它只是借助于音乐表现出来,音乐只是情感的表达工具。不同情感的人对同一种音乐的认识也是不相同的,审美主体存在差异,对审美客体的认识与理解也不同。同时他也指出人应该有客观判断,“由此言之,则外内殊用,彼我异名”[8],不能因为我情感的喜好与厌恶对客观的事物作情感判断。音乐有其本身的运动形式,与人的哀乐情感没有关系。嵇康对于音乐艺术本身给予了重视。另外,嵇康认为声音没有哀与乐情感划分,然而却有“善”与“不善”之分,“善”与“不善”也不以个体情感评价为标准,而是以“和”为衡量标准。如其《声无哀乐论》所言:“夫五色有好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至于爱与不爱,喜与不喜,人情之变。”[9]意即是说五色有美丑,五声有悦耳与聒噪,这些只是事物自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至于人们喜厌情感,是个人主观性的表述。
三、和乐思想
阮籍和嵇康认为和是音乐的最高准则,但二人却背道而驰。阮籍认为音乐符合天地自然和谐、平和的规律,这是音乐本性的体现,圣人作乐的最高境界是尊崇音乐自然平和的属性。他继承了儒家音乐观的审美准则,倡导音乐要有节制,要符合礼的要求,到达中和、平和的情感状态。他认为音乐的和,使人精神得到教化,从而使人可以上下不争不怨,政治达到和的目的。阮籍所讲的和并不是音乐意义上的,而是人文思想内涵,通过音乐的和,到达人与人关系之间的和睦,把音乐与政治相通,通过音乐的教化功能实现政治上的目的。阮籍以道家自然思想出发回归到了儒家政治理想。
阮籍所谓的“和”与音乐本身“和”内涵不一样,更多是把音乐作为工具,凸显出音乐的工具性。与此同时,阮籍还推崇礼,认为通过礼与乐的教化,人际关系能达到美好的境界,把音乐融入政治,教化民众,维护政治统治。阮籍以道家思想为出发点,但最终归向儒家,是儒道思想的复合。嵇康受老庄以及汉代自然元气说的影响,把音乐看作天地的元气,音乐本身就是和谐的存在,无论音乐如何,它所体现的都是自然之和,音乐是乐器动静和谐的表现。嵇康站在道家思想立场上,追求“放任自然”,嵇康所追求的“和”是纯粹的艺术美学。
对音乐的审美功能而言,阮籍与嵇康也同时追求“和”。阮籍追求的和,偏向儒家的“合通和一”。圣人之乐,是为了让人通天地之规律,理解万物之性情,到达和谐的状态。嵇康的和,是超越哀乐情感,追求一种自然平和的心里状态。音乐是自然规律和谐的体现,不带有哀乐的情感,音乐的目的不是体现情感,而是中和,达到“和”的心理感情。
四、音乐社会功能观
阮籍在《乐论》中,以刘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观点开篇,逐一展开陈述自己的观点。阮籍以道家思想的自然无味来论述雅乐,认为雅乐简单、无味,百姓自然会和乐。这与庄子的“法天贵真”的思想相同,音乐应该表现自然性情,认为音乐的审美标准应该是简单不造作。圣人建立的平和之乐,使用钟鼓、羽旄之舞节制听觉、视觉,这样音乐有节制,使人心气和顺,这都是音乐移风易俗的功效。这里可以看出,阮籍以道家思想为基础,与儒道思想相结合,但总体上表现出了近儒的倾向。他完全继承了儒家礼乐观。
嵇康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夫言移风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后也”。移风易俗的功用不在于音乐。音乐的本体是以精神、情感、意识为本体,无声之乐才是至乐,音乐本体应该表现的是自身的客观规律。嵇康认为儒家所说的音乐的移风易俗作用是被夸大了,风俗的移易应该是依靠统治者的治国之道。嵇康表现出了“近道”的音乐思想。他的音乐美学思想是纯艺术性的,音乐不存在功利作用,音乐的形式与内容是声音自身组合的表达,不能达到治国的目的。
汉武帝崇尚儒学,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儒学逐渐变得僵化与教条,“名教”成为政治统治的特色。汉末社会混乱,到处征战,受道家“自然”“超越”思想的影响,士人开始追求“才性”“言意”,玄学思潮一度兴起。阮籍以道家的自然观为根基,与儒家礼乐传统相结合,同时把礼乐作为教化百姓与统治社会的工具。阮籍在《乐论》中具有明显援儒入道德思想倾向。他认为音乐是“天地之体,万物之性”,就乐的作用而言,强调音乐的教化与移风易俗的作用,但他赋予了音乐使人复归自然、超越自然的道家色彩。嵇康好老庄,以道家为尊,“越名教而任自然”,崇尚自由,是为了在儒家思想统治下打破僵化教条的模式,使人性得到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