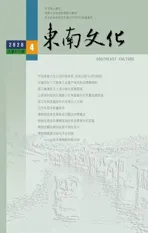汉代双层木椁墓研究
2020-09-26索德浩
索德浩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内容提要:汉代双层木椁墓可分三型,每一型最早都出现于岭南地区,之后有各自流行地域和演变序列:A型流行于西汉时期的成都地区;B型流行于两汉的岭南地区,以广州地区发现最为密集;C型发现于西汉中晚期的湖北地区。木椁墓的双层结构来源于岭南越人的架棺墓,是越人架棺习俗与汉式椁墓融合的结果。双层木椁墓的形制还影响到了后来岭南地区的砖室墓。双层木椁墓进入蜀地,其路线很可能是经由夜郎道—僰道再进入成都地区,为岭南与蜀地的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证据。
双层木椁墓系在椁室内分成上、下两层,一般是上层放置葬具及部分随葬品,下层为器物室。主要发现于广东、广西、湖北、四川等地,流行于两汉时期。楚地发现有在器物箱内分层的木椁墓,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M7、M11[1],器物箱内分成两层,两层皆置器物,而棺室内无二层结构,很明显器物箱中的二层结构只是为了增加器物储存空间。而双层木椁墓内二层结构主要是为了承棺,很可能是受到南方干栏式房屋防潮思维的影响。故楚地这类墓葬不在本文讨论范畴。前人虽已注意到双层木椁墓形制特殊,但少有深入讨论者。《广州汉墓》中对广州地区此类墓葬的形制演变进行了初步归纳和断代[2]。近来罗二虎、李晓对广州、成都两地的双层木椁墓进行了比较,但尚不能确定两地双层木椁墓是“独自发明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相似现象,还是两地间文化传播的结果”[3]。笔者拟在详细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双层木椁墓的源流、演变及相关问题。
一、双层木椁墓类型分析
根据木椁内隔层的形制,将目前考古发现的双层木椁墓分成三型。
A型:隔层面积与椁室底相同。根据隔层位置可以分成四式。
Ⅰ式:隔层位于椁室中上部,用纵横木枋构建。《广州汉墓》M1048,在底板之上0.56米处有五条横列的长木枋,两端出直榫,插入壁板的卯眼中,形成一个水平的疏底木架(未见有铺板),木棺置于其上,之上还有盖顶。随葬器物放置于下层(图一︰1)[4]。该式墓葬发现不多,时代均为西汉早期。
Ⅱ式:隔层位于椁室下部,用横木构建,横木上既可以铺木板,又有分箱作用。成都凤凰山园艺场M1,椁室底部用三根近南北向横木置于底板上,上铺木板,形成底室。三根横木将底室分成四箱,内置器物。椁室上层置2具独木方棺及器物(图一︰2)。时代约为文景至武帝铸造五铢钱之前[5]。其他还有成都龙家巷汉墓[6]、老官山M2—M4[7]、青白江区磷肥厂M13、M14[8]等。该式墓葬以文景时期为多,西汉中晚期也有零星发现。
Ⅲ式:与Ⅱ式接近,只是横木上直接架棺,不再铺木板。成都石羊木椁墓,椁底上东西向置横木两根,隔出三底箱。横木上南北向置3棺,其中1具为独木剜制(图一︰3)。随葬器物主要置于两边箱及东部。时代为文景时期[9]。成都青白江跃进村M1、M5也属于此式。其中M5有腰坑,椁室底板上纵放两枕木,其上东西并列独木方棺4具。腰坑位于墓底西部,内有大量器物。时代为西汉晚期[10]。

图一// 双层木椁墓A型
Ⅳ式:横木简化成墩柱,墩柱上放置横梁,类似广州汉墓中的“立架式”双层结构。仅见四川新都五龙村M1,木椁中部和南部靠着椁壁放置两对对称木墩,木墩上各置一根横梁。横梁上铺木板,木板未铺满。木椁西部的中心位置,用素砖砌一道与木板相同高度的矮墙。上置3具独木棺和1具箱式木棺(图一︰4)。随葬器物主要发现于底室。时代为王莽时期[11]。
B型:隔层面积小于椁室底。椁内分前后室,仅后室分成上下两层,上层置棺,下层为器物室。根据双层结构可以分成五式。
Ⅰ式:真双层,用横枋搭建分层支架,有“连壁减柱式”“立架式”两种构造。广州M2040为“连壁减柱式”结构,在椁底当中分立三个方形短柱,短柱固定在底板上。柱头上架一根直梁,组成一个侧视如“Ⅲ”形的立架。在立架上两边等分四条横枋,分别插入壁板与直梁的卯眼内,前端再压上一根长木枋,组成一个支承底架,底架上铺板。隔层约占底面积的六分之五。上层放置2具独木棺,下层器物室内置陶器(图二︰1)。广州M2050属于“立架式”,在两侧壁板下,分立三对方形的短柱,每对短柱上架一根横梁,组成三个立架,在上面铺板四块,分成上下两层(图二︰2)。隔层约占底面积的四分之三。棺架上置方箱木棺1具。器物主要置于下层。广州M2060也属于“立架式”,结构比M2050复杂[12]。该式仅见于西汉中期。
Ⅱ式:真双层,“横隔板式”结构,横木同时具有分箱作用。如广州M2043,在椁室后部约占全长七分之六部分立三块隔板(隔板上窄下宽),上面铺板,构成上下两层。横隔板将下层分成4箱(图二︰3)。隔板上置木棺2具。上下层中均有器物。时代为西汉中期[13]。此种结构与A型Ⅱ、Ⅲ式接近。
Ⅲ式:横前堂双层结构,其结构与BⅡ式相同,只是在主室前增加了前堂。如广州M3031由斜坡墓道、横长方形前堂与主室三部分构成。前堂底部比主室高0.5米。主室在后部约占椁室全长五分之四部分作“横隔板”式双层结构,中间一块隔板有门洞。前堂无双层结构(图二︰4)。有棺2具。时代为西汉晚期[14]。
Ⅳ式:假双层结构,后部高于前部成假双层,前部构建双层结构。广州M4013墓圹底部分前后两级。双层结构位于前室的后部,由壁板构成箱型器物室,以棺室底板作为器物室的盖板。棺室位于后室,左右分置独木棺(图二︰5)。器物主要放置于器物室、前室。时代为东汉前期[15]。
Ⅴ式:横前堂假双层结构。结构与BⅣ式接近,只是有前堂后室。广州M5001,带斜坡墓道,横长方形前堂。后室纵长方形,前部与横前堂高度一致,后部高一阶,棺、椁已朽。根据墓坑形制及器物位置推测为假二层结构(图二︰6)。器物主要发现于前堂,器物室无器物。时代为东汉后期[16]。
C型:楼房式双层结构,上下层之间有楼梯连接。根据结构演变分成三式。
Ⅰ式:内部分层结构简单,用纵横木枋构建。广州M1134,椁室正中有一座棺房,外周用板、枋组成双层结构。三条短木枋横架在木椁侧壁和棺房两侧,上铺薄板一层,形成上下两层的结构。下层为棺房的回廊,两侧各设独木梯以供上下。棺房内置两重套棺1具,棺底垫有横木。随葬器物分置于上下两层(图三︰1)。时代为西汉早期[17]。
Ⅱ式:内部结构复杂,上层错落有致、高度不一。如湖北光化五座坟M3是一座模仿当时楼房的双层多室建筑。椁室中间立四根方形木柱,柱子的顶端架一根方形直梁,将整个椁室分成南、北两部分。南半部分在靠西侧的三根柱子中部和南椁板之间,架三根方形横梁,其上铺板,筑成“南楼”,南半部分的东侧约有三分之一的空间无二层结构。北半部分在四根柱子中部和北椁板之间,架四根方形横梁,其上铺板,筑成“北楼”。北楼高于南楼,两楼之间有隔板和门的装置,之间用楼梯连接。方箱木棺放置北楼西侧,棺底用八只木马承托,其南侧有楼梯与底层相连。底层放置大量器物(图三︰2)。时代在武帝时期[18]。湖北荆沙市瓦坟园M1、M4(图三︰3)也属该式墓葬[19]。
Ⅲ式:分层结构与Ⅱ式接近,只是局部用砖。瓦坟园M3,外为砖椁,内为木椁。椁室内用立柱、隔板、门窗等分隔成前室、后室、侧室。三室之间有门道、台阶相通。前、后、侧室各设有楼板和供上下的楼梯等设施(图三︰4)。有方箱木棺1具。器物主要置于侧室中。时代为西汉晚期至王莽居摄二年之前[20]。
由于木质棺架保存不易,能确认的双层木椁墓并不算多。但从已知的双层木椁墓形制和器物分布规律可辨识出一批双层木椁墓。例如广西合浦母猪岭M4,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发掘者认为“该墓的葬法比较少见,是先将陶器和铜器等大件器物摆在椁内底层,棺放在北侧的大件器物上,墓主手握的铜钱、银手圈、铜棺饰等都散落在大件器物上”。时代为西汉晚期[21]。大件器物明显不足以承受棺和死者的重量,且高度不一。椁内应该存在双层结构[22],上层置棺,下层放器物,棺椁腐朽后,棺内随葬品散落于底室的器物上。由于此墓棺、椁已朽,结构不详,无法归入以上型式中,但足见汉代双层木椁墓的实际数量远比所见之多,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葬俗。
通过以上类型学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双层木椁墓可归纳成三型,每型有各自的演变序列:A型承棺支架逐渐从椁上部下移到中部、下部;B型从真双层演变成假双层,其器物室最初为器物主要置放处,后来仅具有象征作用,存放少量或者不放器物;C型二层结构逐渐复杂,呈错落有致的楼房状,由木结构演变成砖木混筑结构。总的演变趋势:三型承棺结构最初都是由纵横木枋搭建而成的支架,AⅠ、BⅠ、CⅠ式都是这种结构,后来A、B型演变成横隔板式,C型演变成结构复杂的楼房结构。

图二// 双层木椁墓B型
2.A、C型在演变过程中都受到B型影响:A型横隔板式架棺结构在B型中很流行,AⅣ式架棺结构很可能受到BⅠ式的“立架结构”影响,五龙村M1支架上木板未铺满,与B型结构相近;C型也受到B型的影响,如五座坟M3南楼前部无二层结构,明显是受到广州地区的影响。

图三// 双层木椁墓C型
3.三型木椁墓内的随葬品汉化程度均较高,深受中原影响,其主要器类、组合与同期中原地区的大致相近,但在器形上各具区域特色。三型墓内的器物群之间并未表现出甚多联系,毕竟木椁、棺可以就地取材,按照墓主的设想建造,而大量随葬品只能从当地采购。故双层木椁墓族属的考察主要依靠墓葬形制和葬俗的分析。
4.岭南和蜀地双层木椁墓内都流行使用方形独木棺,如凤凰山园艺场M1、跃进村M5、石羊场汉墓、五龙村M1和广州M4013、M2040等皆葬这类由整木剜制的木棺,表明了两地葬俗的联系。
5.从墓葬规格和随葬品数量来看,墓主皆具有较高经济能力。
二、双层木椁墓的时代与传播
三型墓时代明确。AⅠ式出现最早,西汉早期已经有发现,仅发现于两广地区。AⅡ式时代为西汉早期偏晚,即景帝至武帝颁行五铢之前,老官山M2—M4、凤凰山园艺场M1等皆是此时;西汉中晚期也有零星发现,如磷肥厂M13、M14等。AⅢ式最早发现于西汉早期偏晚,如石羊场汉墓;西汉中晚期也有发现,如跃进村M1。AⅣ式时代最晚,为两汉之际。可见A型起源于西汉初期的岭南地区,之后流行于成都地区。其传播路线将在下文讨论。
B型流行于广州地区,形制最为复杂。据《广州汉墓》,BⅠ式流行于西汉中期,以后不见;BⅡ式流行于西汉中晚期,东汉仍有发现;BⅢ式出现于西汉晚期,东汉仍常见;B型Ⅳ、Ⅴ式流行于东汉时期。
CⅠ式出现于西汉早期,CⅡ式流行于西汉中晚期,CⅢ式流行于两汉之际。CⅠ式仅发现于广州地区,后两式流行于湖北地区。也就是说,西汉早期C型出现于广州地区,约于西汉中期传播到湖北地区,广州地区消失不见。楚地和岭南相邻,两地文化交流存在地缘优势。自先秦以来,楚与岭南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随着楚国向南扩张,不断侵蚀南越之地,两地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战国时期,楚悼王任吴起为相,“于是南平百越”[23]。《后汉书·南蛮列传》亦云:“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24]。秦汉以后,岭南与楚地同属中央版图,两地交流更密。楚与岭南通道众多[25],但由于发现资料甚少,具体传播路线目前还难以确认。
通过上文类型学和时代分析,可将汉代双层木椁墓分成三期。
第一期:西汉早期,为双层木椁墓的初始期。本期流行AⅠ式、CⅠ式。仅发现于岭南地区,以广州地区数量最多。
第二期:西汉中晚期,为双层木椁墓的盛行时期。流行A型Ⅱ—Ⅳ式、B型Ⅰ—Ⅲ式、C型Ⅱ—Ⅲ式。岭南、楚地、蜀地都有发现,且数量较多。
第三期:东汉时期。B型Ⅱ、Ⅲ式仍有发现,流行B型Ⅳ、Ⅴ式。本期双层木椁墓仅发现于岭南地区,而楚地、蜀地的木椁墓逐渐为砖室墓所代替,双层木椁墓也消失不见。
综上可以得出:双层木椁墓起源于岭南地区。A、B、C三型的最初形制都是先出现于岭南地区,该地域的承棺结构最为复杂,序列完整,且发现数量最多,其核心区域当在广州地区。稍晚传播至四川、湖北两地。两地将双层结构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形成了各具区域特点的双层木椁墓。
三、双层木椁墓的源流分析
《广州汉墓》推测双层木椁墓是对岭南干栏式建筑的模仿,“是按照当时生人的居处并仿照干栏特点及使用方式运用于椁室的建筑布局上”[26]。结论过于宽泛和抽象。笔者认为双层木椁墓的架棺结构直接来源于战国时期的架棺墓。
蒋廷瑜最早注意到架棺葬俗,他根据岭南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铜柱形器,结合广西南丹崖洞葬中的架棺习俗(图四︰1、2)[27],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越人流行架棺习俗,铜柱形器是棺架上的柱头饰[28]。郑君雷根据蒋文的线索对岭南架棺遗迹作了进一步梳理,根据棺椁内器物的分布及墓内的“柱洞”和“凹槽”等遗迹现象辨别出一批架棺墓葬。文中将广州汉代椁内双层结构归为架棺结构的一种,但未讨论与早期架棺墓的关系[29]。
蒋廷瑜毕竟是利用晚期民族学材料对春秋战国时期岭南地区墓葬中的架棺结构进行的复原,但由于保存关系,两广地区并未发现结构完好的早期架棺来证实其观点。实际上,架棺葬俗并不局限于两广地区,云南也有。如云南楚雄万家坝墓地就发现一批架棺墓,其中M23保存较好。该墓两侧有6个对称边桩,东壁有生土二层台,二层台上有数根横木。葬具为独木棺,棺下有东西向3个垫木,垫木东端置于二层台的数根横木之上,西端则放置于两对并列倒立的铜鼓上(图四︰3)。

图四// 架棺墓
铜鼓、二层台、垫木及两侧边桩共同组成棺架,其结构与南丹崖洞葬中的棺架非常接近。M57结构与M23大体相近,也有架棺结构。南北两侧有四根边桩,东端横置枋木两根。棺底垫木三根,西端嵌入墓壁,东端嵌于生土二层台侧边。二层台上另有横木一根。棺身为独木刳成。棺身侧面有穿通的四圆孔,考虑棺身是独木,四圆孔中很可能插有横木,与两侧边桩共同组成架棺结构。该棺原应置于棺架上,只是棺架及垫木腐朽垮塌,掉落墓底(图四︰4)。参考M23、M57结构,M1、M25、M35等亦可能为架棺墓。这几座墓葬时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30]。该墓地棺架结构保存较好,为研究架棺习俗及族属提供了重要信息:1.为两广地区架棺墓复原提供了参考实例,万家坝的棺架结构确实与广西南丹县岩洞墓中的棺架相似,证实了蒋廷瑜的观点。2.为架起木棺,必须有对称的4、6个或更多立柱支撑,立柱上有榫卯结构以安装纵横木枋,构成支架置棺。立柱则会在墓葬两侧留下对称柱洞,或可据此推测有对称柱洞的墓葬为架棺墓。如广西平乐银山岭 M55、M64、M94、M97、M114、M115[31]、广州瑶台北柳M46[32]、广东乐昌对面山 M183、M151[33]、广州 M1060[34]等都有这种对称柱洞。四川地区也发现类似墓葬,如成都中和镇红花沟墓地发现多座,其中M3(图四︰5)保存最好,长方形竖穴岩坑墓,无椁,墓葬四角有方形壁柱,应起架棺作用,木棺位于墓室中部,时代约为西汉早期偏晚[35]。3.这种架棺习俗为万家坝墓地族属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万家坝墓地族属主要有两种观点:靡莫之属,与滇同属于一个系统[36];嶲、昆系统[37]。从目前材料来看,架棺习俗主要流行于岭南的越人之中,而棺架结构、独木棺葬具在滇文化中并不流行,这在族属判别时候是需要注意的。
入汉以后,随着汉文化在帝国内的推广,汉式木椁墓流行于岭南地区,吸收、融合了当地流行的架棺葬俗,形成了双层木椁墓。理由如下:首先,二者结构相近,两种结构最大特征就是将棺架起,棺在上,底下随葬器物;其次,据上文类型学分析来看,双层木椁墓的架棺结构最初形制是由纵横木枋搭建而成的支架,西汉中期以后才演变成其他各种形制,而这种纵横木枋搭建的支架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棺架非常相近,特别是流行于广州地区的“连壁减柱式”“立架式”棺架与早期棺架都是先立柱、再搭建横枋形成支架置棺,二者应该存在继承关系。再次,二者核心分布区均位于岭南地区。双层木椁墓在岭南发现最多,其他地区的皆源于此;架棺墓分布虽然较为广泛,但以两广最多。最后,二者时间上相互衔接。架棺墓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以后逐渐减少。而椁内双层结构最早发现于西汉早期。因此,椁内双层结构来源于越人的架棺葬俗,秦汉大一统之后,岭南地区逐渐融入汉文化之中,葬俗上接受了汉式木椁墓,但保留了本地早期流行的承棺结构,于是在木椁内形成二层承棺结构。
双层木椁墓的出现、流行过程伴随着架棺墓的衰落。以架棺墓(带对称柱洞)较为集中的平乐银山岭墓地为例,共发掘墓葬165座,其中战国墓110、汉墓45、晋墓1座。虽然报告未详细说明架棺墓数量,但从报道的墓例和各时期墓葬数量来看,显然带对称柱洞的墓葬在战国时期更为流行,西汉晚期发现较少,东汉前期未见报道。从文化特征来看,战国时期墓葬具有“较浓厚的地方色彩葬”,至汉代“地方色彩逐渐减少”,表明越文化逐渐融入到中原汉文化之中,架棺墓亦不能避免这一历史潮流。郑君雷辨别出的架棺墓也以战国、西汉早期为多。故西汉早期是架棺墓葬俗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此时恰恰是双层木椁墓在岭南的出现时间。可见,架棺墓与双层木椁墓互为消长关系,二者的兴衰伴随着汉帝国对岭南的政治统一和文化融合。
双层木椁墓还影响到后来的砖室墓形制。岭南地区常见前室低于后室的砖室墓,与假双层木椁墓相近。如《广州汉墓》中的Ⅳ型2、3式前室部分比后室低一级,与Ⅲ型结构接近,明显存在继承关系。编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认为Ⅴ型墓无疑是由Ⅲ型4式双层横前堂木椁墓演进而来,“两者的室内平面布局一样,所异的是建筑用材不同,一为木椁,一作砖室”[38],如广州M5039(图四︰6)[39]。
综上,椁内双层结构起源于岭南架棺墓,是岭南越人架棺习俗和汉式椁墓融合的结果。双层木椁墓形成以后又向相邻的楚地、蜀地传播。
四、四川双层木椁墓的来源分析
蜀、越两地相邻,文化交流频繁。《华阳国志·蜀志》云:“(蜀)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40]特别是在南中地区,夷越错居。《华阳国志·南中志》:“南中在昔,夷越之地。”[41]诸葛亮也提到:“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42]蜀、越习俗相互影响。如越人、蜀人均椎髻。《艺文类聚》卷六引《太康地记》:“秦灭六国,南开百越,置桂林、象郡……汉高革命……始变椎髻袭冠冕焉。”[43]《蜀王本纪》载蜀人“椎髻左衽”[44]。蜀人和越人都流行船棺葬,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还有上文提到的架棺墓,在两地皆有发现。雷雨将越南北部和四川地区考古遗存进行了对比,认为“至迟从商周之际开始,蜀文化的因素已远播至越南北部了”[45]。越南北部也属于越人分布区。
至西汉,武帝大规模开通夜郎道,蜀和岭南交往更加方便。夜郎道(牂牁道)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

图五// 蜀地汉墓中的岭南文化因素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弘因子言西南夷害……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46]
该文说明几个问题:1.夜郎道很早就作为商道存在,汉武帝时期只是出于军事目的大规模开通;2.汉武帝时期,长江中游与岭南通道不便;3.僰道与夜郎道相连,通向岭南,连接番禹;4.夜郎道非常重要,迫于艰难的形势罢了西夷道,但仍然保留“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很大原因是出于其重要的交通作用。从蜀地墓葬来看,夜郎道开通以后,岭南文化因素明显增多。如双包山的陶瓮M1︰15(图五︰2)[47]、都市花园的陶盒 M21︰1(图五︰1)[48]、青村的陶提桶M1︰10(图五︰3)[49]都是岭南常见器物。
关于夜郎道的路线争议比较多,争议点在于夜郎的地理位置。但不管夜郎位于何处,四川有一条经西南夷而进入岭南的道路,一般认为此路线为:成都—僰道—夜郎地区—牂牁江—红水河[50]—番禹。此条道路是两汉时期蜀地与岭南的重要通道,直到三国时期仍是如此。《三国志·蜀书·刘巴传》云:“巴复从交趾至蜀。”裴松之注引《零陵先贤传》:“巴入交趾……与交趾太守士爕计议不合,乃由牂牁道去。”[51]
岭南的双层木椁墓很可能经由夜郎道传播到四川地区:1.双层木椁墓在蜀地出现时间与夜郎道大规模开通时间接近。四川双层木椁墓约出现于景武之间,武帝中期以后开始流行,而唐蒙开夜郎道正是武帝前期。2.此时四川与岭南交通路线有很多条,但最方便的还应该是僰道—夜郎道。东下长江沿湖北、湖南也可到岭南,但路途较远,且“水道多绝,难行”。3.湖北地区的双层木椁墓与蜀地差异甚大,非同一演变序列,排除了经由楚地传播而来的可能性。4.岭南和蜀地双层木椁墓内都流行使用方形独木棺,如凤凰山园艺场M1、跃进村M5、石羊场汉墓、五龙村M1和广州汉墓M4013、M2040等皆葬这类由整木剜制的木棺,说明两地葬俗存在联系。5.木椁墓的双层结构来源于架棺墓。从考古发现和民族学资料来看,架棺墓主要分布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52]、四川等地,虽然时代早晚不同,但这种特殊的葬俗往往和特定的族群相对应。将这几个地区相连接,似可以勾勒出一条架棺墓族群分布和迁徙路线:岭南—云南—贵州[53]—四川,此条线路与汉代夜郎道基本吻合。因此,本文倾向于岭南双层木椁墓是经由夜郎道而进入四川地区。
结论
本文将考古发现的汉代双层木椁墓分成了A、B、C三型,三型均最早出现于岭南地区,然后传播到湖北、四川。每一型有各自的流行地域:A型墓流行于西汉时期的成都地区;B型墓流行于两汉的岭南地区,以广州地区发现最为密集;C型墓发现于西汉中晚期的湖北地区。三型墓融入各自的文化区,形成不同的演变序列。春秋、战国时期,岭南地区流行架棺墓,其架棺结构系汉代木椁墓中的承棺支架前身。秦汉时期,汉式木椁墓流行于岭南地区,与越人架棺习俗相融合,形成了双层木椁墓。岭南地区常见前低后高的砖室墓,形制应该是继承假双层木椁墓。越与蜀、楚相接,文化交流甚密,系双层墓木椁墓传播的基础。岭南双层木椁墓很可能是沿着夜郎道进入蜀地。此种特殊葬俗往往与特定的人群相对应,其传播很可能伴随着人群迁徙,为岭南与蜀、楚的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证据。
[1]《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5—8页。
[2]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3]罗二虎、李晓:《论汉代岭南与巴蜀地区的文化交流——以双层木椁墓为中心的考古学考察》,《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年。
[4]同[2],第55—57页。
[5]徐鹏章:《成都凤凰山西汉木椁墓》,《考古》1991年第5期。
[6]四川省博物馆:《成都凤凰山西汉木椁墓》,《考古》1959年第8期。
[7]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考古》2014年第7期。
[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青白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同磷肥厂工地汉墓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8,科学出版社2010年。
[9]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石羊西汉木椁墓》,《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
[10]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青白江区文物管理所:《成都市青白江区跃进村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8期。
[11]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县三河镇五龙村汉代木椁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
[12]同[2],第191—201页。
[13]同[2],第192—194页。
[14]同[2],第264页。
[15]同[2],第297—304页。
[16]同[2],第359—361页。
[17]同[2],第57—65页。
[18]湖北省博物馆:《光化五座坟西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19]荆州博物馆:《湖北荆沙市瓦坟园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11期。
[20]同[19]。
[21]广西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汉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2期。
[22]郑君雷:《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架棺”葬俗》,《考古》2012年第3期。
[23]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六五《吴起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168页。
[2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31页。
[25]王元林:《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辑。
[26]同[2],第479页。
[27]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南丹县里湖岩洞葬调查报告》,《文物》1986年第11期。
[28]蒋廷瑜:《铜柱形器用途推考》,《考古》1987年第8期。
[29]a.同[22];b.郑君雷:《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柱洞”》,《四川文物》2010年第4期。
[30]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31]a.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b.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32]黄淼章:《广州瑶台柳园岗西汉墓群发掘记要》,载《穗港汉墓出土文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3年,第248—252页。
[33]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乐昌市博物馆、韶关市博物馆:《广东乐昌市对面山东周秦汉墓》,《考古》2000年第6期。
[34]同[2],第51页。
[35]资料存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36]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37]宋治民:《云南西部地区一些青铜文化墓葬的初步讨论》,《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38]同[2],第363页。
[39]同[2],第367页。
[40]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志》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3页。
[41]同[40],卷四《南中志》,第229页。
[42]晋·陈寿:《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913页。
[43]唐·欧阳修撰:《艺文类聚》卷六《州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6页。
[44]汉·扬雄撰、张震泽笺注:《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43、244页。
[45]雷雨:《从考古发现看四川与越南古代文化交流》,《四川文物》2006年第6期。
[46]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2993—2995页。
[4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博物馆:《绵阳双包山汉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48]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博瑞“都市花园”汉、宋墓葬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1,科学出版社2003年。
[4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双流县文物管理所:《四川双流县青村汉、唐、宋代墓地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10,科学出版社2012年。
[50]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2页。
[51]同[42],卷三九《刘巴传》,第981页。
[52]贵阳、安顺及黔西南、黔南等地区的岩洞葬中多见井字形棺架(李飞:《贵州崖葬略论》,《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贵州崖洞葬主要分布于珠江上游红水河水系内,与广西南丹县的架棺墓应该同属于一系。
[53]贵州是岭南双层木椁墓向四川传播的关键节点,但由于木椁易朽,在贵州汉墓中极少见到保存完好的木椁结构。清镇M15为木椁墓,该墓器物堆放奇怪,铁剑压在一堆器物上,部分残余木椁也压在器物上。如果是单层结构的汉代木椁墓,铁剑一般贴死者身置于棺室中,其他随葬品则堆放于周围。而这种叠放方式很有可能是该墓存在二层结构,上层置棺,下层放器物,棺椁腐朽后,墓主贴身的铁剑掉落在陶器上。M1形制似也与岭南木椁墓中的双层结构有关,该墓为砖室墓,“甬道及墓室低于中部二层砖”,与《广州汉墓》中的Ⅳ型2、3式砖室墓接近,而这两型砖室墓由双层木椁墓演变而来。且该墓中室“两壁近起券处发现铁钩5个;其中南壁2个,北壁1个(另一个未发现),西壁两个,这铁钩或悬棺用的。”可能该墓中有特殊的二层承棺结构。两座墓葬信息较为简略(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附记于此,期望将来能发现确切的双层木椁墓,以完善岭南至四川的传播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