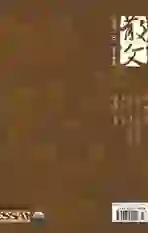宝马跑过戏台
2020-09-23陈美者
陈美者
他高且瘦,长相俊朗,穿夹克外套、内搭白衫,配冷灰的纯色卫裤,看上去真是一副家世良好的城中少年气派。阿成见到我时,悄悄抬了下左手腕。
我略感抱歉,抓起阿成的手腕,不错啊,名表呢。他笑了,看起来已原谅我的不守时。我心中亦漾起一丝久违的对人的亲昵感。这是我在本市唯一的亲人啊。阿成是我二哥的儿子。论辈分,我是他姑姑,不过只比他大十岁。他一般只叫我名字。我总记得的画面是,我妈妈一手汤匙一手碗地追在菜园边,圆脸短腿的小阿成一边扑蝶,一边时不时被塞几口蛋羹。村里偶尔来了叫卖零食的小贩,雪白的蒸米糕,金黄的麦芽糖,我妈就会买上一点点,只给阿成吃——那时我对他的嫉妒之心,更像是一个姐姐看弟弟时才会有的。
青念店门口,排队的人居然意外的少,我甚至怀疑之前关于门口的长队,是不是自己的一种臆想。想到这里,我叹道,能吃到青念真是不容易啊。阿成对我的浮夸口气颇为不解,这有什么难的。我只笑了笑,没再说话,挽着他昂然进店。他不知道,我畏惧人多,畏惧时尚,已许久没有走在繁华市区里了。
店里倒也没有多神秘。诡异的是,进到店里了,又觉得顾客并非我想象中的年轻人,他们衣着简单,身形也谈不上瘦削,喝饮料、吃面包,有点吵,散发出接近中年的舒适和无趣。
阿成则打量我的戒指,颇为赞赏地问:“很贵吧?”我低头看自己的戒指,主石是马亨盖尖晶,火彩好,但尺寸小,倒也不值什么钱。不过镶嵌款式却是我自定的。我没告诉阿成那么多,店里面包香味袭人,并不适合聊宝石。
我挽着阿成,忽然想到好久没有可以这样挽着的人,就昂着头对阿成说,你陪我逛商场吧。
阿成熟练地带我到化妆品区,推荐迪奥和纪梵希。他还说,前阵子情人节活动价,口红、粉底液等一整套才两千多,算起来一支口红比现在便宜七十块吧。我看着镜子中有红艳嘴唇的那张脸,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对阿成说:“很好啊!”阿成淡淡说:“必须买。她高兴好多天。”我听了只能点头,阿成显然比我更懂生活。除劝他少刷手机外,我已然给不出别的人生建议。
从商场出来,我们回到街上,继续闲晃。
我问阿成:“你周末都干吗呢?”
阿成说:“陪行里领导打球、爬山,去健身房。”
自从阿成买完房子,最大愿望就是换房子,换个大房子,才敢生小孩。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我二哥二嫂总这样劝他,并企图通过我向阿成传达。我却有负于自己的使命。每次不管我多么小心翼翼地、狡黠地提及这个话题,阿成总会动怒:“房子都还没搞清楚,怎么有条件生孩子?”“他们就会乱叫,一点都不懂人生规划,又帮不上忙。”平时话少又简洁的阿成,一谈及这个问题就会怒气冲冲连声质问。他说他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的父母对人生都没有规划,辛苦一辈子还这么穷,天天守在农村里做什么。他不能理解的还有他堂哥,我大哥的儿子,大学没念,二十岁结婚,娶一个邻村女孩,一口气生三个孩子,现在吃住全在父母家。阿成似乎一开始就清楚自己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大学毕业进了本市一家银行。至此,我二哥二嫂能给予的爱似乎已尽。想想也是,一个人要在城市立足谈何容易,加上单位里的氛围,身边同事动辄有三两套市区房子外加一个郊区别墅,终日谈论豪车。阿成就工作特别拼命,用心研究相关的政策规章和专业书籍,然后成为行里业务最优秀的那位——农村出身的人。他能拿出来的,也就这点了。
我们来到南街,最繁华深处。其实,我一直不太明白什么叫真正的繁华,南街算是一个城市的中轴线,但眼中所见,亦不过是一个由寿山石雕玉器珠宝崖柏沉香建盏糖画泥人蛋卷烤鱿鱼土豆龙卷风组成的大集市。繁华,更多是在我的想象之中,在坊巷深处,在青石白墙的老宅故居里,那里有云鬓香影、翡翠绫罗、旧肆藏书、悠扬雅乐,还有两三百年前宅院主人种下的杨桃树、杧果树、苹婆树,值得良久观望。
我带阿成去看衣錦坊的水榭戏台。
“建于明万历间,建筑总面积两千三百六十八平方米。原是郑姓住宅,清道光年间,为孙翼谋家族所有。花厅的最大特色是建有水榭戏台,面积三十平方米,福州地区仅存此一处……”我慢慢看着门口的简介,回头发现手中已没有挽着阿成。他晃来晃去,没有耐心看简介,只念叨着:“这还有日文、英文、韩文的介绍啊。”
买票时,阿成惊叫,还要买票,刷信用卡能打几折?
我们来到天井,只听阵阵清脆鸟鸣。这宅子边上有棵大榕树,枝叶繁密壮阔,适逢天晴,小鸟飞进飞出,啁啁啾啾,不晓得是在迎接什么热闹节日,更不晓得到底树上有多少鸟。但我感觉得出来,它们过得比人喜气多了。
阿成见我在天井站住不动,也只好站住。他还沉浸在刚才的话题,说,你要办张信用卡,刷信用卡的积分可以换很多礼品,我有膳魔师的水杯、泰国的乳胶枕头,都是积分换的。
我不再抬头看树上的鸟,转过身问他,刷卡要还吗?然后皱眉道,要的话就很麻烦啊,算还款日、算积分、算折扣、算礼品什么的好辛苦,费那种心思干吗?
这有什么辛苦的?钱你都不费心思,那你整天到底在琢磨什么呢?我琢磨阿成看我的复杂眼神,猜他心里这样想。但他终究忍住没说。
我们穿过大厅,又过了边门,看见一个院中院。粉紫、冰白的玉兰花开得傲然、雅致,龟背竹从长势看,似乎有百来年。三面墙角均种竹子,细细瘦瘦的竹叶最是耐看。院中这个单独的小楼,会不会是宅院主人藏书读书的地方?刚才进来时,见门口简介上说“生平嗜书,收藏丰富,藏书印有‘看云馆藏书”,我甚至能想象在小楼里,细密的竹帘后,宅院主人看书、品石、读碑的情形。
“哪里有戏台?”阿成问。这一瞬间,我才突然觉出他的索然,试探地问:“你会不会觉得这里不好玩呢?”“空荡荡的,没什么可看,票都买了就走走吧。”阿成终于憋不住似的说。我甚是不好意思,这里此刻的确门庭冷清,参观者寥寥,空落落的一个宅子,只有我和阿成两个人,而我刚才居然盯着红砖和苔藓看了良久,于是赶紧也找起戏台来。
穿过一条走廊,又过了一道边门,就来到花厅。
双层楼阁,楼在花园中,园中有雪洞、石桥、鲜花、游鱼。阳光洒下,清楚看见阁楼每个悬钟上雕刻的松鼠、玉米、葡萄,雀替则刻龙头鱼尾。戏台在水池对面,如同亭子一样,立在水上。我似乎能想见当年的盛景,穿锦绣官服的人在厅中一一落座,仆人奔走园中的小长廊里传递戏单,角亭里坐着乐师,忽而乐起,横箫声、唢呐声、头管声、青鼓声、锣声、钹声……台上走出将帅,穿大靠,配两肩飞袖、护心镜,背后插四面三角形背旗,战盔,战靴,手持马鞭,凛然走来。一时间,二楼的太太小姐们也不再留意邻座的娇艳红唇和翡翠手镯,一双双美目安静看向戏台。
忽然,一阵电话铃声刺破我的美梦。是阿成的手机。
他的妈妈、我二嫂打来电话说,托人给阿成带了些鸡蛋,让阿成去取,到家要放进冰箱……阿成皱着眉听,忽然打断道:“我不要!”我嫂子半哄半骂:“自己家里母鸡下的蛋,舍不得吃,好不容易攒九十个……”阿成越发烦躁,吼道:“我说了我不要!我不会去拿的!”
我在旁边不敢言语,免得二嫂催我去拿鸡蛋。阿成挂掉电话,像是要为自己开脱似的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每天三餐都在食堂吃,整天寄那么多东西干吗,我房子又小,真是搞不懂他们怎么想的。”
我明白阿成不喜欢那些塑料袋包装的农家土货,鸡蛋、紫菜、花生、地瓜粉……他向来痛恨土地,在城里几乎不用家乡话和我聊天,也不到珍惜农家菜的年纪。况且工作节奏那么快,实在也没心思自己做饭,食堂里吃省钱又省时间。我当然是劝他要体谅父母的苦心,家里能给的就是这些了,他们无非是想对你好,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
阿成越发皱眉,说他们只会骂他不懂事电话都不爱接。他每天上班接好多工作电话,晚上总加班到八九点,哪里有力气再跟他们聊什么。如果不是生在农村,又或者如果早生十年,他或许有更多机会改变阶层,也早买好房子。
我心里十分有愧。我也不是每次都乖乖接我妈电话,心情不好时常畏惧与任何人说话。早生十年说的也是我。可我并没有抓住什么机遇,一直以来只凭感觉在活,痛恨日常,却并未真正面对人生。工作十二年,只落得沉郁的心境和受损的身体,眼伤,肝也伤,胃亦不好。长年积累的结果就是,似乎迎来一个全新的节点——终日琢磨着如何告别过去,去另一座城,投入珠宝设计行业。阿成如此优秀和年轻,他还不太能理解“人生如戏”。人生更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只得承认情感的变化,接受命运的祝福和诅咒。如果让阿成知道,我这样的年纪还想着一切清零,放开已经拥有的一切,会不会也觉得我很不懂得规划自己的人生?
我们在戏台的对面并肩站着,任凭阳光照耀,暂时陷入一阵沉默。我悄悄看着阿成的侧颜,一时恍惚。他英俊、严肃的脸,常令我想起二哥黝黑、灿烂的笑容。
他们父子关系一向紧张,几乎不聊天。阿成买房子付首付时,二哥掏尽家底。阿成在福州办婚礼那天,二哥穿紫红色暗纹的西装外套,搭深灰色圆领毛衣,裤子是黑的,配黑皮鞋。这一套行头是全新的,就算过年他也没有穿这么新。但在城里,这样穿也并没有多隆重。
那日,阿成原本不大的家里,被欢乐、鲜艳的红以及陌生感填满,屋里有新娘的娘家人,大红喜字、红雨伞、红披巾、红被套、红隔帘。新娘则穿洁白婚纱,大裙摆撑满白色的新床,她坐在那片白色山河中还向我看了一眼,手上的红指甲鲜艳夺目。阿成的脸色与他胸口那朵红玫瑰形成反差,他时不时看向新娘的娘家人,又看向坐在客厅角落里的父母。他的父母穿得簇新,像是两位前来做客的远房亲戚,显得局促不安、无所事事。二哥一根接一根地抽着自己跑下楼买的烟,没有笑意,脸上是一副中年农民的表情。
婚礼既毕,二哥二嫂回老家,还带回好几大袋糖果。二嫂还穿着那身新衣服,一到家就去左邻右舍分糖果,笑嘻嘻地把同样的话说了好几遍:“是啊,城里的先办,在大酒店办的,城里的婚礼真是麻烦,好多仪式啊,还是我们农村简单,要办要办,等孙子生了一起办,是啊,在银行上班呢,哎呀,钱多但是累呀……”最后,她来到她的妯娌兼死对头家。我大嫂正在用铁勺子给一个一岁多的娃喂苹果泥,院子里跑着的还有两个,一个三岁多,一个两岁多。我二嫂手握糖果这种神器,显得无所畏惧,不分年龄段一并收买,她慈眉善目地往每个孩子手里塞满满的一大把,然后扬长而去。
二哥则一直在家,静静泡茶,一句话都不肯多说。几天后,他打电话给阿成——他一向很少打电话给他儿子。我二哥对着手机慢慢地说,阿成,我们到家了。阿成说,哦。二哥說,幸好我还有零钱坐车回来。阿成没吭声,他总是话少而简洁。我二哥也不吭声,更加不善言辞,那么多复杂情绪,在电话里哪里说得清,沉默一阵后,终于迎来他人生中的第二次崩溃,痛哭起来——上次是在失去父亲时,这次是因为身为父亲。桌上还有半包抽剩的中华烟,是他儿子结婚那天他自己下楼买的,带回老家就没再去碰。中华烟贵,他一向只抽七匹狼。
谁也不知道那半包中华烟后来如何,就像现在,我二嫂托人送来的九十个鸡蛋,也将是下场不明。我不知道到底是谁错,或者哪里出了问题,只是对阿成生出一些心疼,努力想开解他:“你那些同学当中,你一定是你们班最优秀、工作最好的。慢慢来,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阿成脸色缓和些,他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买一辆宝马M3,同学聚会的时候开过去。”
我望着池中的游鱼,又望向池上的戏台,仿佛也看见宝马。那个穿大靠、配两肩飞袖,背后插四面三角形背旗的将帅,正挥舞手中马鞭,抬腿跨马,身上裙袂飘动,英姿飒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