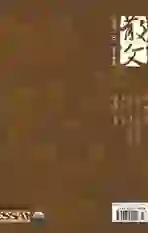药草
2020-09-23李骏
李骏
黄安城原来盛行草药治病的传统,革命者们在山林里打仗负伤或得病,全靠草药治疗。到了我们那一茬,幸存的革命者进了城,不再用草药而用西药了。
草药来自于药草。黄安城有各种各样的药材,我们本吴庄附近的山头,最多的是苍术、桔根、蛇扇子、柴胡、鱼腥草。这几种药草在当地最流行,代销店里就收这些东西。我们村子里人们的额外收入,也是靠这几样药草换来的。大人闲了时挖,我们几乎是有时间便上山去挖。虽然那时山上有狼,有毒蛇,有野蜂,但我们不怕。大约从五岁起,我们便开始跟在大人屁股后上山扯柴胡。柴胡在山上的产量最大,几乎我们黄安的每个山头上都有。在印象中最早扯柴胡,还是我父亲为生产队承包砍窑柴那年。所谓砍窑柴,就是村子里要盖屋时,将土坯放在窑里烧制,需要大量柴火,一烧就是三天三夜,我们黄安少煤,只能烧山上的柴草。父亲常常是从一个山头砍过去,从山脚一直砍到山顶,柴草一汪汪地倒下,晒干,然后一担担地挑回来,码在村头像小山一样。父亲砍柴时,边砍边能遇到柴胡,砍掉了可惜,要弯下腰去扯,又费事误工。于是有一天,父亲便把我和姐姐带上,让我们在前面把柴胡扯起来,他再砍过去,便不痛惜了。
扯柴胡一般是在夏秋。那时天气正热,我们掉进人高的茅草里,像在丛林中行走的动物。早晨的露水凉侵入骨,像一根根寒针,挨着骨头走;而一到了上午八九点钟,阳光从空中射下,衣服和草丛的水汽一蒸腾,仍然像钢针扎在肉上一样。但父亲砍得很快,我们必须把柴胡扯完。常常一捆捆地晒干,码在一起,挑到镇上去卖。其实也卖不了多少钱,但大体可以补贴家用,也可以挣点学费,不至于在上课时因为没有交齐学费被赶出来。更多的时候,我们不是跟着父亲到大山上,而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从这个山头窜到那个山头。村中的哥姐们跑得快,我个子小,经常跟不上。一邊怕走丢了,一边又怕狼和野猪,所以有时也蹲在山头上哭。但哭归哭,还是要尽量跟上的,便又扯起脚跟着他们跑。好在我能吃苦,扯的柴胡一般并不比他们少。
柴胡过了季节,我们更多的是挖桔根和苍术根。桔根开花,那苗一眼便可看见。桔根又比其他的药草值钱,所以大部分时间,我扛着一个小锄,提着一个篮子,满山满野地挖桔根。桔根挖回来后要先剥皮,在水里洗一下后放在阳光下暴晒,等干后再送到供销社去卖。那时一般是一块钱一斤,在我们眼里还是挺值钱的,虽然一天也挖不到多少。至于苍术根,因为叶子刺手,加之不怎么值钱,一般不是我们的首选。苍术根挖回来后,还要等晒干后把毛烧掉,往往弄得人黑不溜秋的。当然,我们有时也挖蛇扇子,这种东西一般长在潮湿的地方,很少,但比较值钱。
在少年时的记忆里,我们村庄周围大大小小的山,从山脚到山腰再到山顶,我几乎都跑遍了。每年哪里长了什么,第二年我会准时到达。所以,后来我总是比村庄的人们挖得多也挣得多。以至于后来,他们开始喜欢跟着我一起找药草了。
药草符合条件,便要送到镇上去卖。镇上收药草的那个中年人,听说是从县城下来的。他个儿高,脸黑,不苟言笑。我们总是要看他的脸色,比如,嫌你的药草没有晒干,嫌药草太嫩。他同意了,就过秤,不同意,还得拿回去。所以,每次看到他我都紧张,生怕他说不合格。因为是替公家收,他想说谁不合格就不合格。但很快,四里八乡的人都喜欢去他那儿卖药草了。老一点的,喜欢看他老婆,他老婆很漂亮,对人说话也和气。这样好的女人,听说他却老是动不动就打她。至于年轻一点的,包括我,也喜欢到镇上去,因为黑脸有两个女儿,那个大女儿,穿着白色的裙子,也显得很漂亮。要知道,在我们黄安县本吴庄周围,还有谁家的孩子能穿得起裙子呢?但问题就在于,中年人训我们时,如果遇上他女儿在,我往往觉得很没面子,头便跟着低下了。去镇上的次数多了,便产生理想了。那时最大的理想,就是希望以后能到隔壁的供销社里当一名光荣的售货员。那些供销社的售货员们,大热的天也不用出去,就是坐在有糖味散发的屋子里扇扇子、嗑瓜子、聊天,看上去非常舒服,不用像我父亲他们那样,天天风里雨里雪里,面朝黄土背朝天,还吃不饱穿不暖的。但供销社里的人,对来买东西的人爱理不理的,又让我特别反感。
挖草药基本上到初中为止。上了高中,到更远的地方上学了,偶尔有时间回来,跟着我姐姐一起去挖过,但次数渐渐少了。那时,我姐姐已彻底加入了劳动大军,全心全意无怨无悔地供我读书。我偶尔手中有点零花钱,全是姐姐挣来的。所以直到今天,我还觉得欠她的。她的孩子转眼也上高中了,每次提到挖药草的事,姐姐像没事似的,而我总是感觉,有泪水要从眼眶中掉下来。
油菜花
每年三月,故乡黄安的油菜花漫山遍野。四处像涂了金子的黄色,也像抹了颜料的绿色,让阳光一照,分外惹眼、刺眼和养眼。或是雨水时节,江南漫无边际的梅雨扑洒下来。匆匆地穿过村庄的小路,那些油菜地的芬芳直扑鼻孔,让人对野外产生无穷的向往。而向往却跑不了太长,因为油菜地那边,就是山和峰。那是黄安革命者们当年曾翻越的地方。当年,他们也像我们那么大,大多十几岁便参加红军,到山那边革命去了,一季季油菜花谢花开,最后却少有人归来。他们中,一部分人牺牲在革命路上,一小部分人在城市里当官安家,很少回来。母亲说,每当油菜花开,多少人望眼欲穿,最终,山路上经过的都是外乡人,革命者们了无踪影。我们家族如此,黄安的村村寨寨如此。
我那时不懂革命者,也不知他们翻山越岭所追求的理想。我最喜欢在阳光普照的时刻走在油菜地里,看蜜蜂在花间飞舞,嘤嘤嗡嗡地乱窜,偶尔掠过我的前额,让我瞬间有点惊慌失措。那时乡下都穷,革命前与革命后都是饥肠辘辘。田野里那金色的花与绿色的枝叶,在田野里总是给人一种希望的感觉。希望曾是山那边的事,那些革命者们的英雄事迹停息之后,慢慢变成游子的愿望——几乎每个人都盼望着离开田地,离开大山,离开故乡。
我那时同样如此。躺在开满油菜花的田岸上,一个劲儿地胡思乱想。阳光落在花上,折射在叶上,打在我的脸上,让我觉得自己迷迷糊糊的。为什么如此贫瘠的土地上,生长出的庄稼竟然如此金黄!于是我经常为自己生活在如此偏远的乡村悲哀,为自己在山那边没有任何熟悉的事物而自卑失落。但没有谁在意我的失落,草一年年照旧谢,花一年年照旧开。我只是伴着田野,打草、扯草、拔草。那时,父亲的希望都在田野里,都在庄稼上。他的目光飞不过田野,像花尖上的蜜蜂,只在意那一亩三分地。而我,虽然也在田野里,却总是在斑驳的阳光下,幻想着山的那边会有奇迹。山那边偶尔进来一个陌生人,就让我在田野里踮起脚尖张望,在一丝惊慌之中,看到那些人穿着光鲜的衣服,在阳光与绿色的田野中晃眼,于是我的头便慢慢低下去,看自己的脚尖。那时我还光着脚呢,有一条菜花蛇甚至从我脚边滑了过去,对我不屑一顾,连咬我的欲望也没有。我于是含起一根草,我们把它叫作茅针——抽芯后可以吃的——我坐在油菜田里,看着金黄色的花把我覆盖,一边幻想未来的时光。但我知道,这纯属胡思乱想,这些幻想,如果蹿出了油菜地让我父亲看到,多半要挨他的耳光。一切不合实际的行为,在父亲面前的收获只有一种,耳光。
我不喜欢待在家里。那时乡下的人真多,人们在地垄里劳作,锄草,施肥,也在山间播种花生。花生多半是套种的,有的种在油菜田里,有的种在小麦地里。村庄里没有一片闲田,也没有一个闲人。放学后,我们不是被大人们赶到地里打猪草,就是扯田地里的野草。我多半是打猪草,我家的猪每年全靠我喂呢。饲料不够,我放学后便要到地里打野草了。那时我认识各种各样猪喜欢吃的野草,因此每年都把猪喂得又肥又胖。我惦记的是我们家的猪,它对我有感情,每天我回家它便跟在我身后转圈,哼哼唧唧的,像个孩子。我也舍不得它,以至于每年年关杀猪时,我都要撕心裂肺地哭。那时乡间的大人们的脾气都非常暴躁,我父亲尤甚。我一哭他的耳光便飞过來。在我童年时期,他的眼里对我全是敌意,不像我今天看自己的儿子那样温柔。只要我偷一点懒,或者在油菜地里胡思乱想一会儿,被父亲发现后便会有耳光飞来。一种响亮的声音在我的脸颊与他粗糙的巴掌中产生,我像油菜地里惊飞的鸟一般逃窜。委屈的泪水只有对着油菜花流淌。我不喜欢回家,只在地里和山里头转来转去。我羡慕树头上的小鸟,它们可以飞过山头随意歌唱,而我却始终看不到丝毫飞过山峦的希望。
在油菜地里待的时间长了,我便非常喜欢金黄色。金色的梦和黄色的希望漫无边际地生长在我的心头。我夸张地对父亲说,总有一天我会走的。父亲不信,骂我说大话,而母亲总是护着我。记忆中,她总是站在田头地垄,太阳出来时,汗水便从她的脸颊渗出,在阳光下晃眼。其实母亲的脸晒得很黑,她的眼里总是盛满忧伤。这让我觉得偶尔路过村庄的风,也带有了这种忧伤的气息。于是黄安城山上的树,虽然一片又一片的,与这原野里的金黄相比,却显得那样暗淡。母亲一边劳动,有时也会一边对着原野唱歌。她的歌很古老,大都是些黄安人曾经出去闹革命时唱的歌曲。那些歌曲像白云飘荡,有时欢声笑语;又像河流汹涌,有时无比忧伤。当然,母亲有时也坐下来,招手让我过去,对我讲她幼年时跟着大人们在我们黄安的山上逃难的旧事。无非是国民党的兵或日本鬼子进村扫荡了,往往是枪声一响,村里逃得干干净净,敌人便一把大火将村庄烧个干净。再后,当枪声停息,人们纷纷从山上下来,再建村庄。母亲讲这些事时,我便觉得油菜地里因此有了革命的气息。那些革命者们善于打伏击,枪法很准,以至于到了油菜花开的季节,鬼子不敢进村,还乡团不敢叫嚷。于是,人们便纷纷盼望春天,盼望油菜花开和小麦抽穗的日子。因为那时,村庄将变得格外平静。
现在,革命者和他们的敌人一样,都渐渐消失了。村子里的人又渐渐多起来,生活又慢慢恢复平静。我们本吴庄的小孩们一拨拨地像油菜花一样疯长,一茬茬地很快就长大成人了。金黄色的田野,便成了村庄的希望。收成的好坏取决于天气,而大人们脸上的阴晴取决于脾气。我父亲喜欢动手不动口,所以我就得以在油菜地里,多消磨一些童年的时光。我有时也与村子里一般大的孩子在油菜地里打仗,拿着自制的木枪,把自己在地里藏得严严实实。那时,我多半是孩子王,不管大的小的,都喜欢站在我这一边。我也在自我陶醉之中,无限地放松,以至于连蛇也不怕,直接躺在草中睡着。直到我姐姐将饭煮熟,站在门口高喊我的名字,最后跑到田野里找到我,用脚踢醒我时,我才慢吞吞地从梦中醒来,回到无比饥饿的现实之中。就是在一个油菜花开的春天,由于我们家供不起两个人读书,我姐姐便主动承担了家务,走向农村广阔的田野……
许多年后,经过连滚带爬的努力,我终于挣扎着离开了那儿,来到异乡。异乡除了大商场里的金色饰物,看不到一点活生生的金黄色。我要翻过山峦的梦彻底实现了,但也丢掉了许多金子一般宝贵的东西。这时,我们本吴庄里的年轻人,一窝蜂都跑到城市打工去了,田野里种的油菜也少了。美丽的田园慢慢荒芜下去,无边的杂草迅速占领了阵地。偶有几亩鲜艳的油菜花在山间像一条黄色的带子在空中飘动,也仅是杯水车薪,再也不复当年的美景。而那些与我一同玩打仗游戏的孩子,也四散于八方,每个城市都有他们的足迹,我们再也不曾在本吴庄遇到过。他们留下的孩子,每天伴着那些老下去的爷爷奶奶,在擦黑便熄灯的村庄中,陷入了更为漫长的沉睡。有好几次清明节回故乡时,我站在那熟悉的田埂上,闻到油菜的花香,看到蜜蜂仍在花间飞舞,突然便落下泪来。我问自己: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人类还不能像一条狗那样忠诚,不能像一只蜜蜂那样执着地去爱呢?
我回答不了。因为那时,我回本吴庄去只能见到母亲的坟地了。她的坟在山头上,那块她生前自己选的地,与本吴庄的墓地隔开。在她曾洒落过歌声的土地上,我已找不到原来的记忆。每次,我在异乡梦见母亲,总是担心她穿过油菜地后就会迷路,其实真正迷路的,不过是远在异乡城市中生活的我。在城市,在异乡,我们经常迷路,不知所以,不知所云,不知所往和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