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者聚会
2020-09-17金仁顺
金仁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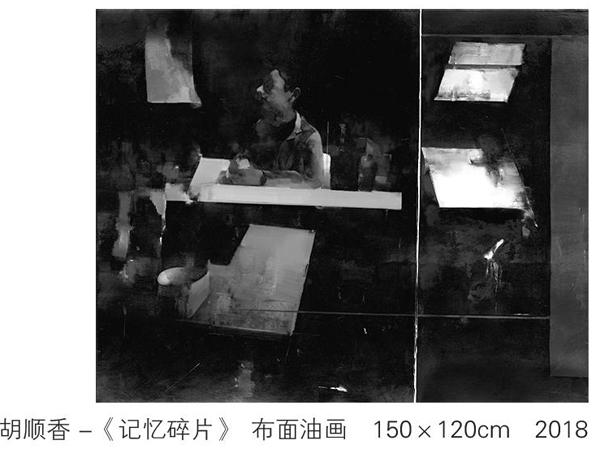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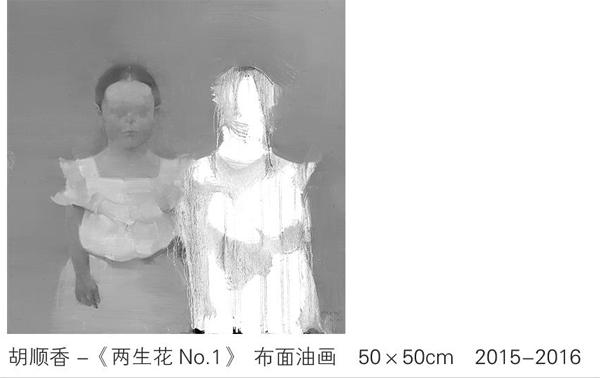
会议的主题是:和平与沟通的平台。
韩国翻译院问我愿不愿意来开这个会,我说愿意。时间很好,五月初,首尔气温适宜,风景美丽。如果日程不是特别满,还可以继续寻找美食小店。以前发掘的几家也很想再去。一个是汤饭馆,石锅里面黄豆芽煮得刚刚好,打进去的荷包蛋煮到七分熟,端上桌的时候汤“咕嘟”“咕嘟”沸腾着,热气和香气很难说哪个更浓郁。米饭整碗扣进石锅里,就着泡菜和萝卜块吃,一直到汤饭吃光光,石锅还是热乎乎的。汤饭馆隔壁是家烤肉店,肉倒没什么,亮点在免费提供的几种山野菜上,新鲜、干净、绿色叶片紫红色叶脉,颜与味俱美。弘大附近有家小店卖炸鸡胗,鲜嫩脆爽,研究半天也没搞明白,肉筋筋的鸡胗是怎么料理成这个样子的。有次去北村,回来时,在一个地铁站附近找到家米肠店,肠衣里面装的是猪血、绿豆芽、粉丝、芹菜丁,煮熟后切段,放进牛杂汤里炖,上面铺着切碎的紫苏叶,叶子上面再撒上一把炒熟的苏子,香得能让人打一个激灵。辣鸡爪倒是很多家店都做得不错,跟冰镇啤酒搭配,宵夜最佳——相比之下,炸鸡和冰啤酒的搭配完全是电视剧的捆绑产物:大家喝的不是啤酒,是剧情的狗血;吃的不是美食,是男女主的颜值——配啤酒更好的是用辣酱生拌的螃蟹,味道绝佳,但太寒凉了些。还有很多人点一种类似福建蛤仔煎的东西,几种蛤蜊肉,八爪鱼须,加面粉和鸡蛋,还有一大把整棵的韭菜,一起煎成饼,吃的时候要用剪刀剪开。首尔的夜店,半夜十二点人声鼎沸,呼朋唤友,到处都是兴致勃勃的面孔。
这次会议订的酒店在光化门附近,市中心,去哪儿都方便。我入住时已经是下午了,晚上没什么事儿,出去在街头乱转,找到一家专门吃鱼的店。店里面挂着大幅的照片:炭黑色的明太鱼一排排挂在木架上,灰黑色鱼身上覆盖着白雪。好的明太鱼干要在冬天晾,低温、冰雪、昼夜温差,能让鱼肉一点点地发生变化,日后拿鱼干下酒时,鱼肉可以像棉絮那样一层层撕下来。晾鱼只能选冬季,其他季节温度太高,或者空气太干燥,肉很快会变僵硬,鱼干变成了棒槌。
这家鱼店里卖十几种鱼,十几种做法儿,最招牌的是几条明太鱼用整锅辣椒来炖,黑白灰的鱼,鲜艳红火的辣椒,上面撒着翠绿嫩白的香葱末,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可惜四人份才起订。我挑了一款单人套餐,三种鱼,煎炸炖,附送米饭、海带汤和八碟小菜,满满当当地摆了一桌子。我很努力地吃光了两碟小菜,老板娘贴心地问我,要不要再加?我连连摆手。
说到沟通,有什么能比美食更适合?酸甜苦辣咸,在舌尖缭绕,冷暖自知,进而深入胃肠,沉潜下来。食物的记忆是身体的,也是精神的;是愉悦,也是惆怅;既当下,又古老。吃完饭走路回酒店,穿行街道仿佛走在城市的胃肠里面,人并不比一粒米更大。
第二天在酒店吃了早餐,到大堂集合。大堂里面挤满了人,不知道谁跟谁是一伙儿的。我翻了翻会议资料,发现参会的作家分成两部分,一半是韩国作家、诗人、评论家;另外一半是拥有韩裔(朝裔)血统、来自十几个国家的作家和诗人。
我的翻译过来找我,她有详细的日程安排。开会的作家们被召集起来,分乘两辆中巴车前往会场。中青老都有,男女各半,不约而同地沉默着,偶尔眼神碰到一起,就点头微笑,转头去打量着车窗外的风景。
离酒店不远有个三岔路口,路边摆放着一件雕塑作品:一大把五颜六色的气球放飞在空中,用一把线固定在地上。
路程很长,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到达会场。
开幕式很简单,翻译院院长是诗人,笑容满面,致辞简洁:欢迎作家们来到首尔。他介绍了这次会议的主旨,是提供一个平台,来自世界各地的韩裔(朝裔)作家们济济一堂,谈论文学和生活,交流创作感受。他相信本次会议将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他对接下来的活动抱有很高的期待。最后,当然了,希望每位参会作家在首尔期间心情愉快。
开幕式后有十五分钟茶歇,大家都过去喝咖啡、吃点心和水果,几种语言同时响起来。在饮品和甜品的催化下,气氛松快了很多,大家被介绍或者自我介绍,从彼此的脸孔上面找到很多熟悉的特征:单眼皮、薄嘴唇、羞涩的笑容、鞠躬问好的姿态。血统这事儿说起来很奇妙,在人的身体里像红珊瑚盘根错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又都枝蔓交缠,源远流长。
茶歇时间结束后,进入第一组讨论。六个作家坐上讲台。除了国外来的作家,每场都有两到三个韩国作家搭配,讨论会的主持人也是由韩国作家、诗人或者评论家来担任的。
这一场讨论会给我留下印象的是来自俄罗斯的作家,七十岁上下——作家们的简历中,大多数人都没写年龄,有些人可以猜个七七八八,有些人则是谜——老作家很和善,没有留长发,没有奇装异服,也没有任何虚张声势的东西。像普通人家的老爸,泡杯绿茶喝杯小酒,说话慢条斯理。他介绍自己,祖父辈移民到俄罗斯,他在俄罗斯出生,生活至今,他的画家身份远重于作家身份,他靠卖画维生,也靠卖画来养活自己的文学理想。
朝鲜半岛的人移居俄罗斯,从很早就开始了,就像当年他们到中国东北垦荒一样。起初是十个八个,春去秋回;慢慢就家族搬迁,固定不动;再后来,形成了村落,被俄罗斯人泛称为“高丽人”。人在异乡为异客,俄罗斯幅员辽阔,冬季漫长,生存不易,但一代又一代移民却也扎下根来,他们并没有多喜欢移民身份和生活,但流浪也是一种惯性,处处无家处处家,时间久了,冻土里面也长出了温情。他们的生活圈子分内外,对内维系着传统和文化,生活上彼此照顾;对外与周边环境、人、事交融,渗透。他们这一辈大多数人不会讲韩(朝)语了——他的韩(朝)语是后学的,不是特别流畅,但交流不成问题。他的女儿很早就开始学习韩国语,回韩国留学,毕业后嫁给了韩国人。前几年他和妻子在韩国买了房子,每年回来住几个月。他这么做,不是有什么叶落归根的情怀,他喜欢开放的生活,哪种生活让他感觉到自由和舒服,他就选择哪种。
他对生活所求不多。画画和写作,都是他最喜欢的。这两项工作在哪里都可以完成。他的写作主要是身边的人和事,并不拘于什么,一切随缘。
笔会倒数第二天的晚上,作家们去看俄罗斯作家在首尔举行的小型画展。他绘画的题材很常见:树林、道路、花朵、家禽,也有欧洲和非洲题材,他的画作颜色艳丽,天真烂漫。他喜欢画树,要么枝条稀疏,要么呈现絮状,还有的树树冠被他画成蒲公英式的花球,随时都会被风吹散似的。不管什么树,树根都跟豆芽儿似的,浮于畫面之上,而那些鲜艳的颜色,也因此变成了明丽的忧伤。
来自丹麦的女诗人曾经是弃婴,在冬天被遗弃在教堂门口,后来被丹麦的父母收养。她打扮中性,头发也是男生的样式,她作品的主题是关于遗弃和孤儿。
她长着东方人的脸,被带到陌生的国度,谁都能一眼看出她的不一样,进而知道她的经历。她是有父母的孤儿,在成长过程中跟谁都不一样的存在。她的成长是疼痛的、尖锐的、孤独的。她对被遗弃这件事情无法释怀:因为是我,所以被遗弃?还是遗弃凑巧发生在我身上?她的父母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们把婴儿扔掉?他们会想念那个弃婴吗?还是在遗弃的同时就选择彻底忘记她?
她直言,回到首尔的心情是复杂的,各种复杂。
午餐为我们准备了林延寿鱼套餐。
林延寿是个人名,生活在几百年前,热爱垂钓,钓技高超,出神入化,尤其擅长钓一种海鱼——就是现在被煎好后,摆在盘子里的这种鱼——他一个人钓的鱼,比其他人加起来还要多,久而久之,大家在谈论这种鱼时,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他是鱼的克星,是鱼的劫数,他的名字居然被用来为这种鱼命名。
林延寿鱼通常用大粒海盐先腌成咸鱼,吃的时候洗干净,整条鱼劈成两片,文火慢煎,鱼油慢慢渗出,给煎成金黄色的鱼上了层釉彩。米饭是用一人份小石锅焖熟的,旁边配着几个小碟子,是洒了芝麻的凉拌青菜、泡菜以及鲍鱼。
院长坐在我对面,怕我不会吃,示意我跟着他有样儿学样儿。
米饭用冷矿泉水泡了,用勺子捞着吃,这样的米粒更有嚼劲,配鱼吃非但没有腥味儿,反而强调了鱼肉的咸香。米饭盛出来后,要把一杯大麦茶倒进空的热石锅里,盖上盖子,米饭吃完的时候,石锅里的锅巴也泡软成了锅巴粥,锅巴粥不只养胃,也能让人把剩下的鱼吃完。
林延寿鱼中国也有卖的,买这种鱼的大多是朝鲜族人,所以多是在朝鲜族人聚居区的市场里卖。我妈妈对这种鱼情有独钟,每个人都有几样饮食,会通过舌尖深入到灵魂,跟亲情、离绪、乡愁联系在一起。我去延吉开会的时候,会专门跑趟农贸市场,替她买一箱回去。她转手就把这些鱼分给大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怀旧也要多人一起才有意思。
午餐结束时,盘子里的鱼变成了另外一副样子:孤零零的鱼头,眼睛还瞪着,身体却只剩下了一根刺,像是一场行为艺术。失去了肉身的鱼,变得狼籍,也变得狞厉,这时候再想起林延寿鱼这个名字,意味就完全不同了。林延寿抓了数不清的鱼,但更多的,多出几千倍、几万倍、几亿倍的鱼被蚕食的时候,林延寿的名字也被一次次凌迟。如此说来,名字因为鱼得以流传,竟成了报应。
下午的研讨会,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女作家朴实和来自美国的非虚构男作家以马内利。朴实很年轻,三十岁左右,扎着两根染成大红色的辫子,一身潮服,像是刚从东京涩谷、首尔江南夜店里晃悠出来。以马内利白衬衫配西装,皮鞋锃亮,头发一丝不乱,像商业精英。
朴实讲述她的个人成长史。在日本,她个头儿偏高颜值也偏高,女孩子引人注目并由此遭遇各种美好,那是偶像剧。在生活中,美丽出挑,吸引眼球,对少女而言是件危险的事情。她初中的时候被老师性侵。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每天下午被老师带回家里,被绑在椅子上,强迫她做各种事情,同时还伴以各种恐吓:如果你说出来,你会如何如何。她担惊受怕,天天噩梦,无助至极。朴实讲着讲着,声音哽住了,泣不成声——以马内利递纸巾给她,拍了拍她的后背,坐在她另外一侧的女作家接过来她的发言稿,替她读了下去。
朴实恢复了两分钟,女作家把发言稿递还给她,她接着发言:少女时代遭遇的事情,让她身心俱损,了无生趣。她开始逃课,与家人和学校对抗,和最好的朋友一起吸毒,变成了问题少女。她知道自己在沉沦、堕落,也知道这种沉沦、堕落的结果是什么。但那又怎样?或者说,她又能怎么样?很偶然的机会,她去参加了一个创意写作班,她随意写出来的东西被老师大为推崇,夸她有写作天赋。老师的反应让朴实吃惊不小,这是第一次,她被人如此正面地对待和评价。她受到了鼓励,写了几篇小说,她的小说给她带来了更多的读者和赞扬,还得了新人奖。她意识到,生活并不全是黑暗的,乌云也镶着金边,她应该换一种生活方式。她去美国,学英文,也学写作,这期间,跟她一起吸毒、堕落,同时又相伴相依的好友自杀了。好友的死亡重创了她。她自责自己的离开,质疑自己还能不能摆脱掉从前的阴影,她又变回那个孤独、无助的小女孩了,她也想自杀。如果没有写作,她早就不在人世了,写作对于她,是一种救赎方式。
我们都为她鼓掌。这么年轻,这么勇敢。她的写作是生命写作。少女时期的黑暗,被践踏过、伤害过的青春,送入文学的熔炉里,炼出绝世丹药也未可知。
以马内利在华盛顿长大。他的个人简介罗列了他关注的写作方向和他出版的作品,丝毫不提及个人经历。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到美国的。弃婴还是移民?他是非虚构作家,对朝鲜的一切他都有兴趣。他费了很多周折,努力了很长时间,终于去了朝鲜。他以记者的身份在那里待了几个月,被带到一些地方,采访一些允许他采访的人。国际社会对朝鲜有种种传言,实际上,就他的所见所闻而言,朝鲜没有外界说的那么妖魔化。物质生活是很贫乏,但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夸张。他在那里的几个月,他自认为是“深入生活”的,交了几个朋友,对很多问题——敏感的以及不那么敏感的——都有充分的交流。朝鮮很容易被各种想象涂抹,因为他们不透明。
在他的讲述过程中,有人微笑,有人摇头,有人不置可否。
在韩国讨论朝鲜,或者在朝鲜讨论韩国,都容易越谈越乱。以马内利的身份加剧了这种混乱。他这个有韩(朝)血统的美国公民,在朝鲜人眼里,未尝不是怪力乱神。他带着新奇的眼光去看朝鲜,朝鲜也同样审视着他。他对朝鲜的一切津津乐道,韩国人回以微妙的笑容,“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李沧东也参加了这次活动,以作家的身份。他们那一组上台时,他坐在最靠边的位置,仍旧是最抢镜的。
李沧东年轻时当过中学国文老师,功成名就后出任国家文化观光部长官,几年后又辞掉,专心当导演。他早期靠写作崭露头角,因为编剧进入电影界。二十多年前,韩国兴起一拨儿“作家电影”,好几个作家都改行当了导演,并且成绩斐然。作家导演的电影通常比较细腻、文艺,比起“观看”,更像“阅读”——李沧东算是其中的翘楚——但同时也沉闷,缓慢。文艺片一直孤芳自赏,韩国的文艺片可以加上“尤其”两字。
李沧东的电影认可度很高,一方面很文艺腔;另一方面,也不缺少冲突和戏剧性。十年前,《密阳》大火了一阵子,那个电影,故事有明显的漏洞,但也有来自内心深处或者说灵魂的碰撞,人物之间有很多硬对硬的磕碰。女主角的扮演者全度妍,演技大放华彩,像她的名字“度妍”一样,把这个电影作品变得熠熠生辉。去年,李沧东把村上春树的小说《烧仓房》和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烧马棚》糅合在一起,拍摄了电影《燃烧》,得了好几个奖。估计只有作家出身的导演,才会烧出这样的脑洞,把村上春树和福克纳联系在一起。
多年来,他一直以作家自居,“作家”是标签和符号,意味着原创、深刻、独特,还有那么点儿超凡脱俗,他的电影都是自己编剧,这次他来参加讨论会谈的是电影《燃烧》,他为什么要拍以及拍摄过程中的一些思考。他的存在,让一些听众很兴奋,尽管听众们是奔着文学来的。而作为国际知名导演,李沧东来参加这种活动,一是强调自己仍然在文学现场,另外也是对韩国文学的致敬和肯定。
来自瑞典的阿斯特丽德跟我同年同月生,也是个弃婴,被遗弃在釜山,警察捡到她后把她带回首尔,五个月大的时候被一个瑞典家庭收养。她瘦瘦弱弱的,衣服颜色灰暗,体量上像个未成年人,但她已经有个二十岁的儿子了。
她在瑞典身兼数职,作家、编辑、校对、自由职业者、语言教练,做着这么多的工作,她还坚持写作,出版了好几本书。
她的身量让人想叹息,这么瘦小,在童年少年时代,在瑞典那样的国家,几乎是个现实版的“拇指姑娘”吧?她不会讲韩语。收养她的父母为了让她多了解韩国,尽可能地让她多接触东方文化,而真正让她有印象的是中国杂技和日本文化。直到她成年,开始写作,参加文学活动,才开始阅读韩国文学作品,看几部韩国电影,听听韩国流行音乐。
她必须了解韩国吗?血缘必须寻根?她的童年少年时代该有多么纠结啊。有些事情确实是没法儿轻易翻篇儿的,树欲静,风都不止。她的淡眉细目,她的羸小瘦弱,会激起多少异国他乡的所谓关心啊。他们会在派对上一遍遍问起她的来历吧?会提醒她追溯自己的血统和文化吧?鸡汤一勺勺倒进她的碗里,没人问她是不是讨厌鸡汤,没人在乎她需不需要这种关心。很多人的善良是用来表现和表演的。
她其实已经走得很远了,北欧瑞典,丈夫是瑞典人,儿子是混血;但还是走回来了,回到她生命开始的地方,回到她被放弃的地方,开始了解和学习关于韩国的一切。
中午我们去吃素斋。这还是我第一次在韩国吃素斋。一楼是个商店,卖念珠、香炉、线香等等佛教用品,二楼是饭店,顺着过道隔成一个个隔间。我们被分配到不同的隔间里面坐下,服务员穿着僧服,一道一道地上菜,态度平和,简洁地介绍几句菜品:用果酱腌制的圣女果,端上来时很像蜜枣;放了松仁的南瓜粥;四种山野菜凉拌的沙拉;蘑菇、木耳、藕片炒成的合菜,上面撒着芝麻;野生橡子做成了橡子冻,切块拌成的凉菜;添加了大枣、板栗的杂粮饭;野果果汁、藜麦茶。
食材简朴,摆盘却漂亮、精致。每一款食物端上桌的时候都像件艺术品,吃饭这件事变得郑重、端庄,大家下意识地正襟危坐,优雅进餐。
纪录片《主厨的餐桌》里面介绍过一个韩国尼姑静观师太,是个做素斋的高手。曾经被请到纽约做菜,惊艳了众人,参加那次聚会的一位美国纪录片导演路转粉,追着她的脚步跑来韩国拍她。
静观师太六七岁的时候就模仿妈妈给家人做面条,出手不俗,妈妈夸奖她说,有这样的天分和能力,以后她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她十七岁的时候,没有像普通女孩子那样谈恋爱,到深山里面的白羊寺当了尼姑。
寺院里的生活原始而又艰苦,凡事都要亲力亲为,十七岁的少女静观,每天早上三点钟起来做早课诵经,然后忙上一整天,睡眠严重不足。她有一次出门打柴时爬到一棵树上睡着了,睡梦中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身体上,睁眼一看,一条粗大的蛇正从她的脖子边滑过她的身体,她居然没害怕,又睡过去了。她给父亲写信,说自己好困啊,想回家了。她父亲和兄弟姐妹来接她,她却不是真想回家,只是想念家人,想见见他们。因为这个插曲,寺院里后来允许她不做早课,每天多睡几个小时。
静观做菜的天分在寺院里发挥到了极致。《主厨的餐桌》介绍的都是米其林顶级大厨。静观师太是个例外。静观师太的食材都是普通谷蔬,她的菜园和林地交融在一起,种菜相当随意,栽上芽苗后,就把它们交给土地、阳光、雨水,让菜苗自然生长。野猪偶尔会来拱菜园里的菜,虫子就更多,把菜叶咬出许多孔洞,她不以为然,因为:众生平等。她从不认为自己是厨师,对她而言,做菜是一种修行。她的素斋不需要食客的追捧和美食家的鉴定,她的每一道菜都是一道禅,让吃的人心静平和,摈弃尘杂。厨师们惯用的生猛海鲜、新鲜红肉,让人在口腹之欲得到极大满足之后,内心火气飞扬,而素斋与之相反,是让人沉静、冥想的手段。
素斋是饮食教育。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滚滚红尘。素斋就像“攘外必先修内”的课堂,一道道菜像一个个哲学话题,严肃深沉,相比之下,那些油炸食品和香气四溢的快餐,倒像娱乐节目,艳丽、喧嚣、空洞少营养。
静观师太的父亲后来又去寺院看她,住了一段时间,每天跟她们一样吃素斋,有一天抱怨说,每天都吃这样寡淡无味的东西,怎么可以?靜观师太给他用香菇烧了一道菜,她父亲吃后,感慨说:丝毫不比肉逊色,既然有如此美味,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第二天他离开寺院时,在院子里给静观师太,也是他自己的女儿鞠了一躬。回家后没多久,他就过世了。那些寺院里的素斋,是父女二人红尘空门之间的对话。静观师太用食物说服了父亲,让他安心离去。
来自巴西的尼克是作家、编剧,以及电影制片人。十几岁的时候跟随父母移民去巴西,在巴西,东方人是少数族裔,韩国人被称为“鲑鱼色”人,由于巴西日本人众多,他常被人当成日本人。在他上学的学校,除了他以外,另外一个韩国人是他姐姐。他们非常孤独,打破这种壁垒的是足球。他的足球踢得很好,经常被同学拉出去一起踢。在踢球的过程中,尼克学会了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随着语言能力的提升,沟通没有了任何障碍。他融入了当地社会。而巴西的历史本来就是移民史,只是大家来自的国家不同、到来的时间有早晚罢了。巴西近年来的状况让人不安,经济低迷,民粹主义盛行,社会治安差,犯罪率极高,文化艺术变得奢侈而边缘,各族裔之间又开始形成鸿沟。
尼克讲话时,忧国忧民忧局势忧互联网忧全球,刚下场就急不可迫地问主办方:明天的晚会我来当DJ吧,我强烈要求当DJ!
还有一些有意思的人,话不那么多,性格内向,言行低调的:来自夏威夷的韩裔英文教授绅士气十足,谦和有礼;来自日本的舞台剧剧作家永远是笑眯眯的;来自德国的作家、剧作家兼导演,年轻轻的却鲜有笑容;还有一位从法国回归韩国国籍的女作家,也曾经是弃婴,人到中年,患了严重的抑郁症。每个人身上都杂糅着两方面的特质:一是生活经历形成的礼貌和教养,二是内在血统延展出来的眉眼间的相似。
我的发言是关于个体的。我们曾经是同一条河流的石子,这把石子被命运的手抓起来,撒出去。新环境里面的融合并没有那么简单,不停地迁移,流动,寻找安身立命的最佳地点,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移民为了契合进新世界新秩序,不得不磨掉了身上的特质和一部分性情,而现在,这个会议像两根手指,把我们从世界各个角落里拈出来,重新聚拢成一把石子。我們彼此好奇、感慨,但同时也清楚:我们回不到那条河流了。
最后一个下午和晚上,是派对时间。地点选在一个小山上,那是一个石刻公园,摆放着各种石雕石刻作品。有古代传承下来的,也有艺术家新近创作的。历史和现实杂糅在一起,既随意又和谐。
派对在公园小博物馆的二楼平台上举行。因为地势的缘故,这个平台跟上山的坡路是平齐的。靠近建筑物的那侧和平台正面,各有两堵大理石墙壁,这两道壁垒加上山势和缓坡,圈出了一块既方正又开阔的平地。这个空间不止能摆放几十张桌子、自助餐菜品、饮料区,还布置、搭建了一个临时舞台。我们在山上四处欣赏石雕作品时,乐队在调试音响,电吉他、架子鼓时不时轰隆隆地响上一阵。
派对从傍晚时分开始,天色正在由明转暗,灯光逐渐亮起来。之前我们已经被提醒室外派对气温会比较低,朴实、以马内利,还有德国作家,好几个人直接把酒店的浴衣套在外衣外面。在天色变得昏暗的时候,他们几个像北极熊出没,引得大家笑起来。尼克如愿以偿被允许在演出结束后充任DJ。
菜品、酒、饮料准备得非常丰盛,除了韩国的烤牛肉、烤海鲜、炒五花菜,还准备了十几种西式菜品,无论来自哪个国家,都不难从中找到一两种自己喜欢的菜式。几天来我们一直在吃“韩式”餐饮,饮食是另外一条回故乡的道路,比创作更直截了当,更深入肺腑。派对菜式的多样性,让大家瞬间找回自己的日常慰藉,选择自己胃肠最熟悉的那些。但这也是我们本次会议最没特色的一次聚餐。兼顾大局,可能都要以消灭个性为代价吧。饮料倒很韩式,韩式烧酒里面兑上啤酒,用力地在桌面上一磕,在啤酒沫涌出时,一口喝光。
餐饮的同时,演出就开始了,一个摇滚乐团先开场,女歌手弹着吉他唱了几首歌。气温在不断下降,两个刚上场的美女穿着吊带红裙,跳探戈舞,身材曼妙,动作撩人,热情火辣,但裸露的肌肤在这样寒冷的夜晚,唤醒的却不是性感而是担忧:别感冒了啊。节目表演的间隙,有几个人上去朗读自己的诗歌。丹麦女诗人读的还是那首关于遗弃和收养的长诗。这几天她好像没换过衣服,维持着中性的、特立独行的作风。
气温越来越低,主办方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几十件羽绒服,给大家分发下来。年纪大的人先穿上了,然后是女人。
阿斯特丽德也上去朗诵诗歌,可能是身材细弱,女性气质更突出的缘故吧,她仅仅是站在舞台上面,一股悲伤的气息便已传来。人群中有人发出惊叹声,一些人扭过脸去,我们都跟着转过头:不知道什么时候,侧面的那道大理石墙壁上面,一个舞者全身上下被一层贴身红布裹挟着,在墙上慢慢地、一边做着各种动作一边往前走,这个红色人体——活着的、不断变形的现代雕塑作品——既是精神化的体现,又像幽灵。阿斯特丽德的诗很长,但这位舞者的路更长,这个红色的、血色的人,在高处,在窄处,在幽暗处,一步步前行,像蒙着红布的不同塑像。我们看不到他的面目,却因此更能清晰地感觉到他的生命律动和复杂情感。阿斯特丽德的朗诵结束了,舞者从高高的石墙上下来,但舞蹈并未结束,他扯掉了红色的布,露出赤裸的、涂成白色石膏般的身体,不知道是不是被红布沾染的缘故,他身体上有一块块黄色的印迹,就像陈年的被磨损的石膏像。舞者的脸也被涂白了,在我们捂着羽绒服瑟瑟发抖的时候,他拿着一个花园浇水的水龙头,将喷水的水柱对着自己从头到脚地浇下来。在舞蹈的最后,他从花圃里摘下一朵红色的玫瑰,走过去递给一直站在舞台上的阿斯特丽德。她接过花,他们拥抱在一起——
艺术家们不发一言,一个舞蹈就把这次会议的灵魂剖出来放在大家面前,三天前刚来首尔的时候,会议还像冰山,露出来的那一角,宛若明媚的水晶。作家诗人们客气而疏远,随着写作和个人经历的剖白,冰山不断融化,这个沟通与交流的平台,像个大海绵吸了太多太多的水分,变得越来越沉重。
这一次离散者聚会。每个人都坦露了一些伤和痛,有相似的,也有不同。血之源头,是生命的起源,但并非是每个人的家园,哪怕冠以“心灵”或者“精神”字样,也不可能。命运就是命运,不争论,不废话,命来如山倒,剥茧抽丝以及其他种种,那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
离别将至,每个人的表情都是平和的,回酒店时,街边那把气球仍在,它们被线固定在地上,想要飞却注定飞不起来。作家们彼此拥抱、告别,阿斯特丽德和我想象的一样瘦弱,仿佛翅膀合拢的鸟儿,拥抱过后,她问:我们还会再见吗?
我觉得不会。
但我回答:当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