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光年
2020-09-17李静睿
李静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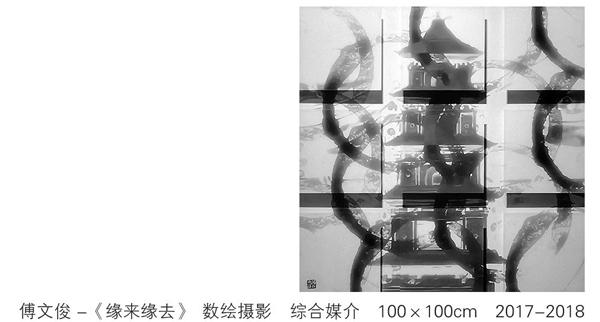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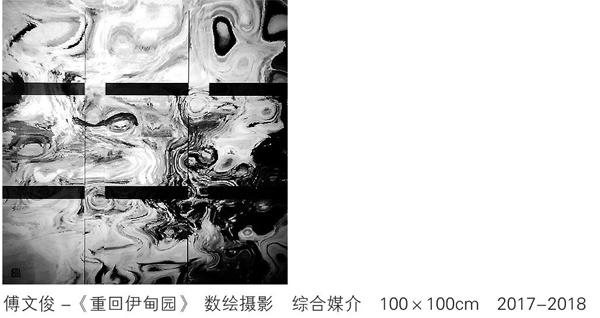

1
春天,一切都遵从秩序,如期而来。起先是持续而可以忍受的霾,后来刮了几天沙,到了四月十号,我进地铁前看见风中有两朵孤零零的杨絮,盘旋许久,最终粘在一个坏掉的共享单车的把手上面,但等我出地铁,漫天杨絮已经像海浪,把所有停滞在岸边的人席卷。
我就在那场海浪中看见黑洞的照片的,糊里糊涂的一个洞,也不是特别黑,旁边有一圈金边,像用老早之前的诺基亚拍的照片,也像一个甜甜圈。
半夜我下楼喂猫,带上清水、猫粮、罐头和一盒甜甜圈,小灰闻到罐头味,先在围墙上张望了一下,确定是我,这才跳下围墙,从排水孔中钻出来。这堵围墙一共有十二个排水孔,但小灰只从数过去的第三个孔钻出,每次出来都一股焦味,浑身奓毛,脚心肉垫沾满闪闪尘埃,像这短短十秒中,它走了一段过于漫长的路,比如从这一颗星,走向那一颗星。我挠它的下巴,又倒了整个罐头,小灰这才平静下来,喝水,吃罐头,躺下来打滚,邀请我抚摸它的软软肚皮。
我摸着小灰的肚皮,对着围墙那边说,我看见了,黑洞照片。原来长这样,就像一个甜甜圈。
过了一阵才有回音,我今天晚了五分钟,他大概是走开又回来,他的声音又近又远,像一个人同时在天边和眼前:什么是甜甜圈?
我从盒子里拿出一个,咬下去满嘴糖霜:说不清楚,我给你带了几个。
谢谢,上次的草莓冰砂也很好。
化了没有?
什么?
草莓冰砂,到你那边融化了没有?
哦,没有,还是满杯的冰。
那就好,小灰挺快的。
是啊,小灰很快。
我们都沉默了。小灰听见自己的名字,以为又要去到那边,不怎么高兴,竖起飞机耳,又亮起眼睛。小灰的眼睛一绿一黄,像某个路口的闪烁路灯,但这条路并没有灯,我看见的一切,都只能借助月亮、星星,或者小灰的眼睛。
现在它们都在这里。初六的月亮,顶上的木星,小灰亮起的眼睛,我看见这条路直直向前,尽头处也没有墙,只是在一棵桑树前戛然而止,前面是一片拆迁后的废墟。最早它大概也计划通往某个地方,但后来大家都忘记了到底怎么回事,就像这里拆迁时说要建个社区公园,但好几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最早小区里的人会在傍晚散步到路的尽头,对着砖石瓦砾,想象一个公园,后来就只有拾荒的男人在废墟里翻拣那些来不及搬走的东西,巨大的铁锅,一叠叠铝碗。再往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车,也没有人,只有两排大树,流浪的大狗在倒塌的房梁下拉屎,路旁稀稀拉拉有几个木椅,修路的时候也精心设计过,每个木椅都正好在树影下面。桑树长得比围墙更高,自顾自结出满树桑葚,又自顾自掉在地上,早上出门时远远看见,我想,要是刚才有桑葚就好了,我就可以用来拌光明酸奶。
我在半夜下班回家,突然想起这些桑葚,又想起明天早晨我依然吃光明酸奶。我就是那时候第一次见到小灰,我向路口走去,它则从路口数过去第三个排水孔里钻出来,月光下小灰近乎银白,身上闪闪发光,像星星坠落了,而它沾满碎片。小灰开始有点蔫,过了一阵才高兴起来,吃我從包里翻出来的一袋海苔饼干,后来它每次过来都这样,我总觉得小灰更喜欢我们这边,他却说,小灰去那边的时候也是这样,猫的活动半径原本应该只有五百米,它们天然恐惧陌生和遥远。
但小灰还是又去了那边,带着两个甜甜圈,我用保鲜袋包好扎紧,挂在小灰的脖子上面。我靠着围墙坐了一会儿,等待他吃完,排水孔中似乎有风声,可能那边也是春天,今年的桑葚还要等两个月,去年最后那批在秋天来临前我做成果酱,让小灰带了过去。
可以蘸馒头吃,我挨着围墙说,比涂面包好吃。
其实什么都是不确定的,比如那边有没有馒头、面包或者秋天?我从来没有问过什么,整件事都太荒谬可笑了,我甚至无法鼓起勇气和对方确认任何细节,以问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到底是哪里呢?我是说,你们那边?
但这一次我下定决心要确认一点什么,科学家观测了十几年,又花了两年,仅仅为给一个黑洞拍摄糊里糊涂的照片。我也应该为人类做点什么吧?如果我真的每晚坐在一个黑洞旁边?如果我真的每晚给黑洞那边的人或者其他不知道什么东西,送去果酱和甜甜圈?
我等待小灰再次回来,它还是那样,蔫不拉几,浑身奓毛,脖子上挂着的两个甜甜圈不见了,空气中只有一点糖霜的甜香,那种香味让人痛苦,既实实在在,又无迹可寻,你不可能在夜晚的风中抓住一个并不存在的甜甜圈。
他在墙那边说,谢谢了,甜甜圈很好吃。声音拖着一点尾巴,这代表今晚结束了,我应该回家涂晚霜、吃褪黑素、戴上蒸汽眼罩,等待睡意在四十分钟后来临。我应该做狂乱而适度的梦,然后在明天七点准时起床,洗头,化妆,坐地铁去国贸上班。他则不知道会在哪个宇宙哪个角落继续哪种生活,就像多年前刚开始用ICQ,我有一个在英国的网友,当头像的灯暗下去,伦敦就略等于火星,或者更远的星系。
我突然说,你等一等。
他愣了一会儿才回答,什么?
我让你等一等。
等什么?
你知道吗?我们拍到的那个黑洞,和地球隔了5500万光年。
知道,我看见了。
看见?
是啊,你们那边的事情,我都能看见。
我们呢?我们到底是更近,还是更远?我们……我们中间是不是就是这个黑洞?5500万光年?
这条路多安静啊,连小灰从这一棵树走向那一棵树都有所惊动,连风都显得吵闹。桑树还没有到夏天极盛的样子,但树影已经密密匝匝投在地上,树叶和树叶的间隙有闪耀光斑,像一个个亮起的ICQ头像,但他的头像暗了下去,没有留下回答。就这样,他暗了很多天。
2
这套房子是租的,一室一厅,户型不大好,卧室是个三角形,客厅不小,但有一堵歪着的墙。看房的时候我和胡楝刚在一起,他说,找来找去也麻烦,这里挺好的。
对方似乎认真想了想,是吗?我们都觉得它是小灰。
连这个时候我都没有问下去:“我们”是谁?我只是接受了这是小灰,也接受了有一个人不在那个红色沙发上,却在排水孔的另一边,看过那么多科幻小说和电影,我含含糊糊知道那一边意味着哪里,却始终不敢确认。
从那天开始,我每天晚上和他聊一会儿天,哪怕是胡楝过来的时候。亲密完之后我说,我要下去喂一下流浪猫,胡楝嗯一声,裸体坐在地毯上,打开笔记本回公司邮件,有一次出门前换鞋,低头时正好看到他的隐秘部分,这个部分早就是流程的一部分,但我突然撇了撇嘴,进了电梯我还在反复回想那个撇嘴,好像是一种久违的叛逆。
就这样,小灰、排水孔和他猛然进入了我的生活,像一场不为人知的剧烈碰撞,没有声响,但留下痕迹,我并没有试图把整件事纳入新的流程,我只想在流程之外,偷偷藏起来一些可能与之对抗的东西。
他再次出现的时候,我让小灰送过去一小瓶槐花蜜,瓶盖没有拧好,滴了几滴在排水孔门口,没多久就聚集一队蚂蚁。
我放在茶里了,很甜,谢谢,他说。
是啊,槐花蜜真的很甜。我们这条路上就有槐花啊,你能看见吗?我指了指天上,除了桑树,这条路还有白蜡、臭椿、银杏和槐树,错落长在围墙两边,但树是不知界限的,树盖似云,无差别地在两边投下树影。如果他坐在红沙发上面,春天就能看见满地槐花,臭椿有一股奇异香气,秋天银杏黄了,落下心形树叶,冬天一切都枯萎了,像一个人决心暂时死去。如果,如果他真的坐在红沙发上面,他就能看见这些。
可以啊,我能看见,他说。
真的?你能看见?
是啊,我不是告诉过你,你们那边的事情,我什么都能看见。
大概蜂蜜茶实在太甜,这些话像水一样轻易地流向我这里。他浑然不知这在春天意味着什么,正是四月底,北京的春天又急又短,但那时候还是确凿无疑的春天,我们穿波点真丝衬衫和露出脚踝的大摆裙,用玫瑰色口红,怀着好事会和玫瑰一样在夏天来临的幻觉,而这些话是幻觉的证据。
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3
好事并没有在夏天来临,一件都没有。导演那边终于正式回话拒绝,因为一个影视中心找他去拍一个连环杀手落网的电影,“剧本还是不错的”,他倒是客客气气,直接和我发了微信,也没有用语音,对他来说,他大概觉得这就算尽了力,毕竟在此之前我只是一直和他的助手联系。助手是个一直客客气气,但长期不回微信的女孩子,五月底我忍无可忍,拉黑了她,又在半个小时候后悔,加了回去,理由是“不好意思哦亲爱的,清理通讯录误删了,爱你”,她把我加回来,仍然沉默不语,甚至没有发一个表情,从那时候开始,我再也看不到她的朋友圈。
老板很生气,认为是我没有跟紧,又怪我没有同时接触几个备胎,但四个月之前,在导演的助手又一次一周没有回微信之后,我找过一次老板。
剧本发过去都三个月了,我们要不要催一催?我问。
那时候暖气已经停了,真正的春天却还没有来临,大办公室全在阴面,大家都穿高领毛衣,喝滚烫的热水,为不那么热的外卖郁郁寡欢。但一进去老板办公室,整面朝南落地玻璃窗,老板穿一件墨绿色法兰绒衬衫,像伍迪·艾伦电影中的男人。他桌面上确实放着一本《伍迪·艾伦谈话录》,墙上是《曼哈顿》的海报,老板正在看项目策划书,这几年公司靠批片挣了不少钱,但挣钱意味着需要做更多挣钱的事情,我们并没有找到更多挣钱的事情,所以上上下下还是不开心。
听了我的话,老板犹豫了一会儿,任何事情他都是这样,总会犹豫一会儿,这也像伍迪·艾伦电影里的男人,都是知识分子,看起来也体面,住在上东区或者上西区,参加名流聚会,但每一个都东张西望犹犹豫豫。
不要了吧,大导演是这样的,手上几十个项目找,前几天饭局上还遇到了,他说咱们的剧本不错……再等等吧,你老催别人也烦。
那我要不要再找找别人?找几个新导演,万一这边不行,起码能保证今年能开机?
他再次犹豫了一会儿,把婚戒反复取下又戴上,又一个需要他决定的时刻,而每一次决定都让他痛苦和犹豫。
算了吧,圈子太小了,传来传去总会被人听到。
老板说得都有道理,但道理并不改变结局,而现在结局就摆在眼前:项目今年是铁定无法开机了,这意味着上映时间起码拖到了后年,我们是都市爱情片,很多细节根本无法拖到后年,于是又得再改一次剧本。上次合作的编剧已经在做别的项目,另找编剧意味着双方重新磨合,也意味着另一笔钱,和所有老板一样,他当然不想花出另一笔钱。他对自己感到愤怒,这种愤怒在三十平方米的办公室里上升盘旋,寻找出口,然而没有出口,每一面落地窗都死死封住,最终这种愤怒毫不犹豫地指向我。到了这时候,他又突然变得果断,因为我是无足轻重的,他对办公室里的琴叶榕也许都比对我客气。
骂了十五分钟,老板说,你自己想想应该怎么办。又一次地,他下意识逃避做决定,把球扔回给我,然后转头开始做越南冰奶咖啡。应该怎么办?我税后月薪一万五,最贵的包是一个打折COACH,去年因为整个部门没有一个项目真正开机,大家都只拿到八千块年终奖,年会是去昌平泡温泉,我只是一个规规矩矩按照流程往前的人,为什么需要决定应该怎么办?
小半年时间里我都在无所事事地加班,但等到确实需要加班的时候,我五点半准时打了卡,同事们齐齐戴着耳机看我走出大门,露出憐悯眼神,他们大概以为我很快要被开掉了,出写字楼时候连保安都在偷偷看我,整栋大楼二十几家公司,这个时间大家甚至连外卖都还没有开始叫。我们每天都会为此痛苦,就像我们为每一件事痛苦:五点半就叫外卖会不会有点早?好像别的人都还没有开始叫?那六点半呢?那样送到的时候就是七点,但七点是不是又有点晚,总是这么晚吃饭,会不会对胃不大好?最后大家都决定在六点订外卖,订单太多了,所有人都等到了七点半,米线糊掉了,烤肉拌饭又油又冷,只有索性在楼下“7-11”买盒饭的人,吃着热乎乎的麻婆豆腐和西红柿炒鸡蛋。我们大部分人都懒得去“7-11”,因为从一号楼走到五号楼也需要一点时间,那点时间没什么用,但我们都对时间太过焦虑,就是无法浪费一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