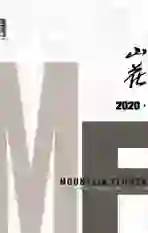典故中的中国(一)
2020-09-17鲍鹏山
鲍鹏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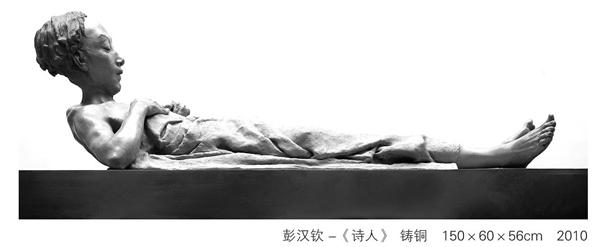
引 言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年2月23日—1969年2月26日)在1949年出版了《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他站在世界文化的旷野上,对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人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这个时代在中国,就是春秋战国时代。
雅斯贝尔斯把这个时代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间。)在这个时代,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里,人类的文明精神出现了重大突破,出现了一些伟大的精神导师——中国有孔子、老子,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
雅斯贝尔斯认为,这种突破,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雅斯贝尔斯称之为人类“终极关怀的觉醒”。人类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宗教开始出现。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就是出于他们各自不同的超越和突破类型。
如何理解雅斯贝尔斯所说的“终极关怀的觉醒”?
我的理解是:
第一,人类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对宇宙现象予以抽象,把世间万象逻辑化,而不是零敲碎打,个别地孤立地认识世界。同时,人类开始严肃地思考人类和宇宙的关系,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认识论出现。
第二,人类开始有了类的自觉和个体自觉,开始认识人类的种属特性和每一个个体的自我身心,认识到人和世界的关系——世界观觉醒。
第三,开始思考人我关系,开始认识到人是有道德使命的,即,人是道德的存在,从而区别于一般动物。而且,人还负有建设道德世界的责任——伦理学展开。
第四,人类有了明确的时间意识,开始关注人类历史,意识到人类是一个文化的存在并且有着文化的使命和宿命,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历史观诞生。
其实,在中国,在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过去不到一百年,汉朝的汉武帝时代,一位太史令,一个大学者,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对中国的轴心时代作了深刻的总结。他的一篇专题论文《论六家要旨》,总结了轴心时代六个重要流派的主要思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
大约再过二百年,东汉的一个大学者,史学家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中,在六家之外,又加了四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于是有了“九流十家”之说。
其实,“九流十家”仍然没有囊括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信仰、思想与知识,比如:兵家、医家……
他们是这样一些人:老子、孔子、墨子、孙子、孟子、庄子、商鞅、荀子、韩非子……
他们鼓吹着这样一些概念:道、德、仁、义、礼、智、信、勇、法、术、势、王道、仁政、兼爱、尚贤、大同、小康……
每一个概念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对整个人类文明和人类道德使命的思考。这些思考变成了文明的成果积淀下来,这些积淀最后就成了人类生存的价值观和价值基础。
并且,这些价值观,既是普世的,与世界各民族的基本价值观相一致,还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特色和呈现风格,以及价值的实现路径。中国,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开始了!
这个时代,是活色生香的时代,是龙腾虎跃的时代,是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时代。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故事,包含着一个民族的文化DNA,在这些故事里,藏着中国,藏着中国的过去,现在,更藏着中国的未来。
紫气东来
司马贞索隐引汉刘向 《列仙传》:
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一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是孔子描述的春秋时代。
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其所说的公元前600年,其实,就是老子的诞生。
关于老子,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这样记述: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做过周朝掌管藏书室的史官。
看,老子是哪个国家的人我们知道了,哪个县也知道了,哪个乡也知道了,甚至哪个村我们也知道了,姓也有了,名也有了,字也有了,官职也有了。说得非常非常明白。
但有关老子的一切,自古以来就神秘莫测:去了其实是来了,死了好像才是出生了,结束了其实才是开始了,明白的其实是不明白的。你看司马迁这段记载,讲老子籍贯,姓氏,特别明白却完全不明白。为什么?
第一个不明白:姓名问题。
既然他姓李名耳,我们叫李耳就是了,或叫李聃不就行了,为什么又叫老子呢?司马迁偏偏不说。
于是就有各种解释。有的是这样解释的:
长寿。老子寿命很长,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的后面也讲到了。
还有“老”这个字和一个字的字形非常相似,就是“考”,最后一笔往上面一勾就是老,往下面一勾就是考。“考”也是长寿的意思,有一个词:“寿考”。所以老子大概是个很长寿的人。但是司马迁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李耳之所以叫老子,是因为他长寿,一句话的事情,司马迁没说,或者就是不说,或者他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这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疑团。
还有的是这样解释的。晋朝葛玄《道德经序》说,“老子生而皓首”,一生下来就满头白发。我觉得这个说法,倒符合葛玄这样人的思维特征。他其实不是在讲历史,也不是在講事实和科学,他在讲寓言。他用的是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所谓“生而皓首”,实际上是指他一生下来就饱经风霜,历史的一粒灰尘,落到一个人头上,就是一头白发。并且,这个隐喻还不仅指他一个人,不仅是有关他个人经历、心灵与智慧的隐喻性象征,更是有关我们这个早熟民族的心灵与文化的深刻的隐喻。他的职业:“周守藏室之史”,实际上也可能是一个隐喻,与前一个隐喻是一个因果系统——我们历史悠久,饱经风霜。我们少年老成,老奸巨滑。读《道德经》,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一个民族的早熟。
还有第三种解释。张守节《史记正义》:“李母怀胎八十一载,逍遥李树下,乃割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玉女梦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经云:李母昼夜见五色珠,大如弹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娠。”
这就还是那个伟大人物都有不平凡的孕育和生育的古代神话套路。
当然也有从事理上理解的,《正义》引张君相曰:“老子者是号,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教众理,达成圣孳,乃孳生万理,善化济物无遗也。”
这是从圣人思想考教众理,教化万物的角度来解释“老子”一名。但这样的解释,就太师心自用了。不靠谱的。
撇开“老子”称呼的不可解,“李耳”一名,其实也很有意思,《正义》:“姓李,名耳,字伯阳,一名重耳,外字聃。”那个时代人们起名字有一个特点:往往以身体的某一特征起名。孔丘者,头顶不平如丘也。李耳,字聃, “聃者耳大也”,现在老子的画像也好,塑像也好,福建清源山老君岩老子的石刻像,耳朵都很大,大到肩膀上,这个也是有根据的。我们中国人老讲“耳朵大有福气”,这个文化就来自于老子。你看,老子,不仅他的思想和智慧影响了中国,连他的耳朵都影响中国了。
大概老子生下来,耳朵比较特别,所以他的父亲就给他取个名字叫“李耳”。对李耳的外貌,还有这样的说法:南朝梁人殷芸在其笔记中,对老子的形貌有这样的记录:“老子始下生,乘白鹿入母胎中。老子为人:黄色美眉,长耳广额,大目疏齿,方口厚唇,耳有三门,鼻有双柱,足蹈五字,手把十文”。唐人张守节据此在《史记正义》里添油加醋地写道:“老子……身长八尺八寸,黄色美眉,长耳大目,广额疏齿,方口厚唇,日月角悬,鼻有雙柱,耳有三门,足蹈二五,手把十文。”殷芸这样说就算了,毕竟他是写“小说”,可以虚构。张守节这样干,就不对了。毕竟,你是注史啊。
只能说,老子此人,能量太大,使得靠近他的人,眩晕。乱方寸。
好,再看看老子的官职问题。
官职是“周守藏室之史也”,什么叫“守藏室”?很多人说是图书馆,实际上那时候不存在什么图书馆,更没有现代公共图书馆,应该是政府档案馆,文献资料室,兼有图书馆的一些职能,如历代的图书都放在那个地方。他是这里的“史”,馆长,研究员,王朝大事书记员和档案管理员。所以说“道家出于史官”,是有根据的。
这还不算太大的问题。司马迁写老子传,写着写着,却突然自己疑惑起来:我是在给什么人写传呢?
一个历史学家,给人写传,写到最后,自己却眩晕了:不知道在写谁,这可以说匪夷所思了。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写到最后,竟然写了三个老子:李耳、老莱子及太史儋。到底哪个才是老子?
司马迁确实没搞清。但是,我们其实不用太纠结。我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把问题倒过来——
我们不管谁是老子,我们只管谁写了《道德经》。谁写了《道德经》谁就是老子。
我们不管谁是老子,我们只看谁见了孔子。孔子见的是谁,谁就是老子。
正如历史上关于屈原之争,其实也可以这样简化:谁写了《离骚》,谁就是屈原。既然有《离骚》,那就一定有作者。谁是这个作者,谁就是屈原。哪里用得着那么费事。
于是,老子的出生年月,也就简单了:孔子是公元前551年出生的,老子比孔子至少大一辈,算他公元前600年出生,大孔子50岁,不算太离谱。
所以,我前面说,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公元前600年,是按照老子出生来确定的。
好,说完了老子的出生,我们再谈谈他的死。
关于老子的死,有一个说法:老子其实没有死,而是出走了。出关西去了。
说到老子出走,就要说到一个典故了:紫气东来。
其实,这个典故也可以用以说明世界文明:在那样的时刻,世界的东方,一片祥云升起,为世界带来文明。
关于老子出关的原因,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样记载: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
老子研究道德学问,他的学说以隐匿声迹,不求闻达为宗旨。他在周的首都住了很久,见周朝衰微了,于是就离开了。
“以自隐无名为务”,这句话有意思。因为,人必须已显行迹已有名声,才有隐藏行迹埋没名声这样一层烦恼与需求,否则,历史上漫漫而来又漫漶而去的芸芸众生何其多耶,谁又需要一门专门的学问来泯灭行迹名声?恰恰相反,一般人要的是如何追求名声的学问。只因老子是他那个时代的大名人,所以才有这层烦恼。后来孔子不远数百里求教洛邑,给他带来压力[1],话不投机,还要勉强自己应付,也可印证他的烦恼。
但他一直郁郁寡欢高冷孤傲的原因,却不是这层烦恼,而是作为周朝的档案馆馆长,看多了残酷的历史,又看到了周朝的衰败。并且,作为一个思想家、历史学家,他看到的,还是更深层次的衰败:文化的衰败,哲学的衰败,文化已经不足以提振和凝聚人心。
于是,他黯然离去。
离开了周,老子去哪里呢?
据说是出关去西域了。
出的关据说就是函谷关。
函谷关当初大概在今天的河南灵宝县,后来关口移到了今天的河南新安县。这里两山对峙,中间一条小路,因为路在山谷中,既深又险要,好像在函子里一样,所以取名为函谷关。
老子出关,一件大事发生了。
按说,离去,是一个结束。没想到,却是开始。
是的,老子离去了,但是,老子的时间却由此开始了。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到了函谷关,关令尹喜对他说:“您就要隐居了,勉力为我们写一本书吧。”据说这位关令尹喜是周之大夫,也是一个隐德行仁的高人。一般人也是看不到东方天际线上慢慢西移的紫气的,并且也不知道老子的价值,思想的价值,他哪里会要老子著书,要老子脑袋里的智慧,他只会要老子麻袋里的盘缠。
老子肯定觉得,碰到专业的了。赖不过呢,于是老子就撰写了本书,分上下两篇,阐述了道德的本意,共五千多字,然后离去,从此再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司马贞索隐引汉刘向 《列仙传》:
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
老子出关的时间,大约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公元前500年左右。反正在孔子见了他之后。
既然老子要无名自隐,自然也不会有什么著作昭示众生。如果没有此时此地此人——关令尹喜,以不给通关文牒要挟老子著书,《道德经》一书就没有了。
紫气东来,紫气,指瑞祥的光气,多附会为圣哲或宝物出现的徵兆。老子横空出世在世界东方,给世界带来文明的曙光。
“紫气东来”的典故和成语,其来源就在这里了。
你发现了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出关而去”,变成“紫气东来”!
不是去,而是来!
人去了,启示来了!智慧来了!
时间开始了。轴心时代开始了。
紫气东来,东来紫气,后来都是汉语成语,用来象征祥瑞的到来。
唐杜甫《秋兴》诗八首之第五:“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写大唐鼎盛,就用了这个典故。
清洪升《长生殿·舞盘》:“紫气东来,瑶池西望,翩翩青鸟庭前降。”也用这个典故写大唐玄宗之时的绚烂之极。
司马迁还说,老子著书而去之后,莫知所终。据说,关令尹喜读到《道德经》,深深地陶醉了,被吸引了。他对老子说:“读了您的著作啊,我再也不想当这个边境官了,我要跟您一起出走了。”老子莞尔一笑,同意了。关令尹喜真的跟着老子出走了,去那儿了呢?传说就越来越玄了,其中一个说法是,二人“化胡”去了。
老子的生平,对我们而言,是无始无终的: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到了哪里去。我们不知他的生,也不知他的死。他自己说“出生入死”,他好像是来自宇宙中某一个星球的高度发达的物种,在我们这个星球的东方落脚,然后,又飞升而去。据说,甘肃临洮的“超然台”,就是他的飞升之所。
后来道教的仙人,都是以“飞升”的方式离开这个星球。难道他们都是一群来自星星的你?
二
班固《汉书·艺文志》上,这样说道家的前世今生: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先看“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注意一下班固这句话里的用词:他一连提到好几组反义词:成败、存亡、祸福、古今,班固很准确地找到了道家的特征。反义词。反者,返也。反者道之动:成可以变成败,存可以变成亡,祸可以变成福,古也可以回来成为今啊。當然,这一切倒过来也易如反掌:败可为成,亡可为存,福可成祸,今天,你一眨眼,那过去的日子又回来了——今可成古。道家对这样一种自然的变化,非常关注,但也非常无奈——
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班固这个概括又非常准确,“清虚自守”它不是一种张扬的力量,而是一种内在的收敛的力量。“卑弱以自持”,永远保持弱者的地位,以此立足。道家知道任何一个事物到了它最强盛的时期,就开始转向衰败。“物方生方死,日方中方睨”(《庄子·天下》引惠子语)所以要“卑弱以自持”。中国最大的数不“十”,而是“九”。为什么?到了“十”就往下走了,就走下坡路了。这种思想观念,就是道家的思想,就是老子的观念。
《汉书·艺文志》还说: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作为史官的老子,在守藏室里,看什么?干什么?看的是历史,干的是记录历史和整理历史记录。
但是,像他这样有极高思维能力的人,他会总结,会提炼,历史在他那里,总有一天会变成哲学;现象在他那里,总有一天会便形成本质;偶然在他那里,总有一天成为必然。
“本质”出来了,“德”就呈现了。“必然”现形了,“道”就显形了。“德” “道”就显形了,《道德经》(其实就该叫《德道经》)就问世了。
《道德经》,来自历史,来自历史的哲学化。
既然他的《道德经》,来自血污斑斑的历史,那么,这样的哲学,就一定有着历史的沧桑,有着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与否定。
于是,我们看到,《道德经》全文:235个“不”字,100(或98)个“无”字,21个“莫”字,4个“弗”字(不同的版本,这些字有些混用,但不影响整个否定性数字)。
这让我们看到老子的否定性思维方式。
如果说,孔子试图建立信仰,老子就是极力破坏信仰。
孔子给了我们一大堆肯定的东西,老子给我们的,几乎都是否定的东西。
孔子塑造世界,而老子却是把世界打碎,给我们一地的碎片。
问题是,这样的一个破坏者,却几乎和孔子一样伟大。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反叛,是一种“创造性反叛”。
我们从他打碎的世界碎片中,看到了世界的本相,看到了我们智力的盲点,道德的弱点,文化的缺点。
并且,这些碎片,还可以重新捏合,造成新的世界图像。
老子,给了中国文化迥异于孔子的景观,给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我们知道,我们所认知的世界,乃是语言构建的,用合乎逻辑的语法编织的,所以,要改变我们对于世界的观念,最彻底的办法,就是使用“正言若反”的吊诡语言,一方面彻底摧毁原有的世界秩序,一方面重建自己的知觉世界。老子在这方面,是真正的大师。
吊诡(digui)一词,起源于《庄子·齐物论》:“丘也与汝皆梦也,予谓汝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 陆德明释文:“吊,如字,又音的,至也;诡,异也。”庄子所说的“吊诡”,其实是一种悖论(Paradox)。
简单地说, “正言若反”,就是一种“反的逻辑”:
逻辑命题公式:A是A;或A非“非A”。
“反的逻辑”的命题公式:A是“非A”
我们看看《道德经》中这样的句子:
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免)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41)
至大之白能并存污点,至大之面无有边界,至大之器无有终成,至大之象无有其形。“大音希声”,哦!至大的声音你就听不见了。什么叫希?听了,听不见,就叫“希”。老子说:
听之不闻名曰希。
人耳能够听到声音的范围是20—20000Hz,在这之外的声音,人就听不见。
晋代的陶渊明,蓄“无弦琴”一张,他喝醉酒以后,就坐在那里弹。没有弦弹什么呀?你没有听见,可是他听见了。这就是老子的启示:启示他听希声的大音。
还有像:
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45)
后来,我们都会学着老子的腔调,说出很多很有哲理的话了:
大辩不言,大奸似忠,大智若愚等等,甚至,我们还能说:大忠似奸,大愚若智——在老子的启发下,我们都有了哲学头脑。这种思维的基本特征就是:辨证思维。
是的,老子的这种“正言若反”的思维和表述方式,促成了辨正思想的产生。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不自见(现),故明;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22)
自见(现)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24)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33)
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
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42)
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
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78)
老子的这种正言若反的辨正思维,就是产生于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极大怀疑。当我们能看到事物的正反两面时,就是辨正思想的产生之时。
三
道家思想中有明显的反智反文明倾向,也与老子有关。
庄子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 “桔槔”( jié gāo)∶井上汲水的一種工具。也泛指吊物的简单机械)”。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
有间,为圃者曰:“子奚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为圃者曰:“子非夫博学以拟圣,於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乎?汝方将忘汝神气,堕汝形骸,而庶几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无乏吾事。”
——《庄子·天地》
北方的子贡到南边的楚国游历,返回时经过晋国,到达汉水南边时,见一老丈正在菜园里收拾菜圃,他打了一条地道直通泉水,然后抱着水瓮下去汲水,再抱上来浇水灌地,吃力地上上下下,用力甚多而功效甚少。子贡见了说:“如今有一种机械,每天可以浇灌上百个菜畦,用力很少而功效颇多,老先生你不想试试吗?”种菜的老人抬起头来看着子贡说:“应该怎么做呢?”子贡说:“用木料做一种机械,后面重而前面轻,提水如同吸水,快速犹如沸腾的水向外溢出一样,它的名字叫做桔槔。”种菜的老人忿然变了脸色,讥笑着说:“我从我的老师那里听到这样的话,有了机巧的工具必定会出现机巧之事,有了机巧之事必定会出现机巧之心。机巧之心存留在胸中,那么不曾受到世俗沾染的纯洁空明的心境就不完整齐备;纯洁空明的心境不完备,精神就不会专一安定;精神不能专一安定的人,大道也就不会充实他的心田。我不是不知道你所说的办法,只不过感到羞辱而不愿那样做呀。”
子贡满面羞愧,低下头去不能作答。
隔了一会儿,种菜的老人说:“你是干什么的呀?”子贡说:“我是孔丘的学生。”种菜的老人说:“你不就是那具有广博学识并处处仿效圣人,夸诞矜持盖过众人,自唱自和哀叹世事之歌以周游天下卖弄名声的人吗?我告诉你,你抛弃你的精神和志气,废置你的身形体骸,恐怕才可以逐步接近于道吧!你自身都不善于修养和调理,哪里还有闲暇去治理天下呢!你走吧,不要在这里耽误我的事情!”
庄子编这个故事,就是要通过反孔子来反文明,反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学生中,庄子随手拈来加以一起嘲弄的,是最聪明机变的子贡,而不是心思耿直的子路,也不是颇有道家风范的颜回。这是学术上的定点清除。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18)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去义,民复孝慈;绝巧去利,盗贼无有。 (19)
这是道家反智思想的最经典表述。显然,老子看到了,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人类传统道德正在崩溃。智力的发达往往与本性中的淳朴善良的丧失同步。生产力的进步,物质的积累,仅仅满足了人类的动物性的肉体欲望,而促退了人性的真善美。从某种角度看过去,道德也确实好像更适宜在艰苦与匮乏中培养与体现。正如庄子后来观察到的,即便是鱼,在泉水干涸时,也会“相濡以沫,相呴以湿”,而一旦泉水充足,则往往“相忘于江湖”。
类似反智乃至被称为“愚民”的言论,还有下面这些:
古之善为道(引导)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65)
不过“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则显然是指统治者应该少一点政治手腕,少一点政治策略——想想后来法家的那些“制民”手段,看到老子这样的话,还是很温暖的。
至于远古常见的杀人政治,老子更是深恶痛绝并予以诅咒: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74)
不知道祖述老子的韩非,为什么偏偏把老子这样的告诫忘了。
老子认为人是自足的,不需要有什么另外的人来管制。只要你给他自由,他就会自然——自然,在老子那里,是“自我实现”的意思。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25)
人的法则是地,地的法则是天,天的法则是道,道的法则是自在的、自足的。
人被地规定圈定,地被天规定覆盖,天被道规定引领,道被自己规定主宰。
人取法地,地取法天,天取法道。道,是万法之法,道,就是法则自身。
自然一词,《道德经》中出现了四次。其中都有独立自由之意。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17)
在老子看来,好的政治和好的社会,就是让自然人自我实现,而不是戕残人性去塑造他们。政府的职责,不是要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治国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殚精竭虑地去做什么,而是只要我们把现在正干的事停下来,什么也不做就是了: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为。(3)
一口气说出八个“不”字,四个“无”字,听起来就是摇头摆手避之如恐不及,口里一连串的“不不不……”和“别别别……”,这是对统治者的制止,也是对当时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盘否定。
所以,老子的政治,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儒家其实也是这样的思想。儒家经典《尚书·武成》:“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下》有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都是讲的民众自治。质言之,“礼制”岂不就是无为而治,“为国以礼”就是民众自治。中国古代,政治而有了“梦想”,那是法家出现时,法家的梦想就是“富国强兵”,然后折腾国民。而儒道两家,其实都是要求政治不折腾,无为而治,礼乐教化,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所以,老子要的是——自然之治。无为而治,是否定形式的“治”。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正道);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57)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狡诈)。(58)
治人事天,莫若啬(少做,惜力)。(59)
不受体制制约,没有社会约束,推到极点,就是没有社会关系,只有自然关系,这就是“小国寡民”了——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阵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80)
国小,民少,这是老子对他理想国所定的规模。实际上,这里的“国”,已经不是那个意义上的“国”,它只是一些原始的自然村落与集镇。可见,他竟然反对国家。所以,胡适先生认为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四
实际上,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更关注的是个体在这个处处充满险诈陷阱的世界上,如何自处,他们的人生哲学比他们的政治学更有影响力。关于人生,老子有一个“人生三宝”: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67)
第一宝:慈,对他人,就是慈爱;对自己,就是保重;对世界,就是悲悯。所以慈包含三重:珍重、保重、承重,珍重他人,保重自己,承重世界——庄子讲“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就是对自己的“慈”。韩非子《解老》:“慈于子者不敢绝衣食,慈于身者不敢离法度,慈于方圆者不敢舍规矩。”讲得更加全面。
第二宝:俭。是节俭,是简单,是节制——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孔子的个性,“温良恭俭让”,就有一个俭。 “俭”,也是“约”——约束,节制。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4.23)
中国文化中的知足常乐思想,就是老子教导我们的。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9)
第三寶:“不敢为天下先”。注意,老子讲的是“不敢”,而不是“不愿”。为什么要“不敢”呢?因为: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73)
如果说“勇于敢为”是个人的优质品性,但导致优质品性的人常常被杀戮,那正是“强梁者不得其死”的社会。
据说有这样一个有关老子的故事,《说苑卷十·敬慎》:
常摐(chuāng,即商荣,纣王时大夫,因直谏被贬)有疾,老子往问焉,曰:“先生疾甚矣,无遗教可以语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虽不问,吾将语子。”常摐曰:“过故乡而下车,子知之乎?”老子曰:“过故乡而下车,非谓其不忘故耶?”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过乔木而趋,子知之乎?”老子曰:“过乔木而趋,非谓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尽矣,无以复语子哉!”
不光舌头因其柔弱而长存,自然界和社会更是普遍可以观察到“柔弱胜刚强”的现实: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76)
而天下最柔弱的事物,莫过于水: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也。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78)
天下还有比水更柔弱的么?还有比水更随和而没有个性的么?随物赋形,是其温柔,是其卑弱,但攻坚胜强,舍水其谁!它“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是老子思想的最典型体现。
而老子本人及其思想,其实也以其阴柔软弱之态,显示出柔韧不绝的力量。
老子曾经感叹: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70)。
其实,他死后并不寂寞,以他为代表发源的“老庄哲学”和儒家的“孔孟之道”并驾齐驱,儒道互补成为中国文化的阴阳两极。而他的“五千精要”也被看作至高无上的东方智慧。他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成为中国人的世界观的一部分;他的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人认知世界的一种重要方法;他的个性也成为中国民族性格的重要特征。
前面我们提到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纵论六家,指点圣贤,各有褒贬,大气磅礴。但是,有着黄老思想的他,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给予了全面的肯定。
他这样说老子的道家: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
司马谈眼中的圣人,不是孔子,而是老子。他的儿子司马迁不仅把老子写成孔子之师,还借孔子之口,称服老子为“龙”。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孔子是“凤”,老子是“龙”。绝代双圣,龙凤呈祥,共同成为中国人的祥瑞。紫气东来,不仅是中国人的福气,还是世界的吉祥。
杏坛弦歌
孔子游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庄子·渔父》)
一
老子出关走了。其实,后来的孔子也曾经有这样的去意。他曾经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一个西去流沙,一个东浮大波。当然,孔子毕竟坚持“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留恋人间,不舍大众,最终没有成行,他只是离开了鲁国,周游列国,做“避人之士”而绝不避世。甚至,老了以后,还是回到鲁国,整理六经。他整理六经,著述《春秋》,也是老子著述《道德经》的意思,用文字走进未来的时代。
其实,在老子被尹喜强迫留下五千言之前,孔子也曾用几乎同样的方式纠缠过老子,让他留下教诲。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这样一则动人的故事: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身。”
此刻的老子,估计应该在六七十岁吧,孔子,三十四岁。面对这样一个血气方刚的后生,老子不动声色地点出两个字:藏和愚。
其实,愚就是藏。把智慧藏起来,示人以愚,大智若愚。这就是老子的基本处世之道。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得到:三十而立之后的孔子,是何等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是何等志向远大,理想崇高,是何等意志坚定,自信自负……
他此刻最需要的,就是收敛和藏蓄,是心性的稳定质朴。
严格地说,此时的老子,是体制中人,而孔子,则是江湖的。孔子以后,诸子百家,都是江湖学派,来自私学。所以,和老子做着国家档案馆馆长,深居简出,言简意赅,要言不烦不同,孔子的世界,则是开放的空间,明媚的阳光,他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我们来看看孔子的场景,与老子的那个阴暗的档案馆,是何等不同,《庄子·渔父》:
孔子游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
庭院深深的档案馆,和风高日丽的杏边高地,这是体制与江湖的绝佳象征。
现在的曲阜孔庙里,即有一个杏坛赫然矗立。不明白历史的人,还以为当初孔子教学,就是这么一个场所,就有这么一个场所。
但细揣庄子之意,他笔下的“杏坛”,乃是孔子带着弟子从茂密浓郁的森林中走出,恰好碰到的一个水边高阜,上有一树杏花正艳,于是就此停住,弹琴读书。此水既是渔父打渔之地、谋生之所和隐居之处,芦苇丰茂,绝无可能在鲁国都城之内。也就是说,“杏坛”,本来就只是庄子随口诹出的一个词,绝无可能是孔子专门讲学之所,则今天孔庙里的杏坛,就只能是后人望文生物而造出來的。顾炎武说:“《庄子》书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渔父不必有其人,杏坛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苇间、依陂旁渚之地,不在鲁国之中也明矣。”(《日知录·卷三十一》)
但是,一个道家人物随口诹出的词,为什么却被坐实,一个虚构的寓言,如何竟然成为历史?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这个寓言,不是生活的真实,但却有着本质上的真实;不是物理上的真实,却是精神上的真实——它确实是孔子日常教学生涯的高度概括。而这样的开放、开阔、阳光明媚而春意盎然的物理空间,正是孔子和煦明媚的心理空间和思想空间的直接外化,与老子的那个充满霉变气味和历代亡灵的守藏室的物理空间以及老子本人阴郁高冷的心理空间和思想空间,形成鲜明对照。老子是肩负文化传承使命的史官,而他却心灰意冷意兴阑珊,不仅放弃责任一走了之,走之时,连一句话都不想留下;孔子却以一个江湖人士的身份,挑起了这个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官方不给教席,他就私人办学,而且终生以之,诲人不倦,不知老之将至。
老子的精神状态是过去时代的,有老贵族百年老宅子的阴暗气息,代表着王官之学的深沉与颓唐;而孔子的精神,则是新时代的,代表着私学的兴起,有新一代的开阔与敞亮,生意盎然:他在唤醒这个民族,唤醒这个民族的一代新人,他在孕育一个百家争鸣的新时代。
庄子为他题名的“杏坛”,后来甚至成了教育行业、教育界的一个代名词。
晚年的孔子,曾经这样概述自己的一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十五志学,此后的三四五六七,都是“学”,可谓“学而不厌”,“不知老之将至”。但这个“学”,还真不是自家一人之学,不是“自了汉”之学,而是普度众生之学。是以学渡人。“志于学”云云,乃立志于追求学,立志于传承学,并立志于弘扬学,而后顺理成章建立自家之学。所以,“学而不厌”之外,另有一个“诲人不倦”,这才是孔子“志于学”的比较全面的意思。
学而不厌的结果,我们看到了,十年一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所立,到了七十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进入人生化境。
而“诲人不倦”,则使得孔子创立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所私立大学。
二
周王朝礼乐文化的崩溃,直接导致了周王朝政治秩序的破坏。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篇》)所以,孔子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持批判态度。对时代持批判态度,对于一个从事教育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素质——赋予受教育者一种批判精神,是教育的基本责任和目标。
从西周一直到孔子的时代,一大批贵族子弟已落到社会底层,士阶层空前扩大。这些“士”需要一条上升的通道,也需要有就业的能力。而当时的贵族,往往自身的礼乐修养很差,正好需要一批专业人士给他们做礼仪方面的指导。比如,孔子的学生公西华,曾表明自己的志向是“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论语·先进篇》)。另一方面,士也需要有相应的专业知识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在此情况下,礼乐文化的教育就变得非常迫切,孔子的私学,就是在这个大的需求背景下出现的。
不过,这个士阶层只是个身份意义上的概念,指的是天子、诸侯、大夫、士中的“士”,和孔子以后的,作为知识分子的“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孔子以前的“士”是“志于仕”的士,而孔子培养的,是“志于学”“志于道”的“士”。作为伟大的圣人,孔子的教育理想不会仅仅是完成对“士”的就业教育,孔子开创私学教育的立足点和价值,我们还可以从下面两个概念来看。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观念中,有两个词:王道、霸道。王道,指的是,在“王的时代”,道是由王来承担的。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这些人都是王,也都是孔子所尊崇的。这些王承担着道,所以叫王道。自周朝进入东周后,王衰弱了,历史进入“霸的时代”,道义在一段时间里由“霸”来承担,这就是所谓的霸道。无论是在“王的时代”,还是在“霸的时代”,道都有承担者,道并没有失落。可是到了孔子的时代,王没有了,霸也没有了。孔子对晋文公的评价是“谲而不正” (《论语·宪问篇》),诡诈而不正派,就是说晋文公所行的已经不是正道了。
所以,孔子看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社会的失序。而社会的失序,是因为天地之道、人间正道缺少了担当者、承载者。
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认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就是传承文化,弘扬道义。他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承载道义的阶层。在孔子内心中,是把自己作为道的承担者的。他曾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论语·子罕篇》)周文王已经死了,周代的文化遗产不都是在我这里吗?“文不在兹乎”的“文”就是“道”。孔子把自己当成了一个道的承担者。可能也正是因为孔子自己是个士,并且他认为自己是继承文王之道的人,他充分地意识到了今天不是王的时代,不是霸的时代,而是士的时代,当下的道,不在王,不在霸,而在士了,这就是“士道”。孔子对此的表述是“士志于道”——士立志于担起道义的担子了。
孔子来了,“士的时代”来了。
所以,孔子做教育,目標在于培养一批道义的承担者。孔子最终是想通过教育,赋予当时最落魄潦倒的一个阶层新的历史使命,通过承担这一历史使命,让这个阶层重新焕发出自己的内在生命力。他后来果然开创了一个士的时代,那就是百家争鸣的时代。
经过孔子改造以后的士,已经不再是以前身份意义上的士了;孔子改造以后的儒,也不是以前的儒了。以前的儒是被人瞧不起的。孔子同时代的晏婴,就曾在齐景公面前用很瞧不起的口气谈论过这样的儒。甚至稍后于孔子的墨子还在用很轻蔑的口气讽刺过这样的儒,他们认为这些儒都是无聊而没用的。应该说他们谈的都是当时的事实。孔子也看到了这个事实,但是孔子更看到了儒的未来、士的未来。
孔子把士从患得患失的 “志于仕”的状态下解脱出来,给他们一个新的人生价值定位:“志于学”,“志于道”。孔子为什么要弟子们成为君子?孔子为什么要弟子们成为大人?为什么孔子的学被称为“大学”?这都是在传递一个信号:文化人格的养成和文化使命的承担,是受教育者的天职。孔子弟子中具有这种天职意识的,最典型的就有四人:颜回、子贡、子路、曾参。
颜回作为孔子最欣赏的弟子,他对道的孜孜以求,对出仕为官的坚决弃绝,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雍也篇》)的安贫乐道,都是这种新型人格的体现。
子贡和子路都曾问过孔子同样的问题:“何如斯可谓之士矣?” (《论语·子路篇》)如何才算得上士?“士”作为一个概念,其内容本来是不需要问的,因为几百年来按照天子、诸侯、大夫、士这样的次序,各阶层本来都有其确定内涵。但是子贡和子路都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怎么样才能称为士?显然,他们意识到在孔子心目中,士,不再只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种身份,一定还要具备某种素质、某种社会功能,担当某种社会责任,如此,才可以叫做士。所以,他们的这个问,比孔子怎么回答更重要,因为它暗示我们,什么是士或具备何种品格和功能、担当何种责任才能成为士,竟然成了一个问题。这就说明,子贡和子路意识到了孔子试图赋予士以新的内涵,而他们也想着让自己获得这种新素质。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来,那就是,孔子的教育在汉代以后逐渐演变为国家的“教化”,这种以道德伦理为基本内容的“教化”,不僅成了“文化”的可见形式和有效形式,还兼具了宗教的功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民众信仰的基本来源。其实,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不仅是一个思想流派,不仅是一个哲学流派,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信仰体系,这才是儒家的本质性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孔子和任何一位西方哲学家相提并论,都不得要领,唯有把他和耶稣对看,才知道他的价值。孔子终生所做的,都是教化。他没有创立教派,他创立了学派,他教化民众的方式,不是“宗教”,而是“文教”。但是,他的文教,其功能,正如同西方“宗教”在社会中的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就认为,儒家,其实也就是“儒教”,并且,还有学者提出建立“儒教”以整合民族信仰体系。
孔子私学教育的最原始记录,就是《论语》。这是子书时代最伟大的著作,也是由子书上升为经典的第一本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地位超越了《道德经》。《道德经》虽然称之为“经”,却并没有进入古代中国国家经典的大名单。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三记下了这句话,并在后面有一句说明:“唐子西尝于一邮亭梁间见此语”。唐子西,唐庚(1069-1120),字子西,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唐子西文路录》记载:“蜀道馆舍壁间题一联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不知何人诗也。”
老子走了,孔子来了。
老子因失望而离去,孔子为拯救而到来。
老子是史前史的后记,充满叹息和诅咒。
孔子是新纪元的序言,充满期待和勉励。
《道德经》作为历史的总结,智慧高超,冷静到冷酷。
《论语》作为新历史的开篇,仁德蔼然,热心到热切。
老子留给我们巨大黝黑的背影,孔子展露给我们宽广明亮的前额。
由于《道德经》的高度抽象和理性,很多人认为,相较于孔子,老子代表了更高的哲学质性。但是,我的看法是,在老子身上,我们能看到他的时代,他的生活,乃至他的职业给与他的影响,无论是他的思想、思想方法,还是他的个性。也就是说,他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
后来者中,连孟子这样至大至刚的人,都被时代带坏了脾气。庄子这样超凡脱俗之人,都被现实沾染了刻薄。
但是,孔子不一样。在孔子身上,我们看不到历史、时代、时代中的那些人,以及他自身生活遭际在他身上的痕迹,虽然他的思想资源来自他的时代以及历史,他的思想目的也顾及和照应他的时代,但是,时代没有扭转他的思想方向,更没有影响他的个性。颠倒的世界扭曲了老子的世界观,但混乱的时代没有影响孔子的清澈,嘈杂的现实没有影响孔子的静穆,复杂的世道没有改变孔子的单纯,机变的政治没有戕害孔子的自然——显然,正如孔子自己所说,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这样的人,显然是一种更加纯粹的天纵之圣,不可被磨损,不会被玷污。老子讲的“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之赤子,惟孔子可以当之。
历史和时代创造了老子、孟子、庄子。
而孔子则创造了历史和时代。
墨子之楚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
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
一
儒家非常强调家族共同体,其实周王朝就是一个大家族。周朝分封之时,就是要建立一个家族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直到春秋之际,孔子还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论语·尧曰》),孔子还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而孟子则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下》)。所以儒家强调“亲亲”,来自周朝立国的遗传密码,这是礼制的基础。《诗·小雅·伐木序》:“亲亲以睦友,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 孔颖达疏:“既能内亲其亲以使和睦,又能外友其贤而不弃,不遗忘久故之恩旧而燕乐之。”《孟子·尽心下》:“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告子下》:“亲亲,仁也。”
《礼记 · 祭义》:
子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
《孟子·滕文公上》:
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
盖孟子反对的是夷子的“爱无差等”,并非反对“施由亲始”。在儒家看来,人总是会对亲近的人多一份关爱。
这个被孟子批评的夷子,是一个墨者,是墨子的后学。
墨子的观点是什么?兼爱。“兼爱”,是要“求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天志中》),是要 “爱利百姓”(《鲁问》)。
他创造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要在孔子的“仁爱”之外别树一帜。这一树,可就树出了高度:
古今中外哲人中,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23 页)
为什么梁启超要把墨子和基督放在一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墨子的“兼爱”,最为接近基督的“博爱”!
“兼爱”简单地讲,就是天下所有人乃至所有国家,无论贫富贵贱、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相爱。这确实是天下最高尚的道德境界,也是最富有鼓动性的一个道德口号。
墨子认为当时天下大乱的根源就在于人们道德上都自爱而不爱他人,都只爱自己的亲人而不爱偏远的人。他说:
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 ; 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 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墨子·兼愛上》)
儿子只知道爱自己,但是不爱父亲,结果是损害父亲而自私自利。同样,弟弟爱自己不爱兄长,所以结果是“亏兄而自利”。这是家庭内部,那么国家呢?大臣爱自己不爱国君,结果是“亏君而自利”。这是下对上。那么反过来,上对下怎么样呢?也同样如此 :
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 ; 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 ; 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 ; 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墨子·兼爱上》)
父亲爱自己不爱儿子,兄长爱自己不爱弟弟,国君爱自己不爱大臣,那么天下所有的人都只爱自己而不爱别人。在他看来,只要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够兼爱,天下就没有乱政了。他说,假如天下的儿子爱父亲像爱自己一样, 天下的弟弟爱兄长像爱自己一样,天下的大臣爱国君像爱自己一样,天下哪里还有不孝呢?哪里还有不慈呢?哪里还有不忠呢?同样,天下的小偷爱别人家里的财物像爱自己家里的财物一样,哪里还有小偷小摸呢?爱惜别人的生命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哪里还有杀人的事呢?
读墨子这样一段文字,让我们想起另外一段,孟子的文字,它们非常相似: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 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 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把墨子的爱,改成孟子的利,或者把孟子的利,改成墨子的爱,是不是文字中的事理逻辑仍然成立?
兼爱从道德提倡的角度来说,当然很好,如果天下人都像墨子一样,互相亲爱,当然非常好,但是天下的人能不能做到兼爱?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叫《方法论》,其中讲到,我们要为解决一个问题找方法,必须是找到这个方法比解决问题容易,这才是正当的方法。比如墨子这里说的盗贼问题,要让一个盗贼像爱自家的财物一样爱别人家的财物,何等困难,相比较之下,要制止一个盗贼去偷盗别人的财物,反倒简单不少。所以,墨子这个要我们用赋予盗贼爱心的方式来杜绝偷盗,真的不能算是一个正当的方法——因为相对于让盗贼爱惜别人的财产如同爱自己的财产,制止他偷盗别人的财产还是容易得多。
二
不过,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墨子用兼爱来反对“亲亲”,并且指出了“亲亲”逻辑会导致普遍的自私,这确确实实是墨子的伟大之处。更重要的一点是,“兼爱”实际上肯定了天下所有人在道德和权利上的平等,而这又必然会延伸到要求政治上的平等。正如“亲亲”不仅仅是伦理上的“爱亲”,更是政治上的“任亲”一样,“兼爱”也不仅仅是伦理上的兼爱天下人,还是政治上的“兼任天下人”。所以,在国家用人上,墨子又有“尚贤”的主张。如果说“兼爱”之于“仁爱”,还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辨析,“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却高下立判。这是墨子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的一大贡献。
还有,既然兼爱天下,当然就会反对攻国。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至战国中期,诸侯国又从春秋时期的一百四十七个锐减到万乘之国七个,千乘之国五个。可见百年之间,战争之残酷与频繁。墨子认为,固然有少数国家,如南方荆吴,北方晋齐,因为好战而扩充领土,成为大国,“以攻战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数千里。人徒之众,至有数百万人”,但是,大多数国家却因为好战而灭亡,“虽四五国则得利焉,犹谓之非行道也。譬若医之药人之有病者然,今有医于此,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万人食此,若医四五人得利焉,犹谓之非行药也。故孝子不以食其亲,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国于天下,尚者以耳之所闻,近者以目之所见,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谁说战争是国家的理性行为呢?
“兵者,天下之凶器”(《老子》)战争是屠杀天下的凶器,战争之中,妇幼老弱一概难于幸免。《墨子·非攻中》:“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在这篇文章里,墨子讲到战争之危害,讲了人民生命财产以及国家诸多方面的损失,用了九个“不可胜数”,其中百姓和士兵死亡之“不可胜数”就有五个。《墨子·非攻下》则描绘了这样一幅惨景:“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这一方面看出墨子揭示战争的实质和最大危害就是杀人,一方面也看出墨子内心对广大人民的巨大悲悯之情,“此其为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厚害矣,而王公大人乐而行之,则此贼灭天下之万民也,岂不悸哉!”(《墨子·非攻下》)这种悲悯之情,与他的“兼爱”,是互为因果的。
虽然儒家、道家也反对战争,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不同:儒家认为,天子之下的国,互相攻伐是不懂规矩的;道家认为,大道之下的国,互相攻伐是不智慧的;而墨家认为:平等互立的国,互相攻伐是不道德的。
儒家从政治秩序的角度反对战争。
道家从哲学智慧的角度反对战争。
墨家从伦理道义的角度反对战争。
所以,墨子反对战争,从亏人自利说起: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并且,有意思的是,针对战争发动者的种种正义美名,墨子直接指出战争的实质是杀人。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
而“杀人”,就与他的兼爱严重冲突了。但是,有意思的是,墨子并没有从伦理学上展开价值判断,他只是把价值判断——杀人不义——作为前提,他的论证,用的是他的看家本领:逻辑。他质问那些战争发动者、鼓吹赞美者和辩护者:你们有逻辑吗?
墨子当然非常强调道德,这是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墨子可能还更加强烈。但有意思的是,墨子对不义之人的愤怒,主要爆发点还不是他们“坏”,而是他们“笨”。他对没逻辑的愤怒超过了对没德性的愤怒。所以,墨子的道德义愤往往转变为智力碾压——他的逻辑学成绩在诸子中佼佼。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宽容德性不高的人和行为,但是,我们无法容忍逻辑上的混乱。逻辑的必然性,使得事情在对错之间没有缓冲地带。
所以,孟子的峻急是道德的高峻,不容宽贷;墨子的峻急是逻辑的严肃,无有余地;商鞅、韩非的峻急是个性上的刻忍,惨礉少恩。
三
说到这里,我们就要说说墨子给我们留下的一个精彩典故:止楚攻宋。这个精彩的故事,就从逻辑开始。墨子是先秦诸子中第一个有意识地运用逻辑利器来战胜对手的思想家。好,我们来看看这篇记录在《墨子·公输》里的故事。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
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公输盘曰:“夫子何命焉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愿藉子杀之。”
公输盘不说。
子墨子曰:“请献十金。”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
墨子劝阻公输盘,已经很有战国辩士的风采。他设套让公输盘入彀,引出公输盘的“吾义固不杀人”,这个“吾义”,可以理解为“吾依义”,我遵循道义不杀人;也可以理解为“吾之义”,我做人的原则不杀人。但不管怎么说,墨子其实了解公输盘:这个人是有原则的,是讲道义的,所以他才设了这样一个让他去做杀手的套,激起他的道德羞耻心和愤懑感。
当公输盘说出这个“义”的时候,墨子就知道,公输盘已经入彀了:因为从逻辑学角度讲,起点有了,结局就不可逃脱。
接下来,墨子的语言一气呵成,有一种擒获强敌之后善刀而藏之的“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气场强大,势如破竹:
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馀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馀,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
公输盘服。
公输盘服。服什么?服了仁、智、忠、强,没错。但最重要的是,服了逻辑——知类。
但不是所有人都会服从仁义和逻辑,比如权力。马上就证明给你看。
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输盘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公输盘曰:“诺。”
对了,作为一个有道德自觉的人,除了仁、智、忠、强、知类(逻辑),公输盘还有一个“信”的问题。“言必信,行必果”是很多执着之人的执念。
于是,墨子还得要说服楚王。楚王才是楚国的代表,才能代表国家终止战争,也才能解脱“信”加给公输盘的制约。
有意思的是,到了楚王那里,墨子自觉地调换了武器,他与楚王之间展开的,就不再是仁义等等的是非讨论,而是利害计算。
當然,墨子可能意识到,如果直陈“利害”,以此立论,他已然在理论上破产——因为他是讲道义的,他是从道义的角度认为国与国之间是不可互相攻打的。所以,他没有直接说利害,他说逻辑——但这是什么逻辑呢?理性逻辑。毕竟,国家理性的本质,就是利害考量。
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窃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为无雉兔狐狸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
这个逻辑就是:作为一个物产丰富到不竭,土地辽阔到多余的国家,去攻打并占有一个物产匮乏、土地局促的国家的土地,牺牲其不足的人口,抢夺其本已多余的土地,实在是不知所谓。顺便说明一下,那时候,人口,是国家的重要生产力,是国家最重要的资源,是国家整体实力的最重要要素。而打仗,总是要死人减员的。在楚国这样有着广袤领土的国家,人口减少才是国家最大的损失。
墨子说的是什么?是国家理性。
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得已经多余的土地,不仅要减少国家人口,还要付出另一个重要的成本:那就是一个国家包括国君本身的道义。
墨子的话是“伤义而不得”。墨子的意思:您这做法挺蠢的,既不得地,还伤义。
但楚王的思路是倒过来:用伤义的方法来得地。如果能得地,那也就伤义吧。只要能得地,楚王根本不会顾忌什么义不义的问题,也不在乎逻辑,更不在乎道义形象。他只在乎“利”。
王曰:“善哉!虽然,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
楚王的意思,是,第一,我有云梯,可以爬上宋国城墙;第二,我的战争机器已经运转起来,不能停下;第三,楚王没说,却也说了:一声“善哉”,就相当于对“义”给一句精神鼓励:说得好说得好。但我敬谢不敏——我不敏,我没有你那么高的境界。一句“必取宋”,你体会一下楚王权力的傲慢:别给我讲道义,我有实力,我必取宋。
到了这个时候,墨子只好走下道义的高地,回到现实的泥沼,在楚王的境界上和他较量。
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馀。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别以为这只是“沙盘推演”,其实这是真实的惨烈悲壮的战斗。悲壮到战至弹尽粮绝,最后“两间余一卒”,只剩墨子一人,血污斑斑,是双方最后胜算的砝码。孤独的墨子,孑然一身,面对着来自一个国家的攻击。而他,只有血肉之躯,且已深陷敌境,斩头沥血,千钧一发。
这确实是墨子的形象。墨子,在历史上就是这样战士的形象,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不过,墨子已经算到了这最后一战,并且已经作了最后的安排:他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是徒手的学者,他竟然有他的私人军队——这可能是墨子和当时所有思想家最大的不同:他不仅有对于世道的武器的批判,他还有批判的武器。这是真实的武器:他有私人军队不说,他还有当时最先进的私人兵工厂,他造出的常规武器天下无敌。此刻,他的弟子禽滑厘率领的三百人决死队,已经猎猎大旗,挺立宋城,掌握着最先进的墨式武器,以待楚寇。当他道义和逻辑的批判无法阻止疯狂的楚王时,他只好动用真实的武装和武器来对楚王进行武器的批判——至此,楚王终于认输,让隆隆开动的国家战车,停在墨子面前。
一个墨者,挡住了一个大国的战车。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觉得墨子胜了,并且胜得如此震撼人心。
但是,只有墨子自己知道,其实,他输了。
他受了致命的内伤。这个内伤就是他的“义”——立足于兼爱的非攻之义,根本不可能在现实中战胜。他战胜对手的武器,其实就是对手崇尚的武器,那就是实力;他取胜对手的逻辑,也是对手的逻辑,那就是“利害”。所以,《墨子·公输》这篇文章,自古至今,都以为是在写墨子的胜利,错了,这是在写墨子的失败。思想家的失败,就是他思想的失败,理论的失败,主张的失败。
有一个小问题:为什么墨子的“义”可以完胜公输盘,而只能完败于楚王?
很简单,国家,一旦有了自己的主体性,就一定有“利维坦”本性。
国家的本质是理性。理性的本質是利害。
道义等等,无法为国家的利维坦病毒免疫。控制国家的利维坦发作,需要国家自身的免疫力。这自身的免疫力,就是制度。用制度来削弱乃至瓦解、杀灭国家的集权体制。
但是,写到这里,难道我们真的得出一个结论:墨子的理论是无力因此是无用的?
其实,我们只要想一个问题:墨子本人,如果没有兼爱的思想,非攻的主张,没有这个强大的道德伦理内驱力,他怎么会摩顶放踵,行十日十夜至楚止战?他又哪里会殚精竭虑造出那么多的守圉之具以抵御战争?如果不是他的道义感召,没有他热血沸腾的“义”,哪里又会有三百死义之士,不计利害不惧生死,去捍卫一个与自己利害无关的宋国?
墨子,其实是给我们展示了道义的力量。
这力量,深藏人性人心之中,一切物质性的力量,无不由此发端。
止楚攻宋的力量,来自于他的技术和武器。但是,止楚攻宋的念头,却是来源于他的道义。
武器,在战场上大显身手。但是,造出武器的,却是一个止战的观念。
做好事,需要能力。但是,首先还得要有一个做好事的念头。这个念头的在与不在,有与没有,才最终决定了世界的品质。
在中国,墨子这样的人,不可有二,但不能无一。
他告诉我们,道义,是一切正当力量的源头。
注释:
[1]《庄子·田子方》,《庄子·天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