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的道德与政治
——以简·奥斯丁的名著《曼斯菲尔德庄园》为例
2020-09-11
18世纪同时作为小说史和园林史的转折点,究其根本,在于面对历史的宏大巨变,两个艺术门类在各自的实践领域均产生了不同的回应,其本身都融于整个“时代精神”之中。简·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 field Park)则是上述两方面交集的表现,它不仅因叙事而涉及时间,同样延续了奥斯丁对空间不平衡性的关注,甚至因此成为了后殖民理论中的重要对象和关键环节,进入后殖民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辩论的领域。过往研究多从道德和政治的其中一面进行阐述,并且缺乏对园林本体意义的考虑,本文正是以园林本体为基础,从不同方面的综合和演进对这一经典进行批判分析。
1 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园林因素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曼斯菲尔德庄园》整体意义上的清晰的园林因素,园林与小说的叙事、环境、美学与思想高度相关,并且这一核心概念指的就是英国私家园林。
1.1 “庄园”概念的园林属性
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原著英文为“Mans field Park”(图1),尽管国内至少还存在另外两种翻译:《曼斯菲尔德花园》和《曼斯菲尔德山庄》,但“庄园”的翻译显然更符合小说的核心特征。翻译成“山庄”可能有与《荒凉山庄》《呼啸山庄》相仿的市场考虑,但“山庄”在《荒凉山庄》和《呼啸山庄》的标题英文中分别指房屋(house)和高地(heights);而翻译成“花园”在类别上的误导性则更为显著,毕竟“自然风致园”(landscape park)概念本身的形成过程中就涉及了对“花园”(garden)与“林园”(park)的辨析[2]。
可以说,同样作为描写贵族家庭婚恋故事的世情小说,大观园是承载《红楼梦》叙事环境的一个基本意象,但《红楼梦》没有也不会以大观园为名,而《曼斯菲尔德庄园》则恰恰是有意为之,也因此成为了不常见地以园林命名乃至作为文本核心张力的世界文学名著。
1.2 《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园林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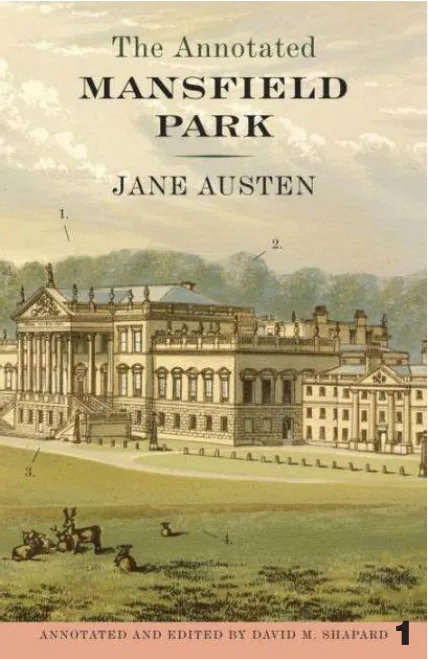
1.《曼斯菲尔德庄园》英文原版封面
《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园林属性内涵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奥斯丁有意安排园林元素的在场,这种在场有时候是以历史现实意味进入小说的。比如,当拉什沃思提出改建庄园的建议时,伯特伦就提到能帮上忙的“应该是雷普顿先生”[3]。这里的雷普顿便是大名鼎鼎的所谓“自然风致之新王”汉弗莱·雷普顿(Humphry Repton),雷普顿不仅与奥斯丁处于同一时代,而且存在现实中的交集,这种交集说明作者本人对雷普顿也是比较了解的[4-5],因此,这绝非附会的闲笔,这一情节本身含有作者对园林内蕴的认识,朱莉·派克(Julie Park)对雷普顿的园林认识论和奥斯丁的相关描述之间有过精彩的互文性阐发[6]。
其二,这一定位也同样持续蔓延在整部小说的宏观架构和字里行间之中。从整体上看,庄园的自然风致已然成为小说发生发展的语境,甚至文中人物的内心常常通过一种与读者互动的“托物言志”由庄园的风貌充分烘托。此外,作品细节之处的园林景致或成为叙事时间动力、或提供“韵外之致”的超越空间,往往构成一种叙事和园林两种艺术体裁的互文见义,具有一种“文体间性”趣味。
1.3 小结
综上,可以得出三个递进的结论:(1)《曼斯菲尔德庄园》这一译名在准确性上要优于另外两个译名;(2)可以确认小说所描绘的对象就是英国私家园林;(3)奥斯丁将自然风致园的代表人物雷普顿这一历史人物设计为小说人物首先就是为了让小说的环境氛围有一个明确、直观的对象——一种乡村风貌,乡愁趣味和诗画意境跃然纸上。
2 园林的道德属性
园林的建设与使用均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从而体现出深刻的道德意味。《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园林属性从一开始就涉及了价值观念的讨论。
2.1 自然风致园的人为属性
雷普顿的园林设计事业是半路出家,却不妨碍他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园林设计师。标志性的“红皮书”,是雷普顿提供给“甲方”的设计方案。在这里他充分发挥了绘画特长,将修缮前后的景观效果同时用水彩描摹,形成惟妙惟肖的前后对比图(图2)。这样的营销极具说服力,但实际改造过程并不简单,仅在直观上就涉及河道改造、树木砍伐和再植,当然还有自然风致园的标志之一——对几何线条(如围墙)的拆解。当奥斯丁在现实中面对这种直观时,才发现修缮可能不仅要用到铲子更可能要用到斧头[5]。

2.雷普顿红皮书中的景观效果对比图
与之相关,《曼斯菲尔德庄园》中所体现的近乎礼教式的道德批判因素是公认的,且是有意为之并饱含深意的。某种层面确实可以说“英国文学史上,使得乡村风景具有最大抒情功能的,奥斯丁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7]。但通过分析,这样的表述掩盖了书中从未缺席的道德批判意味,而将之局限为纯粹的浪漫主义表达。甚至这种认识如此强烈,以至于本身作为对更加人为化的规则式园林的自然属性反叛的自然风致园,在文中却展示出一览无余的人为属性。毛尖指出奥斯丁对曼斯菲尔德的描绘延续了英国文学传统的自然观,自然风致园将自然带来,让静谧的传统陪伴人们,所以在小说中,每一次主人公范妮产生情绪波动,奥斯丁都会适时地将其目光投向庄园的景色,是自然的安慰和爱抚给予范妮内心的平和[7]。然而,需要声明的是自然风致园仍然是人为的自然,它的前提就有对自然的刀砍斧剁,它是“伪”自然,更因为其本身是对“人为”的反驳,甚至可以称之为“伪”的“去伪自然”,换言之,自然风致园致力于园林自然样貌的追求不过是在人与自然的抵牾之中的一种暧昧和焦虑状态。
2.2 奥斯丁的踟蹰
“人与自然”的对立恰恰和“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一点深刻地体现了奥斯丁时代的特征。从自然辩证法的角度来说,通过改造自然这一劳动使人具有了类本质,却也因此造成了自我异化的可能。而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含的发展主义则造成了人的自然属性的根本失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自然风致园在粗糙地吸收东方美学的前提下,深刻体现了卢梭式的浪漫主义怀旧情绪。比如,当范妮得知林荫道两边的树将要被砍倒时,曾经引用英国诗人考珀(William Cowper)的诗句表达自己的质疑:“你倒下的荫路大树啊,我又一次为你们无辜的命运悲伤。”周丹丹对此有个切中肯綮的批语,她指出这一诗句来自考珀《工作》的第一卷,描写的是约翰·斯罗克摩顿爵士对其地产划定范围并进行改建的过程,所以范妮对这一诗句的引用无关其个人文化修养,而是体现一种对传统价值的捍卫,这一向后的姿态与其他人追求发展和新变的精神是相左的[8]。
事实上,自然风致园背后的意识形态并非来自某种自然主义,而更多的是来自于辉格党的自由主义[2],那么这一“城市与乡村”和“人与自然”的连接在当时的社会形态变化中的轨迹就更为清晰,即从根本上仍然体现出了启蒙理性对自然的主客对立姿态,所谓以自然风致对“几何风致”的超越是付之阙如的。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奥斯丁对此的态度是朴素甚至暧昧的,有学者倾向于认为奥斯丁更为认同文中其他人物的意见[5]。如果一定要说作者在小说中的态度,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古典人文主义昨是而今非的叹惋,仅仅是一种诉诸感性(sensibility)的道德批判。尽管其中的裂隙是若隐若现的,如上文所说,当奥斯丁通过范妮表现出对雷普顿的质疑时,需要意识到,这个布朗的传承者在园林设计方面较其前辈反而更为中庸,他不断地消弭了布朗等人自然观中的启蒙成分,并成功地将自然风致园的设计推向职业化,而这种折衷主义[9]显然是对大生产时代专业门类细分的回应,是对其中道德属性的刻意抽离,所以其本身并非对启蒙的反思,反而仍然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逻辑。
尽管也有学者认为《曼斯菲尔德庄园》体现了整体上的道德倾向,比如由范妮的出现而带来的新古典主义对教化的反思[10],但毕竟奥斯丁文本中所透露的这种存有内在龃龉的道德意味,掩藏了其背后的物质基础和政治现实。
3 园林的政治属性
园林的物质性和文化属性是一对辩证关系,这一关系与更为复杂和广泛的社会历史现实紧密相连,从而在根本上体现出有意识与无意识的政治属性。
3.1 作为“帝国版图”一部分的庄园
从文本的分析逻辑来说,结构主义呈现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交错,所以批评者因《曼斯菲尔德庄园》的道德意蕴与怀旧情绪的交织而生发了无数大同小异的分析,直至20世纪末萨义德的出现。
众所周知,萨义德《东方学》的核心议题是指殖民主义话语对东方的想象是一种不合法的浪漫主义虚构,是依附于权力的欧洲中心主义表征,萨义德称之为“想象的地理学”。但“东方学”甫一问世所遭受到的指责中,就有学者指出因其方法论受到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体现出一种文化主义的分析模式,故而往往无法看到权力话语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也因此模糊了权力的不平等关系,同时模糊了殖民历史的残酷事实。这之后的《文化与帝国主义》恰恰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对《东方学》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纠偏。而作为这一文本中的重要章节,萨义德贡献了对《曼斯菲尔德庄园》的新解,如果奥斯丁的道德批判含有对自然风致园不易察觉的“伪”的警惕,则萨义德希望告诉人们的正是这种“伪”自然是“伪”意识的现身,而“伪”意识在这里即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
如果上文中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可以称之为时间上的对位,乡村与城市则可以称为空间上的对位。为此,萨义德首先谈到了雷蒙·威廉斯的名著《乡村与城市》,以说明空间联动是如何体现文化和权力的不平等关系,而萨义德为其惋惜的是:“威廉姆斯虽然确是谈到了英国对殖民地的输出”[11],却浅尝辄止,而从空间性的意义上这却是难以忽视的(所以对于后殖民理论来说,这些有意或无意的回避往往都是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表露),萨义德更为关注的是将这一局限性的空间对位充分扩张。换言之,无论是威廉斯的政治性评价,还是奥斯丁的道德批判都是区域化的,或去地域化的,其囿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姿态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表征。不论是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起“唯物史观”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将其发展成伟大的愿景,还是沃勒斯坦和弗兰克等人从全球联合但不平衡的发展出发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世界体系,这中间最不能忽视的一环,就是由资本主义内在动力所决定的海外扩张的殖民史,而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可能与道德伦理批判脱掉干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人道主义属性所决定的。
3.2 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庄园
萨义德指出推动整个故事发展的庄园主之离去情节,恰恰因为主人的不在场而构成了整个文本的政治基调,为18世纪的英国文化产品的面貌贡献其“帝国版图”,“物质上支持这种生活的是伯特兰姆在安蒂瓜拥有的一个境况不佳的庄园(种植园)”[11]。换言之,曼斯菲尔德庄园处于前景之中,它既是安提瓜殖民地种植园的暗示,又具有了与后者同样的性质,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连接起来,作为对被殖民者和奴隶的剥削。没有殖民地财产的支持,宗主国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是难以为继的。
此外,上文的道德批判除了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调,还有文化主义方面。如一些学者强调,曼斯菲尔德庄园既是“美好舒适的生活空间”,又是“尊礼守制的道德空间”,“除却美学辞藻的描绘外,奥斯丁还对曼斯菲尔德庄园进行了道德辞藻的进一步修饰”[12]。这实际上暗含了一种文化主义的分析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奥斯丁心目中期待的读者解读,而萨义德所要揭露的正是这种诉诸文化的帝国主义掩盖了现实的帝国主义,或者说用文学修辞掩盖了物质现实,而这点对于奥斯丁来说是政治无意识的。“我们不应该误解她(奥斯丁)对外部世界的有限的提及、她对工作、事件的过程和阶级的些微的强调和她的把日常的不可调和的道德抽象化的能力。这种道德最终是与其社会基础相分离的”[11]。
事实上,《曼斯菲尔德庄园》至少提及了四类不同空间,除主体和西印度岛屿外,还有伦敦和朴茨茅斯,前者如上文所述代表了对现代性的反思,朴茨茅斯则作为范妮故乡,因其简陋则形成了与曼斯菲尔德的对比,它“破坏了她(范妮)已经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习惯了的美学与情绪上的平衡”[11]。美学自然是园林之美,而情绪的平衡却并不完全与前者平行。在长时间的对《曼斯菲尔德庄园》的批评中,对其“静”的特点的提炼已经成为一个常识,而这种静恰恰是自然风致园所提供的。曼斯菲尔德庄园的静谧是人为从现实自然中生造出来的;情绪平衡的背后是资本主义“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确定和骚动不安”(《共产党宣言》)的物质保障;乡间的安静表面上衬托了伦敦的现代化都市喧嚣,却在更深的层面“对位”着奴隶种植园的野蛮。甚至,一个可以想象的画面是“曼斯菲尔德”的静谧与得体是由轰隆隆的轮船和血汗的奴隶贸易推动和承载着的。
所以,“与其说《曼斯菲尔德庄园》是一部爱情小说,不如说它是一部有关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爱”[7],这样的认识是需要被加以限定的。诚然,曼斯菲尔德作为最典型的英国庄园,带有着最具民族特色的乡村风貌,以至于寄托了文人雅士的乡愁之情,然而,这种寄情山水只存于现代化与失落的农业文明之间张力的哀叹之中,却因此掩盖了另一对更为重要的对立关系。所以《曼斯菲尔德庄园》的重要意义是象征了以卢梭式的怀旧情怀拒绝了马克思式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遥远的安提瓜与曼斯菲尔德的关系相较于后者和它所在的英国现代社会的关系更近。当奥斯丁将一个事实从书的细节中抛了出去,用法侬的说法,这么做的问题是,欧洲上流社会一边叹息失去的过往,一边享用着资本的红利,却忘了欧洲正是第三世界创造出来的。
3.3 余论
众所周知,在自然风致园的发展中,对东方文化的想象和进口本就是重要前提,且这一前提的基础是工业文明的序曲通过大航海时代的推动而有了对东方的触及与对立。事实上,按照萨义德的说法,这种东方主义的想象方式本身既是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产物,又为殖民扩张提供了文化霸权。萨义德的批判是极为尖锐的,他认为奥斯丁对安提瓜的存在仅做浮光掠影的提及,甚至就是一种不经声张地对帝国主义的支持,在自然风致园向自然现实打开的形态中却对物质现实做了更为彻底地封堵,那么这种自然诉求究竟是什么意义呢。对于杰姆逊来说,《曼斯菲尔德庄园》就是直接与其社会和经济现实环境发生直接联系的,不过是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关系罢了[13],这种言下之意的揭露需要在细节中处理。
4 结论
曾有学者指出,园林景观对于《曼斯菲尔德庄园》不仅是一个主题,还具有空间、认知和技术上的意义。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种相关性更为全面。从不同人物对庄园建设和改造的不同认识,到作者不时在场的安排甚或指责,从奥斯丁私藏的道德批判到批评家以误读揭示的政治无意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曼斯菲尔德庄园》及其批评构成了一篇重要的英国园林发展史的参考文献。它提供了一种反思,园林作为一个集艺术、历史、文化和技术等方面的综合体矗立在曾经的历史剧变之中及延续至今的历史脉络之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园林也就是园林史的物质化,其必然是社会历史现实的重要承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