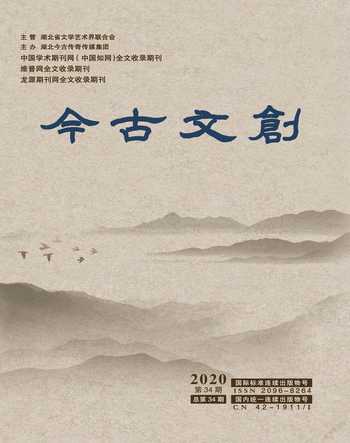侦探故事形式下的启蒙叙事
2020-09-10陈晨
【摘要】 格非短篇小说《追忆乌攸先生》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作。作品借鉴侦探故事的艺术形式,叙述了知识分子乌攸先生被下放山村之后,虽满怀启蒙志愿,却最终死于非命的悲剧。在1980年代“新启蒙”语境下,格非接续鲁迅等“五四”先驱者开创的优秀传统,对启蒙文化面对“前现代”文化的弱势处境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 格非;《追忆乌攸先生》;启蒙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4-0012-02
《追忆乌攸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格非的短篇小说处女作,通常也被视为1980年代先锋文学思潮中的代表作。对于先锋作家,人们往往认为他们“将全副精力倾注在小说的技巧实验之上”,忽视了在文学主题层面的探索。[1]然而格非无论采取何种叙事技法,其实都是一种“外衣”,在这“外衣”之下,蕴含着种种严肃的主题“内核”。《追忆乌攸先生》即是如此。
一、对启蒙悲剧的痛惜
《追忆乌攸先生》的大致情节是:一位叫乌攸先生的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山村后不幸遇害,时代恢复正常之后,警方前来调查真相。经过抽丝剥茧的努力,案件终于大白:乌攸先生当年因与村里的杏子姑娘相爱,引起了山村当权者“头领”的嫉妒,“头领”将杏子强奸杀害后嫁祸于乌攸先生,乌攸先生因此被公开处决了。
仅从叙事形式而论,《追忆乌攸先生》是一篇精彩的侦探小说,格非将警方一波三折的探案过程写得扣人心弦。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精英作家,格非并不满足于讲述一个通俗故事,他希望作品传达出某种“幽愤深远”的“存在质询”“思想拷问”,以及“历史反思旨趣”。[2]具体来说,《追忆乌攸先生》在侦探故事的形式之下,叙述了一个启蒙悲剧。
乌攸先生即是启蒙者。其启蒙精神的主要表现,就是尽管落难乡间,却在一切方面都拒绝为山村所同化。更重要的是,作为拥有现代文明的“外来者”,乌攸先生认可、尊重知识,希望利用自己的知识为村民提供帮助,乃至改变人们的蒙昧状态。例如当村中有很多孩子患上传染病时,村民只会采取巫术方法,“把河里的污泥糊在炉壁上烘干给孩子做枕头”。乌攸先生却“不信邪”,精心配制草药,成功挽救了孩子们的性命。这里的疾病是一种隐喻,知识分子与乡土民间构成了“医生/病人”关系。而这种关系式,一直都是启蒙文学对启蒙者/启蒙对象之间的关系的经典表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疾病成为有关社会、文化、道德、人性等病态的隐喻。作家根深蒂固的‘文化医生情结’,使疾病隐喻与他们的启蒙思想紧紧结合在一起。”[3]
与乌攸先生相对,乡土中国则是启蒙对象。这个山村几乎是一个与现代性绝缘的空间。在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等层面更是混沌未开。当权者“头领”是一个家长制暴君,“有一身强健的肌肉和宽阔的前额。村人都说他是一只狮子。”然而面对这么一个暴君,人们却都像乌合之众一样顶礼膜拜,甚至“没有一刻忘记他们的头领”,即便“知道头领的演说是一种欺骗,他们也止不住被感动得流下泪来”。
然而无奈是,当作为当启蒙者的乌攸先生与作为被启蒙者的乡村交锋时,弱势、无力、失败的却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这就是启蒙的悲剧,也是作家的痛心之处。对此,小说专门设置这样一段情节进行了象征性表达:乌攸先生与“头领”交恶后,两人相约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了一场决斗:“头领把衣服脱了挂在一棵树丫上,露出棕黄色的栗树皮般的肌肉……头领一侧身,挥拳猛击,第一拳就击中了乌攸先生的鼻子,鲜血四溅,像一只烂番茄砸在他的脸上。第二拳打中了乌攸先生的后脑勺,他向前摇晃了一下就摔倒了。”可以看到,在这场决斗中,隐喻了“前现代”文化、力量的“头领”咄咄逼人势不可挡,隐喻了“现代性”文化、力量的乌攸先生几无还手之力,只能“像马戏团的小丑逗乐一样,踉踉跄跄几下,便扑倒在地”。而最后被“头领”栽赃为强奸杀人犯后,乌攸先生同样束手无策,甚至连辩解的权利都丧失了,因为其舌头被“头领”指使人割掉了。这里又是一个令人痛心的隐喻:启蒙者实施启蒙的主要工具是现代性“话语”,一旦失去了“说话”能力,又谈何启蒙呢?
事实上,主要由于“改造现实”的艰难,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下乡”或“还乡”知识分子在“前现代”的乡间启蒙民众时,基本都以失败告终。但《追忆乌攸先生》中乌攸先生的命運并不仅仅是失败,他还最终命丧于被启蒙者之手。枪毙乌攸先生时,行刑的刽子手是村里一个叫康康的年轻人。康康的母亲原本已瘫痪在床多年,是乌攸先生劳神费力治好了她的瘫病。被自己疗治对象的儿子所杀害,恐怕是乌攸先生无论如何也不敢预料的。
二、对“看客”的批判
除了对杀害乌攸先生的直接凶手(幕后元凶“头领”和刽子手康康)进行无情批判,《追忆乌攸先生》还将批判之锋指向了“看客”。表面看来,“看客”对乌攸先生之死并不负有责任,但他们在整个事件中蒙昧、冷漠、麻木和残忍的态度,却使其在客观上成为“吃人者”的帮凶。鲁迅当年在《祝福》《药》《示众》《孔乙己》《阿Q正传》等一系列小说中,都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这种品鉴他人痛苦并从品鉴之中获得乐趣的“看客”。自鲁迅之后,中国现代作家在进行启蒙叙事时,基本都会将“看客”作为审视对象。
《追忆乌攸先生》同样继承了这一传统。如前所述,乌攸先生在下放到山村之后,竭尽所能利用知识造福乡里。然而面对他的悲剧命运,村民的反应却让人悲愤交织。当“头领”殴打乌攸先生时,围观者“把广场塞得满满的”,没有一人表示不平或同情。听到“头领”准备谋杀乌攸先生的消息,“我”母亲只是含糊其词地“嗯咿哈”两声,就沉醉在纳鞋底的“诗意”中了。“头领”在广场上烧乌攸先生的书时,围观者皆津津有味地“看着火焰把一缕缕纸灰往烟囱里送”。乌攸先生被执行枪决时,由于第一弹没有行刑成功,急不可耐的“看客”甚至流露出了“不耐烦”情绪。而乌攸先生刚被枪毙,旁边就来了一队迎亲的队伍,兴高采烈喜气洋洋,丝毫未为身边刚刚发生的惨剧所触动。更有甚者,乌攸先生被害后,村民迅速遗忘了他以及有关他的一切。直到警方前来调查,“人们才不情愿地想起乌攸先生”,而且觉得乌攸先生之死是一件无关紧要之事。面对警察的再三追问,他们觉得无话可说,不是不知道案件真相,“而是他们缺乏热情,这个村子里人对一切都感到无所谓”。
不过,在格非看来,“看客”令人痛心疾首的表现,并不仅仅只是体现了他们对现代启蒙文化的拒斥,而更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轻视。为此,小说特意写到了这样一个情节:枪毙乌攸先生时,“我”对母亲说要去观看,母亲却轻描淡写地对“我”说:“杀人就像杀鸡一样。”换言之,在以母亲为代表的村民眼里,人命和鸡命之间根本不存在本质差别。此时“我”弟弟正在后院杀鸡,也满不在乎地认为“杀鸡和杀人是一样的”。而在目睹乌攸先生被枪毙后,弟弟更是认为“杀人要比杀鸡容易得多。”显然,对人的生命缺乏敬畏和尊重,才是以“我”母亲和弟弟为代表的“看客”最为反现代性之处,也是最该被启蒙之处。否则无论是启蒙理念还是其他理念,在这片土地上都无法落地生根。
值得称道的是,像鲁迅一样,格非也没有陷入悲观主义。当年鲁迅虽然对启蒙民众的可能性表示了怀疑,但同时又充满信心地认为,“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4]。正是基于这种理想主义信念,鲁迅才写出了《药》的结尾:启蒙者夏瑜被害后,雖然一方面成为芸芸众生的“谈资”,但另一方面,却又有人在清明节时往他坟上送了一个花环,这说明并不是所有人都遗忘了这位为民众献身的启蒙者、革命者。同样,《追忆乌攸先生》中也有温暖、温情和予人以希望的“亮色”。这一点是通过对杏子姑娘的形象塑造体现出来的。与其他村民不同,杏子对乌攸先生充满了尊重和崇拜。例如乌攸先生的书籍被烧时,杏子为之伤心哭泣。乌攸先生被打伤后,杏子“解开围裙,小心地俯身擦净他嘴角的血迹”。乌攸先生被全村人排斥时,杏子却主动追随他学习知识,“不久就学会了一百零一种治疗麻疹的方法”。因此,尽管《追忆乌攸先生》的主题和风格是沉郁的,但因为有杏子的存在,依旧能让读者看到希望之光。
借鉴洪子诚的说法,格非许多作品虽然都被视为晦涩难解之作,但他并没有放弃对种种严肃“意蕴”的追寻,其作品“对社会现实和历史情境有着独到的切入,并以此为依托,持续不断地探索命运、人性、文化等宏大命题”[5]。《追忆乌攸先生》对于启蒙主题的叙述,不就是例证吗?
参考文献:
[1]赵卫东.先锋小说价值取向的批判[J].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6):67-71.
[2]蔡志诚.身体、历史与记忆的侦探: 《追忆乌攸先生》的文本分析与文学史意义[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100-105.
[3]李建伟,杨金芳.启蒙视阈下文学中的疾病隐喻[J].齐鲁学刊,2016,(5):151-160.
[4]鲁迅.呐喊·自序[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41.
[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76.
作者简介:
陈晨,女,汉族,江苏泰州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