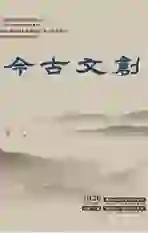浅谈《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的主要女性人物
2020-09-10高源杉
【摘要】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晚年时期的作品,讲述了一位老妇人对自身“非理性激情时刻”的回忆。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文本中两位女性角色的行为与选择,分析在当时的社会处境下女性不自觉扮演的角色,浅谈在与“被建构”的女性形象的激烈碰撞中觉醒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 女性主义;“第二性”;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0-0025-02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是茨威格颇负盛名的代表作品之一,故事发生于20世纪初,以上流社会的主妇莫里哀特太太因“爱”出走抛家弃子的事件为开端,引出了老妇人C太太人生中曾经历过的“绝无仅有”的二十四小时。因茨威格以描写女性心理而见长,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审视他笔下的两位主要女性人物,以波伏娃的“女人形成论”与性别的“文化定型论”来解读莫里哀特夫人与C太太人生中“非理性激情”的时刻,探讨在当时的社会境况中女性为何不得已而成为“被表述者”“依附者”“受缚者”与“自欺者”,浅析女性萌生自主意识的艰难时刻。
一、莫里哀特太太:被表述者
莫里哀特太太本是位循规蹈矩的贤妻良母,却对只结识几小时的法国男子一见钟情,便义无反顾地为了他抛家弃子私奔离去,莫里哀特太太逃离了家庭,也脱离了小说的叙事框架。这之后的故事与她无关,她的名字却被屡屡提及,这种“被表述”的存在方式暗合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的女性存在状态,即“女性的存在总是呈现为被塑造的、非自由的。”
围绕“私奔丑闻”,众人与“我”爆发了一场剑拔弩张的争论。众人对莫里哀特太太肆意指责,先是揣度她与法国男子早有私情,再是兩位先生表白“自己的太太绝不可能做出这样肤浅放任的事来”,最后是德国太太发表高论:世上有两种女人,一种是正经的女人,另一种是天生的“婊子”。在这场批判中可观察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众人的矛头对准莫里哀特太太,却对“私奔”的另一位主人公只字不提,仿佛法国男子没有过错。在父权制所掌控的话语世界中,男性的出轨较之于女性的私情往往受到较少的社会谴责,甚至衍生出诸如“男人天生多情”的辩护言论,颇有褒义的“花花公子”一词便属于此列,但纵观各国语言,很难找出一个以积极意义来形容一个风流多情的女人的词语,常见的多是口诛笔伐和“荡妇”的污名。在这场争辩中众人的言论,无论是对莫里哀特太太人品的贬低,或是对私奔另一方的视若无睹,都显示出一种不对称、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莫里哀特太太沦为众人谈资的存在方式和她被言语随意搓扁揉圆的塑造,都表露了她扮演着“被表述者”的角色。
二、C太太的人物形象
(一)挣扎者
在众人与“我”的争执进入白热化时,老妇人C太太及时入场调解,她因举止高雅,和蔼可亲而受到所有人的爱戴和尊重。在她与“我”的交谈中,“我”敏锐地感受到老妇人对莫太太的严厉指责好似是为了抒发某些隐秘的快感,她对“我”为莫太太辩护之心的反复查验仿佛是在渴望着有人能够对这个“出于激情犯罪”的女人产生一丝认同。
C太太看似矛盾的言行源自身为一个同样犯过“激情之罪”的女人的挣扎内心。她的意识好似分成两个群落,其一忠实地以男性的价值标准来塑造自己,认为自己是可鄙的,该与莫太太一样被捆绑在道德与贞洁的耻辱柱上;另一部分却顺应着自己的感情,深知人类“一生中非理性的激情时刻”的无法避免。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的故事发生在1904年,正处于西方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时期,西方女性向长久不能与男性一样拥有平等的选举权、教育权、工作权等一系列权利的社会境遇发起抗争,女性的主体意识也随着运动浪潮的蔓延而开始觉醒,在此之前社会的主要角色均由男性扮演,无论在社会地位或是性别关系中,男性皆为主体,女性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年迈的C太太即使希冀着认可与同理的关怀,却也不得不将其隐藏在传统的典雅女性形象的外表之下,她被纠缠在接纳过去的自己与无法摆脱的社会规训中,宛如海中溺水的人抱紧浮木扑腾挣扎。
(二)依附者
C太太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二十小时发生在她四十二岁那年,她的丈夫因病去世,孩子也已成家立业,她觉得自己毫无用处,甚至想要“速死以了残生”。在丈夫生前,C太太的生活意义依托于丈夫与孩子,她的前半生一直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在生活,因此当两者离她而去后她就丧失了自己生活的意义。直至现在,女性与家庭的联结仍更为紧密,女性工作者求职时也时常被询问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全职主妇的数量目前仍比“家庭煮夫”多得多。波伏娃认为,女性不独立的经济状况是女人变成“第二性”的第一原因,由此衍生出的“出嫁意识”则将女性与家庭、丈夫、孩子牢牢地捆绑在一起,缺失收入来源使她们只得依附于丈夫,舍弃“天然的自己”,将自己的意识中心指向婚姻,按照丈夫及其家族的要求建构自己。所以当C太太的丈夫去世时,她作为妻子首先感觉到的不是自由,而是生活重心的消失,因为她从未离开夫、子生活,所以不懂如何为自己而活。后来她如痴如狂地爱上年轻的赌徒,其实又是将自己的意识转移到了赌徒身上,在妇女没有就业机会的当时社会,C太太不曾觉醒自身的“女性意志”,她只得如莬丝花一般攀缘在丈夫儿子的身上,依附于他们而活。
(三)受缚者
丈夫离世带给C太太的不仅仅是悲痛,还有深深的孤独。她体会不到儿孙绕膝的温馨,缺少婚姻带来的安定,更感受不到爱情给予的甜蜜,她无疑渴望着被爱。可直至今天,再嫁的女性仍面临着更为严苛的是否不忠的道德拷问,可想而知在一百多年前,一个丧夫的女子更难将自己的心情诉说于口。C太太承受着来自他人口舌和自身心理压力的双重重负,只得将自己的感情藏得越来越深,可无限被压抑的情绪蚕食着她的理智,终于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她走进了与理智南辕北辙的赌场,邂逅了她人生中二十四小时的“非理性激情时刻”。
C太太向“我”讲述她是如何在赌场被一双蕴含激情的手攫去视线,又是如何被手的主人光彩照人富含生机的脸牵动心弦,多年后她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仍饱含倾慕与感动,却对“我”极力否认她想与这个年轻人发展什么关系。丈夫在世时,C太太使自己极力嵌合“贤妻良母”的模子,丈夫逝世后,她又必须遵守丧夫女人行事的“规矩”,于是即便在对莫太太怀有同理之心的“我”面前也遮遮掩掩真心。她就好像被密不透风的茧壳包裹,束缚她的不只有男方家族对她的劝戒规训,还有即使出身上流社会也在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父权制下女性作为“第二性”的传统观念。在神话传说中,夏娃诞生于亚当“多余的骨头”,英雄史诗的主角总是男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女人天生是不完善的”,在全社会对“人类历史是男性创造的”的无意识认同中,女性的存在与自主意识被淡化了。C太太在来自“第一性”、社会、自我的三重束缚下不得不将自己塞进并不合身的角色模具。
(四)自欺者
C太太出于怜悯之心阻止了年轻赌徒的自杀意图,她将他带到了旅馆安顿,绝望而疯狂的赌徒与她发生了关系。C太太形容第二天清晨是“极端可怕的一刻”,她觉得恶心、羞愧、只求一死。一位名门出身的女性,中年丧偶,却与只相识几个小时的陌生人发生了“一夜情”,與清醒一同袭上心头的贬损感和道德拷问几乎摧毁了她。在已经过多次女权运动浪潮洗礼的今天,“一夜情”仍是颇有争议的话题,可想而知当时C太太心中掀起了何等的惊涛骇浪。当女人与“一夜情”联系起来,往往会被道德卫士扣上“滥情”“荡妇”“不知检点”的帽子,这些词语较少指向相反的性别且对女性群体的杀伤力格外强大,因为背离“贞洁”与“干净”等对女性传统品德的“赞颂”往往会使女性受困于厌弃自我的囚笼。实际上,所谓的“美好品质”也只是父权制为女性设定好的女性气质,就如波伏娃所说:“女性无法摆脱男性和社会所强加的实质”,因而无法“以自我为载体去展示最真实的本真存在”。
混乱雨夜的“一夜情”使受过良好教育的C太太无法承受,于是她选择以自欺欺人的方式遮盖自己的记忆。当惊恐交加的C太太在清晨的光线中看清了年轻赌徒“天使般纯洁欢快”的脸庞时,她顿时觉得恐惧与羞愧都离自己而去了,她通过昨夜的“献身”,拯救了一个纯洁的生命。“献身”一词仿佛为夜晚发生的一切洒上了一层圣洁的金光,C太太仿佛化身为勿入歧途的少年指点迷津的圣母,冠冕堂皇的说辞实质为一种自我欺骗,C太太不愿接受自己从“名门淑女”沦为“不正经的女人”的转变,借此粉饰雨夜一切她不愿回首的记忆,也帮助自己逃离他人的道德指摘和煎熬内心。
三、结论
故事的最后年轻赌徒吞枪自杀,C太太经历了救赎、爱欲、绝望的纠缠后随着年龄蜕变成“我”所见的老妇人,终于学会了为自己而活。
一百多年前的社会状况使得女性不得不轮番扮演“被表述者”“依附者”“受缚者”与“自欺者”的角色,她们身负来自社会规训的层层枷锁,却难能可贵的在挣扎与抗争中诞生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的故事虽是围绕着激情与理智的碰撞,却散发着第一次女权运动浪潮带来的光晕,因为它以超前的姿态,舍弃了道德制高点上的批判,肯定了女性情欲的合情合理,正如“我”鲜明的态度:这绝不下流,也绝不可鄙。在女性社会地位获得极大提升、性别议题的热度居高不下的今天,故事中蕴含的理解与尊重仍散发着温情与发人深省的光芒。
参考文献:
[1]斯·茨威格.斯·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M].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合卷本)[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3]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
高源杉,女,汉族,辽宁大连人,大连外国语大学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文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