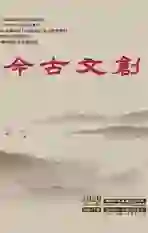图斯奈尔的复仇
2020-09-10王文静
王文静
【摘要】 在戏剧《赫尔曼战役》中所涉及到的政治和军事背景早已为人所熟知,但是对其中的美学内容却尚未有人讨论。本文将在克莱斯特“秀美”理论下探讨图斯奈尔的复仇动机以及她与赫尔曼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图斯奈尔;秀美;赫尔曼;克莱斯特
【中图分类号】I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7-0022-02
克莱斯特在1808年创作完成了戏剧《赫尔曼战役》,以歇鲁斯克酋长赫尔曼战胜罗马人的光辉事迹,显示出德意志民族反抗外族侵略的坚强意志。这部小说中唯一的女性形象是赫尔曼的妻子图斯奈尔,她对自我价值的追寻与克莱斯特在《论木偶戏》中阐述的秀美思想有着密切联系。在完成《赫尔曼战役》的短短两年后,也就是在1810年克莱斯特出版了杂文《论木偶戏》,可以说《赫尔曼战役》的创作为他后来“秀美”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本文将研究历来被学术界所忽视的图斯奈尔的形象、她的复仇与自我救赎。
戏剧《赫尔曼战役》是克莱斯特根据历史上发生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一直以来都被学术界所忽视,直到他去世的49年后才在布雷斯劳首次被搬到舞台。在公元一世纪初,罗马为了扩展自己的领地,派瓦鲁斯元帅带领大批部队北上,试图通过暴力手段征服莱茵河畔的日耳曼部落。酋长赫尔曼为了迷惑敌人,声称要“献出歇鲁斯克的全部力量,向奥古斯都归顺称臣,让瓦鲁斯和他的军团进来……和他一致行动,对付马博德王” ①。这只是他的缓兵之计,私下里他联合马博德将罗马人引诱到条托堡森林,大败敌军。为了使计谋得逞,他利用自己的妻子图斯奈尔引诱罗马使臣温提丢斯,制造出诚心服从罗马人的假象。而天真的图斯奈尔就像是一个被丈夫操纵的木偶,对真相一无所知,还陷入了与温提丢斯的感情漩涡中无法自拔。赫尔曼再次利用计谋使妻子误认为温提丢斯背叛了她,这种毁灭性的打击也激化了图斯奈尔内心的矛盾,用熊杀死了温提丢斯,试图自我救赎。
赫尔曼与图斯奈尔的关系就如同《论木偶戏》中机械师与木偶的关系,一个操纵,一个被操纵。克莱斯特认为,“美在这样一种人的身上显现得最为纯净,这个身体要么根本没有,要么有无穷尽的意识,即在木偶或上帝身上” ②。身处世俗世界中的人类永远不可能实现这种完美理想。对于被机械工操控的木偶来说,只要“重心”在一条直线上运动,就会有节奏地像跳舞一样运动起来。最初的图斯奈尔忠于赫尔曼,就像一个木偶,一切都按照丈夫所说的去做,没有自我意识的觉醒,温提丢斯的到来才让她开始出现“异化”。
图斯奈尔的内心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无自我意识—自我觉醒—自我救赎,这与克莱斯特后来提到的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吻合。克莱斯特认为世界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能够实现秀美与和谐的自然阶段,表现为无意识的木偶和自然界的动物;第二个阶段是人类形成了理性意识,但由于认识的有限性,不能正確解释和把握自然规律,因而远离伊甸园;第三个阶段是神性阶段,在这里只有具有无限意识的上帝,最终实现自然与意识、必然与自由的统一。人类自吃了智慧果以后,再也返回不了原初状态了,只能进行艰苦的旅行,“看看天堂之门是否在后面某个地方又打开了”(《论木偶戏》304)。图斯奈尔在拥有自我意识之后,再也无法成为被赫尔曼所操纵的木偶,她通过熊残忍杀害了温提丢斯,试图救赎自我,却再也无法回到“天然纯洁的状态”。
图斯奈尔就如同被赫尔曼操纵的木偶一样,没有自我意识,看不清当前局势,完全相信赫尔曼说的话。克莱斯特认为,要操纵木偶不需要“一一地摆弄和拉扯每个肢体……把握住木偶的这个内在的重心就足够了;跟钟摆似的四肢,不用动它,它自己就会机械地做出动作。”(《论木偶戏》301)图斯奈尔的“重心”其实是她对丈夫的无条件的忠诚,对他没有任何防备,坦诚相待。而赫尔曼利用这点,让妻子与罗马人周旋,为自己争取时间筹划计谋。
作为一名女性,图斯奈尔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一直处于依附地位,作为酋长的配偶,虽然能过上衣食无忧、受人拥护的生活,但她却没有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社会环境迫使她必须对丈夫的话言听计从。她甚至没有被丈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而只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用来迷惑罗马人。在她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美丽的外表,她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对未来的梦想也日复一日地消磨在琐碎的生活中。
正是赫尔曼有预谋得纵容妻子与温提丢斯之间的暧昧关系,才会导致后来的悲剧,而悲剧的发生正是赫尔曼想要的结果。在一次狩猎中,温提丢斯射杀了被激怒的野牛,救了图斯奈尔的性命,这是双方的首次相遇。赫尔曼看出了温提丢斯对妻子的好感,怂恿妻子接近他,制造表面上讨好罗马人的假象。温提丢斯的出现使图斯奈尔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她对被愚弄的罗马人表示同情,恳求丈夫能“开诚布公地对待他”(《赫尔曼战役》40-41),不想让丈夫继续利用自己。这是图斯奈尔的第一次觉醒,开始反抗丈夫的不公。最后,她还请求赫尔曼饶恕情人的性命,让他可以迅速逃回祖国去。在暴力问题上,身经百战的赫尔曼认为德国多山的地貌有利于围困和伏击敌人,要利用武力对付罗马军团,并要将其全部消灭掉。图斯奈尔却对丈夫的残暴行为感到震惊,认为整个罗马也许是极其凶恶的,但是个别的罗马人会是真诚的。她视自己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愿残害无辜的生命,然而却与赫尔曼的主张背道而驰。她就像一个拥有意识的木偶一样,试图扯断捆绑在身上的线,摆脱机械师的控制,但这也意味着她会失去“秀美”。
温提丢斯的热情、开朗和自信使图斯奈尔想到了曾经的自己,那缕被抢走的秀发正是她丢失的自我 ③。她请求丈夫饶恕温提丢斯的性命,“让他迅速逃回祖国去”。(《赫尔曼战役》117)温提丢斯所能带来的,并非只有炽热的爱情,也为她提供了自我意识觉醒的机会。在戏剧的第4幕中,赫尔曼告诉妻子,她的那缕秀发被温提丢斯放在了写给罗马女皇利维亚的信中,被当作是即将要战胜歇鲁斯克部落的战利品。这封信是否为赫尔曼伪造的,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它已经给图斯奈尔致命一击,使她尝到了背叛和被羞辱的滋味,这也成为了她实施野蛮报复手段的导火索。愤怒使她“变成了一头雌熊,她(我)要重新配做赫尔曼的妻子”。(《赫尔曼战役》157-158)为了重新回到原初状态,图斯奈尔采用和丈夫一样残暴的方式结束了温提丢斯的性命,但是失去的秀美却无法复得。
图斯奈尔在歌中唱到,“一个男孩在水池里,看见了月光,他把手伸进去,想捉住月亮;池边的水混浊了,闪耀的月影不见了,而他的手……(《赫尔曼战役》40-41)”她通过月亮照在水中的影像来向温提丢斯展示自己的“秀美”。就如同在《论木偶戏》中的那个少年,“他偶然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并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无意识地做出的那个动作非常美。照镜子在这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④但是,当他再次有意识地去模仿之前的动作时,却只看到滑稽可笑的自己,弄巧成拙,无法展示秀美。歌曲中的“手”试图去捕获水中月亮的镜像,这种有目的地追寻最后只能导致美的丢失。
人类的行为过分强调自我,不顾客观规律,“人意识到自身的独特性,意识到自身的利益,开始为自身而奔忙,但是人毕竟还处于通向神界的途中,还受到客观命运的影响和操纵,任何违反都将带来报复的苦果。” ⑤图斯奈尔多次试图拒绝赫尔曼让她迷惑罗马人的要求,还为屠杀罗马人的行为感到震惊,这是因为她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没有认清楚周围的形势。罗马统帅瓦鲁斯奉命北上,绝不是为了和各日耳曼部落和平相处,而是要用武力统治他们。他们在所到之处烧杀抢掠,致使“三个最繁荣的村庄被抢劫一空,部落居民四散逃亡,茅舍和帐篷都被烧光”。(《赫尔曼战役》59)一旦赫尔曼战败,那么整个家园都会沦为罗马人的殖民地,他的部落将失去自由,臣民们甚至会沦为罗马人的奴隶。然而图斯奈尔因为自身认识的局限性,没有考虑到这些国恨家仇,没有认清楚日耳曼民族与罗马人之间不可调节的矛盾。克莱斯特认为,“在有机界中,反思越模糊越微弱,美就越闪闪发光,就越主宰一切。”(《论木偶戏》307)有意识的人类因为自身的局限性,无法实现身体和灵魂、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唯有木偶或者上帝才能拥有秀美。这就注定了图斯奈尔的命运,她自我救赎中的失败。
由于温提丢斯的出现,图斯奈尔的自我意识觉醒,要摆脱赫尔曼的控制,从一个无意识的木偶转变为有局限意识的人类,内心出现异化,曾经的秀美也无法再次获得。克莱斯特用美学思想来解释现实社会中的理性膨胀和异化现象,探讨现代人的生存问题,企图找到一条途径,来调节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理性與感性之间的矛盾。
注释:
①海因里希 · 冯 · 克莱斯特著、刘德中译:《赫尔曼战役》,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第32页。(以下直接缩写为《赫尔曼战役》,用阿拉伯数字表示页数)
②刘小枫(选编):《论木偶戏》,《德语诗学文选(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7页。(以下直接缩写为《论木偶戏》,用阿拉伯数字表示页数)
③Daniel Tobias Seger: “Sie wird doch keine Klinke drücken?”Kleists Herrmannsschlacht im Rahmen seines Graziedenkens.In: 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Geistesgeschichte 78.1.(2004)S.426.
④任卫东:《木偶之秀美与熊之神性——克莱斯特对古典美学的解构》,《外国文学》2018年第3期,第7页。
⑤王建:《评克莱斯特的〈论玩偶戏〉》,《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第96页。